张裕民:“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朱悦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张裕民是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于1948年,基于作家丁玲1946-1948年在华北农村的实际生活经验而创作,是她第一次以农村斗争为主题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暖水屯的地方,暖水屯的村民淳朴热情,却常受地主的气。张裕民——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在暖水屯热闹的土地改革中发挥了坚定、突出的党员示范作用。在以张裕民为代表的土改小组的带领下,农民打倒地主,得以翻身。党的政策好,人心变化也快。在这样一场艰难的战役中,张裕民在变,土改组成员乃至暖水屯村民们的思想心态也在变。最终农民分到了土地,也有了当家作主的自信。
“痞子”干部
“敞着棉衣,拿着一顶旧的三块瓦皮帽,预感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是暖水屯第一个共产党员张裕民的首次亮相。“旧的三块瓦皮帽”透露出张裕民的贫农身份。他过去是暖水屯地主李子俊家的长工,自小受苦颇多,8 岁时父母双亡,和刚满周岁的兄弟寄住在外祖母家,跟着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17 岁时便扛起生存的重担,捡柴、烧饭、做活、养活他兄弟。除此以外,张裕民在暖水屯也没什么亲戚,他的伯父倒是有两个儿子,但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一同逃荒到了外地,所以也有人叫张裕民为“三哥”。从张裕民在暖水屯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后,赢得了村民的好感和信任,“三哥”这称呼便流行起来。

丁玲
然而,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张裕民身上也有一些流氓习气。甚至在加入共产党后,他在形象上还保留着“痞子干部”的特点。土改组组长文采的印象证实了这一点:“文采看见他敞开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气扑过来,好像还混和得有酒味。”不仅如此,暖水屯的土改小组中还有李昌、杨亮,以及村工会主任钱文虎、农会主任程仁、副村长赵得禄等人,在这些成员中,张裕民是很不起眼、极其普通的一个。他不像暖水屯的农会主任程仁。程仁曾是钱文贵家烧饭的长工、李子俊家的佃户,他在钱文贵家做工时,和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暗生情愫,纠缠于公理与私情之间;也不像土改小组的文采、杨亮等人。文采在延安住过一年,上过大学,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杨亮以前在边区政府图书馆管理图书,爱读书,爱动脑,是一个沉静、聪慧的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而张裕民不识字,嘴又笨,只会干些粗活,扛锄头、抬木料、拉犁……
加入共产党、参加土地改革是张裕民人生的转折点。之所以能成为暖水屯第一个共产党员,还要从白银儿和江世荣说起。寡妇白银儿,诨名白娘娘。她是暖水屯村上的女巫,家里供着红绸神龛,装神弄鬼,也招揽一些客人赌钱,张裕民曾是她家的常客。江世荣则是暖水屯的甲长,善于巴结,借日本人的力敛老百姓的财。暖水屯有八大地主,俗称“八大尖”,江世荣也是其中之一。有一天,江世荣来白银儿家找张裕民,说八路军写信借粮,想委托张裕民去据点给八路军送粮食。江世荣不敢去前线,他怕八路军杀他,又怕日本人知道他通八路。对于张裕民来说,他早就仰慕八路军英雄,但同时他知道江世荣“两头通吃”的小人之心,便隐藏起内心的窃喜,佯装不情愿地答应了。
这次会见,八路军的温暖给张裕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张裕民不断向党组织靠拢,最终加入共产党。他看到八路军战士衣着简朴,腰上别着短枪,还“倒酒给他暖身体,擀面条给他吃,同他谈这样谈那样。他很注意地看他们,听他们,他觉得这些人很讲义气。打日本,反汉奸是天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张裕民也觉得“劫富济贫”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与八路军的见面激发了他骨子里“替天行道”的英雄情结。多次来往中,张裕民和八路军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八路军亲切友爱,听张裕民讲他过往的遭遇,那些穷苦的记忆翻涌而出。张裕民日益感受到八路军的无私、友爱,他从没对人说过这些掏心窝的话,他仿佛遇到了亲人。于是,在八路军的感召下,张裕民的思想发生变化,他意识到贫困的根源和阶级的不平等,有钱人当家造成了穷人的苦。得益于这样的启发,具有英雄气概的张裕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不再去白银儿家,而是加入党组织,成为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张裕民是土生土长的暖水屯人,是八路军直接培养的干部,过去当过抗联会主任,现在是暖水屯的党支部书记,又兼武委会主任。他对暖水屯的土地状况、村民的性格心理了如指掌。暖水屯是解放区,在抗战时期就有了一定的斗争基础。在开展工作时,相比较其他土改小组成员,他的优势在于能结合农民的利益诉求,把握暖水屯土改的方向。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党的理论的理解上。县委宣传部印发了小册子《土地改革问答》,张裕民、程仁和李昌对这本小册子有各自的解读。其中李昌脑筋灵活,容易接受新事物,但缺乏思考。他依据小册子联系到暖水屯的阶级划分,地主、富农、中农、穷人与具体的村民一一对应,一目了然,因而他对土地改革充满信心。程仁对本村的土地成分比较熟悉,结合小册子上的土地数字,认为土地分配公平是十分困难的。相比之下,张裕民则清醒得多,认识到核心目标是打垮旧势力,但这需要老百姓自觉地团结起来,而农民自身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作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
张裕民对农民“心里糊涂着”的判断,看似简单,但却与他对暖水屯乡村伦理关系的现实把握密不可分。在暖水屯中,农民分为几种类型:以侯忠全老头等老年农民为代表的保守派,骨子里具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侯忠全是侯殿魁家的佃户,同时也是侯殿魁的叔父。当斗侯殿魁时,侯忠全却把分给他的一亩半地还给侯殿魁。生活的磨难让他学会承受,养成了他忍辱负重的性格,宿命与赎罪构成了侯忠全的人生哲学。在土改运动中,这类农民是较难领导、不易调动的;还有一类,是以刘满等青年农民为代表的激进派。黑汉子刘满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头发很长,两眼瞪得圆圆的,闪着焦躁的神气,光着上身,穿一条黑布裤子。”刘满的父亲被逼死,大哥被绑去当兵失踪,另一个哥哥刘魁做甲长,被钱文贵逼疯,一家人都惨遭钱文贵的迫害,内心积蓄了浓厚的仇恨。这是土改运动中最容易调动的一群人。像刘满以及侯忠全的儿子侯清槐、王新田等人,他们年纪轻,干劲足。当然也有一些中间人物,介于保守与激进之间,看重个人私利。比如地主钱文贵的女婿张正典、小学教员任国忠等。这类人碍于自身的处境和思想局限,受到钱文贵的钳制,在土改问题上犹豫、后退。其中任国忠受钱文贵的指使,出黑板报告发李子俊,干扰土改小组的视线。
土地是地主压迫农民的工具。在长时间的剥削压迫中,农民越来越苦,养成了“敢怒不敢言”的思维定式。而村民之间的血缘、邻里关系,诸此种种,构成了他们复杂的伦理观念。土改小组作为暖水屯的“闯入者”,只有把握、整合与农村既有伦理秩序之间的作用力,颠覆暖水屯地主、雇工、佃户、贫农之间的伦理秩序,才能促使农民团结,实现翻身。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裕民对打垮旧势力和农民“心里糊涂着”的判断,正是把“翻身”和“翻心”作为暖水屯土改的两项重要内容,这展现出作为党员领导的张裕民颇具智谋的大局观。
在土改进行中,张裕民胆大心细,善于观察人的神态、动作,能够捕捉党员群众的思想动向。土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散会后,他看到民兵队长黑汉子张正国肩上扛了枪站在街头,果敢坦荡,就暗下判断:“这小子是个靠得住的。”他的心细还体现在对暖水屯干部处境的体察上,本来张裕民担心干部之间存在分歧,预备一一和干部进行谈话,他想通过这种形式在土改会形成打倒旧势力的统一意见。张裕民凭借自己的直觉,认为干部里存在内奸。张正典是钱文贵的女婿,张裕民对他保持警惕,并派民兵监视他。在赵得禄的问题上,张裕民则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因此赵得禄乐于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江世荣曾借给他两石粮食,而且因为赵得禄家穷,他老婆没有衣服穿。江世荣的老婆便有了可乘之机,给她花衣裳和一些吃的作引诱,因此赵得禄的老婆认为江世荣是好人,但赵得禄表示,他在抗日时期就当村长,有坚定彻底的土改的心。这些心里话鼓舞了张裕民:“好赵大爷呢,咱就为的这个事来找你呢。”张裕民跳在地下,走来走去,高兴不已。而在程仁的问题上,张裕民则旁敲侧击,借以判断程仁的思想态势。当程仁提出批斗李子俊时,“不,女人是不拿枪打仗的,女人的本领可多呢,人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嘿……哼!’”张裕民的这些话是说给程仁听的,他期待程仁主动表态,但是程仁一言不发,“只拨着他面前的一个算盘”。因此,张裕民猜测现在找他谈话,可能谈不出结果,所以打算以静制动。这样的一种语言策略显示出张裕民心思缜密的一面。
不仅如此,作为一名党员,张裕民在执行土改任务时,坚持“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工作态度和行动标准,这成为促使土改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正因为他自觉地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才会在土改中得民心,获得村民的仰赖。在分果园时,他向杨亮解释,真正受苦人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那样靠不住,水地果实产量比较稳定。并且在制定任何有关土地的政策时,他都抱着“可得让大伙知道”的态度。在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上,张裕民一改犹豫,十分痛快。考虑到鲜果的时令性,张裕民迅速召开会议,组织老百姓摘果子,运到县城卖。这其中,卖果子的会计、委员会成员都是贫农。在具体的土改事务上充分体现了张裕民“百姓为先”的土改观念。落到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这是张裕民贯穿如一的立场,也是他与文采等人的区别所在。
艰难的战役
张裕民是雇农出身,他深知穷人的不易。在处理暖水屯土地的问题上,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在分革命果实时,也尽量考虑更需要的人。而他自己,仍是和他的兄弟租住在别人的东屋,至今没有隔夜粮食。的确,在暖水屯,土地和钱财掌握在钱文贵、江世荣、李子俊等地主、富农的身上,他们攥紧贫农和佃户的地契,剥削敛财,暖水屯大部分村民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但由于这些地主、富农根基过深,长期遭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敢怒却不敢闹。
在暖水屯,张裕民虽有稳定的干群基础,但是,土改毕竟是新事物。面对新事物的来临,木讷的张裕民由于缺乏宣传经验,并不知道如何把土改政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暖水屯村民听。起先,为了向村民介绍土地改革的内容,提高穷人们的“翻身”觉悟,农会召开了一次贫农会。赵得禄、羊倌老婆、识字班的人都来参加了,有一些中农也抱着兴趣来听,大家都对这次会议充满期待。会议开了五六个小时,文采发表了才华横溢的讲演,从国内外土改的形势讲到群众路线。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文绉绉、书面化的语言无法和他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联系,很多村民怨声连连。
和张裕民一样,这些农民党员大多数年纪较轻,贫下中农出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受自身能力和政治觉悟的限制,在对革命和阶级的认识问题上存在保守、模糊的特点。土改进行不久,小组内部就产生了矛盾,这其中争执最多的是“先斗谁”的问题。表面上看,暖水屯找不出大地主,不存在坏的典型。李子俊、钱文贵等人虽有剥削的行径,但不至于十恶不赦。在对这些地主、富农的认识上,土改成员们各执一词。比如,他们对顾涌的看法存在分歧。程仁认为,顾涌虽是富农,但他的土地是一滴汗一滴血地赚来的;张正典娶了钱文贵的女儿,他说钱文贵有钱、地也多,但他的儿子钱义参加了八路军,不好下定论;暖水屯副村长赵得禄家穷得叮当响,念及江世荣在他吃饭艰难的时候,托人转手借了两石粮食给他,因此为曾和日本人勾结、以权谋私的江世荣“说好话”。
张裕民心里明白,之所以出现党员干部“各有各的藤藤绊绊”、不肯带头的情况,这其中有各自利益的考量。不过他并没有气馁,而是转变工作作风,到群众中去。在党员杨亮的鼓励下,张裕民先在村子里调查摸底,鼓动群众,找地主“算账”。他了解到今年是苹果、梨子、葫芦冰成熟的季节,是果子丰收的大年,这为“算账”提供了契机。全村11 家地主、15 家富农全有园子,还有5家中农、20 家贫农也有果子。于是农会决定把11 家地主的果园管制起来,预备分给贫农。为了有效管制果实,临时成立了卖果子委员会。这些成员有李宝堂,他给李子俊家看了二十多年的果子,对李子俊家的果园比较熟悉;有任天华,是办合作社、会算账的精明人;还有土改积极分子侯忠全的儿子——不怕得罪人的侯清槐。他们带领贫农闹果园、摘果子、装果子。更鼓舞人心的是,郭富贵、王新田等9 位佃户,在农会的支持下纷纷找江世荣要红契,这一举措促使更多的农户告江世荣的状,要求找江世荣算账。不得不说,这是土改的初步胜利。这样的群众热情,张裕民在以往的斗争大会上也很少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胜利似乎就在眼前。
由于入党之前的个人作风问题,张裕民在党员干部中间也面临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在张正典的煽动下,文采怀疑张裕民与江世荣勾结。但实际上,张裕民没有私心。李子俊的老婆看到张裕民他们势头正盛,就开始装穷。张裕民曾做过李子俊家的佃户,为此李子俊老婆还特意做点东西,请张裕民喝酒,但他从未接受这样的“好意”。不仅如此,文采开始对干部队伍有诸多不满,比如顾涌作为一个地主,但他的儿子顾顺却被吸收到青联会当了副主任。这样的组织安排,使他认为干部队伍存在自私自利的缺陷。而杨亮,在对暖水屯贫农的亲近中,判断出老百姓最痛恨钱文贵,钱文贵是暖水屯地主里最阴险的一个。
问题接二连三,党内亟需整顿。但在这一点上,张裕民暴露出性格中延宕、犹豫的一面。他总是怕“闹不起来”,怕“拔尖”不成,怕得罪人。这一性格缺点鲜明地体现在斗钱文贵的事情上,他一方面顾及钱文贵是抗属,不该斗;同时心里清楚,钱文贵是暖水屯不得不斗的旧势力。问题是即使斗了,钱文贵本身也没有死罪。如果遭到报复,或是像以往上级“纠偏”那样,将这些老百姓恨之入骨的人送到县上,讲宽大政策时却再被送回来,就没办法处理了。斗还是不斗钱文贵,成了一个难题。钱文贵是暖水屯的“头尖”,是最大的地主。他十分狡猾,“人没三十岁就蓄了一撮撮胡髭……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他在私塾曾念过两年书,走南闯北,心思熟络,为人精明,不像庄稼人。他会利用黑妮的“美人计”,钳制农会主任程仁;利用小学教员任国忠,吓唬李子俊,分散土改小组的注意力。治安员张正典也是他的眼线,给他通风报信。他的儿子还参加了八路军。而在面对干部内部的争执时,张裕民往往木讷朴拙,甚至没有时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处理张正典和刘满的矛盾时,他也没有放长眼光,直面干部与贫农这一阶级问题,而是将之搁浅,试图交给农会处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局部)
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在成长为一名“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的过程中,张裕民获得了党组织及干部成员可靠而及时的帮助。土改小组的干部成员一直鼓励张裕民,增强了他的信心。杨亮就是最早鼓励张裕民的人。在最初的村干部会上,当时土改小组还是一个人员不多、组织性不强的零散组织,变天思想流行。开会中,干部、群众难免流露出懈怠的消极心理。杨亮多次耐心地激励他,对他讲动员群众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团结一切力量,土改定能取得胜利。而在土改矛盾重重、难以继续时,从区里来的章品来得及时,打消了张裕民“拔尖”的顾虑,解决了斗争会的燃眉之急。章品根据暖水屯土改的情况,开展党员大会,给张裕民反思自身、团结群众的机会。章品是县宣传部部长,有着瘦长的脖子,常常摸他的光头。他本来在六区搞土改工作。六区是在桑干河北岸和洋河南岸的一块狭长的三角地带。他是第一个来暖水屯的八路军,非常了解全村的情况。虽然也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他做事明快、老练。长期在村子里与伪甲长、地主打交道的经历,练就了一双识破地主诡计的火眼金睛。在处理富农、中农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很坚定、果决的人:“土地改革就只有一条,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彻底翻身。”章品刚来到暖水屯时,感受到村干部之间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彼此之间存在猜疑,于是他临时将农会改成党员大会,借以开展干部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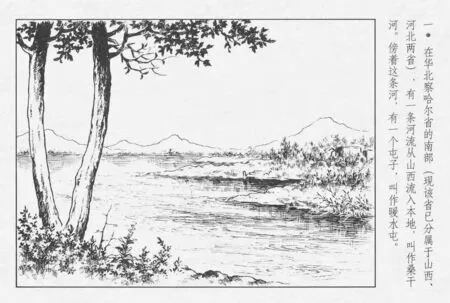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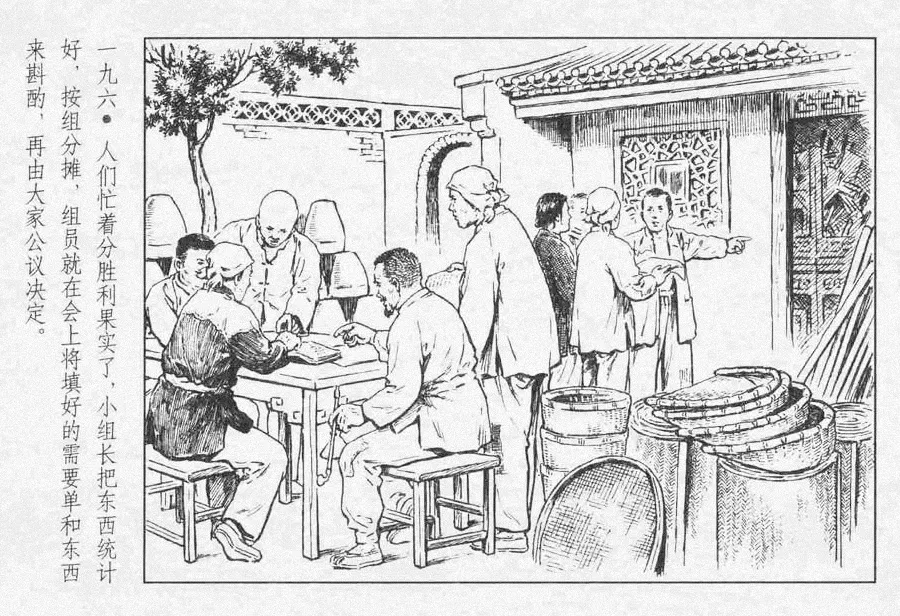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局部)
这次开会的党员干部有二十来人。在党员大会上,张裕民率先开展自我批评,对工作中的“不放手”作风进行反思,起到了党员的模范作用。他说:“咱从头到脚也只是个穷,如今还不能替老百姓想,瞒上欺下,咱简直不是个人啦!”这些心里话感染了大会上的其他党员。随后黑汉子张正国、工会主任钱文虎、张正典、程仁等人纷纷表态,相继进行自我批评。通过这次会议,土改小组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坚定了坚持土改、继续土改的斗争意志。暖水屯原本松散、常产生分歧的土改小组成员忆苦思甜,意识到各自的思想建设问题。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土改成员就斗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最终确立了斗争对象钱文贵。
章品还提醒张裕民,斗钱文贵时“人千万别打死”,斗争的目的是让他向人民低头,“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这一嘱咐是十分必要的。在土改的初级阶段,人民只想痛快地报复、消灭地主。章品为斗争会的开展提供了许多有预见性的意见,张裕民受到极大的鼓舞,斗争情绪高涨,终于坚定地开始“斗钱文贵了”。这次斗争集中体现了暖水屯党群一心、同仇敌忾的团结力量。
在钱文贵的斗争会上,张裕民走在群众前面,引领农民翻身,展现出性格中坚强、具有爆发性的一面。会上的张裕民十分活跃,不仅克服了自己的木讷和犹疑,而且敢于宣传,善于发动群众,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他一会儿指挥号令;一会儿跳上台中央,发表报告;一会儿伸开拳头,喊口号,鼓士气。他的报告与文采的报告不同,没有繁复的名词,通俗简洁。“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和钱文贵算账。咱们先算算,算得差不多了,改天再当着他算,咱们农民自己来主持这个会,咱们选老百姓来当主席。你们说成不成?”“‘成!’‘就是张裕民!’”台下的村民纷纷应和,回应张裕民,这是暖水屯村民对张裕民的肯定。借着老百姓高涨的积极性,张裕民在大会上给受过压迫的农民“算账”的机会。钱文贵是土改运动中最难啃的“骨头”,他几次利用小学教员任国忠、侄女黑妮、李子俊、张正典等掩人耳目。即使在斗争会上,钱文贵也很犟,“他站在台口,牙齿咬着嘴唇,横着眼睛,他要压服这些粗人,他不甘心被打下去”。钱文贵气场强大,在暖水屯为非作歹多年,老百姓们怕他怕到骨子里,不敢言语。这时候,程仁从人群中跳出来,一呼百应。刘满等人也纷纷走到台前诉苦、算账。钱文贵终于渐渐消了气焰,向百姓投降。最终除了钱义的25 亩地外,钱文贵的所有财产都被充公。在这一过程中,老百姓实现了翻身,也有了当家作主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张裕民谨记章品的嘱咐,护住被人群踩踏的钱文贵,使斗争会不至于陷入失控的局面。从中能看出,这次斗争会展现了张裕民日趋成熟的领导能力,使他完成了从幕后走到台前的转变。而暖水屯土改“翻身”与“翻心”的实现,是以张裕民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和农民互相信任的结果。张裕民聚人心、察民意的领导作用,在此也真正凸显出来。
暖水屯的土改过程,也是张裕民从“痞子”干部到“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的成长过程。张裕民不是一个完美的土改领导,他有英雄气,也有流氓气,近似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梁山泊好汉;而性格中的诸多顾虑,诸如延宕、犹豫构成了他的突出特质,这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戏剧主人公哈姆莱特。但他同时又具有秉持公心、勇敢敏锐、善于反思的一面,能够战胜自己的性格弱点,最终带领暖水屯村民打倒地主,成为了一名高素质的党员干部。张裕民是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在土改中真实成长的人。土改内外之间,暖水屯村民的“翻身”与“翻心”显示出更深远而持久的意义。张裕民,作为一名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党员干部,形象也更加鲜活、亲切。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丁玲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4 页、25 页、34 页、27 页、31 页、132 页、36 页、129 页、126 页、126 页、130 页、6 页、175 页、190 页、202 页、203 页、208 页、208 页、21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