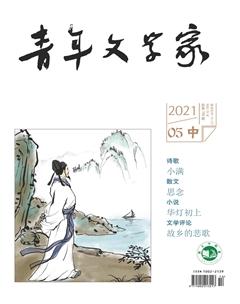论《小癞子》表层空间叙述模式下的时间形式
吕坤宁
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将长篇小说的历史类型按照主人公形象的构建分为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传记小说和教育小说四类,并指出在漫游小说中人物完全是一种空间状态的游历,在其中几乎看不到时间的流动,主人公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仅仅勾勒出了轮廓,全然是静态的,就像他周围的世界是静止的一样。”然而,漫游小说确如巴赫金所说是一种纯空间性质的位移吗?在其中“不知有人的成长和发展”吗?全盘否定漫游小说中人物存在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未免有失偏颇,仍须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与界定。在上述文章中,作者明确提到“这种塑造主人公和构建长篇小说的形式……对欧洲骗子小说(《来自托尔曼斯海岸的拉萨里奥》等)来说,具有典型性。”承接作者探讨,我们试对《来自托尔曼斯海岸的拉萨里奥》即为后人熟知的《小癞子》——这部开启西方流浪汉小说体裁的著作从时间形式方面做更深入的探讨。
“时间形式”是巴赫金在其小说理论中明确提出的重要概念,正式出现于《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一文的标题中,然而在学界却没有得到如“时空体”那般重视,“其相对独立的理论含义也湮灭在对‘时空体的众多解读之中”。在巴赫金看来,“时间”是人们用以把握世界的时空关系中的主导因素,而小说家“感受时间”的方式则对小说体裁及文学形象的嬗变起了根本性的作用。空间只是为具有时间性特征的文学形式的展开提供了可视化界面,在空间中呈现的众多元素,如人物外貌、性格、场景等,则是小说家得以表达时间观念的具体内涵,时间在这些元素的组织安排与描绘中具有了感性直观的性质。而若干年后学界对“现代性”的关注正与巴赫金的“时间形式”研究一脉相承,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巴赫金將《巨人传》视为现代性时间形式的典范,并因其刻画出以成长的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而作为教育小说体裁的代表区别于上述三类传统小说,然而在同一时期,当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席卷欧洲大陆时,于西班牙的国土上诞生的第一部以流浪汉为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自叙流浪经历的漫游小说《小癞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性时间形式的影貌,并非全如巴赫金所言“时间范畴的研究极其薄弱”。
本文将以《小癞子》于空间维度下展开的情节架构为始点,论述文本呈现的单向度波浪型的表层空间结构,其次表明空间视域下主人公以“第三者”的身份观察他人、认识世界,进而在空间的转换中确证世界的统一与不变,从而体现人物的孤立性与世界的统一性。最后论证文本通过空间叙述模式串联起主人公内部的性格变化与外部的饥饱状态,从而在主人公面向未来的未知命运中呈现出一种流动的时间结构,进而证明《小癞子》中存在现代性时间形式的萌芽。
一、单向度波浪型的表层空间结构
《小癞子》的叙述结构是以小癞子为核心,通过主人公在空间维度下的流浪经历串联起所有场景地点及故事情节,采用单向度叙事即顺叙的方式记录如波浪般此起彼伏的情节走势。在这样波浪型的单向度叙述模式中,开端往往较为平和,主人公在初始阶段处于相对安稳平和的环境。其后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常在状态遭到破坏,主人公被迫进入经历磨难、忍受痛苦、品味辛酸的历程。在一次次反抗绝望、挣扎求生过后,主人公以更加顽强的生命力与坚强的灵魂重新回到稳定的状态,甚至拥有更加完满的结局。历经磨难后的主人公的存在状态往往高于起始阶段的水平,而非如希腊小说般回到一模一样的过去,是一种更高程度上的成长和归来。
后来的流浪汉小说以《小癞子》为原型与范式,基本延续了上述单向度波浪般的连缀式情节结构,而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创新。如马提奥·阿列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几乎亦步亦趋地模仿小癞子的流浪模式,而更大规模地反映西班牙的社会图景;克维多的《骗子堂巴勃罗斯的生平》“也师承《小癞子》的创作手法,为我们塑造了巴勃罗斯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流浪汉形象”,而增加了象征性比喻手法的使用;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则在串联起整个历程的核心人物之外又增设了对情节发展起侧面衬托作用的次要人物,他们在故事中反复出现,从而增强情节之间的逻辑关联,使情节顺序基本固定。
在《小癞子》中,主人公通过跟随不同的主人共经历了空间维度下七个地点的位移。从被母亲托付给盲人以后,主人公便开启了他的流浪历程,从阿尔莫罗斯、马凯达再到托莱多城,小癞子先后为教士、侍从及差役等七个不同社会角色,始终过着悲惨辛酸的生活,直至在托雷都城跟随大神父当报子并与其佣人骈妇成亲,最终拥有了自认满意的物质富足却毫无尊严的“好日子”。整个历程是由小癞子串联起的空间转换形式下“出发—旅途中—遭遇问题—解决问题—继续流浪—终点”的叙述模式,“叙述重心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上‘有意义的片段,落实到身体痛苦之上的时间生活的每一点琐碎都被曝光”。情节之间并不具备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的“一致性”即严密的逻辑与连贯的结构,而是“主角像一条绳束,把散漫的情节像铜钱般穿成一串”,每个情节都展示出小癞子流浪生涯中的一次经验教训或一个生存道理,由此体现他逐渐形成的“市侩哲学”,同时借此为读者描绘出真实凄凉的底层社会图景与纷繁复杂的世态人情。
二、时间在世界层面的静止
主人公以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流浪汉”与“仆人”身份观察世间百态,并在空间地点的不停转移中认识人性善恶,觉悟世界的“不变”,时间以静止的样貌服从于世界的统一。
一方面,小癞子在被母亲托付于盲人之手后即成为社会中的流浪儿,处于一种被抛弃的状态,这就使得他与社会几乎不发生联系,而是充当社会中的“他者”,以富于孤立性与独自性的内在特征更加冷静客观地观察他人与看待世界。通过精明狡诈的盲人、虚伪吝啬的教士与坑蒙拐骗的推销员,小癞子在辨别人性善恶中学会各种求生之道,也在流浪世间的旅途中逐渐认识到世界的样貌——到处都充斥着欺骗、伪善与荒淫。小说假借流浪儿之口“揭露了新旧制度交替时代的种种社会矛盾,首次鲜明地突显了文学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因而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另一方面,小癞子通过跟随不同的主人以“仆人”视角窥视各种人物的另一面,揭露真实私人生活中的日常隐秘与不被广而告之的真正世相。正如巴赫金所说,“仆人在主人的私人生活里,永远是个‘第三者。仆人主要是个人生活的见证者。对仆人……是不大顾忌的,同时仆人又理应参与私人生活中一些隐秘的方面”。借助小癞子的仆人身份,我们看到了自奉不薄、顿顿珍馐的教会人员说着“教士应该吃喝得很清苦,所以我不像别人那样大吃大喝”的谎话;表面风光无限、气度翩翩的侍从却要依靠小癞子乞讨来养活两人;售卖赎罪券的教会人员竟与差役勾结串通坑骗无知民众、搜刮民脂民膏。这种以主仆模式为人物关系安排情节表现主题的叙事策略在《吉尔·布拉斯》《痴儿西木传》甚至流浪汉小说的变体《堂吉诃德》中仍典型存在。
《小癞子》以流浪汉与仆人双重身份下“第三者”的人物形象巧妙处理了小说表现形式的公开性与表达内容的私密性这一矛盾,其中描绘的上层贵族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底层百姓却生活艰难、贫苦不堪的真实世界毫无遗漏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然而,通过“第三者”的眼睛我们看到,整体的世界只是随着流浪历程的前进而逐渐显露完全,却丝毫没有因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有任何改变。赤贫者的绝望处境依然如故,“要生存不要尊严”的市侩哲学是唯一出路,教会的丑恶幽灵依旧游荡人间,这便体现了世界“不变”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故事情节的演进逻辑背后体现的时间形式没有作用于世界这一要素,世界在故事的起点与终点之间经历了超时间的空白,即巴赫金所谓“传奇时间”,时间在世界层面处于静止状态。
三、时间在人物层面的流动
有赖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破茧而出,“现代性”观念逐渐得以形成确立,“尽管现代性的概念几乎是自动地联系着世俗主义,其主要的构成要素却只是对不可重复性时间的一种感觉”。而现代性时間形式即是带有现代时间观念的文学形式——时间以一种不可逆性与未知性存在于文本空间的各要素中。在《小癞子》中,虽然时间在世界维度仍采用经典希腊小说静止的传奇形式,但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变化与事件经历层面,时间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流动状态,因而迸发出现代时间形式的萌芽。
一方面,在一次次空间位移的短暂驻足中,主人公在性格成长层面多次经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每个节点发生的事件都促使其心态情绪与认知经验产生变化,从而使文学形象于性格变化中展现时间流逝的痕迹,鲜明地表现出世俗时间的不可逆性,这与神话和史诗中循环性四季更替的传奇时间截然不同。在和母亲一起生活时,小癞子还是一个心地纯良的孩童,然而在遭遇世间诸多险恶后,他逐渐长成为唯物质利益至上、甘愿牺牲尊严与人格的市侩小人。当主人公被盲人欺骗、第一次见识到人言难测时才如梦初醒,“我无依无靠,得心尖眼快,留心照顾自己”,标志着其性格转变的开端;侍从一味追求外在形象的尊严甘愿挨饿受冻,甚至靠仆人乞讨养活自己,小癞子虽同情可怜他却也鄙弃这种空虚无聊的精神生活,决心不择手段地谋生以过上“好日子”;最终小癞子与大神父的骈妇成亲,对一切流言蜚语充耳不闻,甘当他人的笑柄。纵观全程,主人公“从饥寒交迫到成家立业的生活发展史,就是他的精神堕落史”,他希望通过劳动谋生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摧残,逐步走向精神堕落的深渊,人物形象在性格上的“变”则使我们看到了世俗时间的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地点与主人的不断变化,小癞子每一段历程中即将发生的事件都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读者抑或主人公都无法预料下一个主人是良善纯德还是贪婪奸诈,这就使得情节具有了面向未知的开放式的时间形式。如兜售免罪符的推销员串通差役演戏时,小癞子也信以为真,直至后来主人将其当作笑谈才觉悟。在小说结尾,小癞子说道:“我那阵子很富裕,正是运道最好的时候。”不禁引发读者猜测,主人公之后的经历是何种模样?既然是最好的运道,他又是怎样走入人生下坡路的?小说结尾呈现出未完待续的状态也使得后续的情节发展及人物形象成为不确定性的表征。总体来说,《小癞子》的时间形式是一种“现在性”的存在,“被时间折磨的是他的身体,饥寒交迫是他最大的困境,所以他的全部智慧也都被用于挣脱当下每时每刻存在的肉身痛苦”。但是在现在时叙述之中孕育着现代性即自我的改变与未知的时间观念的种子,而这一萌芽在《堂吉诃德》中得到延续与发展——不仅人物在变,外部环境即世界也在发生变化(参见第二部中加入堂吉诃德与桑丘对读者的反馈和对伪造的讽刺),从而实现现代性时间在人物与世界维度的展开。
综上所述,《小癞子》在主人公流浪地点的位移中呈现出单向度波浪型的表层空间模式,也正是在“移步换景”的空间转换形式中,时间的标志得以展现:主人公以流浪汉与仆人的双重身份展露人物的孤立性,进而在“第三者”的眼光中确证世界的统一性,体现时间在世界层面的静止;而主人公的性格变化与自身经历在一定程度上的未知则体现人物形象在时间层面的流动,即在《小癞子》中蕴含着现代性时间在人物这一维度上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