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存在论思想对比
葛玉海,曹志平
(1.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2.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技术本体论向技术存在论的转变,是哲学上“ontology”含义的演变在技术哲学上的投射。作为“本体论”的“ontology”,关注的是“存在”自身的本质特性,其主要问题是“什么存在”以及“什么优先存在”;而作为“存在论”的“ontology”,关注的是“存在”具有什么特征,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存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力图认识“存在”。不同之处体现在:一是在对“存在”的定位上,“本体论”认为“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存在论”认为“存在”是不断变化的;二是在研究方式上,“本体论”讲究的是“一线分千丝”,重点是“线”,“存在论”则是“千丝聚一线”,重点是“丝”。由此可见,由“本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变,其实就是从“是”向“如何”的转变,这集中反映了现代哲学的特征。
在技术哲学领域,技术本体论回答的是“什么是技术”“技术存在吗”等问题,其目的在于揭示技术的本质,并将技术与非技术区别开来;技术存在论回答的是“技术是什么”“技术如何存在”等问题,其目的仍是揭示技术的本质,但同时还涉及技术的具体形式和技术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技术是否存在和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往往是不能分开的两个问题”[1],因此,技术本体论和技术存在论总是相互交织的,而且在现代哲学背景下,广义的技术存在论是包含技术本体论的;另一方面,技术本体论和技术存在论作为对技术的终极探讨,又与对技术的具体经验现象的探讨密不可分,而且广义的技术存在论表明技术哲学研究的参考点已从“逻辑和概念分析”转向“历史和人的自我形象”[2]。由此可见,广义的技术存在论是技术哲学现代研究的基础平台。它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认识论研究,其核心问题是“现代技术是怎样的”或“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技术价值论研究,其核心问题是“技术的价值是怎样的”;技术本体论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技术”。
在技术哲学史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分别开创了广义的技术存在论研究的不同进路。马克思“透过技术表面上的‘物质形态’”,揭示了“现代技术与人的生产方式、存在方式以及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性关联”[3];海德格尔“分析了技术与存在的关系,揭示人与存在关系中发生的、由技术发展引起的重大变化,表明技术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2]。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目的在于“揭示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3],这既体现了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表达的一般哲学原则,又表现为以《资本论》为样式论述技术与经济发展和现实社会的具体关系的理论。海德格尔把现象学的任务规定为把存在从存在者中显露出来,诠释存在本身,并在阐述人的现象学存在中,强调运用工具的劳作即技术实践优先于科学认识、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这两种广义的技术存在论研究进路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上述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和技术本体论三个维度来展开。
一、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区分
在技术认识论领域,对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非常引人注目。马克思对“工具”和“机器”的区分是一种“客体上的区分”,而海德格尔对“技艺”和“现代技术”的区分则是一种“认识论-存在论”的区分。
(一)马克思在客体上对工具和机器的区分
马克思关于“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体现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分。在马克思那里,“工具”,尤其是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可以看作是古代技术的代表,而“机器”,特别是自动化的机器系统,则是现代技术的主要形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评了有关工具和机器关系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并无本质的差异,工具就是简单的机器,机器就是复杂的工具;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差异,它们的不同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而机器的动力是牲畜、水、风等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马克思直接举例反驳了以上观点。他认为,按前一种观点,像杠杆、斜面、螺旋等也会被称为机器,但这样做并无丝毫用处;按后一种观点,牛拉犁是机器,而由人手推动的织机不过是工具,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则是机器,这显然是荒唐的说法。
在马克思看来,工具和机器的区分需要借助于对机器的结构分析来显现。他指出,所有机器都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这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作为整个机构动力的发动机可以分为两类:自己产生动力(如蒸汽机、电磁机、卡路里机等)和由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所推动(如水车、风磨等)。传动机构则由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传轴、飞轮、蜗轮、齿轮、皮带、杆、绳索、联合装置等。传动机构的作用在于调节运动,如改变运动的形式(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将动力分配或传送到工具机上。发动机和传动机构只是把动力传送给工具机,而工具机则是直接面向劳动对象,并以一定的目的使之发生改变[4](P410)。
马克思表示,机器相异于工具之处体现在两点:第一,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工具的组合,这些工具由同一个机械同时来推动;而工具则是分散的,通常一个工具由一个人来推动。简言之,机器的工具在规模和动力上均不同于工人的工具。第二,机器内的工具并不是简单地放置在一起,而是不管在动力、规模上还是在作用、范围上都呈现出统一性,就像各式各样的锤都集中在一个蒸汽锤中一样[5](P451-452)。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实质上是可以用“工具机”或“工作机”替换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与工具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工具机和工具的差别[6](P94)。这种差别既反映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又体现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中包含的社会批判向度[8]。
以机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或工业生产使工人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转变。工人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是利用工具,而在工厂中则是“服侍”机器[4](P463)。生产工具的这种转变带来了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比如,在手工业技术时期,人们普遍爱惜自己的工具,甚至视若珍宝;而到了工业技术时期,对待机器的态度却明显分为两端:资本家对之肯定和称颂,而工人则对之深恶痛绝。
对资本家而言,首先,机器是追逐剩余价值的利器,是适应资本的现代生产方式。这是因为,如马克思所言:“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5](P365)其次,机器强化了统治地位。工厂主由于掌握着工人的就业手段,因此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工人的生活便不得不依赖于他[9](P643)。最后,运用机器是应对工人反抗的有效手段。机器一方面是工人强有力的竞争者,可以随时让工人“过剩”,另一方面它还被资本家有意识地宣传为一种可以利用的与工人相敌对的力量。在镇压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周期性暴动或罢工时,机器成了资本家最强大的武器。马克思借用盖斯克尔的话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4](P476)
对工人而言,他们眼中的“机器”则是另一番情形:首先,机器直接导致了他们地位的下降。一方面,工人的技能转移到了机器上,由于机器的运行成本低于人力劳动,故资本家对机器的依赖得到加强,而对工人的依赖则趋于减弱;另一方面,工人现在是终身侍奉某一种机器,而不再是使用某一种工具;机器的大量采用已使工人从一开始就变成某一种机器的一部分,工人只能依赖机器,依赖工厂,依赖资本家[4](P462)。其次,机器除了导致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6](P112)。最后,机器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强度。这一切都成为工业革命初期工人抗拒机器的原因。然而,即便颇具破坏力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也未能撼动资本家对机器的进一步制造和应用。正是在这种反复斗争过程中,机器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工业技术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核心内容。
(二)海德格尔对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在认识论-存在论上的区分
围绕技术与真理的关系,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海德格尔将技术看作是真理展现的一种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一致性仅表现在它们都是解蔽,两者的不同则在于:古代技术“把自身展开于ποíησι意义上的产出”[10](P12),而现代技术则“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0](P12-13),并“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10](P14)。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的区分不仅是本体论上的,而且也是认识论上的。原因有二:一是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框架。通过古代技术,人们看到的事物是“天、地、神、人的聚集地”,譬如,壶匠之“壶”。海德格尔说:“壶之壶性在倾注之馈品中成其本质。”[11](P179)这种馈品可以是一种饮料,比如水或酒。他解释道:“在泉水中,天空与大地联姻。在酒水中也有这种联姻。酒由葡萄的果实酿成。果实由大地的滋养与天空的阳光所玉成。在水之赠品中,在酒之赠品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10](P180)除此之外,水或酒还是“终有一死的人的饮料”[10](P180),或奉献给不朽诸神的祭品。譬如,一座被“筑造的桥”。海德格尔写道:“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桥已经为天气极其无常本质作好了准备……同时也为终有一死的人提供了道路,使他们得以往来于两岸。”[10](P160)除此之外,“桥”还象征着终有一死者通向诸神的道路。总之,不论是“壶”,还是“桥”,通过它而向人们展现的都是“四重整体”。通过现代技术,人们看到的事物只是单纯的事物。“壶”仅是一个起着容纳作用的器皿,“桥”也只是起着沟通两岸之功能的东西。
二是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还象征着“真理”尺度的变化。在海德格尔那里,“真理”指的是“本真状态”,即“无蔽”。追求“真理”的活动就是“解蔽”。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都是在“解蔽”。然而,由古代技术所得到的“真理”是“天、地、人、神的会集”。而由现代技术得到的“真理”仅是“正确性”[11](P101)。这种“正确性”是以满足“技术需要”为准绳的,换言之,是否适应现代技术是衡量“真理”的标准。
二、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技术价值的分析
在对技术价值的反思上,马克思以技术乐观主义统摄技术悲观主义,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海德格尔的观点则以技术悲观主义统摄技术乐观主义,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的高级阶段。然而,这一地位的获得都是依赖同样的努力:将狭义的“技术”扩展为广义的“技术”,并将后者视作解释或建构生活世界的依据或核心。由此出发,下一步便自然涉及技术与人的最初关联及其意义。也正是在此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分道扬镳了。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为人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技术的“器官延长说”,认为技术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海德格尔虽然并未否认技术是为人所必需的,但却认为,就“人”而言,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海德格尔将“最重要的”这顶帽子给了“思”,对“存在”之思。
(一)技术进步与技术作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
马克思的技术进步观是在技术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工具、技术与机器、技术与生产力,以及技术与科学、知识等理论关系的阐释中确立的。虽然马克思也在广泛的意义上,从人类改造自然的知识、方法、技能等方面,从技术是科学的应用的角度,理解技术和技术的进步,但马克思对技术和技术进步阐述的创造性和理论地位主要体现在狭义的技术方面,即马克思从生产工具、生产工艺、制造技能和方法等的创造、革新和改进的角度,对技术与生产、生产力和社会革命等关系进行阐释。
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技术形态日益多样,落后技术不断淘汰或原有技术日渐更新,以及技术效率逐步提高。首先,从利用生物的生理机能或通过强化和控制生物的生长过程以取得物质产品的农业技术,到借助生产工具并在手工业者个人经验和手艺的配合下加工大量的农业产品的手工业技术,再到利用机器对原材料和农业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工业技术,都表明技术形态日趋多样。其次,落后技术不断淘汰或原有技术日渐更新表现为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例如针、信封和钢笔尖等的制作,仅在很短的时期内是用手工业方法和工场手工业方法进行的,此后很快就采用机器方法了[5](P447)。最后,工业技术在生产的连续性、自动化和运转速度方面都优于手工业技术,这表明技术效率在逐步提高。例如,在钢笔尖的制造中,钢坯的切割、穿孔和开缝等在机器的一次运转中就可以全部完成[5](P443)。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进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技术革新的“链式”传导[6](P144)和技术的累积式发展。例如,在下游部门,机器纺纱使得纱的数量急剧增大,这就要求有机器能够织布,而这又必然带动染色业、印花业和漂白业等的快速革新。同样,在上游部门,棉纺业的革新引起了轧棉机的发明,而这一发明又促使对棉花的大规模种植[4](P421)。这体现了技术革新的“链式”传导。另外,马克思也曾以“磨”为例来说明技术的累积式发展:“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转入第一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18世纪末美国大量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5](P419)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技术的本体论地位是由技术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确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P78-79)人的生产和其他动物的生存的本质不同,在于人的生产是运用工具改造自然、创造财富,并在这种创造性活动和过程中形成和变革社会组织形式。这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技术作为生产工具,就成为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技术进入了人及其历史的定义。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生产,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这种“狭义的生产”含义外,还包括物质资料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的“广义的生产”含义。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决定着其他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性质和内容,制约着人自身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构和性质”[13](P782)。因此,技术进步不仅表现在技术推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进步上,也表现在技术推动精神生产的性质和内容的变化,以及人的生产及其社会组织形式的进步等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技术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生产”“物质生产”“实践”等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广义的技术。正是运用工具和技能的劳动,即技术生存,使自然性的人,成为社会性的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表明了人的社会性,它使人获得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首先体现着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能够从事生产,而动物最多只是搜集,即“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4](P383)。人通过技术让自然为自己服务、支配自然界,这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的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也比较了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P46)在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了对象性活动、脱离具体物质的技术和抽象的规律对于人类生产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动物的“片面的”生产也运用技巧和尺度,但动物的这种技巧和尺度是物种与生俱来的,不能脱离具体物质和生物需要存在的;动物用技巧适应自然界,而人却用技术,并以对象性的技术活动改造自然界、支配自然界。
其次,人类通过技术表明自己是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明确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2](P46)作为“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的生产劳动,在将自然界改造成人类自己的作品和与精神相对应的物质现实的过程中,证明技术是人类劳动的本质,人通过技术展示和延续自己的本质力量,也在他用技术所创造的对象性世界中直观自身。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作为人的类生活,使人成为社会性存在的条件和本质力量的意义更为明确了。一个人只有成为“被技术”的人,才有条件、资格和力量被看作是“社会人”,否则,不仅他的生存和生活无法维系,就连要认识世界、理解他人和社会,都会没有立足点。
最后,技术表明人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者。技术体现着“现实的人”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并不单单指的是人的物质躯体,更重要的是人从事劳动所依赖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马克思说:“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不过,这些肢体必定只是他本身占有的。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5](P105)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其实质便是“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4](P203)。
第二,技术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人的本质体现在人的感性劳作之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4](P580)人类的劳动过程不间断地维持着个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存在与运行。马克思强调,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在于“能够生活”,这要求人们必须从事生产,生产满足自身吃、喝、住、穿等所需的资料。这是一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2](P78)。“能够生活”才能够“创造历史”,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5](P310)。
第三,技术塑造着人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产方式“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换言之,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存在一致性。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2](P67)
(二)技术异化与技术作为存在者的出场方式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主要是指“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它来概括“劳动者”在私有制条件下同他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关系,从而提出“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可以看作是“技术异化论”的最初形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之后的一些学者,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都在不同方面对“技术异化论”有所贡献。这些贡献之一便是将“异化”与“自由”对立起来,并与“技术”相联系。海德格尔更是深刻地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它作为存在展现的方式并不受人们的控制;现代技术严重威胁着人的自由,即人的“本真”状态或“自身性”。以这种技术实体主义为基础,海德格尔的技术异化思想已不同于马克思的技术异化观。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技术化时代,技术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包括人在内的诸多存在者的出场方式。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认为,技术时代的人类被促逼进入解蔽之中从事订造。他们不仅是订造者,也是被订造者。作为订造者,人类的订造行为首先体现在精密自然科学中。这种精密科学将自然视为能量的储存器,“把自然当作一个先行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16](P311)。这是“集置”促逼的结果。“集置”要求现代物理学的“表象领域始终是不可直观的”,要求作为持存物的自然具备可订造性,即“自然以某种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的方式显露出来,并且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始终是可订造的”[16](P312)。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化自然观是现代技术的自然观基础。除此之外,人类的订造行为还指向各种具体的事物,这与“促逼意义上的摆置(stellen)”相一致。树木不再是植物,而是被订造的木材;鱼也不再是动物,而是被订造的食物。作为被订造者,人从出生就贯彻着被订造的要求:从妊娠、保胎到生产,从护理、喂养到教育,再从择业、提升到养老等;在被订造中,人们可能成了某种教育产业的对象、人力资源、潜在客户,甚或是某些医院的病人资源。因此,在现象学中,技术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也因为人的订造行为而成为其他存在者的出场方式。
作为命运的“集置”,现代技术既危害着人,又危害着解蔽。“集置”在人与一切存在者的关系和与其自身的关系上发生着危害。而它对解蔽的危害则体现为:驱除或遮蔽其他种类的解蔽,以及遮蔽解蔽本身、遮蔽无蔽状态。“集置”要求“以对抗为指向”,通过对持存物的保障和控制,建立与一切存在者的关联,这种解蔽排斥了如古代技术那样的“产出”(ποíησι)式的解蔽。另外,“集置伪装着真理的闪现和运作。”[16](P315)“集置”要求人们把自然解蔽为“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进而单纯根据因果关系来解释或描述一切存在者。人们“按照制作的因果关系来规定无蔽领域和遮蔽领域,而同时决不去思考这种因果关系的本质来源”。于是,“在一切正确的东西中真实的东西自行隐匿了”[16](P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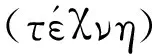
三、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探析
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不能归为芬伯格所说的“技术的实体论”(substantive theory of technology),也不能简单地归为狭义的“技术的工具论”(instrumental theory of technology)。其相关观点,首先符合“广义的技术的工具论”,即认为技术在根本上依赖于人类,并始终具有“工具性”这一本质特征;其次在价值论上表现出兼有“技术价值中立论”和“技术价值负荷论”的特征,但更偏重于前者。因此,我们可称之为“工具论意义上的技术本质观”。与认为技术具有不变的本质的“工具论意义上的技术本质观”不同,“实体论意义上的技术本质观”或者认为技术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或者认为技术的本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或者认为技术将会具有自己的独立本质。海德格尔的技术本质观,正是属于这种技术本质观。不过,“本质”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海德格尔这里已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的界定。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包括技术知识以及将这种知识付诸实施的设备)所共有的东西,而是“在所有这些技术中发生的东西”。
(一)技术作为人的本质的表现或外化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技术”一词的具体使用或“技术”在马克思那里的所指,密切关系到对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的正确理解。马克思经常使用“工具”“机器”“手段”“生产力”“劳动”“劳动资料”“分工”“发明”“工业”等与“技术”相一致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既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又是人类的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方式。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性,以及技术本身的工具性,决定了技术并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马克思说:“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17](P481)
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分析,更为直接地体现在他对工业的分析上。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存在内在一致性。首先,工业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构成全部人的活动。马克思说:“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5](P306-307)马克思在这里用“技术”“劳动”“工业”表达了人的非自然性,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以及人从原初的自然存在状态的远离和发展。其次,马克思还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15](P306)。最后,工业的进步标志着人的自由程度的提升。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2](P74),才能使人从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自由个性”[18](P107-108)。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P135)由“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一观点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的本质不是某种抽象的物,它体现着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自我解放。技术是历史的、发展着的,但技术的这种本质却是不变的。
(二)技术作为“集置”和“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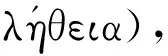
其次,现代技术是一种促逼着的解蔽。海德格尔指出,古代技术是通过“引发”或“招致”的方式使某物进入在场,“是在产出之范围内起作用的”。这种“产出”(ποíησι)既包含自然意义上的“从自身中涌现出来”,如花朵开放,又包含人工意义上的“使……显露”,如工匠制作银盘。现代技术(如动力机械技术)进行的解蔽则是通过“促逼”(Herausfordern)这种方式“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6](P306)。如果说古代技术是在“关心和照料”着自然,那么现代技术则是“在促逼意义上摆置着自然”。这种促逼意义上的摆置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开采”,换言之,被开采的对象虽然客观上是某种现成存在,但实际上却是被“订造”者。煤炭不再是开采出的自然物,而是被要求提供能量的“矿物”。
再次,现代技术是全部这种促逼着的解蔽的聚集,是“集置”。由于“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都是解蔽之方式”[16](P307),且构成一个序列,因此解蔽不会简单终止,而摆置也将继续。形形色色的摆置的聚合或聚集,称之为“集置”(Ge-stell)。德语的“Gestell”通常是指“骨架”“框架”“底座”“书架”等,而海德格尔则用“Ge-stell”(集置)来指代促逼意义上的“摆置(Stellen)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16](P310)。
最后,现代技术是一种支配着人类而又给人类指点道路的命运和意志。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需要通过“集置”来体现,但“集置”本身还不是现代技术的本质,除非“集置”是作为“解蔽之命运”的其中一种方式而被理解。“解蔽之命运”本身并不是预测未来的、不可更改的、不可回避的事件,而是已经发生的、被我们经验到的、为人指点道路的事件。在德语中,“给……指点道路”便叫做“遣送”,而“聚集着的遣送”便命名为“命运”(Geschick)[16](P313)。“集置”作为命运,为人类指点的道路是“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采取一切尺度”[16](P314)。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此道路上,对技术的追问却可以让我们发现危险之地,并于此找到出路。
四、总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代表的是从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出发对技术所进行的研究,而海德格尔的技术现象学代表的是对技术的形而上存在意义的追问。两种进路都从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中导出技术作为人的生活方式、技术体系具有自主性,都从对技术价值的分析中导出技术作为人的价值载体,都从对技术本质的解析中导出技术作为人的本质体现,而且三个结论分别在认识论、价值论和本体论层面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两种进路除了具体内容的差异之外,还在出发点、使用语言和最终归宿上有所不同。首先,从逻辑上讲,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研究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研究,它立足于抽象的人来阐述人的存在;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研究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研究,它立足于现实的人来阐述人的存在。其次,马克思很少抽象地使用“技术”一词,而是经常使用“生产力”“工具”“机器”等具体概念;而海德格尔使用的则是“解蔽”“摆置”“集置”等抽象概念。最后,马克思关于技术的思考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而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考则形成了抽象的形而上学技术观。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是其存在主义思想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应用。总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和海德格尔的技术现象学,都因其宏观性、深刻性,以及较高的系统性和合理性,而成为20世纪哲学诠释技术和人类生活的两种“范式”,也为以后的技术哲学研究奠定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