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地区壁画看唐代琵琶的孤柱现象
温 和
内容提要:五弦琵琶曾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件弹拨乐器,也是隋唐时期宫廷音乐活动中最活跃的乐器之一。然而由于这件乐器唐代以后突然消失在音乐史的舞台,后人对它的认识日渐贫乏,倚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注引的来自五代陈游《乐苑》的一条文献,人们将文献中提到的“孤柱”视为五弦琵琶最重要的柱制特征,并将其视为区别于其他琵琶类乐器的标识。由于《乐苑》一书的佚失,《乐府诗集》转引的寥寥数句并不能使我们十分清楚此条文献的源出与时代,而从出自新疆地区的几种壁画图像以及考古实物可以发现,“孤柱”并非五弦琵琶所特有,其内涵也远较传统的认知更复杂。本文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揭示与解读,结合与其他历史文献的比较,提出“孤柱”并非五弦琵琶的特有而是见诸唐代琵琶类乐器的一种普遍性柱制设施的观点。
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收录的唐代元稹《五弦弹》诗题下注引五代时期陈游《乐苑》曰:“五弦未详所起,形如琵琶,五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五,隔声二十,柱声一,总二十六声,随调应律。”这里的五弦指的是南北朝至唐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直项五弦琵琶,因为这件乐器唐代以后逐渐失传,使欲了解它形制的后人不得不倚赖历史文献对于它的描述。由于陈游《乐苑》原书已经佚失,《乐府诗集》的注引成为目前所知描述这件乐器的唯一历史文献,受这条文献的影响,人们注意到文中提出的一种独特的柱制名称——“孤柱”,并将之视为五弦琵琶的重要柱制特征,尽管现代的学者对它的所在无论弦次与位置均提出过不同的设想,但对它作为五弦琵琶区别于其他琵琶类乐器的标识性设施这一点则深信不疑①。
关于“孤柱”的含义,虽然陈游文中并未对它进行具体的说明,但由于“柱声一”的描述,人们因此普遍相信它是单独设立于五弦琵琶某一弦的一种特殊小柱——因为只有当此柱仅被设立于五弦中的某一弦,才能只对该弦起增置一处音高也即为整件乐器只增“柱声一”的作用。从字面上看,这种理解也能与“孤柱”的“孤”字相契合:正因小柱专设于某一弦而不涉他弦,所以可以被理解为只涉一声,堪称“孤柱”。
尽管笔者早年曾在对唐传五弦琵琶乐谱的研究中对“孤柱”作为五弦琵琶的特征柱制提出疑惑,但一直只作为一种旁论内容附加于五弦琵琶谱字的论证。直到2018年下半年,笔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首期邀访学者的一员在考察新疆地区的石窟壁画过程中,综合比较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发现的“孤柱”与早年从吐鲁番地区剥除壁画的德国探险家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著作中披露的胜金口寺、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壁画中的“孤柱”形象,越来越意识到“孤柱”作为一种唐代琵琶类乐器的普遍性设施所具有的独立研究价值,遂对此开展专门的探索,并分图像与文献两篇予以专论。
一、《乐苑》所述“孤柱”在古龟兹地区壁画中的图像表现
在正式谈论吐鲁番地区壁画对“孤柱”内涵的丰富之前,很值得花费一些篇幅来进一步审视《乐苑》中提到的五弦琵琶柱制。由于正仓院所藏的存世唯一五弦琵琶在明治时期曾因缺失三柱接受过修缮②,《乐苑》所写也因此失去了传世五弦琵琶孤本对它的实物论证,尽管亲自考察过这把乐器的林谦三先生发表过相当可观的论证,说明这把乐器现有的五长柱柱制实为工匠修补时的误作③,但由于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乐苑》的描述本身,是故无论这把唐代遗物的现有柱制是否可疑,它本身都不能作为一个例子为“孤柱”提供任何验证。而另一方面,从隋代张盛墓出土的持五弦琵琶乐俑所持可以看到,五长柱的五弦琵琶并非空想,它确曾作为隋唐时期五弦琵琶的标准柱制广泛应用于宫廷燕乐,这种柱制在隋唐燕乐调中具有一种重要的功能,它的意义可由唐传日本的五弦琵琶乐谱中的一首得以揭示。④
尽管正仓院所藏五弦琵琶修缮前的柱制形态未明,而由张盛墓出土乐俑等材料证明隋唐时代标准五弦琵琶为五长柱的柱制,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乐苑》所写的“孤柱”,却频频见诸以写实风格著称的新疆地区石窟壁画,而现存克孜尔石窟135窟正壁说法图右侧的五弦琵琶头部残留,更似《乐苑》所写柱制形态的完整写照(图1)。

图1 克孜尔135窟正壁五弦琵琶残留
如图1可见,尽管壁面损害严重导致图像漫漶,但是最能描写五弦琵琶头部的重要特征竟无不保留,泥土局部掩盖下的直项、五轸依旧清晰可辨。值得一提的是,其三上二下的弦轸位置与见于丝绸之路各类遗址的五弦琵琶完全一致,可见为对五弦琵琶实物的准确描绘,而从施色的分别上看,则可以断定为画作描写的原貌。
更为难得的是,除了弦轸的数量与位置,这幅壁画将乐器的柱制展现得一览无遗:其琴颈部分以深色绘出如同四弦琵琶所设的四柱,而第四柱下方,豁然可见一特别小柱被单独施设于高音弦。毫无疑问,这当然就是因《乐苑》的描写而被我们熟悉的“孤柱”,而《乐苑》中“四隔,孤柱一”的柱制描写,也仿佛因与眼前四长柱下方设一小柱设计的完全吻合,被证明它的史料价值,使人不得不感叹如此历经千年的完整信息,竟似为了证实文献的真实而幸存在破损严重的壁面上。
从画面上看,壁画描绘的五弦琵琶柱制与《乐苑》的重合已是显而易见,然而它所包含的学术信息却远不止于此,以笔者之见最值得珍视的有两点:其一为这幅壁画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时代;其二为乐器柱制方面的信息,其中最值得提请关心的,是“孤柱”与第四柱的间距,但其意义之重大,须经与以往研究的比较方能指出。
自1940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在《国宝五弦谱的解读端绪》一文中发表对“孤柱”的位置判断以来,尽管现代学者对由《乐苑》所提出的“孤柱”是为五弦琵琶的特征柱制深信不疑,但对“孤柱”的具体弦次与位置并未达成共识,包括林谦三先生的最初意见在内,至今发表过不少于三种的设想:
1.第五弦上较【五】字——也即高音弦最高音——高二律的位置⑤;
2.第四弦上“乘弦与第一个长柱之间”——也即较空弦高一律——的位置⑥;
3.第四弦上较【也】字——也即第四弦最高音——高一律的位置⑦。
以上三种设想的第一种和第二种都曾由提出者以唐传五弦琵琶乐谱的研究作为合论,第三种设想则是因否定前二种的设立而予以假设。
而由于克孜尔135窟这幅壁画的“孤柱”与第四柱的间距与其他柱之间大约相等,可以判断图中所绘的乐器其“孤柱”被设立于高音弦上较第四柱高一律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之前学者们正式提出的关于“孤柱”所在的三种设想不仅得不到克孜尔135窟壁画内容的支持,相反,135 窟壁画内容对《乐苑》中所写“孤柱”所在给出了“新的”意见。考虑到该壁画所属135窟处于克孜尔石窟衰落期也即公元8-9世纪,我们可以相信这幅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乐苑》的成书,其中所写,正是对一个世纪前在龟兹地区出现过的某种五弦琵琶形态的忠实记录。
二、吐鲁番地区壁画中出现的另类“孤柱”形态
在对克孜尔石窟呈现的古代龟兹地区壁画中的“孤柱”与《乐苑》中所写进行的追认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将目光聚焦在吐鲁番地区壁画中所呈现的“孤柱”内容。我们知道,吐鲁番即古代高昌故地,地处西域与中原的交汇点,是西域各国中保持汉族文化最著名的一个国家。正由于古代高昌地区与龟兹地区文化品格的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跨地区文化中呈现的异同是深入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历时性差异的重要参照。
首先值得我们援引以重估“孤柱”内涵的是1902-1907年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Koeni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从吐鲁番剥去的一幅佛寺壁画,这幅壁画被刊载在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913年发表于柏林的《高昌》一书(图2-1、图2-2),被收藏于原来的柏林民俗博物馆、现在的柏林国立博物馆群(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下属的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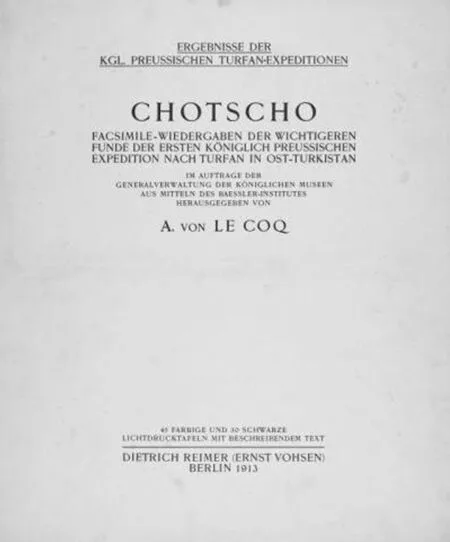
图2-1 1913年出版的《高昌》一书扉页

图2-2 《高昌》中的胜金口佛寺壁画图片
根据勒·柯克书中的说明文字,这幅壁画出自于胜金口峡谷(Schlucht von Sängim)中的佛寺⑧,编号第7。从壁画左下角可以看出一抱弹琵琶以供奉菩萨的伎乐童子,虽然图中琵琶并未绘出琴轸,但从琴首的形态可以看出来是一面直项琵琶,除了琴身的月牙形音孔和捍拨,最夺人眼目的无疑是琴颈上的音柱:除了被童子左手握持而遮拦的音柱之外,我们尚能看清左手下方的三长柱,而出人意料的是长柱以下靠近高音弦的部分,赫然二枚我们已熟悉的“孤柱”。
显而易见,这是《乐苑》所述的“孤柱”的一种通融或者说发展,这种可谓“孤柱不孤”的另类柱制使我们重新省察从前对“孤柱”的认知时进一步确认“孤柱”的意义——它的实质是为了乐调的需要而增设的附加性构造,而不同的设置体现了不同文化区域各自的乐学需求。尽管我们尚无直接证据阐明吐鲁番地区与龟兹地区的分别音律,但是从胜金口佛寺壁画上两枚孤柱与其他柱的关系看来,这件乐器可以在高音弦的长柱下方演奏两个半音。
考古资料显示,这幅壁画的年代约在公元10世纪。
再来看“孤柱”所属的乐器。前面提到,尽管这幅壁画没有出现琴轸而无法推测弦数,但是从琴首的表现来看显而易见是直项琵琶中的一种。这仍然符合我们由《乐苑》而得到的“孤柱”是为五弦琵琶特征柱制的传统认知,因为就隋唐时期乐器的主流而言,五弦琵琶是直项琵琶中最重要的代表,这一点无论从丝路沿线遗址的石窟壁画还是中原的历史文献或者出土的各式乐俑都能得到确认。也就是说,“孤柱”作为五弦琵琶/直项琵琶所特有的标识性设施的这一点判断到现在为止仍然成立。
然而吐鲁番地区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另一例“孤柱”图像则推翻了这种必然(图3-1、图3-2)。

图3-2 柏孜克里克石窟16窟“婆罗门奏乐图”局部

图3-1 柏孜克里克石窟16窟“婆罗门奏乐图”
这幅壁画来自柏孜克里克16 窟著名的“婆罗门奏乐图”,图像绘于正壁“涅槃变”的一侧,表现婆罗门外道对佛陀的涅槃表达内心的欣喜而奏乐庆贺,尽管演奏各种乐器的婆罗门外貌尤其脸部已遭严重破坏,但从身体发肤的形态以及线描的风格仍然呈现出典型的汉族风格,婆罗门演奏的乐器清晰可辨的有横笛、筚篥、琵琶、拍板、大鼓等,其演奏姿态的生动逼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考古资料显示,这个石窟的年代与壁画内容相当,约为公元9世纪⑨。
虽然画面的整体破坏颇深,图中的琵琶形态却侥幸保存完整,琴首的形态与四个弦轸将这把琵琶的性质展现无遗,毫无疑问这是一把隋唐时期典型的曲项四弦琵琶,也是当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乐器之一。然而正是在这件毫不陌生的四弦琵琶上,我们可以从婆罗门正在按弦的左手四隔之下发现一枚清晰的小柱,难以置信地施设在靠近高音弦的面板边缘。
毫无疑问,这幅壁画彻底颠覆了以往将“孤柱”视为五弦琵琶特征柱制的习惯认知,这枚意外出现在四弦琵琶上的“孤柱”暗示了受《乐苑》影响所致将“孤柱”以为五弦琵琶特有的旧知识需要重新审视:因《乐苑》而被人注意的“孤柱”不仅仅在唐代前后的五弦琵琶上以不同形态出现过,也曾在唐代前后的四弦琵琶上出现过。
有意思的是,除了四弦琵琶之外,笔者在《旧唐书·音乐志》中也发现了两种在唐代曾经出现过但未流行的乐器。大概正因为这两件乐器的微不足道,这两条文献似乎从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因为从未有人谈及这两件乐器共同的一个特点——它们都用到了“孤柱”:
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长,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旧唐书·音乐志》)
毫无疑问,文献中所写的“六弦”以现代的认知习惯可被称为“六弦琵琶”,正如同“五弦”之作为五弦琵琶的传统名称。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件近乎被遗忘的乐器在后代没有获得传承,细心的读者却可以注意到《旧唐书》对它的描述与《乐苑》中对五弦琵琶的描述同出一辙。尤其是对柱制的描写,可以看出来与《乐苑》的“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五,隔声二十,柱声一,总二十六声,随调应律”几乎出自一个人的笔下——因此既可以看出六弦琵琶与五弦琵琶在柱制上的类同,更可以看出《旧唐书》与《乐苑》的这两条文献从写法来看显然辑录自同一史料来源⑩。这条文献在此出现说明:在“孤柱”被施设于五弦琵琶的时代,这一只作用于某一弦而只产生“柱声一”的特殊小柱,同样也被施设于以五弦琵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最早见于天宝年代的“六弦琵琶”上。
除了与五弦琵琶形制相近的“六弦琵琶”外,《旧唐书》还记录了一种与五弦琵琶形制较远的“七弦琵琶”——当然在尚未失传的当时仍被称为“七弦”:
七弦,郑善子作,开元中进。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旧唐书·音乐志》)
可以看出,这种“形如阮咸”、弦隔也如阮咸琵琶的“七弦琵琶”跟五弦琵琶并没有特别的渊源,更像是一种汉制琵琶的发展,然而即使在这种几乎完全发展自中原旧制的“七弦琵琶”,依然设有产生“柱声一”的“孤柱”。
三、结论
除了图像学、文献学方面材料所揭示的孤柱现象,过去二十年的考古工作也为“孤柱”的研究提供过更为具体的出土实物材料——现存新疆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的“国内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琵琶类乐器实物”⑪证明,出现在和田地区的这把被证明长期演奏过的“三弦琵琶”唐代以前实物上,与本文所案例的新疆地区壁画上出现的五弦琵琶、四弦琵琶一样施设有作用于高音弦的“孤柱”,这个至今仍遗留在乐器实物上的“孤柱”的所在,正相当于位于较最高音高一律的半音位置。⑫
综上,既然同样意义的“孤柱”可以在五弦琵琶之外被施设于三弦琵琶、四弦琵琶、六弦琵琶、七弦琵琶,将它作为五弦琵琶的特征音柱这种认知依据显然是正被证伪了的。这几种按照传统认知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来源的琵琶——代表波斯系曲项琵琶的四弦琵琶、代表印度系直项琵琶的三弦与六弦琵琶、代表中原系阮咸琵琶的七弦琵琶——在相近的历史时期施设过同一功能的“孤柱”,证明“孤柱”在丝绸之路上曾经作为一种被跨文化应用于不同弹拨乐器上的普遍设施,正因如此,这种普遍出现在各类琵琶乐器上的特别设施不能被视为某种琵琶乐器的标识性音柱,而只能被视为琵琶乐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另一方面,从集中出现在新疆地区壁画的孤柱现象以及出土实物来看,这种在唐代文献中被人认知的“孤柱”并非中国的创造,而是古代西域既有的一种旧传。尽管这种临时增设音高的柱制设施在唐代以后的琵琶上随着琵琶乐器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论数量还是乐学内涵都颠覆“孤柱”之名的标准施设,但是正如上文所及,曾经出现在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的琵琶乐器上的“孤柱”证明,它的早期应用是丝绸之路上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唐代文献对它的记载显然并不能证明它是唐代中国的独创。而出现在《旧唐书》中显然发展自阮咸琵琶的七弦琵琶则证明,孤柱现象在唐代中国不仅仍旧流行,甚至被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汉制乐器上予以实用。
注释:
①以明治时期接受过修缮的正仓院藏唐传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为例,由于这面唯一存世的五弦琵琶现有五长柱而无“孤柱”的施设,实地考察过此五弦琵琶孤本的林谦三因此引用《乐苑》论证断定它现有的柱制为工匠在修复过程中错误地“参照琵琶而补上了一个长的第五柱”使然(见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第292页),其后学者也多持此见从未提出异论。
②“The label attached to the instrument states that three of the frets were missing,but all of the present frets seem to be of new material,added during the MeiJi era repairs.Although some may represent the positions of the original frets,the present fret layout is not of primary significance as source material because all seem to have been repaired.”见《古代楽器の复原》,日本音乐之友社,第31页。
③林谦三:《东亚乐器考》,第292页。
④五弦琵琶这种五长柱的柱制形态在张盛墓之外另有多种出土乐俑与壁画可以佐证,对此笔者曾发表多篇论文予以专论,可供参考。
⑤[日]林谦三:《国宝五弦谱的解读端绪》,载《音响学会》,1940年第2期。继林谦三之后,中国学者何昌林先生在1983年发表了同样的判断。见《唐传日本〈五弦谱〉之译解研究(上)》,载《交响》,1983年第4期。
⑥[澳]Nelson著,赵维平译:《五弦琵琶的柱制及其谱字配置》,载《音乐艺术》,1992年第1期。
⑦庄永平:《〈五弦谱〉中的“小”谱字研究》,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
⑧另据收录此壁画图像的《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9)的文字资料,此幅壁画的出处“胜金口佛教寺院与石窟位于吐鲁番东50千米的火焰山谷口”。
⑨《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
⑩有关这两条的文献的史料来源,笔者将另文予以专论。
⑪这把三弦琵琶于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在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对托普鲁克敦佛教寺院2号遗址作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从农民手里获得并随之现场勘查其出土位置,被初步断代为5-8世纪之间。
⑫张寅:《达玛沟出土琵琶的柱制结构研究》,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