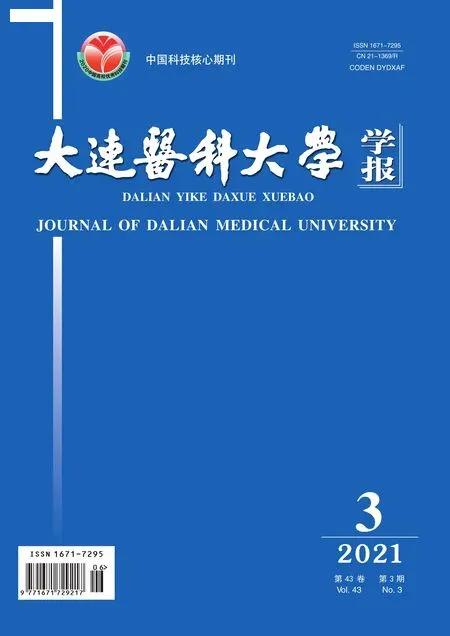糖尿病患者肺功能损害的特征及机制研究进展
郑淑妹 综述,王镇山 审校
(1.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呼吸病院 呼吸肿瘤科,福建 厦门 361021;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呼吸科,辽宁 大连 116027)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是影响全身的一种常见代谢紊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2013年我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显示,18岁及以上人群DM患病率为10.9%[1]。以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多见。DM的并发症主要是代谢、血流动力学和炎症因子所致的大血管和微血管损伤,导致视网膜病变、肾病、周围神经病变和截肢,以及危及生命的大血管疾病[2]。庞大的毛细血管网和丰富的胶原和弹性蛋白纤维使得肺脏成为慢性高血糖的潜在目标。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DM患者存在肺功能的损害,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percentage of predicted, 占预计值%)下降10%被认为是DM患者全因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3]。本文主要对DM患者肺功能的临床特征、肺组织的病理变化及肺功能损害的机制进行综述。
1 DM患者肺功能的临床特征
1.1 肺功能的改变
1.1.1 肺通气功能变化
DM患者存在肺通气功能损伤,主要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大量研究表明,DM患者的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和FEV1低于健康人群,部分研究发现DM患者同时具有更低的肺总量(total lung capacity, TLC)、肺活量(vital capacity, VC)、最高呼气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 PEF)、最大吸气压力和最大自主通气量(maximal voluntary ventilation, MVV)。并且证实了DM对肺功能的负面影响与DM类型、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吸烟史、肺部基础疾病及心衰病史无关。有前瞻性研究发现,DM患者发生限制性肺功能损害的风险是非DM患者的1.6倍,而患阻塞性肺功能损害的风险并未增高[4]。拉美裔社区健康研究和哥本哈根城市心脏研究均发现DM组与非DM组相比具有更低的FEV1和FVC[5-6];在无慢性肺部疾病并且从未吸烟的患者中,多项研究发现T2DM患者存在多个肺功能参数下降,包括VC、FVC、FEV1、PEF、TLC、MVV、最大吸气压力、最大呼气峰流速和最大吸气流量[7-9];另外,两项荟萃分析均一致证实了T2DM患者存在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10-11],其中2010年的荟萃分析观察到1型糖尿病患者具有相同的肺功能损害[10]。因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时肺充血状态会使得FEV1和FVC下降,而DM患者中出现HF的比例高达15%,以上部分研究未排除潜在的HF对肺功能的影响,但有研究表明DM对肺功能影响与是否合并HF病史无关[12]。
1.1.2 肺换气功能变化
大量研究表明DM患者同样存在肺弥散功能下降。荟萃分析结果显示,DM组患者存在肺弥散量(lung diffusing capacity for carbon monoxide, DLCO)占预计值%的下降,并且与DM类型无关[10]。在排除了合并心肺疾病及吸烟因素的干扰后,Anandhalakshmi等[8]研究发现T2DM组的DLCO和单位肺泡一氧化碳弥散量(ratio of DLCOto alveolar ventilation, DLCO/VA)均比对照组显著减少,进一步证实了DM患者存在肺弥散功能的下降。有趣的是,DM患者由坐位转为仰卧位时DLCO并不随之增加[13-14];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即使在静息状态下T2DM测得的DLCO与健康组未见明显差异,但在运动高峰期,肥胖和非肥胖T2DM组与对照组相比DLCO均有所降低[15]。静息及运动状态下肺弥散功能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肺脏具有巨大的贮备功能所致,当DM对肺弥散功能的负面影响在机体代偿范围内时,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测得的DLCO可没有明显变化。
1.2 肺功能的影响因素
1.2.1 通气功能的影响因素
DM患者的肺通气功能与血糖控制水平、DM病程及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在前瞻性研究中,弗里曼糖尿病研究观察到血糖控制欠佳的T2DM患者存在多个肺功能参数的下降,该研究表明T2DM患者的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和血红蛋白A1c(Hemoglobin A1c, HbA1c)均分别与VC、FVC、FEV1和PEF呈负相关[3];同样,在对T2DM患者进行的长约(4.9±0.6)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血糖控制较差的T2DM患者(至少2次HbA1c年平均值≥7.5%)具有更低的MVV[16]。并且,DM患者的肺功能水平也与DM病程及有无DM并发症相关。Yeh等[17]研究发现DM患者的FVC和FVC占预计值%随着DM病程的延长而降低。弗里曼糖尿病研究发现DM并发症视网膜病变及慢性心脏病与VC占预计值%、FVC占预计值%和FEV1占预计值%独立负相关[7]。另外,也有研究表明血糖水平与肺功能的负向关联同样存在于DM前期患者和正常人群[5,18-19]。
1.2.2 换气功能的影响因素
肺弥散功能也与血糖控制水平和DM并发症相关,在合并微血管病变的患者中尤为明显。有研究表明,HbA1c>7%的DM患者具有更低的DLCO[8]。糖尿病患者存在DLCO下降,这既反映肺泡毛细血管膜的增厚,也反映存在肺血管网的微血管病变。与其他器官一样,糖尿病似乎通过增加血管壁厚度对肺微循环造成损伤[20]。因此,糖尿病患者DLCO的降低与其他血管并发症的严重程度相关,如视网膜病变、肾微血管病变和糖尿病神经病变[15,21-22]。其中,尿微量白蛋白是发生肾小球微血管病变的最早期的指标之一,有研究表明尿微量白蛋白是DLCO/VA的独立预测因素[23]。但是由于肺的储备较大,在同等严重的解剖器官破坏情况下,其他器官出现症状和残疾的时间早于肺部。
1.3 肺功能损伤早于DM诊断
许多研究表明DM发病之前即存在肺功能损伤,主要表现为FEV1和FVC的下降。美洲原住民强心研究在代谢综合征或T2DM发展之前就检测到肺功能受损[17],ILERVAS研究也发现DM前期患者存在FEV1占预计值%和FVC占预计值%的下降[18]。而在随访研究中,同样观察到DM发病前期已经存在肺功能的下降[24-25]。其中,标准化老龄化研究发现,发展为DM的男性病例组在确诊为DM之前就具有更低的FEV1和FVC,但差异仅在有吸烟史人群中具有统计学意义[25]。由于吸烟降低了男性获得的最大FEV1值并且增加其FEV1下降率[26],故当患者同时具有吸烟史和DM时其肺功能损伤更加明显。由于DM发病时间点难以确定,故对于在DM发病之前多久开始存在肺功能损伤难以评估,也有研究认为肺功能下降大约在T2DM诊断前1~3年[3]。
1.4 肺功能下降速度
肺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有部分纵向研究试图确定DM是否加快肺功能的下降速率,研究结果因随访时间、实验设计和研究人群的种族背景等差异而有所不同。在随访期间从平均11.9年至15年的研究中,结果表明DM患者FEV1及FVC的下降速度并未增快[6,25]。然而,在较短的随访间期中,有研究观察到DM患者存在较快的肺功能下降速度。其中,哥本哈根城市心脏研究在随访5年的研究发现,新发的DM患者具有更快的FEV1和FVC年下降率[27]。同样,弗里曼糖尿病研究在随访7年的观察中发现,T2DM患者的FVC和FEV1的年下降率接近于普通人口的2倍[3]。综上,DM是否加重患者的肺功能下降速度尚存在争议。不排除患者在确诊DM之前由于高的FPG和IR水平从而加快肺功能下降速度,但患有DM本身可能并不加快肺功能的下降速度。
2 DM患者肺组织的病理变化
DM患者肺组织病理学表现为肺泡上皮和肺毛细血管基板增厚,肺泡间隙缩小,纤维化和微血管病变加重,黏液分泌减少[28]。DM患者尸检和经支气管活组织检查显示与肾脏相似的肺泡-毛细血管基底膜厚度增加,肺泡壁结节性纤维化[29-31]。在动物的糖尿病肺模型中,研究发现,肺组织肺泡间隔甘油三酯含量升高,细胞内外脂质沉积,巨噬细胞聚集,间隔增厚,胶原纤维和间质基质增加,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气-血扩散屏障平均厚度增加,并伴有Ⅱ型肺泡细胞形态的改变[32-33]。这些肺间质的改变导致肺的纤维化和硬化,进而导致肺体积及其顺应性的减少,从而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而肺泡-毛细血管基底膜的增厚和肺纤维改变导致肺泡内部与肺毛细血管内红细胞之间的气体交换距离和时间延长,可导致肺弥散能力降低。
3 DM患者肺功能损伤的机制
肺功能降低与DM之间的联系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目前评价解释DM患者肺功能损伤的可能病理生理机制包括: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低度慢性炎症、肺泡毛细血管和肺小动脉微血管病变、累及呼吸肌的自主神经病变和肺实质胶原糖基化所引起的弹性回缩丧失。
3.1 IR
DM患者糖代谢紊乱是由于胰岛素缺乏、IR或两种机制共存引起的。多项研究一致表明,IR与肺功能差相关,肺功能损害增加患DM的风险。英国女性心脏与健康研究显示IR与高龄非DM女性的肺功能(FEV1和FVC)之间存在线性负相关[34]。在一项对75例非DM肥胖女性的研究中,发现IR是FEV1占预计值%的独立决定因素[35]。瑞典两项在非DM受试者进行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同样观察到了肺功能与IR及DM之间的负向关联,其中对中年高加索男子的研究发现[36],低FVC、早期胰岛素应答受损和晚期高胰岛素血症均是T2DM的独立预测因子;另一项研究发现,基线FVC占预计值%与随访的IR和DM患病率显著负相关[37]。
3.2 低度慢性炎症
低级别慢性炎症是T2DM病理生理学固有的[38]。血清的高炎症状态与肺功能损伤相关。韩国针对不吸烟健康男性受试者的大型研究显示,最低的FVC占预计值%和FEV1占预计值%四分位数与较高的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独立相关[39];英国地区心脏研究对4 434例无心血管疾病或DM病史的受试者研究发现,基线FVC、FEV1和FEV1/FVC与血糖水平和炎症标志物(C-反应蛋白、白介素6和白细胞计数)呈显著负相关[40];Yeh等[17]研究发现,DM患者的FVC、FVC占预计值%、FEV1和FEV1占预计值%均随着C-反应蛋白和纤维蛋白原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在动物模型中,观察到DM肺组织中氧化应激增加,抗氧化酶SOD活性降低[33,41]。这些结果强化了炎症标志物与DM患者肺功能下降之间的潜在联系。
3.3 微血管病变
DM微血管病变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糖尿病足和神经病变,发生率约为53.5%[42]。已有研究表明DM患者静息及运动状态下测得的DLCO存在下降[8,13-15],并且下降程度与微血管病变相关[21-22]。其中,Fuso等[13]研究发现DM的存在是肺毛细血管容积姿势改变的预测因子,可能反映了仰卧位时上叶肺毛细血管缺乏募集。在动物模型中,Yilmaz等[43]研究发现,肥胖的T2DM大鼠的平均肺血流量、DLCO、膜弥散量和肺毛细血管容积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在给定的肺血流量下测得的DLCO降低了20%~43%,并且T2DM鼠的肺体积和顺应性降低了13%~35%,表现出明显的限制性肺损伤。
3.4 自主神经病变
神经病变是DM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周围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在DM患者中,膈神经与周围神经一样存在病变。Yesil等[44]研究发现DM前期组和DM组双侧膈神经的波幅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也有研究发现,T2DM患者存在呼吸肌力下降,并与肺容量和代谢控制质量密切相关,而呼吸肌耐力下降在合并有微血管并发症的患者中尤为明显[9]。部分病例还报告了DM膈神经病变导致膈肌瘫痪,并出现呼吸困难[45]。其中,Rice等[45]研究发现酯药物可能是治疗顽固性膈肌麻痹和表皮内神经纤维再生的有效药物。
3.5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增加
晚期糖基化终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是由糖代谢控制中断产生的稳定共价化合物。已有研究表明AGEs的形成和积聚参与了DM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制[46],AGEs也可引起肺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非酶糖基化,导致肺弹性降低[2]。正常肺组织能够表达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RAGE),RAGE在Ⅰ型肺泡上皮细胞中可能参与了肺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异常高水平的RAGE表达可能表明肺中存在严重的病理生理条件,如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47]。AGE-RAGE结合激活病理生理学级联,导致肺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促炎症效应和细胞凋亡[47]。
4 小 结
综上所述,目前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DM患者存在肺功能损伤,以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及弥散功能损伤为主要表现。临床上许多DM患者并没有表现出呼吸功能障碍等临床症状,这可能是由于肺脏大量的血管和通气储备功能弥补了部分的肺功能损伤。然而,在因衰老、高原暴露、吸烟或原发性肺部疾病而使得肺功能储备减少的情况下,亚临床肺功能障碍变得明显。因此,在对DM患者临床管理中,应关注对肺功能的检测,加强对患者的血糖管理,以更大限度地保护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