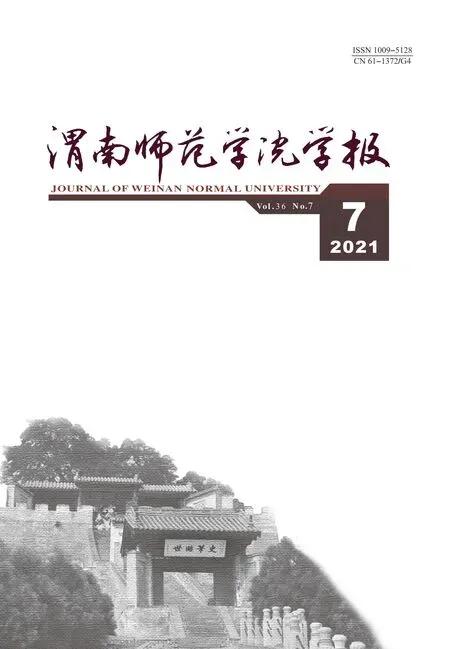文体互见: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三体的关系
——以《楚世家》为中心
尚 洁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2200)
“互见法”是《史记》中常见的一种述史方法,自宋代苏洵首次论及以来,历代学者多有发端。其中刘松来认为“互见法”与《史记》全书结构布局相关,它的产生“与纪传体这样一种新的史学形式相适应”[1]93。赵生群进一步阐述:“互见法的产生,是《史记》采取纪传志表综合性述史体例的必然结果。……《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五体分工不同,各有侧重,同时又存在大量的人事交叉和重叠。因此,《史记》全书的布局和五体结构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互见法的运用。”[2]177他将此总结为“五体互见”。靳德峻《史记释例》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各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则互文相足尚焉。”[3]14若以“详此略彼”为重要的互见标准,则以本纪、世家、列传此三体关系更为紧密。
此前关于本纪、世家、列传三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多以刘知几所论为主。《史通·本纪》言:“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4]34《史通·列传》又言:“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4]41由此说明本纪体似《春秋》之经,为《史记》之纲,列传体似《春秋》之传,为《史记》之目。至于世家,实则亦似《春秋》之传,与列传不同的是,世家为王侯之传,列传为士庶之传,相同的是,都与本纪之间存在诠释关系。然而有关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下尚无过多论述。若想深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还需结合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统计发现,《楚世家》与《秦本纪》互相参见最多,有30条,加之《秦始皇本纪》4条,共计34条,其次则为《吴太伯世家》,有13条,接着依次为《陈杞世家》12条,《郑世家》9条,《伍子胥列传》9条,《管蔡世家》8条,《宋微子世家》8条,《晋世家》7条,《白起列传》《春申君列传》均有5条,《周本纪》《鲁周公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均有4条,《越世家》3条,《齐太公世家》2条。现分别以《楚世家》与《秦本纪》《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的文本互见为例探究其行文义例。
一、限定与诠释:《楚世家》与《秦本纪》的文本互见
张大可指出:“表与纪、传互为经纬,是联系纪、传的桥梁。”[5]38也就是说“纪”与“表”同样承担着提纲挈领的作用。《秦本纪》中与《楚世家》文本互见的部分恰恰与《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大致相同,多为事件梗概。如城濮之战,《楚世家》记载为:
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6]2049
《十二诸侯年表》中“楚表”记为“晋败子玉于城濮”[6]734,《秦本纪》记为“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6]242。《秦本纪》与“楚表”均只记载战争胜败结果,“楚表”较《秦本纪》更为详细,点出楚将为子玉,《楚世家》则是详述战争细节,补充成王之言,记录惩处结果。
又如庄王问鼎,《楚世家》记载为: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6]2051-2052
《十二诸侯年表》中“楚表”记为:“伐陆浑,至雒,问鼎轻重。”[6]751《秦本纪》记为:“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雒,问周鼎。”[6]249二者均是只记载存在庄王问鼎这一现象,“楚表”较《秦本纪》更为详细,点出了“伐陆浑”这一细节,《楚世家》则是详细记载了楚庄王问鼎之始末以及与王孙满关于问鼎之对话。
再如伍胥奔吴,《楚世家》记载:
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6]2065-2066
《十二诸侯年表》中“楚表”记为:“诛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吴。”[6]794《秦本纪》记为:“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6]250二者均是简述概况,对个中缘由一概不论。“楚表”还记述诛伍奢、伍尚,点明太子建奔亡之国为宋,《秦本纪》对此略过不记。《楚世家》则详细记载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着墨于无忌、伍奢等人之言论,通过言语勾勒出费无忌奸馋过人以及伍子胥智勇双全的形象。
除以上三例之外,庄王围郑、申地之会、啮桑之会、张仪相楚、黄棘之会、重丘之役、武关会盟、白起拔郢等亦是如此。总体来看,《秦本纪》与“年表”之记载要素基本相同,通常包含事件对象/人物+地点+结果。只是《秦世家》记载着眼较大,较为笼统,而“年表”则更为具体。《楚世家》则是在基本梗概具备的情况下,填充背景、缘由等细节,尤其是增加大量对话,使得叙述骨肉丰润。
《秦本纪》中与《楚世家》互相参见的文本分别牵涉到若敖、楚成王、楚庄王、郏敖、楚灵王、楚平王、楚昭王、楚宣王、楚怀王、顷襄王十个时期,其中若敖时期记事为: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6]2045
楚宣王时期记事为: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6]2074
此均非楚国内部大事,而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因而实际上《秦本纪》与《楚世家》互相参见的文本涵盖成王、庄王、郏敖、灵王、平王、昭王、怀王、顷襄王八个时期。以成王时期为起点是因为此时期秦楚两国才开始外交往来。《诅楚文》记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枼万子孙,毋相为不利。”[7]296秦楚两国缔结盟约。而后着重于庄王、灵王、平王、昭王、怀王时期,恰恰勾勒出楚国的兴衰走势,庄王至灵王时期为楚国兴盛期,灵王末期、平王时期楚国逐渐衰退,直至昭王时期吴人入郢,怀王时期楚国彻底走向灭亡,再之后不过是强弩之末。
司马迁通过三种方式折射《楚世家》之编纂主旨,一是在各个时期选取能够说明兴亡原理的事件加以排列;二是通过《楚世家》后的“太史公曰”赞语部分及《太史公自序》中所下论断阐明主题;三是借助《秦本纪》中与《楚世家》文本互见的内容提纲挈领。这是因为“本纪”与“世家”是一个同心圆,它们既表现为一种同心弥散的关系,又表现为一种垂直的君臣关系。[8]410就文本而言,本纪与世家之间还存在着后者对前者的诠释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限定关系。
二、独立与勾连:《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的文本互见
观《吴太伯世家》内所记楚国之事涵盖五个时期,分别是楚共王、郏敖、楚灵王、楚平王和楚昭王。其中楚共王时期记事共有三件,而《楚世家》均不载。
其一是共王七年,楚国重臣申公巫臣奔晋后联吴制楚: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犇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6]1751
其二是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伐吴:
(寿梦)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6]1751
其三是楚共王三十一年,吴国伐楚落败之事:
(诸樊元年)秋,吴伐楚,楚败我师。[6]1753
此三件事,虽然《楚世家》不做记载,但是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均有所体现。申公巫臣虽原是楚臣,但后来奔晋,因而司马迁在“晋表”中记载:“以巫臣始通于吴而谋楚。”[6]762后两件事则记录在“楚表”之中,“使子重伐吴,至衡山”[6]768;“吴伐我,败之”[6]773。共王时期处在吴楚相争第一阶段中的初始期,吴国尚在探索崛起之路,还未对楚国构成大的威胁,故而《吴太伯世家》“楚表”有所记载,而《楚世家》对此则没有着墨,因而《吴太伯世家》与“楚表”都对《楚世家》起到了补充作用。
徐少华在《论春秋时期楚人在淮河流域及江淮地区的发展》一文中将吴楚之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楚略强于吴,大致从鲁成公七年至襄公二十八年(楚共王七年至康王十五年);第二阶段:楚吴相持,大致从鲁襄公二十九年至昭公十六年(楚郏敖元年至平王三年);第三阶段:楚弱而吴盛,大致从鲁昭公十七年至定公十四年(楚平王四年至昭王二十年);第四阶段:楚势复苏,逐渐收复、全面统治淮域,从鲁定公七年至悼公二十年(楚昭王十三年至惠王四十二年)。[9]380-388《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文本互见的部分实际为郏敖、楚灵王、楚平王和楚昭王时期,即吴楚相争的第二、三阶段,这也是吴楚争霸的胶着期与关键期。其间记事有详有略,各有侧重。
《吴太伯世家》中与《楚世家》互相参见的文本可大致划分为三个类型:
(一)涉及楚国内部记事
凡涉及楚国内部记事者,《吴太伯世家》记述较简,如灵王弒郏敖、楚诛齐庆封、弃疾弒灵王、伍子胥奔吴、楚平王卒、申包胥适秦求师等,多是一笔带过,分别记载如下:
七年,楚公子围弒其王郏敖而代立,是为灵王。[6]1763
(余祭)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6]1763
王余眜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6]1764
(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犇,公子光客之。[6]1765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6]1767
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6]1772
楚国是吴国在淮河流域的一大劲敌,因而《吴太伯世家》简略记载自郏敖至楚昭王时期的楚国内部大事也在常理之中,其简单记载既保证了吴国在《吴太伯世家》中的记述主体性,又凸显了此时期楚国对于吴国而言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关涉吴楚之间重大军事对抗且吴国获胜
凡关涉吴楚之间重大军事对抗且吴国获胜者,《吴太伯世家》记述较详,如败楚豫章,《楚世家》记载:“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6]2067《吴世家》则多添一笔,胜败之外又点出获楚一城:“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6]1770又如吴人入郢,直入楚都,此乃吴国对战楚国取得的最大胜利,亦是春秋史上的突出政治事件之一。现将《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有关“吴人入郢”的文本摘录如下,《楚世家》记为: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6]2068
《吴太伯世家》记为: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庐弟夫槩欲战,阖庐弗许。夫槩曰:“王己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郧。郧公弟欲弒昭王,昭王与郧公犇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6]1771
《楚世家》先总述参战对象为吴、唐、蔡与楚,记述战争结果有三:楚国大败、吴人入郢、伍子胥辱平王之墓。再依照顺序记述战争过程:楚国子常领兵迎战吴蔡等国,夹汉水阵,结果落败奔郑。吴国五战及郢,楚昭王仓皇出逃,吴人得以入楚国都城——郢。
《吴太伯世家》则依照时序记载,并且增加了许多言语对话,使得战争过程详细立体。两相对比来看,《吴太伯世家》乃是在《楚世家》记述之“缝隙”内加以扩充,铺陈成文。《楚世家》记载“吴兵之来”,《吴太伯世家》增述吴王阖庐与伍子胥、孙武之言论,制定伐楚策略。《楚世家》记载吴楚对战汉水和子常落败,《吴太伯世家》在此之间增述吴王弟夫槩对吴王之语及其率领五千部众追击楚兵之事。此皆本于《左传》。《左传·定公四年》记载:
若如《楚世家》记载,则易误认为汉水之战与子常落败存在因果关系,《吴太伯世家》在与《楚世家》文本互见的基础上增补柏举之战,则逻辑圆洽。但是,很明显的是,《吴太伯世家》所增补的内容多从吴国本体出发,与吴国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楚世家》中不做记载也在情理之中。因而这恰恰体现出互见法的优势,既能够通过文本互见勾连出事件的完整过程,又能够保持各个文本之间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昭王出奔和吴人入郢的记述顺序,《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恰恰相反。《楚世家》先叙出奔,再叙入郢,最后详述走郧奔随之始末,“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昭王亡也至云梦。……王走郧。……乃与王出奔随”[6]2068。《楚世家》之记载顺序与《左传》相合,“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庚辰,吴入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奔郧……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10]4639-4640。而《吴太伯世家》先记述昭王出奔之概况,后记述吴人入郢,将昭公奔随置于吴人入郢之前,“楚昭王亡出郢,奔郧。郧公弟欲弒昭王,昭王与郧公犇随。而吴兵遂入郢”[6]1771。
台湾学者李纪祥认为历史叙事中的时间具有可断性,所以史官才得以进行种种叙事活动,如断代、事件序列安排、衔接、聚合、重组等。也就是说,史官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可以通过插叙、倒叙、补叙、预叙等手法打断一条线性时间插入另一条线性时间,待后者叙述结束后还能继续沿着前一条线性时间进行叙事。[11]42-50正是由于历史时间的可断性,司马迁才能介入历史时间进行操作,在《吴太伯世家》中预先记载发生在“吴人入郢”之后的昭王奔郧奔随事件,“奔郧。郧公弟欲弒昭王,昭王与郧公奔随”乃是借着“楚昭王亡出郢”顺带将出奔后续事情一并提前叙述,此后再转而回到“吴兵遂入郢”。需要明确的是,此记述顺序并不代表着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吴太伯世家》记载“吴人入郢”较《楚世家》更详,《楚世家》记载“昭王奔随”较《吴太伯世家》更详,盖“吴人入郢”乃是吴国对战楚国获得的里程碑式的胜利,而“昭王奔随”为楚昭王积蓄力量,为《楚世家》下文昭王复归入郢张本。
可见司马迁在处理互见文本时,既能够通过文本互见勾连出事件的完整过程,又非常注重保持各个文本之间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三)影响两国局势或于政局影响不大
凡影响两国局势或于政局影响不大者,二者记述相当,前者记载均较为详细,如鸡父之战,后者记载均较为简略,如伯嚭奔吴、取楚六潜、伐楚取番等。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两存而传疑”,二是“各有舛误”。
关于“两存而传疑”,靳德峻《史记释例》言:“史贵征实,而于两说之疑而不能决者,则两存之,盖其慎也。”[3]2《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之文本互见部分就存在“两存”之例。如“争桑”事件中卑梁的归属问题,《楚世家》言“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6]2066,《吴世家》则言“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6]1766,前者言卑梁为吴邑,后者言卑梁为楚邑。又如伯嚭之身份,《楚世家》言“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6]2067,《吴世家》则言“楚诛伯州犂,其孙伯嚭亡奔吴”[6]1770,前者将伯嚭与郤宛联系在一起,后者则直言伯嚭乃伯州犂之孙。梁玉绳驳《楚世家》之记载云:
郤宛见杀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州犂为楚灵王所杀,远在昭元年也。《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谓郤宛即州犂,盖缘此致误。而《楚世家》称“郤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徐庚本《潜夫论·志氏姓》,谓“伯州犂之子郤宛,郤宛之子伯嚭。宛亦姓伯,又别氏郤”,恐不足据。定四年《传》云:“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孙嚭为吴大宰。”伯氏乃郤宛之党,而非同族。对此,《史记》则两存之。[12]1198
各有舛误者,则为吴二公子奔楚之事。《楚世家》记载“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6]2067,《十二诸侯年表》之“楚表”“吴表”亦记载奔楚者为吴三公子。而《吴太伯世家》明确记载:“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6]1769即奔楚者为吴二公子烛庸和盖余。观《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10]4616《吴太伯世家》所记二公子为是,《楚世家》及“楚表”“吴表”则为非。然而,《吴太伯世家》记载此事为“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梁玉绳云:
《左传》烛庸、掩余二公子奔楚而已。《楚世家》是,此与《伍子胥传》云以兵诈降楚,误一。阖卢元年(引按:事在昭二十七年,当吴王僚十二年,非阖庐元年),掩余奔徐、烛庸奔钟吾,至三年二公子奔楚,此云奔楚在元年,误二。楚城养,使二公子居之,与以城父、胡田,无封舒之事,此与《伍子胥传》云封舒,误三。[12]840
分别从时间、过程细节和结果三个角度指出《吴世家》所记三处错误。《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各有舛误,互辨正误。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楚世家》与《吴太伯世家》同为“世家”之体,二者互见之文本有详有略,其秉承的原则是保持各自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在此基础上互相参见、互为补充、互辨正误。
三、实录与想象:《楚世家》与《伍子胥列传》的文本互见
列传与世家相对本纪而言,在功能上都等同于“传”。在方法上都是“以人系事”。但是,相较而言,世家倾向于一国之传,侧重国家的兴亡嬗变,列传则倾向于一己之传,侧重个人的成败得失。世家之中除君主之外的人物事迹都非常简略,他们只是作为历史事件中的一员而存在,在当时的语境下体现出特定的一面,个体的形象并不立体丰满。例如伍子胥这一千古奇崛的人物,《楚世家》着墨不多,简单点明一个复仇者的身份。从《楚世家》与《伍子胥列传》文本互见的部分可以看出《楚世家》的内容多贴近于《左传》,《伍子胥列传》则体现出司马迁对史料的会通和创新,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出入。
一是伍子胥拒补逃亡之事。《左传》记载此事为伍尚主导,其独发议论,伍子胥则未言一辞。
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10]4541
《楚世家》与之记载大体相似,仍是伍尚独言,不同之处在于压缩了他的言辞,并且在之后增加了伍子胥弯弓属矢面向楚使的细节,营造出一种紧张对峙的氛围。
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6]2066
而至《伍子胥列传》,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伍尚之独言转为由伍子胥主导的兄弟之间的对话:
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6]2642-2643
《伍子胥列传》虽然与《楚世家》形成文本互见,所载事件大体相同,但在故事细节、主体选择和人物塑造上显然不同。在《伍子胥列传》中,出奔一事由伍子胥提出而非其兄伍尚,伍子胥的拒捕出奔由《左传》和《楚世家》中的被动变为了主动。他毫不迟疑地选择借力雪耻,以报父仇,正合乎其父伍奢所言之“刚戾忍询,能成大事”,是其性格的集中体现。《楚世家》依照《左传》行文虽然掩盖了伍子胥的风采,但实际并无不妥,《伍子胥列传》则更多聚焦于伍子胥,突出其个人性格特征。
二是伍子胥掘墓鞭尸之事。《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6]2647言辞激荡,尽显伍子胥举止之刚戾。而《楚世家》之记载相当克制,只言“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并未提及掘墓鞭尸。《左传》及《公羊传》对此均无记载,只有《谷梁传》言及“挞平王之墓”,此与掘墓鞭尸迥异。《史记会注考证》认为《伍子胥列传》中掘墓鞭尸之记载有误:
中井积德曰:平王死经十有余年,纵令掘之,朽骨而已,非有可鞭之尸。《吕氏春秋·首时篇》云:“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王之坟三百”, 是稍近人情,似得实。愚按《楚世家》云“吴兵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年表》“伍子胥鞭平王墓”,《淮南子·泰族训》“阖闾伐楚入郢,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贾子《新书·耳痹篇》“挞平王之墓”,此与《吴世家》言“鞭尸”,盖误。[13]2805
中井积德与泷川资言的论断从尊重史实的角度出发,而司马迁此记载从塑造人物形象角度出发,用前者来衡量后者,只能落得个“盖误”的评价,但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此论断未免过于死板。不掘墓鞭尸,何以平伍子胥之愤?何以显伍子胥之“怨毒”?想必司马迁下笔那一刻已经与伍子胥共情。至于挞墓与鞭尸之差异,司马迁应是早已考虑到此问题,故一事两出,文本互见,一在《楚世家》从史实录,二在《伍子胥列传》想象虚构。前者乃是一国之传且受辱对象又是楚国君主,故行文克制,实录以尊重历史。后者乃是一人之传且又是传主复仇成功的重要时刻,故行文激荡,虚构以揆情度理。
由上述文本互见部分之差异可知,在涉及具体人物时,《楚世家》行文较平实,以实录为主,《伍子胥列传》则更为具体详细,综合采用移花接木、想象虚构等手法,以突显人物性格为主。
综上所述,本纪、世家、列传之间存在三组关系:本纪与世家之间存在限定与诠释关系、世家与世家之间存在独立与勾连关系、世家与列传之间存在实录与想象关系。具体而言,当世家与本纪互相参见时,一般是本纪简而世家详,本纪中所载之事往往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本纪对世家有限定功用,世家对本纪有诠释功用;当世家与世家互相参见时,一般是有详有略,各自保持其主体性与独立性,在此基础上互相参见、互为补充、互辨正误;当世家与列传参见时,一般是世家简而列传详,世家偏于实录,列传偏于创新。由此若是同一件事于本纪、世家、列传中有二者或三者互相参见,则从本纪到世家再到列传,叙事愈发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