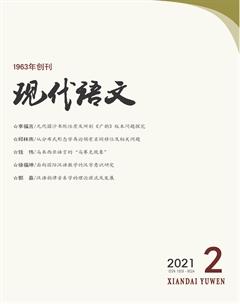标记理论下的“被”字句句式语义新解
刘琪
摘 要:“被”字句按照标记度大小可以分为无标记“被”字句和有标记“被”字句。这种标记性不仅体现在句法上,也体现在语义和语用上。“被”字句(A被B+VP)句法标记度大小取决于“A”“B”和“VP”三个成分:当A为原型受事、B为原型施事、VP为二价或三价动作动词时,“被”字句是无标记的,其句式语义为“施受/被动关系”。随着句式标记度的提高,A不再是原型受事,B也不再是原型施事,此时VP往往为心理动词或性状谓词,句式语义强调的是“使因—结果”。像“被授予”类承赐型“被”字句和“被自杀”类新兴“被”字式,它们都属于高标记的“被”字句,这些句式中不再凸显“施受/被动关系”和“使因—结果”语义,转而凸显的是一种情态语用义,表达主观态度、价值或情感。“被”字句并不是历来被认为的“一个特殊句式”,而是一组具有共性特征的句式的集合。标记度的引入解决了以往关于“被”字句句式语义的纷争。
关键词:“被”字句;标记度;句法;句式语义;主观倾向
一、引言
关于“被”字句到底表示什么样的语法意义,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观点有:一是以王力为代表的“不幸或不愉快”说[1](P430-433);二是杉村博文的“意外”说[2];三是以祖人植为代表的观点,强调其表“被动”的基本语义性质[3];四是以薛凤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它表示“由于B的关系,A变成C所描述的状态”[4];五是邵敬敏、赵春利的观点,作者认为,“被”是用来引进发生某个动作或行为事件的动因,但因为“被”字句中受动作的影响者才是句子的语义重心,动因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可以省略,因此,“被”字句可以分为“动因被字句”和“省隐被字句[5];六是施春宏的观点,他指出,“被”字句的语义表示“凸显役事受到致事施加的致使性影响的一种结果”[6]。以上这些观点,无论是对“被”表义内容的探讨,还是对“被”性质功能的界定,关注点都是该语法范畴所表现出的某一方面,是从解决局部出发的,这也是“被”字句语法意义至今没有定论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以往关于“被”字句的争论所指向的,并非是“被”字句各句式互无关联的个别问题,而是针对“被”字句不同标记度而产生的不同功能类。本文认为,“被”字句不是一个单一的句法语义结构,而是一个多义范畴,无论是表“被动关系”还是表“意外事件”,都只能反应“被”字句语法意义的一个侧面。从原型范畴的角度来看,“被”字句是一组具有共性特征的句式的集合,不可能用某个单一属性来解释。就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而言,“被”字句无疑是一种有标记的句法结构[7]。因此,从标记的角度来看,“被”字句标记度越高,就越需考虑语义、语用的解读。因为随着句式标记度的提高,需要付出的认知努力也就越大,甚至要依靠语用推理来理解“被”字句的意义。
二、“被”字句的句法标记度
张伯江指出,不应给“把”字句里的成分贴上“施事”“受事”的标签,而是应该研究句式赋予了这些成分什么角色[8]。我们认为,对待“被”字句各成分的语义角色也应持同样的态度。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将“被”字句的句法结构码化为:A被B+VP。从标记理论出发,“被”字句各句法成分的语义特点体现了不同标记程度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主语A、宾语B和动词词组VP上。
(一)A的标记度
宋玉柱指出,“‘被字句的主语是受事——几乎所有语法书都是这样说的。对于绝大部分‘被字句来说,它是符合事实的,但对一部分‘被字句来说,则没有概括力。”[9](P64)在“被”字句中,主语所充当的语义角色,除了受事之外,还有系事、感受主体、当事、处所、时间等。虽然A的语义角色可以被客观分析为多种类型,但这些类型是存在共性特征的,从宏观来看,A都是说/写者认定的受影响的对象。
根据对“被”字句主语A的语义角色的分类,我们确定了“被”字句主语的经常充当的六种语义角色类型。举例如下:
(1)杯子被我打碎了①。(受事)
(2)整个星期天都被他花在了扑克上。(时间)
(3)天井被雪花装饰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处所)
(4)老园头被她哭得心软。(当事)
(5)为什么那一本充满血腥味的《列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系事)
(6)他被那件事愁死了。(施事)
Dowty依据认知心理学理论创立了“原型角色”理论[10],提出了原型施事(Proto-Agent)和原型受事(Proto-Patient)范畴,还进一步提出了论元选择原则,即施事、致事、感事等这些具有原型施事属性的论旨角色最可能出现在主语位置,而受事、役事、目标等具有原型受事属性的论旨角色最可能出现在宾语位置。这就形成了句法论元和论旨角色的两组无标记组配。陈平参考Dowty的研究内容,建立了充任主语、宾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并指出,以上这些语义成分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施事性和受事性强弱的不同[11]。
在“被”字句中,主宾语充当的语义角色倒置,因此,越是具有原型受事属性语义角色出现于“被”字句的主语A时,越是无标记的。根据“被”字句主语A所充当的六种主要的语义角色的受事原型性,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标记度等级序列:受事>时间/处所>当事>系事>施事。该序列从左到右代表了各语义角色受事性的减弱、施事性的增强。也就是说,它代表了“被”字句主语标记度由低到高的一个序列。位于序列最左端的受事主语受动作影响强度最高,具备原型受事的属性,是典型的受影响对象,因此,它是无标记主语;而施事主語则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为有标记主语。
再来考察上面的例子。从主语充当的语义角色来讲,例(1)中,“杯子”是典型的受事主语,是无标记的。例(2)中,“整个星期天”表时间,句子可以转写为“他花了整个星期天在扑克上”,表示“他”和“时间”之间的施受关系,因此,“整个星期天”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受事。例(3)中,A为处所,这类处所可以从整体上被看作一种事物,而作为动作的接受者出现。“天井”在例句中就是被装饰者,有较明显的受事性质。例(4)中,“老园头”作为当事,表示因B发生的“哭”这一动作而使A产生了“心软的”情绪或感受,A只与谓语部分有某种关系,不是V的受事。例(5)中,A与“女人的榜样”是等同关系,A很难说是V的受事;邢福义将这类“被”字句称为承赐型“被”字句[12]。例(6)中,A是施事,句子可以转写为“因为那件事,他愁死了”,“那件事”是致使“他愁死了”的原因,“他”发出了“愁”的动作。可以看出,从例(1)到例(6),动作对A的影响依次减弱,反映了A从无标记到有标记的变化。
(二)B的标记度
以往关于“被”字句的常见误区之一,就是把“被”作为引进施事的格标记。从理论上来看,“施事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应具有生命度和自主性”[5]。张伯江指出,施事的意愿性强度和其典型性有关,具有强意愿性的施事是典型的施事[12]。就此而言,如果“被”仅作为引进施事的格标记的话,那么,处在宾语B位置的语义角色应当具备[+生命度]、[+意愿性]、[+自主性]。事实上,许多实例并不支持“被”作为引进施事的格标记这样的论断。例如:
(7)方方试图跟陈伟玲聊天,被她噎得直背气。
(8)衣服被风吹走了。
(9)我刚出楼门,被高压水枪射出的一束水柱砸了个满脸花。
(10)自己怎么又会被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希望攫住?
(11)他脸上的花影都被欢跃给浸渍得红艳了。
(12)他被那件事愁死了。
在上述例句中,充当宾语的成分并不相同。从B所充当的语义角色来看,它不仅可以表示施行动作的人,如例(7);也可以表示施行动作无生的事物,如例(8)、例(9);还可以表示原因,如例(10)、例(11);甚至是受事成分,如例(12)。由此可见,“被”引进的对象不一定是意愿性强的,甚至谈不上具有生命度和自主性。
邢福义认为,虽然B有时候表示无生命的事物,但是它被说话人主观意念上认定为动作的施行者[13]。因此,在格式上B的位置似乎有了语义的限定:任何成分,哪怕是没有生命度的事物,一旦进入B的位置,也具有了施事的意味。即使如此,和典型的施事比起来,无生事物虽然同为动作的施行者,它在认知上却具有更高的复杂度,在对动作的控制强度上也存在区别。对动作的控制力越强,越是典型的施事。Dowty指出,“具有原型施事属性的论旨角色出现在主语位置是一种无标记组配”[10],这是对于一般的施受句来说的。在“被”字句中,由于主、宾语的施受关系对调,“被”字宾语位置和原型施事也能构成一组无标记组配。语言的标记模式和原型范畴理论密切相关,一个范畴中有典型成员、非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典型的成员往往是无标记的,而非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则是有标记的,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据此,我们可以通过“被”字句中不同的宾语B对动作的控制力强弱判断其标记度大小。例如:
(13)日本队被中国队打败了。(施事)
(14)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准施事)
(15)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喻施事)
(16)他被烟呛住了。(喻施事)
(17)他被门槛拌了一下。(伪施事)
(18)阳光被山遮住。(伪施事)
邵敬敏、赵春利对“被”字句宾语B的施事性强弱进行了探讨,将施事划分出四种类别[5]。例(13)中,B“中国队”是表人的集合,具有高生命度,是典型的施事,标记度低。相比之下,例(14)~例(18)中的“被”的宾语,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施事。例(14)中的宾语,隶属于人的“思想、意志、精神、信念”,它实际上受到有生命个体的控制,被称为“准施事”;例(15)、例(16)中的宾语,属于“水、气、光、烟、雾、电”等带有散发性能量的物体,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可以看作是一种转喻,这样就具备了一定的生命度和意志力,被称为“喻施事”;例(17)、例(18)中的宾语,属于客观无生命度和意志力的物体,但通过外力的作用也可以具备一定的主动性,可以看作是一种临时的“施动者”,被称为“伪施事”。因此,例(14)~(18)中,“被”所引进的只是发生某个动作行为或事件的动因,它们的标记度较高,属于非典型施事。
除了直接施事之外,B所充当的语义角色还可以是致因、间接施事和受事。例如:
(19)你回到房间,突然被疲倦攫住了。(致因)
(20)我被他派人追上了。(间接施事)
(21)爸爸被一连串的问题问烦了。(受事)
其中,例(20)值得格外注意,处在宾语B位置的“派人”是一个动宾结构表行为事件,而“追”这一动作的发出者,我们可以判定为“派的人”,它是具有[+生命度]、[+意愿性]特征的语义成分,可以归入到非典型施事的一类中。而例(19)中作为心理动词的“疲倦”和例(21)中作为客体的“一连串问题”,都是致使各自的主语达到某种状态的使因成分,它们的施动性需要依靠说/写者的主观认定,除此之外,其致使力无法通过外力或隐喻、转喻的方式得以实现。和非典型施事相比,这类成分的标记度更高,我们称其为“边缘施事”。
B的语义角色看似复杂,事实上它们也是有共性的。无论B是典型施事、非典型施事还是边缘施事,它们都是对主语施加影响的主要责任者和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被”字句宾语B语义角色标记度连续统:典型施事>非典型施事>边缘施事。在这一序列中,B所能充当的语义角色,从左到右的标记度越来越高。
随着“被”字句句法标记度的提高,B所充当的語义角色对动词的控制力减弱,受动作的影响者占据了句子的语义重心,施加影响者的地位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因此,B往往可以承接上下文省略,或者补出B之后句子变得不合法,或者根本不需要B的出现。
(三)VP的标记度
VP的标记度等级差异直接制约着“被”字所表达的意义。一般来说,“被”字前后出现的是典型受事主语和典型施事宾语的时候,“被”字句的基本语义性质就是表被动。这时,VP中的动词往往是二价和三价的动作动词。可以说,这种典型“被”字句的标记度低,如“杯子被我打碎了”。再如:
(22)范登高拿回来的衣服被别人替换了。
(23)一张上好的楠木椅子被他坐断了。
这种典型的“被”字句语义上的施受关系和句法成分是对应的,因此,也最容易和“主动宾”句、“把”字句、受事主语句进行转换。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施受关系,我们省去了句中的修饰性成分:
(24)a.别人替换了衣服。
b.别人把衣服替换了。
c.衣服别人替换了。
(25)a.他坐断了椅子。
b.他把椅子坐断了。
c.椅子他坐断了。
还有一部分“被”字句,主语和宾语的关系是非典型的施受关系,此处的“被”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引进施事,而是着意凸显动作行为对“被”字所标记对象的影响。这时,VP中的动词往往是心理动词或性状谓词。相对于一般的VP而言,其标记性更强。例如:
(26)他被牛奶喝胖了好几斤。
(27)她被繁忙的工作累病了。
例(26)中的“他”和“牛奶”之间、例(27)中的“她”和“繁忙的工作”之间,都是非典型施受关系。其中,“喝胖”属于性状谓词,“累”是心理动词,“病”也属于性状谓词,它们均是非典型的动作动词。“被”字句的各个成分都是非典型的,标记度高,因此,它们无法同“主动宾”句和受事主语句进行自由的转换,只能和“把”字句实现自由的转换。试比较:
(28)a.*他喝胖了牛奶好几斤。
b.牛奶把他喝胖了好几斤。
c.*牛奶他喝胖了好几斤。
(29)a.*她累病了繁忙的工作。
b.繁忙的工作把她累病了。
c.*繁忙的工作她累病了。
三、“被”字句的语义标记度
以往学界试图用一个句法语义关系来解释“被”字句,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我们认为,“被”字句的语义问题也是一个标记度强弱的问题。语言的标记性可以像基因一样被复制到语言的各个层面,反映了标记所具有的同化特性。标记同化要求有标记的意义或功能由有标记的形式来体现,换言之,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必须要保持一致。“被动关系”是“被”字句最典型的语义表达,是无标记的语义。因为它不仅强调句法形式上的主宾语关系,同时强调主宾语和施受关系的对应。从句式变换的角度来说,表被动关系的“被”字句很容易和“主动宾”句、“把”字句、受事主语句进行转换。
如果句法上的标记度提高,主语和宾语不再强调施受关系,“被”的功能不再用作被动标记,而是引进发生某个动作或行为事件的“动因”,强调的是“使因—结果”,那么,它则是一种有标记语义。此时的“被”字句所凸显的是动作行为对其所标记对象的影响。如例(26)、例(27),“牛奶”是“他胖了好几斤”的使因,而“他胖了好几斤”是“他喝牛奶”造成的结果;“繁忙的工作”是“她累病”的原因,而“她累病”是“繁忙的工作”造成的。再如:
(30)那人一口气杀了三条狗,我被这场景吓了一跳。
(31)他本来想帮你,没想到你却被他害了。
(32)他的眼睛被这些小字看花了。
上述例句,如果同样进行句式变换,A和B是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似乎很难用传统的施受关系来解释,而只能从“使因—结果”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和上文中的例子“牛奶”“繁忙的工作”一样,“这场景”“他”“这些小字”都不是动词的施事成分,“这场景”无法主动吓“我”,“他”本无意害“你”,“这些小字”也没办法主动地把“他的眼睛看花”。“场景”“他”和“小字”都是语义上的使因成分。“被”字句强调的意义是“使因”和“结果”,而不再是被动关系。这也说明,句法结构的标记度越高,在语义的认知处理上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使因—结果”的关系不像被动关系一样在句式结构中能够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用“被动”义来统辖“使因—结果”义,也没有必要用“使因—结果”义来统辖“被动”义。无论哪种语义功能,都不能涵盖所有的句子。这是因为“特定的句法形式必然会出现一定的语义内容,相应的语义内容同样需要借助特定的句法形式来表达”[14]。标记度的引入可以化解以往有关“被”字句句式语义的纷争,其句式语义随标记性的强弱而分化:表“被动关系”的“被”字句,在宾语B的强实施性、主语A的强受影响度和VP动作的典型性上,都表现为无标记;而强调“使因—结果”义的“被”字句,从宾语B的低意愿度、主语A的弱受影响度和VP的特征上,都是有标记的。
四、“被”字句的语用语序
典型的、常规的“被”字句属于致使表达方式的一种类型,其语法意义是“凸显役事受到致事施加致使性影响的一种结果”[6](P14)。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被”字句中,表“被动关系”和表“使因—结果”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是“被”字句的基本意义,只有标记度提高,“被”字句才具备后者的表义功能。“被”字句不同的句法和语义标记度,可以清晰地区分“被”字句的语法意义。在语用层面,也更能体现标记度的解释力。语用上,标记度的提高会带来“附加”信息。也就是说,在“被”字句的语用语序中,“被动关系”“使因—结果”都不再凸显了,得到凸显的是一种主观评价、态度或情感。在语法形式上,也表现出很强的标记性。这些特殊的“被”字式往往不要求句法成分的必要性,其宾语的弱施事性说明它本身不是句子的必有论元,因此,宾语可以不出现。下面将要论述的,就是这类高标记性“被”字式的典型代表。
(一)承赐型“被”字句
邢福义指出,现代汉语里承赐型“被”字句的广泛使用,受到社会发展的语用需要的促动[13]。随着现代社会评优授奖活动的日益增多,承赐型“被”字句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系统性的被动称心表述网络。它不仅在内涵上有褒义的规约,在外延上也进行了形式上的圈定:S被(X)授予Y、S被(X)评为Y、S被(X)列入Y,是它的三个代表格式。例如:
(33)他被市长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34)其父也得遂大志,被评为“一级教师”。
(35)刘诗白……被列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名人录》。
邢福义称这种具有褒义性质的承赐型“被”字句为一个小“独立王国”,它独立于一般意义上的、表不幸或者不愉快的“被”字句,这是适应社会社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语用形式。一提到“被授予”“被评为”“被聘为”“被表彰为”“被任命为”等典型的搭配形式,人们便会更自然地联想到称心如意的事。在这类“被”字式中,动作涉及到的施事不是交际双方所关心的,因此,“B”省去之后也并不影响句子的成立,如例(33)省去“被”的宾语“市长”后,就变为“他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相反,人们关注的是评奖评优这件事情本身与受评对象,因此,这两个成分如果省去不说,句子就无法成立。
(二)“被X”
近年逐渐流行的“被X”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新兴“被”字式和常规“被”字句的不同之处,鲜明地体现出“被”字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不同功能类型。施春宏指出,“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语法意义,新‘被字式都與常规‘被字句构成了一种背反状态,因而展现出不同的语用效果。”[6]首先,不同于常规“被”字句VP的述补结构或其他复杂结构,如“被打伤、被摔成碎片”等,新“被”字式出现的谓词性成分往往为单个动词或形容词,如“被自杀、被培训、被结婚”等,更特殊的是,它还能容纳非谓成分,如“被潜规则、被处女”等。其次,常规“被”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达“被动关系”或“使因—结果”,而“被X”的语义内容则体现出更为明显的主观倾向。
“被”字句语用语序特殊的表意功能,还表现在其意义可以随语境等的变化而呈现出相当大的波动性。同样是“被自杀”,在不同语境下,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其一,A属于他杀但被人说成是自杀;其二,A被人强迫自杀但被人说成是主动自杀;其三,A并未自杀或他杀但被人误传为自杀。这说明,只要构建适当的语境,新兴“被”字式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这种多义性的解读,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新“被”字式理解过程中的不同认知方式。这是常规的“被”字句所无法做到的。
上文提到,随着“被”字句中各成员的非典型性的增强,“被”字句的标记度也随之提高,这时,在认知上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像新兴“被”字式这类特殊的有标记句式,“被”的施事宾语隐而未现,其认知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语用推理上。典型的表被动关系的“被”字句本身就是一个“完型”,“被自杀”之所以能成立并被理解,在句法上是类推在起作用。所谓“类推”,指的是原有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因套用某种法则,类推出不同于原来的新结构,新结构的表层不同于旧结构,但两者的底层意义不变[15]。可以说,“A被B+VP”中B不出现,会大大增加理解的难度,新兴“被”字式在语义表达上的不自主性,就需要借助于语用推理。我们认为,新兴“被”字式的出现,可以说是常规“被”字句的语法化的结果,实现了句式在共时平面内功能的分工。在类推的作用下,它是由常规“被”字句发展出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在整体上不再强调句法成分和语义角色在语序上的对应关系,凸显的是这个句式的语用含义,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五、“被”字句的语序、语义和关联标记模式
从语序的角度讲,我们认为,“被”字句可以分为句法语序、语义语序和语用语序三个平面,这三个平面是相互关联的,体现了标记性的强弱。因此,“被”字句的语法意义也就体现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之中。我们之所以用标记性的强弱来说明“被”字句的语法意义,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的对应程度。
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认为,“被”字句有两种最主要的语法意义:表被动关系和强调“使因—结果”。和以往观点不同的是,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分开对待。在句法表现形式上,强调“使因—结果”的“被”字句的标记度要强于表被动关系的“被”字句,甚至可以说,表被动关系的“被”字句在句法和语义上是无标记的,而强调“使因—结果”的“被”字句是有标记的。我们由此可以建立“被”字句的关联标记模式:
无标记组配 有标记组配
A被B+VP A被(B)+VP
被动/施受关系 使因—结果 情态语用义
句法语序 语义语序 语用语序
随着标记度的继续加强,“被”字句不再体现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承赐型“被”字句或新兴“被”字式只能按照语用语序处理,它们是具有特殊语用功能的“被”字句。不过,这种语用意义仍是来源于“被”字句的句法语序和语义语序。
综上,我们认为,标记是汉语语序选择的一种调节手段,标记度的强弱和语序的三个平面密切相关,语言的标记性越强,越对应于语用语序,这是因为标记具有语用信息传递功能和突出信息中心的功能。“被”字句的标记度和语序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主观性 弱 强
标记性 无 有
语序 句法语序 语义语序 语用语序
语义 被动/施受关系 使因—结果 情态语用义
图1 “被”字句标记度和语序的对应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被”字句的标记度和其语序可以构成一个连续统,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动态地、分层地整体看待“被”字句的特点。
本文运用标记理论,从“被”字句的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语序出发,论证了“被”字句句式的标记度和语序的关系。以往有关“被”字句语义的不同解读,实际指向的是“被”字句不同标记度的句式。研究表明,句式的标记度越高,越倾向于语用语序,对句式语义的理解也越要依赖于主观性。“被”字句的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实际上体现出一个标记程度的差异:A为典型受事,B为典型施事,VP的动作性越强,则相应的“被”字句越倾向于无标记,语义上表达的是一种被动关系。随着标记度的提高,句法结构无法再反映被动关系,此时的“被”字句强调的是“使因—结果”,甚至带上一种主观倾向,这种主观性无所谓积极还是消极。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杉村博文.论现代汉语表“难事实现”的被动句[J].世界汉语教学,1998,(4).
[3]祖人植.“被”字句的表义特性分析[J].汉语学习, 1997,(3).
[4]薛凤生.“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结构意义——真的表示“处置”和“被动”?[A].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5]邵敬敏,赵春利.“致使把字句”和“省隐被字句”及其语用解释[J].汉语学习,2005,(4).
[6]施春宏.新兴“被”字式的生成机制、语义理解及语用效应[J].当代修辞学,2013,(1).
[7]施春宏.汉语句式的标记度及基本语序问题[J].汉语学习,2004,(2).
[8]张伯江.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中国语文,2001,(6).
[9]宋玉柱.处所主语“被”字句[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
[10]Dowty,D.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J].Language,1991,(3).
[11]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J].中国语文,1994,(3).
[12]张伯江.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J].语言研究, 2000,(1).
[13]邢福义.承赐型“被”字句[J].语言研究,2004,(1).
[14]张谊生.现代汉语“把+个+NP+VC”句式探微[J].汉语学报,2005,(3).
[15]王寅,严辰松.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法化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