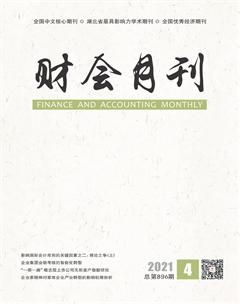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的实施效应检验
郑蓉 李传宪



【摘要】以2006 ~ 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 通过考察差异化分红政策实施期间上市公司分红行为较半强制分红期的变化后发现:差异化分红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A股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与派现水平, 并使“铁公鸡”公司的比例较前期有了显著下降; 同时, 差异化分红标准的设置初步缓解了半强制分红期的“监管悖论”现象, 并使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分布特征。 不过, 由于监管新政对成长性与重大资金支出的界定不明确, 从而导致每一类上市公司的实际分红水平都低于其理论分红标准, 出现了“折扣式”分红现象。 这表明未来的分红改革在政策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及监管的有效性上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关键词】差异化分红政策;半强制分红政策;“类强制”分红效应;监管悖论;“折扣式”分红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04-0017-9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股市的股利分配一直因不分红、低分红甚至根本不作任何分配等现象而受到诟病, 因此, 股利分配在近二十年来也一直是政府股市治理的重症监管区域之一。 2001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号), 对市场普遍不分红的现象做出了规定。 该政策出台的当年分红的上市公司占比增加了31.27%, 监管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但这一增长效应并没有持续下去, 分红的公司比例在2000年后开始逐年下滑。 为了遏制这一态势, 证监会在2004年紧急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政策直指股市过度投机的恶疾——重融资、轻分配, 要求凡近三年未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 既不得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 也不得发行可转换债券。 此举被称为将股权融资与分配捆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强制分红政策。 此后不久, 证监会在2006年再次出台补充规定, 对2004年的定性式半强制分红政策给出了具体的定量监管标准; 2008年的政策则将2006年的这一定量标准进一步提高。 伴随着这一系列密集的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的组合出击, A股派现公司的比例在2005年小幅度波动后开始了持续稳步快速上升的态势。 仅此而言, 半强制分红政策可谓成绩卓著。
而李常青等[1] 指出, 虽然半强制分红政策在规范上市公司分红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但该政策因为“一刀切”的特点而可能形成“监管悖论”, 它对有融资需求的高成长型公司形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 魏志华等[2] 还指出, 正因为半强制分红只能限制有再融资需求公司的派现意愿, 所以它难以约束无公开再融资意愿的公司, 特别是“铁公鸡”公司。 这也导致2006年及2008年后, 发放“微股利”和“门槛式”股利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增加。 为了弥补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缺陷, 证监会在2013年出台了差异化分红政策, 即《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下简称“分红新政”)。 该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应综合考虑自身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3] 。 这一规定改变了半强制分红政策“一刀切”的量化考核特点, 并要求即使处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上市公司, 其当期现金股利支付比例至少也应达到20%。 这一规定扩大了半强制分红监管的范围, 将长期以来游离于分红监管之外的“铁公鸡”公司纳入了分红监管的行列。
然而, 本文通过分析2013年分红新政实施后上市公司分红行为却发现, 虽然派现公司占比總体处于波动且缓慢上升的趋势, 但每年平均仍有25%的非亏损公司未发放现金股利, 近几年平均股利支付率为27.39%, 仅略高于差异化分红标准的最低水平20%。 这不禁使人疑惑:差异化分红政策的分红监管效应究竟如何? 政策的执行结果与预期的差异及形成的原因何在? 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以2006 ~ 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对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①尽管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首次实现了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分红监管的全覆盖, 但无人关注监管范围变化的最终实施效应如何。 本文研究发现, 分红监管范围的扩大还是具有显著监管效应的, 分红新政实施后, A股“铁公鸡”公司所占的比例较之前有了显著下降。 ②本文对分红新政的差异化区间的划分是否切实有效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 分红新政虽使各类上市公司的分红初步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分布特征, 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的实际分红水平总会处于其法定的差异化分红水平以下, 出现所谓的“折扣式”分红现象。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分红新政的整体管制效应
1. 差异化分红政策的“类强制”分红特点。 股利分配虽是企业内部财务决策的一部分, 但各国政府对本国企业股利分配的监管态度与方式却有很大差异。 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中, 由于市场的约束机制、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与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都较为健全, 因此, 即使出现所谓的“股利消失”现象, 政府也未对企业的股利分配决策进行干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 由于外部的市场约束机制、法律保护机制和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均不够健全或完善, 出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和促进资本市场良性运作的目的, 这些国家中部分政府采用了强制分红政策。 强制分红虽然可显著提高分红水平[4] , 但这种政策实施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 明显干预了企业财务决策的自主权[5] ; 其二, 可能诱导那些因主观或客观原因不愿分红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或减小外部强制分红的监管影响[6] 。 总体而言, 新分红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分红新政的强制性显著高于过去的半强制分红政策。 这主要体现在被强制分红主体范围的扩大方面。 半强制分红是通过与股权融资挂钩的附加权限的形式来强制公司分红。 如果上市公司没有股权融资的需求, 则相关分红政策对其不产生约束力。 但分红新政明确给出了最低分红标准:即使是高成长且有重大资金支出的公司, 其年度最低股利分配率也不应低于20%。 这一要求的管制范围涵括了所有A股上市的非亏损公司, 而过去A股中不缺资金而长期不分红的“铁公鸡”公司, 将正式被纳入新政的管制范围。
(2)分红新政的强制效力弱于强制分红政策。 强制分红政策的法律约束效应覆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上市公司, 除亏损外没有任何特别的例外或赦免事项。 2013年的分红新政虽然给出了单一的最低分红标准, 但却是有前提的:①股利分红方案是根据公司面临的各种影响因素综合决策的结果。 ②如果公司在充分自我评价的基础上, 做出的不分红决策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也出具了肯定意见, 证监会在关注核实的基础上是可以认可的[3] 。 即分红新政是以尊重公司自治与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强制分红, 但该强制条款的最低标准是有例外原则的。 不过, 上市公司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这实际上可等同于无强制, 从而去寻找甚至伪造很多例外的理由或借口不分红。 因为分红新政不仅要求企业将股利分配的决策机制、程序及现金股利在分配中的优先顺序权写入章程, 还要求在章程和年报中披露股利政策的具体内容, 如发放的形式、条件、比例、时间间隔等。 同时该政策还明确提出, 未按照规定分红的公司, 证券监管机构应按照《证券法》第193条予以处罚。 这一系列规定都表明证监会在分红监管的态度上较以往更为强硬。 本文将这种分红新政称为“类强制”分红政策。
2. 分红“类强制”特征对分红的整体提升效应。 新的“类强制”分红政策不论是在强制分红的范围, 还是在相关强制披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上, 以及监管部门监管执行的力度上, 其强制性都明显高于前期的半强制分红政策。 首先, 分红新政虽然改变了前期半强制分红“一刀切”的规定, 但并没有免除相关成长性公司的分红义务, 只是将其分红的水平从过去的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比30%降至当前最低的一档——当期分红占比20%。 其次, “铁公鸡”一直在我国A股市场占有不小的比例。 相关研究表明, 即使在2000年开始实施分红管制以后至2013年前, A股市场连续五年不分配的“铁公鸡”公司高达775家, 甚至是连续十年不作任何分配的“铁公鸡”公司都有374家, 占同期观察样本总额的14.79%[7] ; 这些“铁公鸡”公司中, 不论是连续五年不分配的公司, 还是连续十年不分配的公司, 非ST“铁公鸡”公司所占比例都分别为ST“铁公鸡”公司的三至四倍[7] 。 可见, 这些公司过去一直藏在政策监管的真空区, 但都正好属于分红新政所要求的必须分红的对象。 当这些“铁公鸡”公司全部被纳入监管范围后, 整个A股市场分红公司所占的比例会显著提高。 另外, 分红新政中对现金分红优先顺序的强调, 以及对成熟期公司当期最低为40%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 都将促使上市公司的分红意愿与分红水平较前期会有所提升。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相较于半强制分红期, 差异化分红监管期内上市公司总体派现意愿与派现水平显著提高。
H1b:相较于半强制分红期, 分红新政的“类强制”特征使“铁公鸡”上市公司的占比显著下降。
(二)分红监管政策的“差异化”实施效应
1. 差异化分红标准选择的有效性。
(1)生命周期对派现的影响。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企业的运作一般有萌芽、成长、成熟与衰退四个周期。 通常在萌芽或初創期, 企业经营风险很高, 其现金流出远高于现金流入, 因此该阶段的股利支付水平往往很低, 甚至为零。 进入成长期以后, 随着销量攀升和市场高速拓展, 企业的现金流入大量增加的同时, 因销售和扩张而引起的营销或长期资产等资本性支出也迅速增加, 此时企业的现金流入与流出一般仅处于相对均衡, 故该期间通常只是保持较低的名义支付率。 当企业产品进入成熟期, 由于投资力度减小, 销售趋于平稳, 企业的现金流入开始呈现出远高于其现金流出的状态, 该阶段股利支付率显著提高。 而进入衰退期以后, 由于企业的现金流入与流出都显著减少, 为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该阶段的股利支付率一般会达到最高水平, 甚至可以为100%[8,9] 。
该理论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大量验证:如Fama和French[10] 发现, 大多数低盈利、高成长公司不愿意支付股利, 而倾向于支付股利的往往是那些高盈利、低成长的公司。 并且, 当一家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发生明显变动时, 也释放出该公司从一个生命周期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信号[11] 。 正如西方六国的“股利消失之谜”, 其实只是股利支付主体的分布结构发生了变化[12] 。
在我国, 部分学者赞同生命周期理论适用于中国市场。 如李常青和彭锋[13] 研究发现, 国内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虽然会受到证监会配股增发政策的影响, 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公司确实会采用不同的股利政策。 相对于成长型企业, 国内的成熟企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14,15] 。 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仅在分红意愿上表现出生命周期特征, 而分红水平却并不具有生命周期特征[16] 。 笔者认为, 在半强制分红监管期, 高成长公司由于其再融资需求较高, 频繁的再融资需求致使其产生了相对更高的派现意愿以及比成熟型公司相对更高的分红水平。 2013年后, “类强制”分红政策迫使更多的成熟型公司派现, 而不论其是否有股权融资的需求。 并且, 差异化分红政策对成熟型公司的现金分红要求显著高于成长型公司。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差异化分红政策下, 高成长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与派现水平均显著低于成熟型公司。
(2)重大资金支出对派现的影响。 重大资金支出作为差异化分红的标准之一, 其是在综合考虑了企业的投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持有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后提出的。 虽然MM理论认为企业的股利政策与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价值无关, 然而, 由于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市场, 现金持有的数量会受制于企业面临的投资需求和融资约束[17] , 而现金股利的分配又受制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18] , 因而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必须受制于企业的投资需求与融资约束。 在既定的内部资金规模下, 当期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较高时, 必然会降低其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19] 。 同时, 由于现金股利支付的高低又会影响企业留存收益的多寡, 进而会影响未来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规模[20] , 从而使得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的投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现金流水平产生了相当的敏感度[21] 。 据此推断, 当进入差异化分红期后, 不论是成长型还是成熟型公司, 半强制分红约束的取消都将使其股利决策趋于理性:即当企业有重大投融资需求时, 为了维持企业必要的财务弹性, 降低现金分红水平是符合企业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的理智选择。 特别地, 当一个企业步入成熟期, 如果长期缺乏重大的投资需求, 而其现金股利支付却始终保持较低水平, 就会出现因超额自由现金流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 因此, 对于步入成熟期又缺乏重大投资需求的上市公司, 高额分红是迫使企业吐出超额自由现金流、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方式[22] 。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差异化分红政策下, 有重大资金支出的公司其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均低于无重大资金支出的公司。
2. 分红水平的预期“差异化”分布与实际分红区间结构的差异。 分红新政根据选定的差异化分红标准给出了上市公司分红的三个差异化区间:成长期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公司, 其利润分配中, 现金分红占比不得低于20%; 成熟期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公司, 现金分红占比不低于40%; 成熟期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公司, 其最低现金分红比例为80%。 这一分红区间的划分看似十分具体明晰, 但其能否被有效执行却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其一, 市场能否准确判断出一家上市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并掌握其重大资金支出情况; 其二, 各家上市公司是否会如实按照给定的标准和区间分红? 在这两个因素中, 按照差异化分红区间标准判定上市公司当年所属分红企业类型是决定分红监管是否有效的重要前提条件。 但相关文件既没有给出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判断标准, 也未给出处于不同行业及不同规模的企业, 其资金支出是否“重大”的参照标准。 文件仅指出, “当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时, 可以按照前面的分层规定自行判断处理”[3] 。 因此, 不论是外部投资者还是市场监管者, 当无法对企业发展阶段及投资支出程度进行相对准确的分类判断时, 必定不能判定其分红水平是达到了抑或是不符合规定的差异化分红标准。 如此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折扣式达标分红”。
具体而言, 对于成长型公司, 即使其当年无重大资金支出, 其仍可能只按成长期且有重大支出的企业标准支付20%的现金股利, 因为分红新政并未对“重大资金支出”做出明确的界定。 至于这类企业在真正有重大资金支出的年份, 也极有可能支付低于20%甚至低于10%的现金股利。 那些本来处于成熟期至少应支付40%以上现金股利的公司, 也完全可能利用政策监管的漏洞以成长型公司自居:在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时仅支付20%到40%的现金股利, 而在无重大资金支出时则选择支付40%以上、80%以下, 甚至更低水平的现金股利。 至于主动支付80%以上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 按照国内A股长期形成的“微分红”“低分红”偏好, 更是寥寥无几。
分红新政策虽力图改变这一现状, 但由于分红新政不完善以及惩罚力度不足, 上市公司规避高比例分红的趋势依旧显著。 另外, 即使该企业明显地利用政策监管漏洞进行了折扣式达标分红, 根据长期的监管经验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该企业被处罚的可能性极低。 而当信息反馈制度不完善、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时, 路径依赖效应的出现就不可避免[23] 。 以上因素共同作用, 将使得分红的差异化政策演变为具有充分弹性的“折扣式”分红。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差异化分红监管期内, 上市公司的实际分红区间水平总体会显著低于本公司适用的法定分红区间标准。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定量式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于2006年实施, 国内定量式半强制分红期的派现水平显著高于定性式半强制分红期[2] , 而差异化分红政策的颁布始于2013年, 为充分考察和比较新政实施的效果, 本文选择2006 ~ 2018年为样本观测期。 以这一期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以下过程对数据进行筛选:①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及ST样本; ②剔除2006年末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样本,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会影响相关样本当年的分红决策; ③剔除部分亏损但仍然分红的样本, 以及难以准确判定其成长期的样本, 最终得到31680个有效样本。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少量样本缺失数据通过该公司年报信息予以补充。 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选择及回归模型
1. 被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差异化分红政策的“类强制”分红效应, 本文设置了派现意愿(Dum)、派现水平(Payout)和“铁公鸡”公司(Iron)三个因变量, 主要用于考察相较于定量式半强制分红, 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分红整体提升效应如何。 分红新政划分了三个差异化分红区间, 但国内长期存在的“微分红”和“低分红”习惯并不一定会随着监管新规的出现而立即消失。 为了更细致地检验在分红新政的差异化监管下是否存在折扣式分红现象, 本文按上市公司分红的差异化区间设置了五个虚拟变量:“微分红”公司(P05_10)、低分红公司(P10_20)、“门槛式”分红公司(P20_40)、中等分紅公司(P40_80)与高分红公司(P80_100)。
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1)解释变量。 为了考察差异化政策实施的影响, 本文设置了差异化分红期变量Period。 对于分红差异化标准制定的合理性, 本文设置了成长性水平(Growth)与重大资金支出(Invest)两个变量。
对于成长性水平的衡量常见的做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单一指标法, 如以留存收益股权比、销售收入增长率或固定资产增长率等指标的高低来衡量企业成长性的高低。 考虑到单一标准划分一方面难以全面准确地描述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特点, 另一方面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率及固定资产增长比往往有较大的差异, 故本文不采用此方法。 第二种是采用以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三类现金流的量化特征来划分企业的生命周期。 但通过前期数据分析发现, 研究样本现金流的量化特征很不稳定, 难以保证分类的准确性。 第三种则为综合指标法。 本文在参考李常青等[13] 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占总资产的比例以及固定资产增长率的综合指标法来划分企业的生命周期。 首先按行业求出每一指标对应年度的中位数, 然后以各样本对应年度实际指标值是否高于行业年度中位数的结果, 划分出对应单变量下的成长组与成熟组。 再对各样本年度分组结果赋值, 成长期为1, 成熟期为0。 最后根据样本单变量的赋值和进行归类, 赋值和为3的划分为成长期企业, 赋值和为0的划分为成熟期企业。 赋值和为2或1的, 在根据行业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增加留存收益权益比进行类似的赋值追加验证。 追加验证后二次赋值和为3的划分为成长期企业, 二次赋值和为1的划分为成熟期企业, 余下的少量难以确定其生命周期阶段的样本予以删除。
对于重大资金支出(Invest), 本文先以现金流量表中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子公司并购所支付的现金以及所有为投资所支付的现金的总和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年度重大资金支出的表征变量。 然后以各样本次年该指标的实际值与样本所处行业对应年度指标的中位数进行比较, 高于中位数的界定为次年有重大资金支出, 反之表示无重大资金支出。 为了检验新的分红政策的“差异化”分区监管效应, 本文按政策的差异化分类标准设置了四个分类虚拟变量, 分别是成长型高支出公司(HGrowHInv)、成长型低支出公司(HGrowLInv)、成熟型高支出公司(LGrowHInv)、成熟型低支出公司(LGrowLInv)。
(2)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对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前期研究的成果, 选取了盈利水平(ROA)、规模(Size)、负债水平(Debt)、再融资需求(Finan)、股权集中度(1stSh)、经营现金流水平(OCF)、产权性质(SOE)和行业集中度(HHI)作为控制变量。
3. 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前述假设, 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
Logit(Y1)=α0 +α1Period +α2Growth+
α3Growth×Period+α4Invest+α5Invest×Period +
βiCV+ε (1)
Tobit(Payout)=α0 +α1Period +α2Growth+
α3Growth×Period+α4Invest+α5Invest×Period +
βiCV+ε (2)
Logit(Y2)=α0 +α1HGrowHInv+
α2HGrowLInv+α3LGrowHInv+α4LGrowLInv+
βiCV+ε (3)
模型(1)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因变量Y1代表因变量派现意愿(Dum)和“铁公鸡”公司(Iron)。 模型(2)为Tobit回归模型。 模型(3)中因变量Y2代指五个差异化分红虚拟变量, 即“微分红”公司P05_10、低分红公司P10_20、“门槛式”分红公司P20_40、中等分红公司P40_80、高分红公司P80_100。 三个模型中的CV均代指相关控制变量, 即ROA、Size、Debt、1stSh、Finan、SOE、OCF和HHI, ε为残差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由表2可见, 差异化分红期内, 其不派现公司占比总体都在20% ~ 30%区间波动; 半强制分红期的这一比例虽然在持续下降, 但一直处于25% ~ 45%之间。 这表明差异化分红政策下, 上市公司整体派现比例还是显著高于半强制分红期, 即分红新政具有一定的“类强制”分红效应。 但2013年起, 不分红公司占比并未如前期呈一直下降的趋势, 这是否是部分股市“铁公鸡”公司现象難以根治所致,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分红派现的公司中, 从2012年起, 股利支付率在20% ~ 40%之间的“门槛式”分红公司占比一直较高, 每年都维持在30%以上。 这表明“门槛式”分红或“达标式”分红之风并未因分红新政的出台而缓解, 路径依赖现象仍显著存在。 分红水平在20%以下的低分红公司占比在2012年后相对稳定在20% ~ 25%之间。 [10%,20%)和[40%,80%)这两个区间的分红公司占比接近, 而2013年后分红水平在[10%,20%)的公司占比却开始一直略高于分红水平在[40%,80%)的公司, 这初步反映出理论上应进行中等水平或高水平分红的公司并未因分红新规的出台而显著上升, 反而还略有下降。 这是否是新政诱发的弹性选择空间更大所致, 还需进一步验证。 另外, 分红水平在80%以上的高分红公司所占比例一直较低, 甚至一直低于分红水平在[5%,10%)的“微分红”公司占比, 这初步说明:相对于高分红, 国内上市公司显然更偏好于低分红或微分红。
表3的结果表明, 差异化分红政策实施后, 上市公司整体的派现意愿显著提高, “铁公鸡”公司占比较半强制分红期有了显著下降。 股利支付率总体均值虽比新政实施前提高了2.24%, 但差异仅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股利支付率的分布区间结构上看, 除高分红公司占比的增加不显著外, “微分红”公司、低分红公司、“门槛式”分红公司与中等分红公司占比较2013年前都有了显著上升。 这初步表明分红新政的差异化实施效果并不佳。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1. “类强制”分红效应及差异化分红标准选择的有效性检验。
表4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 上市公司在差异化分红期的分配意愿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高于半强制分红期。 模型(2)中, 差异化分红期的“铁公鸡”公司的数量显著低于半强制分红期。 由此可以看出, 分红新政虽没能根除“铁公鸡”, 但对积年形成的“铁公鸡”与潜在“铁公鸡”都产生了较大的震慑作用。 差异化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派现意愿的提升效应较为显著。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成长性水平及重大资金支出与企业的派现意愿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这两个指标与差异化分红期的交乘项显著为负则表明, 进入差异化分红期后, 高成长和有重大资金支出的公司的派现意愿显著更低, 半强制分红期及差异化分红期的分样本比较回归结果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 差异化分红期间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整体显著提高, 假设1a、1b均成立。 模型(3)中成长性水平与差异化分红期交乘项的结果为负, 表明差异化分红期内, 成长性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其支付水平相对下降。 虽然这一变化仅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但结合模型(1)的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假设2成立, 即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对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监管悖论”缺陷的弥补初见成效。 重大资金支出对股利支付率的回归结果无显著影响, 即假设4仅对派现意愿的检验成立。 这表明当国内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资金支出需求时, 更多地倾向于不分红, 而不是低分红。 而这一选择在分红新政的例外选择条款中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 即差异化分红政策下, 上市公司拥有了更大的分红决策自主权。
2. 分红水平的差异化效应检验。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半强制分红期, 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倾向于“微分红”, 唯有最需要筹集资金的成长型高支出公司进行“门槛式”分红的可能性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显著高于其他低资金需求的公司。 这充分证实了半强制分红确实产生了“监管悖论”现象。 到了差异化分红期, 当半强制分红的压力消除后, 四类公司的分红偏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化分布特征:低成长公司分红水平总体较半强制期明显下降, 而高成长公司的分红水平较前期则有了明显上升。 具体而言, 成长型高支出公司倾向于“微分红”和“门槛式”分红, 成长型低支出公司倾向于“微分红”和低分红, 且两类公司都更偏好于“微分红”。 进入差异化分红期, 成熟型高支出公司与成熟型低支出公司进行“微分红”与“低分红”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虽然成熟型高支出公司“门槛式”分红与高分红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但进行“门槛式”分红的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 而高分红的系数仅在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即成熟型高支出公司更可能进行“门槛式”分红。 而成熟型低支出公司仅中等分红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回归结果总体显示, 虽然差异化分红政策实施后, 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偏好区间分布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性, 但每一类别公司的实际分红水平所处的区间均低于政策要求的标准, 即“折扣式”分红现象明显存在, 假设4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重新选择了主要解释变量。 以留存收益股权比作为成长性指标, 以重大资金支出现金流出资产比替代前面“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②将差异化分红区间细分为多个子区间, 如在低分红区放宽到0 ~ 20%, 将“门槛式”分红区间再细分为分红率在20% ~ 30%之间、30% ~ 40%区间进行检验。 不仅进行全样本的分红差异化检验, 还要进行不同期间的差异化分红检验。 通过上述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与表4和表5的结果基本一致。 限于篇幅, 本文不予列示。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6 ~ 2018年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差异化分红政策对A股市场整体分红意愿与分红水平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 ②分红的差异化监管有一定成效, 但总体支付水平低于预期设定标准, 存在“折扣式”分红现象。 这一结果说明分红的差异化标准的选择是合理有效的。 分红水平的差异化监管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依其成长性和重大投资支出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分红差异化特征; 另一方面, 由于分红新政对成长期和重大资金支出的判定标准不明确, 从而为上市公司规避高水平分红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更具弹性的选择空间。 这导致每一类上市公司都存在显著的“折扣式”分红现象, 即其实际分红水平均在法定的分红区间标准上打折或降级分红的现象。
(二)启示
1. 增強法规的有效性。 这既包括对法规内容的完善, 如明确法规中关键条款或标准的界定、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 也包括增强执法和监管的有效性。 “类强制”分红在分红的强制效力上因其例外原则而有其天然的局限性, 但这一局限性不应因执法的宽松而进一步放大, 提高上市公司分红决策依据及结果的信息披露程度是未来持续改进的方向。
2. 深入分析分红水平的差异化监管规定无法完全得到执行的原因。 如果上市公司是因多年分红习惯而形成了路径依赖模式, 则应加强执法的有效性、堵塞执法中的漏洞和降低执法中的不确定性(如对成长性及重大资金支出的准确界定), 从而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 但如果这种现象是政策本身的规定并不完全合理所致, 就应深入调查论证当前的差异化分红标准与符合每个上市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特点的分红标准间存在多大的差异, 总体相对偏低的分红水平是否表明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悖论”? 如何在监管的强度与灵活度之间找到一个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从而满足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和市场宏观调节的目标, 是未来分红改革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李常青,魏志华,吴世农.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 J].经济研究,2010(3):144 ~ 155.
[2] 魏志华,李茂良,李常青.半强制分红政策与中国上市公司分红行为[ J].经济研究,2014(6):100 ~ 114.
[3]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2013-11-30.
[4]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R. Vishny. Agency Problems and Dividend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 J].Journal of Finance,2000(1):1 ~ 33.
[5] Martins T. C., W. Novaes. Mandatory Dividend Rules: Do They Make It Harder for Firms to Invest?[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4):953 ~ 967.
[6] Adaoglu C.. Dividend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Policy of the ISE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The Evidence Revisited(1986-2007)[ J].Journal of BRSA,2008(2):113 ~ 135.
[7] 卓雅心,鄭蓉,干胜道.国内A股“铁公鸡”现状、成因及对策[ J].财会通讯,2015(29):10 ~ 12.
[8] DeAngelo H., L.DeAngelo, R. M. Stulz. Dividend Policy and the Earned/Contributed Capital Mix: A Test of the Life cycle Theor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2):227 ~ 254.
[9] Fairchild R., Y. Guney, Y. Thanatawee. Corporate Dividend Policy in Thailand: Theory and Evidence[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4(1):129 ~ 151.
[10] Fama E., French K.. Disappearing Dividends: Changing Firm Characteristics or Lower Propensity to Pa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60):3 ~ 431.
[11] Grullon E., Michaely R., Swaminathan B.. Are Dividend Changes a Sign of Firm Maturity[ J].Journal of Business,2002(75):387 ~ 424.
[12] Denis D. J., I. Osobov. Why do Firms Pay Dividend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Dividend Polic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1):62 ~ 82.
[13] 李常青,彭锋.现金股利研究的新视角: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5):67 ~ 73.
[14] 罗琦,李辉.企业生命周期、股利决策与投资效率[ J].经济评论,2015(2):115 ~ 125.
[15] 邢天才,黄阳洋.生命周期、财务杠杆与现金股利政策[ J].财经问题研究,2018(8):51 ~ 57.
[16] 宋福铁,梁新颖.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实证研究[ J].财经研究,2010(9):123 ~ 133.
[17] Duchin R.. Cash Holding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J].Journal of Finance,2010(3):955 ~ 992.
[18] Almeida H., Campello M., Weisbach M.. The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 J].Journal of Finance,2004(4):1777 ~ 1804.
[19] 余静文.信贷约束、股利分红与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2(10):97 ~ 110.
[20] Brav A., Graham J. R., Harvey C. R., et al.. Payout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3):483 ~ 527.
[21] 徐寿福,邓鸣茂,陈晶萍.融资约束、现金股利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2):112 ~ 124.
[22] Jensen M.. 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2):323 ~ 329.
[23] 林岗.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 J].中国社会科学,2001(1):55 ~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