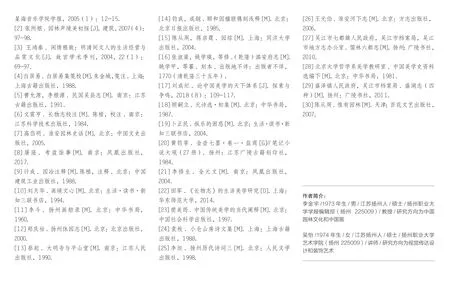试论古代园林中的琴与琴境*
李金宇 吴怡
LI Jin-yu,WU Yi
琴在中国古典园林里,既是装饰环境的器物,如晚明文人高濂以为书斋应该“壁间挂古琴一”;又是丰富园主心灵世界的长物,是抗拒世俗社会的特定符号。由琴声在园林中营造出的氛围,即文中所指“琴境”,更是具有审美上的特殊意义。今人有从比较角度分析琴艺术与园林艺术,有从听觉角度探讨琴在园林中的声境营造,还有从古人闲雅活动中研究琴与园林对文人生活的影响等[1~3]。本文拟从古代园林与琴的关系入手,从历史关联、琴在造境中的虚实、琴在园林中的功用等方面,具体阐述琴在中国园林里的特别之处,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1 园林与琴
中国园林中常见琴的身影。有题名含琴的园子,如清代书画大家汤贻汾晚年在南京筑有琴隐园;也有题名含琴的建筑,如苏州盛湖停云读画楼园中有古鲸琴馆,圆明园有琴清斋、琴趣斋,北京避暑山庄有玉琴轩等,上文提到的琴隐园内也有十二古琴书屋、琴清月满轩、默龛琴台等建筑。
唐代白居易在洛阳建有南园,园内有琴亭,并自谓“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4]2736。宋代苏州的朱长文,除了在园中写出《乐圃琴史》,更在其《乐圃记》中云:“冈上有琴台,台之西隅,有‘咏斋’,予常拊琴赋诗于此,所以名云”[5]595。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把琴放在园林建筑陈设器物一节,按陈植先生言:“园林内必须内外配合,始能形成综合之美”[6]432。又如一些虚构的园子,在文人笔下,也常常以琴命名,如清代文人黄均宰曾写《琴园梦略》描绘其所居的琴园,洋洋洒洒,引人艳羡。但据今人考证[7]157,所谓琴园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作者乌托邦般的想象,是自己的假设之园。但这也反证出园林中的琴对于文人而言多么重要。
此外,琴与园林的密切关系,也是由抚琴、听琴所需的环境决定的。文震亨以为,使琴声透亮清冽的静寂之地,需选在“乔松、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绝”处 。屠隆同样认为,要淋漓尽致发挥琴声之清,应该选在“乔松修竹,岩洞石室,清旷之处,地清境寂,更有泉石之胜”的地方,才可“琴声愈清”。又说,鼓琴最佳的环境是:“鼓琴,偏宜于松风、涧响之间,三者皆自然之声,正合类聚。或对轩窗、池沼,荷香扑人,或水边林下,清漪芳沚,微风洒然,游鱼出听,此乐何极”[8]58。这里所描绘的环境要求,不正是园林的环境—叠石理水,亭台楼阁,花木掩映其间;不正符合中国园林营构所追求的环境—“入奥疏源,就低凿水,搜土开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杂树参天,楼阁碍云霞而出没;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参差”[9]58。难怪今人刘天华在《画境文心》一书中说道“古琴弹奏要求清、幽、雅、洁的环境和古、淡、静、闲的心境,这与古园创造的风景环境和它所要求的观赏心境较为吻合”,并在引用明代杨表正的《弹琴杂识》后指出,“(弹琴)或高堂或静室,或山水林石间,或清风明月夜,均以园林风景中为最佳,这也是士大夫文人均喜筑琴台、琴亭和琴室于园中的缘由”[10]242。
2 园林听琴
在中国园林中,听琴分虚、实两种,一是听有形之琴,一是听意会之琴。有形之琴,此为实境,就是在园中设琴室,置古琴,人可抚操。如苏州留园的琴室(图1)、苏州怡园的坡仙琴馆、惠荫园的松荫眠琴,东莞可园为绿绮台琴而修的绿绮楼,以及扬州瘦西湖小金山下的琴室等(图2),皆是如此。

图1 留园琴室

图2 瘦西湖琴室
意会之琴,此为虚境,即园中并无实琴可供抚操,听琴之名,乃是周遭自然之音入耳后以琴声比拟。有以树木之声喻琴,如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净香园)‘涵虚阁’之北,树木幽邃,声如清瑟凉琴”[11]273。又有以竹声喻琴,如扬州休园,清代方象瑛的《重葺休园记》云:“屋后修竹万竿,有轩曰:‘琴啸’”[12]49。还有以风吹山石声喻琴,如扬州平山堂西苑的“听石山房”,所谓“听石”,其实是听风吹山石而过的声音,古人有云:“山风刚劲,擦壁如琴”[13]59。
在园林中最多被喻为琴音的是水流之声。如苏州拙政园的小沧浪水阁,其旧有联“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就是以水声喻琴。无锡寄畅园的“悬淙涧”,北京颐和园中的“玉琴峡”“清琴峡”,俱是以听溪水潺声如琴闻名,乾隆皇帝《御制诗》中赞清琴峡为“流泉出峡中琴音,即匪宫商与石金,太古以来便有此,笑他师旷未曾寻”[14]187。王稚登的《寄畅园记》描写悬淙涧为“台下泉由石隙泻沼中,声淙淙中琴瑟”[15]174。此外,晋祠孙家别墅园中的“卍”字形小溪,清代刘大鹏《晋祠志》记之为“琮琤荡漾之声,洋洋乎日夜盈耳”[16],虽未明说是琴声,但“琮琤”二字,已不言自明。保定的古莲花池,围绕四周的建筑群分别叫响琴榭、听琴楼、响琴桥等,这是把涧水流觞之音当成琴声最为直接的表达。
意会之琴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峰石姿态来比拟听琴者,让人感受到琴声。如苏州怡园的石听琴室,因在坡仙琴馆外有一石形似伛偻身躯的老人,其俯首之态仿佛在醉心听琴而得名。还有上海南翔古漪园内的“五老操琴”,亦是通过五座姿态各异的石峰和一长方石制琴台,象征听琴者。
从上文有形之琴和无形之琴可看出,是否有人在其中真正操抚并不重要,而是意在琴外,在耳,更在心,是使观者产生妙悟迁想,获得象外之境。古人一句“松风流水天然调,携得琴来不用弹”道出了其中的真意。这与明代沈周《蕉阴横琴图》中题识“抱琴未须鼓,天地自知音”,以及晋代陶渊明置无弦琴,有曲异同工之妙。清代学者、文献学家的陈梦雷,在北京西郊有园子水村,在其《诗集》卷五《水村十二景引》中亦有云:“余兼置琴一张,旧曲皆忘,抚弦适意而已”。可见,园林中的琴,本身虽是有限的,但琴背后的乐感文化却是深刻而广垠的。今人刘成纪从天下观念与音乐的关系,论述音乐建立人文化的审美体系:“在中国社会早期设定的天下体系中,音乐构成了人的生存境域,但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人事原则,渗透进了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据此可以看到,音乐化的天下观念,不仅指人生存的外在时空世界,而且也内置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宏大高远又无微不至,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实现了整体的渗透和贯穿”[17]。这种超越性、渗透性,决定了园林与琴构成、衍伸的想象空间最终将导向审美意识和无尽的诗意。
3 琴在园林中的功用
3.1 身份定位
园林中设琴,是古人生活美学的一种体现,是园主品味的展示、身份的定位。如倪云林的宅园清閟阁,“阁中藏书数千卷,手自勘定,三代鼎彝、名琴古玉,分列左右。时与二三好友啸咏其间[18]2091。”对这些书籍、鼎彝、古琴等物的收藏与展示,起到了强化拥有者身份、地位的作用,是在“传达着一种雅致”[19]245。明代冯梦桢举例代表闲情雅致生活的“十三事”中,“鸣琴”就是其中一项。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提到晚明士人的闲居之趣有五,其二即为“鼓琴”。伍绍棠在《长物志跋》中说,明中叶士大夫以儒雅相尚,其表现之一就是精于弹琴。清代黄钧宰的《金壶浪墨》记载了扬州盐商的容园,其侈靡奢华、池台之精为当地诸园之最,园主张氏每日午前开放园子任人观赏,游人除看到“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異,夏则冰绡竹簟,冬则锦幕貂帷,书画尊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者为贵,古玩无真赝,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史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主人兜舆而出,金钗十二,环侍一堂”这样的画面外,还特别提到园主和侍女的行为—“赏花钓鱼,弹琴度曲”[20]134。由此看出身为商人的园主所展示的物品和活动,不仅标志了个人兴趣,更表明其对士绅精英阶层生活文化趣味的模仿和认同。至于许多文人雅集,如元代赵孟頫的“西园雅集”、顾阿瑛的“玉山草堂雅集”,明代谢环的“杏园雅集”、戴进的“南平雅集”、谢时臣的“高人雅集”,近代叶璋伯的“怡园雅集”,很多都是围绕听琴展开。玉山草堂雅集当时情形为“炎雨既霁,凉阴如秋,琴姬小璚英、翠屏、素真三人侍坐与立趋。歈俱雅音。是集也,人不知暑,坐无杂言,信曰雅哉![21]99”从“歈皆雅音”到“坐无杂言”,再到“信曰雅哉”,反映出园主和众文士风雅、精致的生活状态。
可以说,琴隐喻了古人追求的雅文化。“书画琴棋诗酒花”是我国古代士大夫文人所谓的七大韵事,其中琴是曲的代表,与诗、画、书、酒一样,是文人雅士在园林中主要的精神享受[10]239。这才会出现古人常常说的“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8]52。且即使不会抚操,也应备琴一张,“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6]296”“纵不善操,亦当有琴[8]52”,有琴的生活代表着一种蕴藏审美潜质的高品位、高格调的生活,映射着生活的灵趣与性情,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物化。古人通过拥有这种长物的标识,营造出一种理想状态的、栖息身心的雅境,进而达到超越凡俗的日常生活,实现精神的自由与升华。这亦是对其生命空间与生存状态的一种重塑与呈现[22]17。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琴尚恬静、和润、清远、冲谈、飘逸、古朴、雅致,这些恰是文人士子的个人生活理想格调。也就是说,琴暗合了中国古人尚清的审美理想和生活方式[23]102。
3.2 娱情忘忧
琴对于园林中的人而言不只是乐器,更是精神上的助推剂、催化剂。首先,琴可以助景娱情。如乾隆年间扬州的两淮盐商首总江春,家园康山草堂“有林亭之峙,兼水木之饶”,他常常在其中一面招集名流,优游赏景,另一面则是“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24]1863。又如苏州槃隐草堂,每和风晴日,园主毛逸槎与四方宾客在观景之余,“常得休暇于此,而望衡对宇,时多素心,或弹琴、或对弈、或觞咏……极盘桓游衍之趣,主人之乐,与宾朋之乐”[5]611。园林中,琴声里,既有雅集时听琴助兴的众乐乐,也有园主孑影自适的独乐乐。如清代蒋恭棐在《逸园纪略》中写道:“每春秋佳日,主人鸣琴其中,清风自生,翠烟自留,曲有奥趣[5]609。”扬州个园主人马曰璐亦有“林间鸟不鸣,何处发清响。携琴石上弹,悠然动遐想[25]34。”无论是众乐,还是独乐,从古人众多的表述里可见,园林之景配上古琴之声,对人情绪的影响极大,其既是人情感的触媒,也是激发人特定情感状态的凭藉。身在其中,会神思千里,身心俱爽,即明代屠隆所谓的“月色当空,横琴膝上,时作小调,亦可畅怀”[8]57。清代沈德潜在《勺湖记》中描写了园主方还在自家园中弹琴的状态:“勺湖,方氏园池也……主人无事,辄来园中,或孑影自适,或偕昆弟友生,倚阑槛,坐高阁,弹琴咏诗,酌酒相乐,酣然欲卧,心游玄漠,若将有得焉,而老于斯也[5]632。”园主非常享受这样一种内心自由、轻松的状态,并希望自己能终老于此。
在园林的琴声里,人们体会到了忘怀息心的审美之境,体会到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所说的“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众乐时,琴声渲染了气氛;独乐时,琴声调节了心情。琴之妙处,于此可见一二。
其次,美的园景与雅的琴声,更起到涤烦消虑、忘忧解乏的功效,诚如陶渊明所言,“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因为有了琴,把久在樊笼里的人们从尘世繁琐中解脱出来。据《南齐书》记载,步兵校尉张欣泰兼任羽林监,负责宫廷警卫工作,但每次下班后就脱下武将服饰,换上文士装束,携带一张琴到园林的山水里散心。宋代欧阳修在雍家园里,“我来据石弄琴瑟,惟恐日暮登归轩。尘纷解剥耳目异,只疑梦入神仙村。”听琴声而仿佛进入神仙妙境,就是因为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可以暂时忘掉人世间的纷烦俗务。更值得注意的是,园林中的琴声不但解心理之忧,还能解身体之乏。如清代方苞说自己每当身体疲惫劳累之时,只要在刘昌言的怡园中听其抚琴,就会倦意顿消,神清气爽,“(刘昌言)善琴,得雅声,余每疲疴,辄就君听琴,一再鼓,心常洒然[26]287。”
在园林的氛围里消愁忘忧,有两样东西是在古人诗文中常常并提的—琴与书。明代徐有贞在《先春堂记》中云:“生斯太平之时,承文儒之绪,田园足以自养,琴书足以自娱,有安闲之适,无忧虞之事,于是乎逍遥徜徉乎山水之间,以穷天下之乐事,其幸多矣[5]599。”明代翰林曹镤说在自己的邱园中,因“可琴、可书”,而“皆吾乐也”[27]35。同样,清人王松借榻于淮安河下镇程吾庐的寓园,虽在炎热的夏天,因有琴书相伴,心情由此大好,“使君移节消长夏,博得琴书自在游”[26]239。这一切,正如王鸿泰说的:“士人将其生命获得投注、沉湎于诸种长物,于此开展出丰富的感官活动,用以寄托个人的情感,在感官的伸展与情感的投注下,生活呈现出一种别具意味的情境—一种离异于现实、世俗世界的雅的境界。这种雅境成为文人用来安身立命的处所[3]。”明代造园大师计成在《园冶》“傍宅地”中提出对居游情境的想象:“开池浚壑,理石挑山,设门有待来宾,留径可通尔室。竹修林茂,柳暗花明……常余半榻琴书,不尽数竿烟雨。”
可见,长物之琴,宛自天开的园林,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雅的、屏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家园。
3.3 清音造境
琴声营造出的氛围,具体而言是一种“清”的世界。宋代倪思说琴声是至清之音,“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给人的感受是“试一听之,则澄然秋潭,皎然月洁,湱然山涛,幽然谷应”[28]175,即琴声之清,让闻者有入深山邃谷之想。而这恰恰与园林的审美体验、艺术追求相一致,指向的都是自然之境,都让人生出离尘之想、亲近自然之心。可见,琴声与园林在形而上的艺术层面上有不少的共通,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因为清,人们“听琴弦,可消躁念”(明代倪允昌);因为清,所以“凡声皆宜远听,唯听琴则远近皆宜”(明代张潮) 。古人为了让操琴者能淋漓尽致地传达出琴声之清,让听琴者被感染进而神思冥想,往往把琴室与赏月之所比邻或合二为一。如扬州瘦西湖琴室就毗连月观;而苏州南山斋园中一小屋,则是既可做弹琴之用,也可做玩月之所,“右廊微广,因结为斗室,可以调琴,可以坐月,所以为斋之助者不浅[5]615。”
琴对园林而言,是相辅相成,更是相得益彰。琴声的渲染,更有助于把人们导向一个脱俗的、自然的、畅神的心灵境界。如上文言,水声可作琴声听,其实琴声在古人耳中亦可作水声听,宋代欧阳修有“音如石上泻流水”,清代陈希恕在《重过停云楼》中亦云“古琴要作水声听”[29]417。同时,也可以说,清音的琴声是园中山水发出的另一种语言,古今园林中一些一语双关、涵义丰富的楹联揭示出琴声与园林山水之间微妙的关联性:“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苏州拙政园、扬州瘦西湖),“园林无俗韵,山水有清音”(上海汇龙潭),“桂林无杂木,山水有清音”(桂林书院)。园景、琴声互相映衬,相互激发,从而使得人们超越了有限的所见、所听,营造出一派出世的境界。
4 结语
园林,古琴,都代表了古时社会的最高时尚,是雅文化的代表,是维持文人社会精英地位的独特符号,其背后深藏的文化价值、艺术精神,已远远超过物之本身,它们带来的特有的雅赏的审美体验,可谓是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带来了形而上的愉悦,醇化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中国的文人士子、儒商雅贾在不知不觉间,创造了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范式:园林中实的琴景,虚的琴境,是把可听、可观与可思、可感巧妙统一,不但在物质上追求精致化、细腻化,而且在精神上追求“诗情画意化”,把诗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灌注在日常生活中。这诠释了中国式生活审美化的可能与方向,也为今天和以后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参考。特别是当下,修缮旧园、营造新园之风甚盛,古人的设琴之举,给今人如何传承中国文化,如何在园林中体现中国古代独特的审美观予很好的启示。正如陈从周在《说帘》一文提到中国建筑中的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物件,其实是中国人的用帘,不仅仅是一个功能问题,它是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在内[30]159。而琴,正如帘一样,也是今天园林修缮者、营造者一个不容忽视的“妙物”。
注:文中图片为作者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