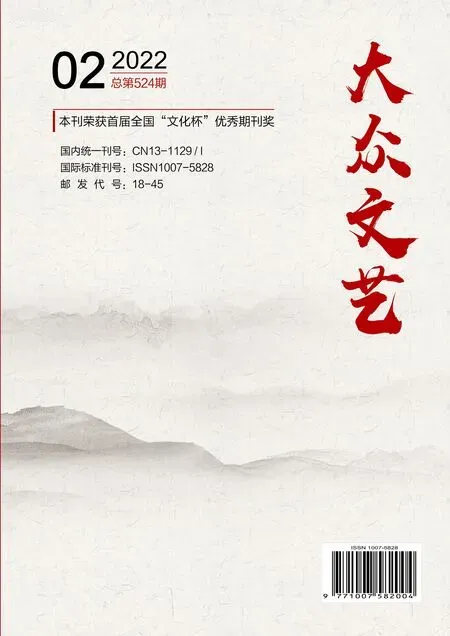论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水”意象的异同点
——以《边城》与《受戒》为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生长于阮水河畔与里下河流域且具有浓厚师生情谊的沈从文与汪曾祺,皆是写水的好手。沈从文自己曾谈道,“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菰蒲深处·自序》中汪曾祺也说:“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二者的小说皆沾染着水意,为当下喧嚣浮华的社会注入了一股股洗净人心的清流。然而二人塑造的“水”意象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所在,而这指向了两人不同的人生旨趣——“漂泊的水手”与“庭院的士大夫”。
一、“水”意象的共通性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沈从文汪曾祺笔下的故事背景,常常发生在水边。水养育了一众百姓,为其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使民众得以繁衍生息,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百姓的生命由水创造,也依靠水得以维持,水不仅是百姓的生活家园,更是其心灵的皈依之所。
(一)生活环境:有容之水,精神家园
《边城》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清澈明净的溪边,在文章起首作者便描绘了主人公的生活环境:“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翠翠与祖父就生活在这小溪边,以撑船度日。而茶峒城则凭水依山而建,在临水的一面设码头进行贸易,顺顺便靠码头起家。水影响着这里的聚落分布形态与建筑走势,也决定了人们的职业,提供其赖以为生的基本保障与娱乐场所。而《受戒》中小英子与小明子的生活环境,也莫不与水发生着联系。小英子的家被水包围着,“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而荸荠庵与善因寺的门前都有一条河流经,建在一片高地之上,显示出选址的智慧;河流深处的芦花荡子则成为小英子与小明子爱情生长的见证,由此足以见得这方百姓与水的密切关联。
(二)人物性格:本真之水,品德寄托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纯净清澈的河流湖泊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使一切肮脏恶毒之物难以滋长,两人笔下的乡民皆忠厚淳朴,善良诚实中透出自然力与人性美。《边城》里的老船夫忠实地守了一辈子渡船,不图钱不图利,气骨凛然;船总顺顺则大方洒脱,慷慨且能救人之急;大老与二老为人光明磊落,为爱情公平竞争愿赌服输;《受戒》中的能干且和气的“全把式”赵大伯、精气神十足的赵大娘以及精通技艺的三和尚仁渡,皆是淳朴百姓的代表。翠翠与小英子作为以上两部作品中最主要的女性人物,则因青山绿水的滋养样貌清秀、富有灵性。而即便是妓女荡妇一类不够正统的女性,在他们笔下同样自然且普遍,甚至因其重义轻利的真性情得到作者的称赞。
江河湖泊以其包容平和浸润着土地,万物得以生长;以其坚韧不屈感染着乡民,健康自然的人格与道德灵气得以传承。在生活环境与乡民性格的维度上,“水”意象的内涵于沈从文汪曾祺笔下大致相同。
二、“水”意象的差异性
无论是魅力迷人的湘西世界,还是充满烟火气息的江南水乡,二人追求的都是一个充满爱与美的理想国度。然而在这样共同的创作主题下,却产生了不尽相同的爱情悲欢与人际遭遇,带来有关人生遗憾或圆满的无尽慨叹。
(一)水之无常:悲惨宿命
可爱乖巧又讨人欢喜的翠翠,却因为一系列的巧合没能与二老造就美满幸福的结局,最后留下的只有朦胧的期待,这希冀或许会成真,又或许将成为翠翠永远的遗憾,一切都未可知。这样的结局究竟是谁造成的?谁也无法说清,“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只留下命运无常的喟叹与造化弄人的伤感。除却爱情悲剧外,亲情在《边城》中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毁灭与挫败。天保由于在和傩送的竞争中失败而自愿退出,却在恍惚间溺水而死,“水”直接导致了大老的死亡。兄弟情分的消亡致使二老内心产生难以摆脱的负疚感,也使得二老对翠翠产生了永远无法消除的隔阂。而在一场裹挟着巨大雷声的暴雨过后,溪水漫堤、渡船消失、白塔坍塌,祖父也在雷雨将息时永远地离开了……翠翠失去了在人世间唯一的依赖,但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沈从文没有试图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他更倾向于把根源归为一种人事无法左右的天意,有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子。”正因无法左右,只得无奈顺从,即使心有怨言,但命定感让人类学会了接受,并敬畏于天意和神的伟大,将现世的人事诉诸神来完成和实现。
(二)水之柔和:和谐图景
相比之下,汪曾祺塑造的苏北水乡则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依托于自身的净化,人性中美好纯真的气质战胜了神性的权威,民间的世俗良善拯救了人类本身。在茂密安静的芦花荡深处,两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互相交换心意,初尝爱情的甜蜜与幸福,留给读者的是青桩鸟受到惊吓、擦着芦穗扑鲁飞走的画面,作者在文章结尾呈现的图景因人事的完满而给人和谐安宁、现世安稳的美感体验。“水”正以其流动性推动了两人关系的发展,也在最后表露心迹之时充当了爱情的见证,罕无人至的芦花荡、沉净安详的河水、生长绽放的水草,爱情就在水的烘托陪衬下悄然降临。水养育了健康的人性,造就了人性的解放,展现了美,保护了人世间最为细腻的情感。正如汪曾祺在回答施叔青关于《受戒》想表现什么时所言:“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美好的人性在汪曾祺笔下得到了肆意的张扬,神则退出了现实世俗的民间,被封锁在另一个完全不被触碰与表露的世界。
比较两部作品中的爱情结局及人物命运,可以发现“水”的意象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异质性,沈从文呈现的是面对至高的神性产生的无奈的命运感,而汪曾祺则是潜入世俗的人性产生的和谐的现实感,而这正代表了两人不同的价值追求与创作风格。
三、漂泊的水手与庭院的士大夫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同样深受水影响的二人,却塑造出如此迥然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进一步审视其成长经历与文化心理,探究更为深层的原因。
沈从文的一生皆与水结缘,前十四年是在阮水河畔,14岁参军后随军队辗转各处漂泊,水教会他做人做事,也教会他思索。深受“人神共处”巫楚文化的影响,浸润着水元素的湘西作为一片敬畏神灵、崇拜神秘的地理存在,浪漫与野蛮并存,自由和剽悍共生。两千年前,屈原曾写下神奇瑰丽的《九歌》,再现了楚地丰富多彩的民俗与浪漫飘逸的民风。而沈从文便通过阮水与屈原联系在一起,虽后来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敬天畏神的印记并没有从其血液中消除,追随着屈原的足迹,沈从文自称是“最后一个浪漫派”。楚文化对于沈从文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他曾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而这种命定的悲剧感,在《边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发与抒写。翠翠母亲的死、士兵的自杀、大老的溺水,在老船夫看来皆是天意,人类既无法改变,也无从怪罪。这正印证了沈从文对于爱与死的独特思考:“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他追求美、向往爱,又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终将归于幻灭,然而正是死之必然才能衬托出生之伟大,确证有限生命存在的意义。沈从文所突出的命定的悲剧感,显示出他对于生与死的矛盾所做的形而上的思考。
而生长于高邮水乡的汪曾祺同样与水产生了不解之缘。他自己曾说:“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除却氤氲水气的影响,带有士人雅气的父亲给予了汪曾祺最大程度发挥天性的空间,其儒雅随和的士大夫气质同样濡染了汪曾祺,使其更加注重现实人事,而这一点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他自己也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情感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汪曾祺追求“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努力在平凡的人生中发掘独特的诗意,用以弥补现实的不完满。因此,《受戒》的题材虽是写和尚,但是他笔下的和尚并无独特佛性,却与凡人别无二致。在他看来,“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因此荸荠庵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息的世俗世界,然而世俗中透出的是一派和谐的景象,他用平和的语言与舒缓的节奏构筑了“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的审美世界。
综上所述,沈从文终其一生的漂泊如同海浪中航行的水手,而汪曾祺则代表着处于庭院中以和谐自然为归旨的士大,一个竭力追寻生命本质,向死亡发问、向世界挑战;一个安于现世美好,与平凡为伴、与和谐相依。看似共同以“水”为题,实则二人旨趣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