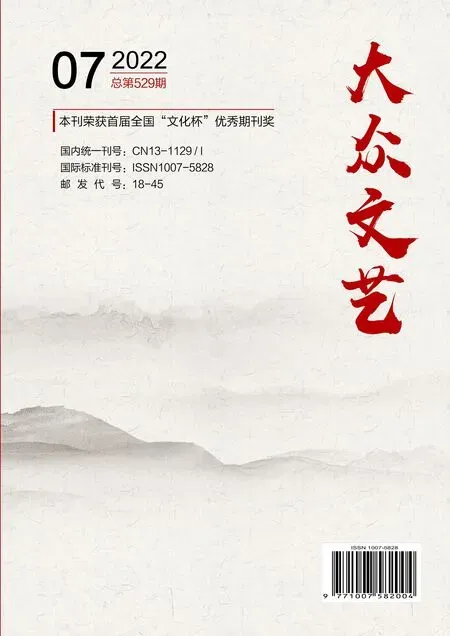女性解放话语下的《伤逝》与《逃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 510420)
女性觉醒并实现解放一直以来都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话题。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鲁迅(1881-1936)《伤逝》(1925年)中勇敢逃离的子君,和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以下简称门罗)《逃离》(Run Away,2004年)中两次逃离的卡拉,虽然都是逃离的行为,两人在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意识的现实检验两方面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模式。身处不同的女性解放话语阶段,以及作家不同的性别体验,造成了两位同是逃出家门的女性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一、女性意识的萌发
《伤逝》和《逃离》分别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意识觉醒方式。在《伤逝》中,子君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在涓生的不断鼓动下的“被动”觉醒。而在《逃离》中,卡拉从第一次选择逃离父母家庭,就向我们展现出了自觉的女性意识萌芽。但二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着特定时代所属的女性解放话语。为各自回答自己所处时代的女性解放问题,身处不同时空的作家塑造出了两个全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一)子君的被动觉醒
鲁迅的《伤逝》作于1925年,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时值中国受西方思潮影响,处于现代思潮勃发与论争阶段。1918年6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刊登了胡适翻译的《玩偶之家》(当时译作《娜拉》),文中不愿继续充当男性囚徒与玩物、勇于冲破男权束缚、走出家庭的娜拉,与时人要求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极其吻合,一时之间掀起了女性解放的诉求和话语探讨。离家出走的娜拉,在女性解放的声声呐喊中成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无数女性从娜拉的名言“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中获得憧憬解放与未来的动力。但鲁迅却并不完全赞同这一风尚,1923年12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中,他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认为,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女性觉醒的条件,“第一,在家应当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稍晚于这场演讲后写成的《伤逝》,便是这一观点的延伸,小说里的子君就是鲁迅笔下受“娜拉出走”神话鼓动而被动觉醒的“中国娜拉”。
《伤逝》中,两人恋爱时一直是涓生跟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而子君终于在涓生不断重复的现代女性解放话语中,向娜拉一样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与其说是恋爱关系,不如说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女性主义理论指出,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指女性从自身经验出发,意识到自己与男性的性别差异,意识到传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施加的有形和无形压迫,从而产生自主反抗,反抗来自男性及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压迫,追求女性自己的独立生活,创造自身价值。而在《伤逝》中,子君对女性意识、女性解放的认识全然来自涓生的灌输,是在女性解放话语引导下的被动觉醒。至于“女性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子君只知其行为而不知其本质。
(二)卡拉的自主觉醒
出生于1931年的门罗,创作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彼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性主义批评已席卷欧美,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同时又是自强不息的主力军。门罗作为在女性解放话语中不断创作的一代,塑造了众多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形象,卡拉(《逃离》)就是其中之一。
成长于重组家庭的卡拉,身材平平,样貌平平,学习成绩更是平平,是姑娘们取笑玩弄的对象。卡拉从小到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与动物打交道,并希望大学可以学习兽医,但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卡拉倾心于马术学校里最优秀的老师克拉克,两人一同谈理想、谈未来,在你来我往的交谈中萌生了爱情,但再次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对其爱好和爱情的双重干预之下,卡拉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仅仅留下一张字条就离开家庭,断绝了与父母的所有联系,凌晨五点坐上克拉克那辆又破又臭的卡车,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卡拉在留给父母唯一的字条中如是写道。卡拉的觉醒是一种自觉意义上的觉醒,反抗父母的权威和安排,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二、女性意识的现实检验
子君、卡拉在不同的时空里,以不同的觉醒方式逃离原生家庭、拥抱自己选择的新生活后,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女性生活姿态。
(一)传统女性模式:子君
子君在挣脱父权制家庭束缚后,和涓生两人在吉兆胡同开始了同居生活。子君承担起了料理家务、烧火做饭的责任,每天“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都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此时的子君,俨然已经不是那个听涓生讲泰戈尔、讲雪莱时眼中充满光泽的子君,在操持柴米油盐之外的乐趣和精神寄托便是与房东太太明争暗斗。因而,与其说她是意识到自己深受压迫、勇敢出逃的“中国娜拉”,不如说她是听从涓生鼓舞、为爱出逃的“现代崔莺莺”。这样的子君,并非启蒙者涓生所期待的现代新女性,她与崔莺莺的区别仅仅在于,子君身处现代女性解放话语风行的20世纪20年代。在女性解放话语影响下,其出逃行为被镶嵌上了现代性光芒。身披虚假现代性外衣的子君,在被涓生抛弃后既回不去传统家庭,也不可能融入真正的现代性话语中,自杀也就成了她有且仅有的选择。在女性解放话语鼓舞下被动觉醒的女性,被裹挟着步入现实生活中,却无法真正自洽于现代性中。这种不可调解的矛盾,酿成了女性的悲剧。
(二)卡拉的现代女性矛盾
门罗笔下的卡拉在逃离父母家庭后,虽未完全重回传统女性模式,但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女性解放的现实矛盾问题。卡拉与克拉克私奔后,两人如愿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但生活终究不如幻想中美好,在学校时温柔绅士的克拉克仿佛消失了,代之以一个狭隘自私、脾气暴躁的克拉克。卡拉忍气吞声,将注意力转移到马场的几匹马和小羊身上。在邻居西尔维亚度假回来请她上门打扫卫生时,卡拉终于崩溃,痛陈克拉克长久以来的种种压迫和冷暴力。在西尔维亚的资助下,卡拉再一次逃离,坐上了前往多伦多的大巴。但事与愿违,卡拉中途下了大巴,哭着打电话求克拉克来接自己回家,“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卡拉的第一次逃离,是在父母的双重压迫影响下做出的自主选择,有着朦胧的女性意识觉醒,克拉克的帮助更加鼓舞了她勇于挣脱束缚。因而,第一次逃离压迫的卡拉,虽说是自主的觉醒,但女性意识还处于一种微弱的萌芽状态。女性意识萌芽状态下的卡拉,再次出逃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出逃路上的卡拉在心理上惊觉克拉克竟然占据了她的全部生活,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她选择与自己和解。回归后的卡拉,重新处理了和克拉克的关系,掌握更多家庭话语权。但卡拉却“像是肺里什么东西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卡拉自主觉醒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与现实发生碰撞后,她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完全放弃了女性意识和平等权利。作为一位已经觉醒了的现代女性,她选择与现实和解,将这份女性意识藏于心中并融于生活,争取更多平等权利。
三、男女作家的女性意识比较
《伤逝》和《逃离》向我们呈现出了两套不同模式的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女性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受检验的过程。除了两位作家身处不同时空、面临的境遇不同之外,我认为还有作家的性别差异带来的认识差异。
20世纪20年代,正值民族国家危亡之际,现代性思想也像轰开国门的坚船利炮一样以惊人的速度恣意蔓延,“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话语便是其中之一。对现代话语一向保持谨慎且极具现实人文关怀的鲁迅,在认识到“娜拉出走”仅仅是现代性话语创造的女性解放神话之后,以子君的悲剧揭示出现代性话语炮制的女性解放话语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鲁迅作为男性作家,虽觉察到了这套话语的空洞,但却无法切身体会女性彷徨无助、无所适从的心理,也无法代替女性做出选择。而当时女性作家笔下彷徨无助、孤独无依,甚至沦为男性玩物的女性,更能揭示出彼时女性解放话语的虚伪性。
成长于女性意识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时期的门罗,加上生活的磨炼,对女性意识的生发有着独特经验。门罗的前半生贡献于家庭,据她回忆,“最开始只能利用女儿午睡的时间写作,第一本著作的写成并出版花费了十五年时间”。但门罗从未放弃女性的写作权利。门罗笔下矛盾的卡拉,是她出于自身经验对女性解放话语进行反思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风靡于欧美国家的女性主义,高声疾呼女性解放,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摇旗呐喊的女性解放代表们家境优渥,能够专注于女性创作和理论研究,但却往往对普通女性表现出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即以自身的女性经验作为范本,鼓励其他女性走出家门。女性是否真的可以在纯粹的理论和作品鼓舞下实现自我解放呢?我认为门罗通过《逃离》表达了这样一种女性解放态度:男性与女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两极,女性的觉醒和解放绝非只能通过反抗男性、脱离家庭来实现。同时,她在探索一种更加温和的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方式,思考女性如何在自我觉醒后与男性平等共处。
现代女性解放自19世纪始,至今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也呈现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如何调和女性解放话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与碰撞,是接下来值得我们思考并探索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②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28,29.
③④⑦⑧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241,241,245,245.
⑤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
⑥⑨⑩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3,36,47.
(11)艾丽丝门罗,珍妮麦卡洛克,莫娜辛普森,杨振同译.《小说的艺术——艾丽丝门罗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