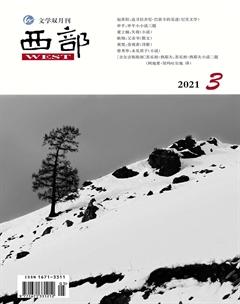陆梦小小说四题
陆梦
枪口
这件事说起来真难为情,从我开始写小说,就抱定一个信念,不能轻易把人写死,我知道不管是真实的生命还是虚构的,他总归是生命,不能轻易判人家死刑。这次这人一定要死,你别以为是我杀的,和我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牛马年好种田,赵武信这个,特意赶牛年包了一百亩地种棉花。
春天的沙尘暴刮一场,赵武的心就抽一次。抽到第三次时,沙尘暴终于小了,重播了三次的棉田也保住了。看着白花花随风起舞的地膜,赵武黑黝黝的脸更黑了。听说,十三团两口子抵押贷款承包了两千亩地种棉花,第三次沙尘暴刮走地膜后,两口子喝药死了,临死把两个孩子也捎上了。趙武默默地为那四口子惋惜。这地方没有工厂,没有企业,该卖的土地都卖完了,大树一转眼也绝迹了。没有遮掩的戈壁,大风还不是想野哪儿就野哪儿?
不信年头就是不行。补了三次棉种,赵武的棉花还是丰收了。打发走拾花工,还掉银行贷款,他捏着手里的五张红票不知所措。赊欠的农资尚有两万五千元没还。那个姓张的老太婆左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催了不下百遍,上门都来了十八趟。要不是害怕银行贷款还不上下年就不给贷款,赵武早就把钱甩到她脸上,要要要,要人命啊!
姓张的老太婆又打来电话让赵武去一趟,赵武开上小四轮就走了,老婆在后头喊:“武子,你喝多了,不能开车,明天去吧!”
赵武回头嚷道:“你以为开的是宝马,这也能叫车?一天到晚就知道叨叨,少人家钱不还,想赖账啊!”
赶到张老太婆的店时,天已经黑了。赵武害怕小四轮摇把子被人顺走,就拎在了手里。
张老太婆一见赵武,脸就拉了下来开始数落:“我好心帮你,棉花也卖完了,钱也到手了,该把账结了……”
赵武赔着笑说:“我没有钱,想给您商量一下,今年的行情您也知道,棉花收购受到了限制,我们都是拿着身份证到指定的收购点卖棉花,价人家定的,一公斤卖不到六块,给人拾花费就去了二块多,后期拾花费涨到三块多一公斤,才卖四块多一公斤。去掉杂七杂八的费用,没有了。今年棉农都不行,种的多赔的就多。您通融一下,等政府补贴下来,或者贷款下来,我再还您行吗?对了,我还可以适当给您点利息。我这人讲信誉,从不赖账,说给您还就给您还。”
“好啊,你个赵武,等政府补贴,亏你想得出,等到猴年马月了,政府哪年能给你补贴?银行是你家开的?没钱你大黑天跑来干啥,看我孤老婆子想抢劫吗?”
赵武哆嗦了一下:“我可没那个意思,你不能冤枉好人,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我开的小四轮,天黑也不怨我,我要是不来,晚上你不把电话打爆了!”
张老太婆翻着账本,牢骚话叭叭像打机关枪,射得赵武身心处处滴血,千疮百孔。从小到大他何曾受这等鸟气,他猛然想到了十三团自杀的两口子。妈的,不就是个死吗?看着老太婆连连翻着账本,嘴里还在滔滔不绝射着子弹,他上前一步,把老太婆扒拉到一边,刺啦一声,把自己的那张欠条撕下来,三两下撕得粉碎。他把碎片装进口袋,掰掉老太婆抓胳膊的老手,向门外走去。老太婆忽然大喊起来:“快来人啊,抢劫啦!杀人啦!……”
跑出门的赵武慌忙进屋,紧张地去捂老太婆的嘴。老太婆抓住赵武的胳膊,喊起来:“快来人啊,杀人啦,抢劫啦,救命啊!”
赵武顺手举起了小四轮摇把子,向老太婆头上敲了一下。老太婆应声闭嘴,连气也没了。赵武的摇把子哐当砸在地板上,稳稳地躺在那儿。赵武呢,鬼知道他此刻想些什么。
事情不可思议地发生了,信不信由你,我其实也不相信。听完事情的发生经过我很惋惜,身为作家,我想我有义务记录下来,警醒自己不要冲动。
回家的路
从什么时候开始刮起了小旋风呢?
他们背着我,操着不同地方的方言,神秘兮兮。我有意无意向那团声音靠近,一近那团声音就消失不见。
沙子真烫,后背已经被炙热的阳光烤得掉了几层皮,同伴们都闪着酱油脸,不停地低头喝水。这是我到白湖农场的第十五年,熬完这个冬季,我就能回家了。
十五年前,我到云南买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妻子。我买妻子纯属赌气。
那时候都流行认干爹的,父亲也给我认了一个。干爹的堂妹翠翠长得很美,有两条长长的大辫子。人家双眼皮是两层,她是三层,看起来就更加幽深、水汪汪。我们同时爱上了对方。晚上在青蛙的喊声里我们沿着淝河散步。白天我干完干爹家的活还要给她家干活。我们的亲密相处遭到了翠翠母亲的强烈反对,说我们道德败坏,乱伦,还说是干爹惹的祸。以后,我只能晚上偷偷到干爹家坐坐,就这样也被翠翠的母亲堵在屋里劈头盖脸骂一顿。我给干爹磕头告别,再没去过他家,也没见过翠翠。
回头再说我那云南的妻子,自从来到白湖农场,我就觉得自己傻了,说啥都颠倒,这次我一定说清楚了。我那云南的妻子,白白胖胖,一根粗大的辫子垂到屁股后头,走起路一甩一甩的。我故意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没事的时候我带着她在翠翠家村头的路上走。走着走着,就没了意思。我那白胖的妻子给我生了个白胖的小子。我还没做好当爹的准备,这小子就急不可耐地来了。
村里年年发大水,收点粮食糊不住我们仨的嘴。妻子又不放我出去打工,她说人生地不熟的如果我不在家她没靠头。总不能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吧。她指点我,可以到别人家抓鸡回来吃,我去了。她又指点我,可以到别人家牵羊,我去了。她又指点我,可以到别人家牵头牛,我又去了。
直到翠翠给人贩子拐跑,我才清醒过来,卖了羊、卖了牛,踏上寻找翠翠的旅途。历尽千辛万苦我找到了人贩子的老巢,我来得太晚了,翠翠已经大腹便便,因为翠翠太漂亮,人贩子不舍得卖留着当了老婆。我让她跟我回家,她流着泪不肯,说她走到了这步没脸回去。我说你还爱我吗,爱我就跟我回。她说我们已经不是从前,你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为了你的儿子。我说那都是因为你我才买的老婆,他们不算数,我心中只有你。
我们跑到一个十字路口,好不容易谈好一辆车送我们到车站,人贩子带了几个人拦住了我们。我满腔愤怒,正恨找不到他,他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我,不是找死吗?我身手矫健,手握尖刀。这刀是我来时特意打造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人贩子的。战斗的结果是五个人受伤,人贩子终生瘫痪,我坐了牢。
来到白湖农场的第二年,我那白胖的妻子丢下我那白胖的小子回云南了。我不怨她,真的,我对不起她,没有给她稳当的日子过。
翠翠生完孩子住到了我家,带着两个孩子过。我想她,想她日子过得一定艰难,幸亏我有个弟弟可以照应着点。我努力改造、努力干活、努力表现,争取早日回家,回到她的身边。
白湖农场身处沙漠腹地,被一望无际的黄沙包围,谁也别想逃出去。我们在这里栽草、植树、种菜、种庄稼,经过几代劳改犯的汗水终于造出一片绿洲。
那小旋风还在刮着,像一团迷雾。
直到那天,他们打死了狱警,搶到了那辆运输车,我才反应过来,他们要逃跑!我拾起狱警的枪,打爆了运输车后边的一个轮胎。我在后面追,大声吼,谁也不许跑,你们跑不出去的!带头的那个无期劳改犯一阵子弹射向我,我看着运输车远去,听到警笛鸣响。
队长喊:醒醒,醒醒,521,醒醒!一直忘了介绍,我的代号521。
我很清醒地对队长说:我要回家,家里有翠翠等我,还有我的两个孩子。
队长说:这就送你回去,你别睡啊,千万千万别睡啊!
我轻飘飘地,急不可耐地上路了。
看,那荒原
从艾其沟泥火山群出来西行约三十公里,有疏离的土墙散落在辽阔的戈壁滩上,那儿灌木茂盛,一看就是适宜庄稼生长的好地方。
时间倒退一个世纪,姑且这样吧,剩下的十年就不提了。还是这片戈壁滩,从安徽来的一群人,在一位老者的带领下开荒种地,修筑了很多灌溉渠,挖了很多地窝子,讨生活。
他们渐渐有了骆驼,有了马匹,有了羊群,有了春暖夏凉的土坯房,更有了大片的土地。
牧羊犬狂吠,把屋子里休息的人都叫了出来。大家三三两两从相距很远的房子出来,看到他们的地头出现了一群人,如当年他们的模样。亲人呐,老者拄着红柳拐棍,颤颤巍巍迎了上去。
这群人住了下来。老者让年轻人帮他们挖地窝子,让他们开剩下的土地,吃自家的玉米,喝自家奶茶。冬季的雪说来就来了。安徽人已经在硫磺沟找到了随处可见的煤,用骆驼一趟一趟运回来。新来的住户,借了骆驼,驮了几趟嫌路途遥远人遭罪就不运煤了。他们砍伐红柳在地窝子里慢慢熬冬。
有人丢了煤,有人丢了羊,有人的闺女眼看肚子大了,不知道是谁的。安徽人全聚到了老者家中。
大家七嘴八舌发泄对那些人的怨气,说戈壁滩上那么多野兔,自己不去套野兔,偷我们家一只老母羊,那只羊看起来最肥,是快要下崽了啊!我在地窝北面发现他们吃剩的骨头,流的眼泪都冻成冰坨子我吭声没?还有人说,荒原上还有很多的野驴、马鹿、黄羊,他们年轻力壮也可以跟我们一样,逮了拿到乌苏县城换点生活用度,也不用向我们吃一口要一口。我们那时还不是依赖县城里那些商户活下来的!
老者沉静地听完大家的牢骚,说人活在世孰能无过,不管怎样都要给人家留条活路。咱们再帮助他们一冬,明年开春看他们的打算,如果他们再这样好吃懒做,咱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找活路去。
说着说着小草就呼啦啦冒出来,雪水欢快地唱起来,雪狐退了毛,狼休闲地散步,春天来了。安徽人开始磨刀收拾农具,给马刷毛,给牛加料,准备春耕了。多美的春天啊,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连空气都透着希望。
那一夜,熟睡中的乌苏人突然惊醒了,旷野里传来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咒骂声、救命声。摊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惊醒的人只能静静地听着,没人敢起来看个究竟。
第二天,在乌苏县城做生意的商户惦念着那帮安徽人,就骑马去探望。哪知道远远地看到血淋淋的尸体,那帮新来的住户正清理尸体呢。
第二夜,旷野里又传来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咒骂声、救命声。从此旷野里没有一个活口,尸体遍布,也没有人去掩埋。一到夜里,遥远的乌苏人总能听到厮杀声,哭叫声随风而来。
时间前进到“文化大革命”吧。我爷爷被人抓起来。有人说那帮新来的住户是我爷爷联合了一群勇士,夜里去灭了的。事后,他们还在乌苏县城做着各种营生。没有人知道他们曾杀过人,杀的还是那么多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处理我爷爷事情的人,调查了整个县城,没人证明那件事是我爷爷干的。爷爷老得不能动的时候,我问起了那帮土匪的事。爷爷伸出颤抖的手说,那晚我们就没想着能回来,我们平时就杀鸡的胆儿,大伙怕那些土匪吃壮了进城杀人。他们能杀他们的恩人,也会杀害我们。孩子,人活着,总有一些事是迫不得已。
每当路过那片荒野,我总能隔着时空隧道,听到厮杀声。我爷爷是英雄,他活在我的心中。虽然他已经成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挂在我家的墙上。
沙漠神鸟
吉瑞在塔克拉玛干追踪贪狼已经整整二十天了。
贪狼是白湖农场的重刑犯,二十天前徒步穿越沙漠潜逃。吉瑞和队长开着车追了三天。细细的沙子起舞后,他们还没来得及找个地方停车,就被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袭击了。风平浪静以后,车里的燃油也已耗尽。队长把所有的水和干粮都给了吉瑞,还有一把手枪,让吉瑞继续往前走追踪贪狼,他往回走搬救兵。
沙尘暴改变了沙漠原有的地形,白天吉瑞根据太阳的方位确定位置。昼夜温差大,除了身上穿的警服,没有御寒的衣服。水在两天前就剩一小瓶,渴的时候吉瑞就润润干裂的嘴唇。干粮五天前就没有了,空旷的沙漠里只有他一个人拄着一根骆驼腿骨蹒跚地走着。这根骆驼腿骨是吉瑞两天前捡到的,他曾搜遍了骆驼骨头,希望能找到一点骨髓或者一点干肉。
吉瑞在十年前成功追踪过一个企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重刑犯。追到的时候,那人已经变成了干尸。
一丝风也没有,气温升到了摄氏五十多度。骄阳炙烤沙漠,热浪也灼伤了吉瑞干渴的肌肤。他艰难地翻过沙丘,在背阴处缓缓躺下,干涩的眼睛用了很久才合上。两天没排尿了,再找不到水源和食物,自己也就成一具干尸了。吉瑞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了,他想,队长可能走错路了。沙漠里原本就没有路,他的思绪缥缈起来。
“滴、滴、滴、滴”,一阵鸟叫声唤回了吉瑞的意识。他动动手,还活着,眼睛干裂得睁不开。他缓缓地掏出那瓶水,喝了一口,又喝了半口,没有咽下去,他用手沾点水,湿了湿眼睛,睁开眼。一只褐色的、尾部是白色的鸟正在他耳边叫着。鸟用弯弯的、钩样的喙啄了一下吉瑞干瘦的脚面。吉瑞幸福地呻吟了一声,他知道自己有救了,鸟叫就预示着离水源不远了。那只鸟是号称沙漠精灵的塔里木神鸟,这是沙漠居民赋予的美好称谓,它的学名叫白尾地鸦。吉瑞又喝了一口水,那只白尾地鸦叫着飞了几步,灵巧地回头瞅了一眼吉瑞,翻过沙丘不见了。
吉瑞翻过沙丘,惊讶地发现一片红柳在沙漠里静静地矗立。这片红柳绵延着伸向远方,他坐着滑下了沙丘,来到红柳下,伸手摘了一片红柳叶。吉瑞冻醒时,已是深夜,繁星深情地眨着眼睛。他在满天繁星中找到北斗七星,确定了方向。黎明时,他看见一个人影,赶紧匍匐下来。那人的囚服已经破烂不堪,白色的镶边还是那么醒目。
吉瑞掏出手枪,借着红柳的掩护悄悄追过去。贪狼忽然蹲在红柳后,一动不动。难道被发现了?吉瑞赶紧也蹲下身子。贪狼没有回头,目光盯住前方。神鸟正在扒一处沙子,等沙子扒出一堆后,贪狼一声叫吓飞神鸟,连滚带爬地过去,从沙子里拿起一只干瘪的虫子塞进嘴里。吉瑞明白了,贪狼一直靠吃神鸟埋藏的食物维持生命。吉瑞趁贪狼全神贯注吃食物的当口,悄悄摸到贪狼后面,用手枪对着贪狼:“827,举起手来!”
贪狼哆嗦了一下,举起了双手,一只虫子还捏在手里。吉瑞用了一秒钟反应过来,贪狼的手举起来了,他没有带手铐,连绳子也没有。贪狼用了两秒钟回过神来,把虫子送进嘴里:“省省吧,管教,能活着出去就是造化了,你要是有本事把我送回白湖农场,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吉瑞无力地瘫坐下去,刚才的精神紧张耗去了他所有的精力。
“我俩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蚱蜢,先保命要紧。”贪狼说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回到紅柳树下,他靠在树上问,“喂,有尿没?给点尿喝喝也行。”
吉瑞走到另一棵红柳下坐了下来,头上的神鸟还在“滴滴滴”叫个不停:“不能停下,我们得站起来走,走就有希望,停下只有等死!”
“你用枪打下那只鸟,我们就有救了。”
“打死你也不能打死神鸟,这是沙漠里的精灵,是濒危物种,我们保护还来不及!”
“死到临头还爱护鸟,你该好好爱护一下自己。”
“废话少说,走!”吉瑞用枪对着贪狼!
“兄弟,省省吧,省下那颗子弹打鸟吧,只要你留着命把我带出沙漠,或者跟我说说话也行。”贪狼呜咽了几声,停了下来,“他妈的,我连哭都没劲了,这么久见到一个人,还是拿枪抓我的。”
贪狼走在前面,吉瑞举着枪跟在后头。走到第三天,贪狼突然回头,跪着对吉瑞说:“管教,前面又是荒漠了,求求你,让我在这儿自生自灭吧!”
吉瑞这几天吃的红柳叶不消化,腹胀难忍,滴水未进,迈一步浑身干辣辣地疼,好像皮肤随时要爆开。
一声微弱的“滴滴”声传入耳朵。身后的红柳后面,有一窝小鸟,正惊恐地挤成一团。贪狼爬了过去,眼睛冒着绿光。
“站住,不许你打神鸟的主意!”贪狼无视吉瑞的威胁,爬到鸟窝前,抓住一只小鸟扯下长了绒毛的翅膀。吉瑞举起枪,却无力扣动扳机,软软倒了下去。
吉瑞是被贪狼用枪托砸醒的。吉瑞看到贪狼脸上、嘴上有干结的血,胃里一阵痉挛,“哇”一声,那些没消化的树叶一股脑喷了出来。
“你善心,我让你善心,我好不容易逃出农场,你竟然一路追了过来。你去死吧,我要喝你的血、食你的肉。”
突然贪狼发出一声惨叫,一只神鸟啄了贪狼的眼睛,贪狼举起枪胡乱射。另一只神鸟啄向了贪狼的另一只眼睛。吉瑞的意识再次模糊。
吉瑞醒来时,雨丝飘在他的脸上,队长笑眯眯地说:“听到枪声我们就赶了过来……”
红柳枝上一只神鸟正滴滴叫着。吉瑞问队长要了几瓶水和一个饭盒,放在树下:“真是沙漠的神鸟啊,竟然能分得清好人坏人。”
“滴、滴、滴、滴……”神鸟飞到瓶子边,好奇地看着装满水的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