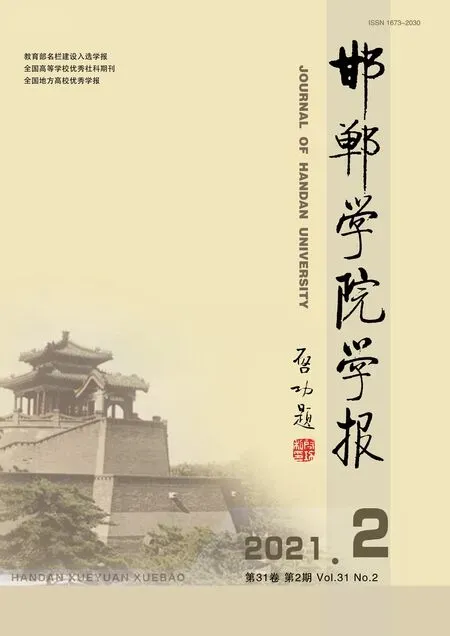民国时期太行山地区的家产纠纷及解决之道——以山西苏家堡王氏家产纠纷案为例
刘晨虹,李楠
民国时期太行山地区的家产纠纷及解决之道——以山西苏家堡王氏家产纠纷案为例
刘晨虹,李楠
(邯郸学院 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 邯郸 056005)
太行山文书中藏有20余件山西文水县苏家堡村王姓家族内部争夺家产的文书,记载了该家族百年间分家析产的情况。从道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家族经历了多次分家,均立有分家文书。民国年间,王姓家族面对家产纠纷,诉之于法院,表明民国时期的太行山地区,村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但无论是民间调解还是法院审判,订立契约依然是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方式。
民国;太行山区;家产纠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诸多的专家学者关注、投身领此项领域的研究,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层出不穷。但与其它地区的区域史研究相比,在研究视角、理论以及民间文献的整理与运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邯郸学院近年来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区搜集了一批民间文献(即太行山文书),这批文书时间上起明朝万历年间,下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前夕,总量达20万余件。由于这批文献是太行山区百姓生活的原始记录,它不仅丰富了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史料,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本文就是在充分利用文书整理过程中所发现的20余件山西文水县苏家堡村王姓家族内部争夺一处家产的文书,重点考察在社会动荡以及政权更替的时代背景下,太行山区的普通百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解决纷争,保护自己的权益。
一、关于王氏家产纠纷案①该批文书发现于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第二箱第52包,编号为HTX02B520001——HTX02B520019。的情况介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作为一种同居共财的社会组织,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未来的发展状况。因而财产权问题必然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财产的争夺成为家庭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此类经济纠纷易发生在分家析产、户绝财产的处理、寡妇再嫁等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
本文所关注的山西苏家堡王姓家族的纠纷案起源于寡妇王韩氏死后留下的一份地产,案件的起因是民国七年王元正、民国年间王广立先后向法院控告王广发强霸王韩氏留下的户产。关于这场纠纷案件的审理至少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而关于这份户绝财产的处置却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为叙述案情便利,现将王姓家族中与本案有关的人物关系梳理如下:

①廷珮无子,廷璋有三子:树宽、树奎、树坦。目前发现了三份王氏家谱,其中两份记载廷珮过继树奎为子,一份记载廷珮过继树宽为子。由于没有其他佐证资料,无法断定究竟是树宽还是树奎过继给了廷珮。
争议家产示意图:

牛房院新院 场基舍基
据此人物关系图,这场纠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长房(吉有)的王广发、王广端兄弟和二房(吉功)的王元正、王广立,争夺的焦点是牛房院西一半、场基西一半以及新院外舍基上的茅厕。
先来看一下这长达十几年的诉讼过程,这场关于家产的纠纷案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国七年王元正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牛房院西一半、场基西一半以及新院门外舍基上的茅厕为该股(次子吉功一房)家产,与王广发无关,王广发系强霸户产。王元正向法院提交自己的契约证据。
作为被告的王广发一方面向法院揭发王元正等人提供的契约为伪造契约,另一方面提供了自家自道光至民国以来的历次分家分单,以此证明自己是通过合法合理的家产继承得到这处家产。
法院在听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之时,派警员到苏家堡村进行实地走访:
“缘苏家堡王元正等呈诉王广发强霸户产等情一案,蒙恩堂讥饬警调查等因,警奉谕速往该村协同村老苏昇霄踩勘验得:该村有东西大街到一条,路北王家巷有王广发舍基四方一块。按王广发取执分单,西一半系王韩氏分到之业,按王广文等取执典契系王树坦出典西一半。验得西北角王广发修盖场棚三间,东邻王元惠,西邻苏培仁,南邻苏昇雲、王元明,北邻护村大堰。警诚恐误公,只得将踩勘缘由据实禀覆伏乞。 上裁施行 四月十二裁禀”。②HTX02B520014(1)警员调查苏家堡王元正等诉王广发强霸户产案禀帖。
据此禀文可知,警员在苏家堡村村长苏昇霄的协助下,验得牛房院与场基西一半现为王广文所有,查其契文,系由王树坦出典。与王广发所执分家文书内容可两相映证,可证明此产业为王广发一房的家产。此案经过了地法院与高法院的两级审判,均判定该舍基归王广发,与王元正一支无关。
第二阶段:王广立、王元正等再次向法院提起王广发、王广端强霸户产的控诉③根据对文书内容的分析,此次诉讼时间应该是在民国十七年后。。在这次诉讼案件中,王广立再次声明所争之基为其股内财产。对此被告王广发、王广端兄弟反驳道:“同治十年间民股内王治平等分家,伊股内王晋燂为办事人,如伊所争之基是伊之基,而民股内两次分家,该股内王树根、王晋燂焉能为民股作办事人耶,此可知孰真孰假矣。然彼面私造伪据,于民国七年有诉头王元正(即伊母此次状语添传之家长是也)因场基与民涉诉在县未洁,乃蒙地法院并蒙高法院验明伊属伪据,判决与伊股无干。有卷存县,乞吊阅目,实为铁案如山。今伊又欲争狡非将地法院高法院之两判决推翻不能发生效力,更能证明民家分单是真。民国十年民家将分到之地卖与树梅堂(树梅堂是彼时村长苏昇霄家之堂名)十亩,当经村囗囗囗地之下,即将民家同治十年分单批照,即係按分单承买,以上上同法院下同囗囗囗早已证明,毫无动摇之余地。今伊又欲争基,显係决人行路。至区长调查囗囗囗是不知法院判决,是以难明真相。兹蒙批令质诉,只得据实陈明。伏乞囗囗恩准吊阅前卷,依法判决,以儆囗囗。否则伊如此履次诉害,则民囗囗万难承顶门户矣,叩乞施行。”④HTX02B520017阴历6月17日苏家堡王广发诉王广立私造伪据案状纸及判决。
王广发兄弟就契约的真伪提出了两点证据:其一,若所争诉的家产确为王广立一股所有,则其股内王晋燂、王树根等人则不会作为王治平等人分家时的中人。其二,在民国七年法院的判决中,地法院与高法院均已认定了他对此争诉产业的合法占有。同时在这篇质诉的文书中,王广发强烈的表达了对王元正等人无休止的争夺家产的愤怒与无奈。此次审判最终以王广发的胜诉而结案。
从法院的两次判案结果和争议家产的最终处理结果可以推定:这是一起恶意争夺户绝财产的家产纠纷事件。根据王广发本人的供述以及王姓家族的分家文书,事情实质上是:牛房院、场基、舍基全属于吉有一房的财产。道光二十五年分家时,牛房院与场基一分为二,王树坦与王韩氏两家东西各占一半;舍基地由王树坦、王韩氏、王治中三家共同拥有。此次分家后不久王韩氏去世,由于无子继承,其名下产业——牛房院西一半、场基西一半成为户绝财产,转授予侄子王治平、王治祥、王治生,牛房院与场基成为王树坦一门的产业。同治年间王治平兄弟三人分家时,牛房院与舍基不忍分割,由三家共同使用;舍基地与王治和四股共伙。之后由于男丁稀少,只王治平膝下有孙王广发、王广端,故而牛房院与场基⑤由于年代久远,牛房院倒塌,与场基上下相连成为一块平地。传至王广发兄弟二人名下。民国十七年王广发兄弟二人分家时,规定牛房院与场基由两家共同使用;舍基地按老分单规定与王治和共伙。1957年由于土改政策的原因,王广泰(王治和之孙)按老门一股继承舍基地北边,王广发、王广端按老门三股继承舍基南边。至此,关于牛房院、场基以及舍基的家产分割暂告一段落。如此看来,关于牛房院、场基和舍基的的继承是无可争议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分家制度,可能由于这份家产的特殊性,也可能是王元正等人眼红这份家产,从而引起了长时间的纠纷。
“所谓的家产分割即分家,是在某个时点在大小不漏地计量现存的家的资产并一块儿分掉的同时,以切断朝着将来的收入消费的共同计算关系并一块儿分掉的同时,以切断朝着将来的收入消费的共同计算关系为内容的法律行为。”[1]92虽然分家析产制度在中国延续上千年,制度上也比较完善,然而自古财利面前是非多,“因诸子均分的家产分割制度,家庭财产不断地化整为零,一个个孤立的家庭必须设法在此条件下维持家计或尽力争取上升。”[2]140对于谋求生存和繁荣的一个个小家庭来说,发展的基础在于家产。而在分家析产的活动中,各个小家庭暂时性的形成了一个拥有不同利益主张和利益冲突的竞争社会,达成利益上平衡并维护每个家庭的既得利益,成为它的必然要求。
二、契约与“确权行动”
正如滋贺秀三先生所言,私法理念在中国是一个空白,各式各样的民间纠纷要完全依靠国家权力加以解决,完全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此类“细故”产生于民间,解决于民间。在民间社会存在着一种事实以及支撑该事实的理论或思想,契约文书的出现只是这一事实的外在表现,成为避免纠纷、保障自身权利的一种手段。契约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早,它伴随着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它所具有的“证”的作用也深入百姓心中。汉代开始民间社会便有“民有私约如律令”,“官又政法,民从私约”。即便是在山西苏家堡这么一个小村庄,村民对契约的重视程度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尽可能长期的同居共财是一种在道德上受到称颂的事件,但在生活中它总是被各种现实阻止,每一个家庭必然要经历分家。在太行山区以及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分家时一定会邀请几位家族中或村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作为中间人,在他们的主持调解下对家产进行分割,并将分割结果写成文字——分家文书,每人保存一份。“中国人在完成重要的法律行为时,为了确定行为的成立及其内容、杜绝日后的纷争而采用的手段,经常是第三者的见证和文书的制作这两种,家产分割也不例外。”[1]95分家析产的过程也是每个人对家产的所有权的确定过程,而分家文书之类的契约文书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给予记录。
在这场旷日持久,跨越三个政权的分家行为中,分家文书等契约的频繁出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契约作为约束双方行为、保障自身权益的一种古老的、传统的势力根植于民间社会,即便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替的时代,也不影响它的地位和作用。所见王姓家族最早的文书为道光二十五年,最晚为1957年,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无论在哪一政权统治下,涉及利益的民事活动都立有契约文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契约游离于政权之外,根植于民间社会自有的一套逻辑之内。第二、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对于村民而言,一份契约意味着一份保障。在纠纷案件中,作为原告的王元正、王广立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的证据就是手里所掌握的契约文书,虽然这些文书被查出是伪造。而作为被告的王广发进行反驳的依据也是自己所保存的历代分家文书,正是这些契约文书的存在才保护了王广发的合法权益。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民国七年王元正向法院控告王广发强霸户产,而就在这年八月王广发为其名下的田产补办契约。他本人宣称原红契丢失,在村长、四邻以及他所出示的分家文书的证明下,官府为其补办了正式的官契。田房契约是田房所有权或使用收益权的一种公证,契约持有人对契约文书的保护极为重视,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免出现契约丢失的现象,契约丢失会对业主的权属主张不利,为保障自身权利,业主按法定法定程序到相关部门办理新的契约,称之为补契。虽然有分家文书,但是正式在官府备案,办理正式的田房契约意义更大。第三、民间契约在法院审判时作为证据出现。纠纷案件发生在民国年间,而被告王广发提供的证明材料是道光以及同治年间的分书,法院在经过实际调查确认了文书的真实性之后,认可了这些证据。虽然年代久远,政权更替,契约文书的法律效力却没有受到影响。第四、“契约精神”根植于立契人的内心。现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数量如此巨大的契约原件,这一现象就说明乡村社会存在着“契约精神”。这一精神在王氏家族的分家行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道光二十五年的分单中规定了新院外的舍基由王树坦、王治安、王治和三家共同拥有,在之后的历次分家中都尊照此项规定,在分书中注明。到1957年由于土改政策的原因,需要对此舍基分割,依然按照道光年间分书的规定:王广泰(王治和之孙)分得舍基北边;王广发、王广立分得舍基南边。虽然时间跨度较大,家族中各房人口也屡有变动,但是家族中的子孙依然遵守分家文书的规定。
三、法院与家产保护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以无诉为德行,以争诉为耻辱。针对民间社会的纠纷,人们倾向于寻找第三方势力进行调节,即便纠纷到了官府,官府的判决也带有强烈的调节色彩。清朝末年,政局变动,西方势力的入侵,使中国传统的法律也产生了变化:放弃祖宗家法,开始法律的西方化与近代化。同时人们的法律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改变。
这场纠纷案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而就政策而言,旧政策逐渐被废弃,新的政策还未完全形成。民国的法律也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在这起家产纠纷案中,可以看出:第一、法院注重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注重调查取证。如上文所述,在案件的第一次审理过程中,法院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之后,派警员到苏家堡村进行实地走访勘验,验明契约真伪;在案件的第二次审理过程中,要求王广发针对王广立的控诉必须提出质诉。第二、法院审理案件有严格的程序,当事人若对本级法院的审判结果不服可向上一级法院上诉。本案就经过了地法院与高法院的两级审判。同时对于调阅卷宗等请求均有相关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第三、正如滋贺秀三教授指出清代的审判缺乏“确定力”或“既判力”一样,民国时期法院的审判,至少关于这场家产纠纷案的审理,也表现出同样的弱点。在案件的第一次审判中,就经过了地法院与高法院的两级审判后才最终定案。尽管已经结案,将家产判与王广发,但事隔几年之后,当事的另一方再次提起诉讼,审判机关就又会再进行一次审理。正如本案中王广发所言“伏乞囗囗恩准吊阅前卷,依法判决,以儆囗囗。否则伊如此履次诉害,则民囗囗万难承顶门户矣,叩乞施行”,深深的表露出一个普通村民对此的不满与无奈。从中也可看出民国时期司法制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第四、人们法律思想的转变。“古代中国人为了寻求指导和认可,通常是求助于这种法律之外的团体和程序,而不可求助正式的司法制度本身。”[3]9然而本文中王姓家族的这场家产争夺选择走司法程序。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对于这一起因贪图家产而发生的纠纷,是无法通过双方的和解,乡里权威人物的参与和中间人的见证来解决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要求法院依法判决,法官也要遵循法定规范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这与传统社会中官府带有浓重的调解色彩的审判有了截然不同。当然,我们对此也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四、结语
分家析产是中国家庭的代际更替方式,也是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它将一个原生家庭分为若干新生家庭,财产是新生家庭发展的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有上升之家,有没落之家,这些小家庭就组成了一个个利益冲突的竞争社会。
从道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王树坦一房经历了多次分家,遵照中国传统的诸子均分制度,在中人的见证下,立下文书,载明个人所分财产及相应的义务,分书若干份,兄弟每人各执一份。分书载明各房所分之产,确定各人的家产所有权,既是划清界限,也是保障个人的权益,避免日后家产纠纷。就分书所起的作用而言,这是一种保守的避免纠纷的方式。因为契约作用的发挥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强有力的支柱,“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愿意服从契约内在的确定性规范时,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契约关系才可能在社会里生根”。[4]309
现实生活中关于家产的纠纷时有发生,传统中国社会崇尚息诉,家族、乡保长等第三方势力的调解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民国时期近代权力观念深入人心,太行地区出现了诉之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村民采取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民间调解还是法院审判,它的依据依然是村民手中的契约文书。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太行地区,虽然解决家庭纠纷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实质没有改变。
[1]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M]//王亚新,梁治平.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4]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M]//王亚新,梁治平.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G275.2
A
1673-2030(2021)02-0038-05
2021-02-05
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太行山民事纠纷文书与近代太行山区民间解纷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B17LS005)
刘晨虹(1986—),女,河北邯郸人,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太行山文书、历史地理学研究;李楠(1986—),女,河北邯郸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太行山文书研究。
(责任编辑:刘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