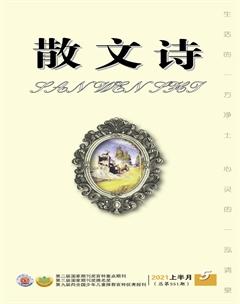变奏
王彦明
橘
淮南淮北,河东河西,是从吐蕊看出果实,从寂静中透出喧嚣,还是就这样从地球抵达月亮,从青春触摸到暮年?痕迹似乎隐藏在龟甲、筮草、掌纹、面相和某一个笔画中,秘密似乎正在暴露。这由内而外的小东西,包裹着水流、酸和甜,不曾消失的是猜疑和嫌隙,即使是一层层剥落皮肤,露出筋骨,以赤诚的爱,来表露心迹的时候,也不曾消去历史结构下的污垢。历史在搭建一排篱笆后,就不会让后来的人轻易拆除。其实,它又何曾在意?酸与甜,本身都是一种生命的魅惑;而处所,并不等同于基因。
源 头
这水从何而来?天上,人间,还是一蓑烟雨之中?那背着琴的先生,他的木偶仍在线的交织和乐音的密网中舞蹈;那山间的野马和尘埃,都被庄子放进梦境,像彼此的对视与辖制。一面镜子和一个鸟笼,都有依稀的幻境,我们仿佛看到流淌和动荡,新雪与落叶,伤口与疤痕。林冲从野猪林抵达沧州,孙悟空从石头内孕育而生,贾宝玉此時正剃发归去……这淘尽英雄的浪花,和逝者如斯夫的远去之泪,从来都是循环,都是从生到死,从有到无,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温暖的子宫到永恒的归宿。而春,从蕊开启。
打火机
他并不吸烟,打火机揣在兜里。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是否还能擦亮火花?他借助日光、星光、月光、灯光、目光……将视线拉向某种沉默的期许。偶尔,他觉得他人也是光,花朵也是光,铁也释放光,妻子和孩子在瓢盆之间散发着光……那么,就不必急于点燃——童年时,他贪食一颗栗子,而被火灼伤,从此,火就在内心悄悄地烧。那明明灭灭的火焰,都贮存在黑暗的匣子里,那么暗,那么黑,那么生硬。而火石,完整如初。
喧 嚣
就是那种嘈杂和傲慢,引起的孤独与消耗,从春延至冬,甚至还在不断地循环:兑入更浓的墨,使得简单的画卷,几乎不留余地,月光由此无法漫漶,流水也只能绕道而行,只能在模糊中寻找清晰——那种持久和永恒的唯一,穿过夜色和邻人,它只投入你一个人的襟怀。所谓的遗弃,或者忽视,都上升为一种孤绝的升腾,那引颈高歌的天鹅,和静立于鸡群的鹤,摩挲着你的脸颊,散发柔和的光芒。似乎又攻占了一座旧堡垒,向着远处递进,触摸的手所到之处,都擦亮了灯盏,像挑开了帷幕,交给我们爱和温暖。以至于你开始正视孤独、花朵、流水和远山。
未曾睁开的眼睛
就这样,永远地闭下去了——像从漩涡中消失,像陷入永恒的黑洞。而光似乎存在着,就那样被隔绝在外;而不曾触碰的目光,就是不存在的世界。仅有流逝,还有更加遥远的梦,仿佛清晰,又仿佛黯淡,那些深夜的鼠啼,还有轻声的呼唤,在踢踢踏踏的节奏中,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就是那一层小小的隔膜,我就无法把我的山川、河流、光芒和无尽的爱意,馈赠给你,只能在谛听中,告知花开花落——我体内的桃花啊,它向着你,探了探枝条。
黑 点
有人说,那是生发于一支笔的错误,那么的不经意,仅仅是放置的疏忽,就在白纸上留下了淡痕,又一直在手和衣袖的摩擦中,向周边洇开,越发显得模糊起来。像出生,也像消失。还有人发现了素描的秘密,仿佛就是一只蚂蚁靠近了面包屑,那是轻微的水痕吗?抑或蚂蚁的唾液、滴落的泪珠儿?似乎还有可能是尘埃,飘散而下,跌倒着,翻滚着,战栗在风中,它已经脱离了颜色和空间的限制,成为流水中的漂泊物;它可能曾停泊在一位皇帝的头顶,或者鸟雀的窝巢,当然,还可能从菩萨的净瓶上滑下,只是现在,它正在变淡。只有奄奄一息的粒子,还有内在的冲突,还活在宇宙间。
回形针
我们当然可以衔接琐碎、凌乱,甚至可以在双循环的结构中寻找秩序。那些交替而来的平静,潜藏了野草和深深的悲哀;那屈曲的方向,对接了永恒和限制。就像是一座小小的寺庙,那金属菩萨,滴下甘露,好似泪水;抚摸人间,就像摸到马的鬃毛。当然,它不是一座楼宇,也换不回我们的倾慕,就是那不经意的消失,也不会惊起波澜,也只是替换。虽然可以进入链条的内部,和群体搭建营垒与星空,但像汇入大海的一滴,只能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生锈,唱起低声的挽歌。那么多融化了的铁屑,进入了你的内部,经受炙烤和挤压,才有了一个完整的轮廓。
听风者
当然是走在琴键上,那踮起的脚尖,小心地移动着。从最细微的鼠啼,到牛羊回圈,还有吸附一切的引力,被逐一按下。树枝在摇曳,风筝脱线,河面上波纹推向了远方,两个人背风而行。似乎还在孕育着最强音,在那低处缓缓摩挲,是叶片的碰撞,是塑料袋飞上了天空,是毛驴磨蹭着墙壁……这奋力的上昂击打在玻璃上,忽然就终止了一切声响——然后就是声音的狂欢,山石崩塌,火车紧急刹车,孤独的猿猴一声长啸,骏马奔腾,军队夺取了战阵,腰鼓齐鸣……它裹挟着世界提前进入黑夜。两个人还没有回到家,一个家都在黑暗中。孩子无法控制琴键,只能和影子相拥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