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也有两面性
唐代彬 严秀芳
专家介绍
唐代彬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内科急症及内科疑难疾病的诊治,在心肺复苏、中毒的救治、危重患者的综合救治及批量伤员救治的组织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专家介绍
严秀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主任护师,全国高等医学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儿科护理》副主编,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儿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对急危重症及儿童疾病的护理、护理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经验。
流感、艾滋病、流行性腮腺炎、风疹、麻疹、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病毒性肝炎,以及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肺炎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疾病。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便是由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与其他致病微生物相比,病毒给人类造成的伤害的确更加凶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谈病毒而色变。其实,病毒除了会致病外,并非“十恶不赦”,它同样有对人类有益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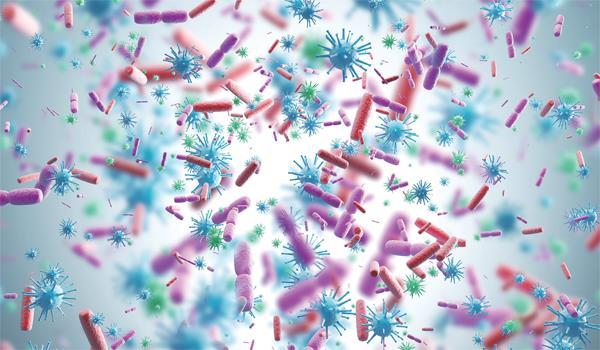
病毒:没有细胞结构的最低级生命体
病毒是一类体积极其微小、没有细胞结构的最低级生命体。病毒的大小是以纳米计量的,其体积只有细菌的1‰~1%,人们必须通过电子显微镜将病毒放大上万倍或数十万倍,才能看到它们。
病毒的基本化学组成成分是核酸和蛋白质,绝大部分病毒通常由一种或几种蛋白质以及一种核酸组成。只有少数几种病毒仅仅以核酸形式存在,如类病毒。
病毒核酸是病毒的遗传物质,携带着病毒的全部遗传信息,是病毒遗传和感染的物质基础。一种病毒的病毒颗粒只含有一种核酸,可以是DNA或RNA,它们以单链、双链或环状多核苷酸组成。因为病毒的结构简单,没有细胞器,它靠自身无法完成“传宗接代”,如果病毒要完成繁殖,必须感染其他活细胞。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病毒可分为多种类型:根据遗传物质的不同,病毒可分为DNA病毒和RNA病毒两类,前者如单纯疱疹病毒,后者如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等。
根据其寄生的细胞不同,病毒还可分为动物病毒,这类病毒专门寄生在人和动物细胞里,如流感病毒;二是植物病毒,专门寄生在植物细胞里,如烟草花叶病毒;三是细菌病毒,专门寄生在细菌细胞内,也叫噬菌体,如大肠杆菌噬菌体。
根据病毒的形状,病毒也可分为多种类型,如球状病毒、杆状病毒、砖形病毒、冠状病毒、丝状病毒、链状病毒、蝌蚪形病毒、有包膜的球状病毒等。
病毒是如何致病的
病毒的致病能力与病毒的蛋白质衣壳有很大关系。衣壳可以保护病毒免受物理、化学因素的破坏。病毒依靠衣壳的特定成分与宿主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然后引起感染,例如新冠病毒就是通过其表面的S蛋白与人体细胞的ACE2蛋白结合,从而引发感染。
与人体组织的细胞发生膜融合后,病毒会被吞入细胞内,然后脱去衣壳,释放出病毒核酸。病毒依靠宿主细胞的酶成分进行生物合成并大量复制,装配后便形成新的个体,接着再释放出细胞并感染新的细胞。
病毒也是人类抵抗疾病的武器
尽管生命的起源让人匪夷所思,然而,病毒对人类社会的有益面早已为人们所利用,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疫苗的研发。在人类历史上,利用病毒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利用低毒性的牛痘病毒对付引起烈性传染病的天花病毒,人类通过接种牛痘疫苗最终消灭了天花。人们熟知的减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狂犬病疫苗等,依然被当作抗击相应传染病的有效工具。目前,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而接种的灭活病毒疫苗,也是人们对病毒的利用。
除了充当疫苗外,某些病毒还被人们用来对抗超级耐药菌的感染,这类病毒被称为噬菌体。噬菌体是感染细菌、真菌、藻类、放線菌或螺旋体等微生物的病毒总称,因部分能引起宿主菌的裂解,故被称为噬菌体。
噬菌体能够杀死细菌的现象,是1915年由英国微生物学家弗德里克· 特沃特(Frederick W.Twort)发现。1958年,我国著名医学家余贺利用噬菌体成功防治了铜绿假单胞菌对烧伤患者的感染,成为我国微生物学界的一段佳话。近年来,因超级耐药菌的产生,噬菌体因其有侵噬细菌的特性,又重新成为一项备受瞩目的“武器”。
随着基因工程及生物合成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利用“解除武装”的病毒搭载基因来治疗一些遗传性疾病。由于病毒能渗透到细胞内化学物质不宜抵达的地方,因此,病毒还可将毒素运抵肿瘤细胞生长的地方从而消灭癌症病灶。
目前主流的病毒载体系统主要包括慢病毒、逆转录病毒、腺病毒和腺相关病毒等。重组腺病毒载体系统是一种复制缺陷的腺病毒载体系统,在基因治疗、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等领域被广泛应用。目前我国研制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就是以腺病毒为载体,把腺病毒基因中的一部分基因替换成刺突糖蛋白基因,也叫S蛋白的基因,这个过程就是重组。
S蛋白是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关键蛋白,将S蛋白重组到腺病毒载体上,腺病毒也具有新冠病毒的特征,接种到机体后,免疫细胞会生产出专门针对新冠病毒S蛋白的抗体,并且保留一部分免疫细胞,就是记忆性免疫细胞。在新冠病毒真正入侵人体的时候,记忆性免疫细胞就会产生大量针对S蛋白的抗体,阻断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细胞,这样一来,新冠病毒就无法增殖,最终被人体的免疫细胞消灭。
病毒也有它的两面性,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它的有益性,并抑制、消除其有害性,这既是当今生物医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范雨舟 整理)(编辑 杨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