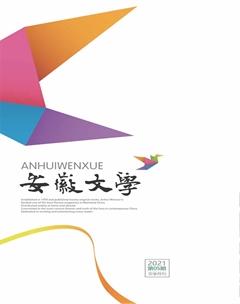“走遍”张爱玲
沈小兰

张爱玲的世界,于我,除了遥远还是遥远。
第一次读到她的小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上的《倾城之恋》。读时,很茫然,有点儿傻眼,久久回不过神来。可还是忍不住,读了一遍,再读一遍,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小说里的十里洋场,旧式大家庭,少爷小姐,还有上海和香港,离我都是远而又远。
很陌生。
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和张爱玲笔下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隔膜的,没有见识过繁华,也没有念过几本书。我自己呢,16岁就到农村插队,17岁又跟着在北京读高中的哥哥转辗陕北,依旧还是插队。连绵起伏的大山,阻断了我们对外界的张望,堆积在心里的只有荒凉与苦寒,还有无法言说的恐惧。
大概就是因为阻断,所以对张爱玲的文章深感陌生。而陌生,又让我百般新奇。来来回回地读,来来回回地想。
陌生的张爱玲和男作家们完全不同,男作家用异性的目光,宽容而理想地塑造温和华美、无私奉献的女性,有时不免怜香惜玉。张爱玲则不。
她写的,如同她自己所说: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可那些小事情却没有牧歌式的抒情。她的笔下,女人头顶的一方天,巴掌大,狭小,宽窄。心呢,也是狭小的,藏着虚荣和欲望,为一己之生存。把支撑着她们的虚荣与欲望拿走之后,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她用近乎刻薄的笔,把人生混浊的一面,很耐心地剥开。整个香港炸毁了,而她却在硝烟飘散之际,成全了一对平凡自私的夫妻。
不留情面,不温情。犀利,透彻。还有她很独特的语言,盘桓在心里,挥之不去。
之后,只要进书店,就搜寻张爱玲。最先找到的是上海书店的《流言》,是散文,薄薄的一本。张爱玲的散文,比她的小说更吸引我,仿佛在黄昏里与她相对而坐,听她喃喃私语:她的身世,世态凉炎,她对音乐、绘画、舞蹈、宗教等等一己之见,还有她对颜色、气味、声音的细微感受。她怎样看“七月巧云”,怎样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怎样去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中的霓虹灯……那些文字,细碎,深远。如同她自己写母亲在她5岁时离家之际的情景,像船舱玻璃上映着的海,有着无穷无尽的颠簸悲恸。
后来喜欢上散文,似乎就是因为张爱玲。
去北京出差,在旧书店里翻到《紫罗兰》杂志合订本,又在那里读到:《沉香屑·第一炉香》。很想把厚厚的合订本买下来,可囊中羞涩,只能站在那儿读。没过几年,张爱玲的作品渐渐多了一点儿,我从书店一一捡拾,老师去香港,又特地请她帮我找寻张爱玲。老师给我带回来《张爱玲资料大全》,欣喜若狂。
因为我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还是个文学编辑,于是就想若能编一套张爱玲文集多好,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就不用像我这样零零碎碎地去找,一套在握,尽览无佘。这样想也就这样做了。报选题时,心里还是有点儿虚,毕竟张爱玲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52年)就去美国了,且离革命远而又远,她的小说散文与革命毫不沾边。虽然国内零零散散出过几本她的书,在我们同行中,知晓她、认可她的人也并不太多。尽管这样,还是很认真地做了很多功课。平时不大会说话的我,在选题讨论会上介绍选题时,竞也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
还是因为喜欢吧。
出乎我意料的却是,选题很顺利地通过了,上报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一经批准,就可以实际操作啦。
更让我高兴的则是,刚刚分配到我们出版社的是山东大学的研究生林敏,和我一个办公室,她与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的于青是同门弟子。据小林说,于青和我一样,也是个张迷,她在图书司具体分管审核全国各个出版社的选题。小林很热心地帮我联系于青,于青呢,当即答应。
选题顺汤顺水地通过。
选题通过了,操作起来却依旧困难重重。一是内容,二是版权。总觉得内容还是不够全,沿着老师从香港带回来的《张爱玲资料大全》一一查找,发现所能找到的小说散文里都有遗漏。很希望这套文集还是尽可能地将张爱玲的作品都收进来,特别是重要作品,当然是越全越好。于青很帮忙,陪着我去北京图书馆查找。北图的资料很全,张爱玲的小说散文也有很多,但因都是解放前出版的,不外借,也不允许复印。
头大!不知如何是好。我很有些丧气。于青却很乐观:“肯定有办法。”
我却无法乐观,问她什么办法?
她笑日:“直接去找馆长,开诚布公。”
行吗?我还是有些担心。我不能在北京久留,匆匆打道回府,就把这事交给了她。
她很快就有了头绪。
周日,她就去了北图。那天,馆长室只副馆长金宏达先生一人。金先生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学的是中文,“文革”后又读了研,研究的是现代文学。自然,他对张爱玲很熟悉,有心得,还很有研究。
于青兴冲冲地告诉我,她与金宏达先生沟通地很顺畅,他答应帮忙,提供尚方宝剑。毕竟,是为出版社尽力,繁荣出版事业。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没有想到竞也还是顺利,就像选题通过一样。我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做具体编辑工作认真负责,还行。但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这些事情若没有于青帮忙,还真是不行。于是,就想若能请她和金宏达先生作为此文集的编者,一定能够推进文集早日问世。
在电话里与于青商量,她很爽快地就一口答应了,还兴冲冲的说,金宏达先生的工作由她来做,估计不会有问题。
果然。
版权问题,随之提上议事日程。那时,国内大多出版社对版权并不重视,已经出版的张爱玲散文大全和张爱玲的小说集,都是没有得到授权的,我不希望我责编的这套文集也这样。
于青和金宏达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他们几经周折,找到当年曾给过张爱玲很多帮助的柯灵先生。柯灵先生很热心,也很支持,当即请张爱玲的姑夫李开弟先生联系在美国的张爱玲,请她授权。李开弟先生很高兴,很快与远隔重洋的张爱玲取得了联系。前前后后,忙碌了几个月。
我得到李开弟先生的地址时,已由忙碌的初夏转而进入寒冷的冬天。正值新年前夕,大雪纷飞。冒雪前往上海,火车缓缓驶进上海站时,心情亦像紛飞的雪花,飘飘洒洒,想象不出李开弟是怎样一个老人,也没想好怎样与他交谈。
从张爱玲的散文中,读到过她的姑姑,还看到过她与姑姑的合影。她姑姑也是高高的,长身玉立,鼻梁上架着眼镜,很大气。她姑姑曾和她母亲一起,漂洋过海,去法国留学。后来,她姑姑回国后就没有再出去,而她母亲一直漂泊在外。在张爱玲的少年与青春时代,关照她最多的还是她姑姑,她和姑姑也最亲。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和姑姑住在一起。李开弟老先生现在就住在她姑姑在世时的公寓里,上海黄河路65号。
很冷的早晨,雪已经停了,太阳温温地挂在空中。我敲开门时,李开弟老先生坐在轮椅上,棉袄外面套着厚毛衣,正在吃早餐。很简单的早餐:一小碗白米粥,一只小碟里放了一小块淋了香油的白豆腐乳,另一只小碟里放了半个白面馒头。
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简单。简单之外呢,还因为是好奇。不知那些阀阅门第的后人,怎样过日子的?如同张爱玲所戏言,我们每个人都有向别人私生活偷偷瞄一眼的好奇心。
太阳从窗玻璃上照进来,屋子里干干净净,很清爽。两只小沙发、窄窄的茶几、写字桌,还有一张大床,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进门是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问。
我带了照相机,但实在不敢冒昧地拿出来。
柯灵先生已经和李开弟老先生打过了招呼。我刚开口说我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他便知道了我的来意。但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和我聊天,很细琐,就是从他面前的那碗白米粥白豆腐乳说起,直至张爱玲的姑姑,他已经去世的老伴。
他的老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那也是一个传奇。
她与李开弟先生相识于去法国的轮船上,那时她还很年轻,与她相伴的是张爱玲母亲。广阔无垠的海,漫长单调的旅程,他们开始不过是很礼貌地点头打个招呼。接下来,相遇的次数多了,也就站在船舷边,聊会儿天。
聊着聊着,就聊出了欢快,相遇恨晚。在张爱玲的笔下,她姑姑说话像发电报,很劲道,一句就是一句。那份幽默,却是他人难比。和相通相知的人在一起,想必那电报也发得快。投缘。不过,他们也只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理。因为那时,李开弟先生已经有婚约。
然而,友J隋一直持续。
后来,张爱玲去港大读书,她姑姑还曾托付李开弟做她的监护人,李开弟亦尽心尽力。
张爱玲姑姑嫁李开弟时,已经78岁,是在李开弟的妻子去世以后。那么漫长的等待,她的青春,在等待中花开花落。最后的温暖,是在摇曳的秋风中,生命的尾端。
不过,等待中,她也没有枯槁,不像大多女人,自怨自艾。一直活得很滋润,也很自在,不靠男人,也不靠她那个曾经显赫的家庭。张爱玲的独立,还有那份从细小之处,享受生活的怡然自得,就是从她姑姑那儿传承来的。一个人,独处,安安静静,细细品味,吃与穿,还有窗外,时时变幻的风景。
令李开弟先生伤心的则是,张爱玲的姑姑还是先他而去。
第一次和李开弟先生交谈,说得最多的就是张爱玲的姑姑。也许,他太闷了。我有点儿心急,好不容易等到他停下回忆,赶紧拿出事先拟好的合同。老先生让我把合同留下,明天再来,他要仔细看看。
第二天去时,老先生已经吃过早饭,坐在轮椅上等我。合同,他没有提出其他什么问题,只是觉得稿费太低了,他不能签。千字才25元。我也觉得低,但是我们地方小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没有版税一说,最高的稿酬千字30元。
我只得悻悻回到旅馆,电话请示领导。
电话没打通,分管领导外出开会去了。
想了又想,不能这样拖下去,我自己先定,以社里的最高稿酬和李开弟老先生谈,想办法说服他。
虽然,30元千字的稿酬还是很低。我很耐心地向老先生讲了我们地方出版社的为难之处,还有我这个普通编辑的为难之处。毕竟,我们是国内第一家想和张爱玲签了约再出版她作品的出版社,签约是对张爱玲最大的尊重。
來来回回,又经过几次磨合。李开弟先生终于在合同上签下了他的大名。而拿到合同的我,除了兴奋,还是兴奋,多坐了一会,又和李开弟老先生聊了一会儿天。告别时,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老先生是否知道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地址,当然也很想见见他。
张子静?
老先生看了看我,摆了摆手:“我们和他没来往,不晓得。”
我也没有再多问,知难而退。回旅馆的路上,坐在公交车里,林立的高楼大厦从眼前一晃而过。也不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蜗居在哪个角落里,想必他姐姐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他的日子更加落寞而孤单,不会很好过。
雪停了,却一直没有融化。回到社里,第一件事就是向分管副社长汇报,磋商稿酬问题。千字30元?副社长笑我:“你也真敢签,这可是我们社最高稿酬。”解释了半天,他总算同意了。我也长长松了一口气,赶紧把盖了公章的合同寄回一份给李开弟老先生。
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老先生的回信,责备我做事太马虎,我们社的公章应该盖在两页纸合同的中缝,这样才能防止做假,以免今后双方因合同而产生歧义和矛盾。
我很吃惊,这么严谨?猛地想起,交谈中,老先生曾告诉过我,他曾在外国银行做过监理,严谨想必是他的职业习惯。而这职业习惯,直至如今。所以,张爱玲才很放心地请他代为签约。
脸红。老先生给马马虎虎的我上了一课。
我开始着手编辑,在编辑体例上,我有些犹豫。金宏达先生与于青,他们所定是:第一卷短篇小说,第二卷中篇小说,第三卷长篇小说,第四卷散文。(补充:四卷本出版后,我们又增加一本:《红楼梦魇》。)而我自己,则特别喜欢张爱玲的散文,很想把散文作为第一卷。为此,我又去了一趟上海,去找柯灵先生,征求他的意见。
柯灵先生很温和。在挤满书橱的不大书房里,他找出一本书,那上面有一篇他回忆张爱玲的文章——《遥寄张爱玲》,让我读一读,也许会对张爱玲有些具体的了解。肯定也是看出我们这一代人与张爱玲的隔膜,毕竟我们和张爱玲所生长所生活的时代,隔山隔水。
他握着手中那杯清茶,思索了一会儿,语气轻缓地对我说:“散文还是放在最后一卷合适。”
我还是心有不甘,反复喃喃,张爱玲的散文最吸引人。
他笑了,还是缓缓的:“放在最后,分量也最重啊!”
我释然,亦豁然开朗。
匆匆读了一遍《遥寄张爱玲》,问他可否把这篇也收进文集,柯灵先生还是很温和地笑:“当然可以。”
文稿收集基本齐全了,与张爱玲的出版合同也签了,剩下的则是琐细的编辑工作,协调印制,与发行科的同志沟通决定印数。而这些则是我的日常工作,心里还是有数的。
但没有料到的则是,那一段时间社里书稿很多,文集的排版安排不上,有点儿拖。我按捺不住,又去找那位分管副社长。副社长笑哈哈,根本没往心里去:“你急什么?张爱玲文集又不是畅销书,拖几天有啥关系?!”
我急了:“张爱玲文集肯定畅销,再拖黄花菜就凉啦!”
副社长依旧笑哈哈的:“我跟你打赌,如果张爱玲文集畅销,我就用手当脚来走路!”
他没好意思说他在地上爬。
说老实话,张爱玲文集是否能畅销,我心里也没有底。只是我自己是个挺坚定的张迷。避开他打的赌,我依旧紧着追问:“你说哪天能让印制科发到厂里?”
他大概看我神情严肃,有点儿恼火的样子,又笑了:“好,好,好,抓紧,这个星期内。如何?”
我一个劲地催,催下厂排版,催校对,催发行科报印数。第一版终于于1992年7月问世。前前后后,忙了两年多。在我自己看来,第一版的张爱玲文集是不尽如人意的,因为匆忙。我这个责任编辑太想赶时间了。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第一版问世,很快就一售而空,紧接着第二版,第三版,印数飞快增长。
那位要和我打赌的副社长,脸上乐开了花,不断催促印制科的同志,抓紧安排下厂开印,快,再快一点儿。他当然没有忘记他和我打的那个赌,我也没忘。他不提,我也没提,心照不宣。相逢一笑,抿相左。说心里话,我还是挺感谢他的。虽然,文集问世之前,他不看好,但也没有阻拦。文集问世后,他一直是大开绿灯,很热隋。
也许,太顺的事,总会波澜再起。
正当社里兴兴头头地忙着加印张爱玲文集时,台湾皇冠出版社在文学报上发表申明,李开弟先生不再代理张爱玲作品版权事宜。张爱玲作品的版权全部由台湾皇冠出版社代理。
很蒙。有点儿找不到北。
不久,皇冠出版社在大陆的律师代理到我们出版社来了。方知,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先在香港,之后又去了美国,并不是很顺利。1965年,张爱玲经香港朋友宋淇介绍,开始将旧作和新作陆续交由台湾平鑫涛先生所办的皇冠出版社。据律师说,皇冠出版社买下了她作品的所有版权,一直按期支付她稿酬。据止庵先生说,皇冠出版社跟张爱玲的关系,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出版社和作者的关系,而是一种供养关系。张爱玲在美国衣食无忧,安心读书写作,与皇冠出版社不无关系。
律师还说张爱玲曾向皇冠出版社婉转地表达过她自己的歉意,承认自己所做不妥。
皇冠出版社要回张爱玲作品在大陆代理权,理所当然。
张爱玲没有和皇冠沟通,请她姑夫代理她作品在大陆的出版权,除了疏忽,大抵还因为柯灵先生的热情劝说,和她自己对家乡故土的深深念想。一直漂泊在外的她,一定很孤独。而孤独中的她,对家乡的怀念,一定千丝万缕。且美国读者,因为文化与生活背景乃至阅读习惯的不同,并不怎样接受她。张爱玲是个作家,她一定渴望更多读者喜欢她,渴望家乡的读者可以再次读到她的作品,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
这是她最后的一点儿期盼。
又很巧,皇冠在大陆的代理律师是陕西人。聊天中得知我曾在陕北插过队,便多了一份热情,到底还算是半个老乡吧。原本是问责的,后来竞答应帮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社众多领导乃至我这个普通编辑都很热隋配合他的工作。
律师回到北京不久,一天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平鑫涛先生已抵达北京,建议我不妨来北京见见平鑫涛先生,争取和皇冠出版社续约。
匆匆赶往北京。
是夏日里,清朗的早晨,宾馆的咖啡厅。我和律师刚到,平鑫涛先生也如约而来。他与张爱玲、柯灵先生是同时代人,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但看上去依旧气宇轩昂。黑色的西装,背挺直,头发纹丝不乱。
他见到我,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丝吃惊。那天因为天热,我穿了一件米白色的T恤衫,深红色长裙。素面朝天。在陕北高原待了那么久,一慣都是素面朝天。是不是太随意了一些?
或许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李开弟先生为何会与我们这么个地方小出版社签约?而且是很落后的安徽。土。
我却不这么认为,在心里暗暗地想,我们合肥可是张爱玲外曾祖父李鸿章的故乡,张爱玲文集由我们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落座,律师点了咖啡,平鑫涛先生却只要了一杯清茶。
几句客套之后,我很小心也很拘谨地提出,皇冠出版社可不可以和我们社续约,我们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这几年一直很畅销,也得到读者的认可与欢迎。当然读者的认可与欢迎,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张爱玲作品本身的魅力。
平鑫涛先生未置可否,他说,他已经老了,大陆这块已经决定由他的儿子陈平来做。我们可以和陈平联系。
律师笑着补充,他有陈平先生的联系电话。
在我与平鑫涛先生已交谈一会儿时,律师小声提醒我,另外北京的两家出版社早已在一旁候着平鑫涛先生了。
起身握手告别时,我从包里掏出相机,犹豫地问平鑫涛先生可否合张影,他挺平和地点头。
没有在相机里留下李开弟先生和黄河路65号公寓,一直是我的遗感。
我们合影时,其他出版社的编辑就已经涌了过来。
走出咖啡厅,只觉得外边的天空湛蓝,蓝得深远而辽阔。续约仿佛很有希望,又仿佛很渺茫。
始料不及地却是,命运突然就拐了个弯。
回到合肥不久,因为一个意外,我离开了文艺出版社,调到安徽科技出版社的《家庭与家教》杂志,改了行。张爱玲从此从我的职业生涯中淡出。但也没有彻底淡出。有一天,文艺社转给我一封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一个陌生人写给我的。她自我介绍说她是40年代上海一个女作家的侄女,她和她姑姑现在都在澳大利亚,当她姑姑看到国内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很激动。她姑姑很愿意将她的文稿交由我编辑。
我很惆怅,也很茫然,不知该如何回复。
2005年,出版社改制,有了一个选择提前退休的机会。非常欣喜,可以只拿钱,而不用再干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提前退休。之后呢,就开始云游四方。
有时,还会想起张爱玲,想起编辑她文集时的一路辛苦与快乐。她去世时,也曾仔细阅读方方面面,长长短短的各类消息,還有回忆她的文章。
2015年,在上海,夏末初秋,傍晚刚走出餐厅,小林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收到过张爱玲送给我的一个包还有信?
不知哪对哪,我一时找不到北。
她让我赶快去买一份三联周刊,那上边一篇文章提到张爱玲曾想送我一只包,还有信。
天已经完全黑了,周身却是一片灯火辉煌。在掩藏在一棵大树下的小报亭里,老板一下子就给我找出那期三联周刊,封面就是张爱玲的头像,还有醒目的标题:《张爱玲的后半生一种传奇的两重叙述》。
就着闪烁的灯光,匆匆读到访谈中止庵先生的一段话:当时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张爱玲的书,那是她姑夫授权的。张爱玲去世以后,我到宋以朗家里去。宋先生拿出一个包,说有一个事怎么办。在张爱玲的遗物里发现一个包和一封信。是写给国内一个人名的,一个女人名。不知道是谁。这事他也跟陈子善说了。后来陈子善找到这个人,原来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已经退休了。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书,张爱玲觉得这个编辑帮了忙了。就买了一个小包,带封信,这封信她自己送不出去。写的时候想送,等送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了,就搁在那儿了。等她死了之后,遗物拉到宋先生家去,这么多年,终于把这事送成了。
很想知道张爱玲会在信中给我写几句什么呢?她的字,像她的人一样吗?
在万盏灯火的夜晚,喧嚣的热闹中,心头漫过的却是张爱玲笔下白公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孤独,苍凉,辽远。如同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