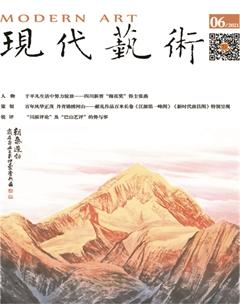大国脊梁 圣境峰光
崔念晗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贵州省美术家协会、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了《大国脊梁·圣境峰光——高原雪山画派作品展》2020年全国巡展。全国巡展的学术研讨会在文化底蕴厚重的国画大省——陕西和山东进行,主题为“中国山水画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群体现象”以及“中国山水画传统的地域特征及笔墨创新”。研讨会汇聚秦、鲁、川三地的理论名家与学者,紧扣地域性、画派群体发展、现代性转型和笔墨创新几个方面,将雪山画派立足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探讨。本文将从两场学术研讨会的论点入手,以明确的史论观点为依据,结合高原雪山画派创始人李兵的作品从地域性审美、画派理论逻辑、崇高审美形态、笔墨意境和现代性转型这几个方面,系统地对各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学术阐发。
一、地域观念:文化特征与民族气质的确立
“中国绘画”(或“中国画”)一词的提出,一开始就包含了对地域范围的界定,指的是区别于“西洋画”的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的绘画,且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中国绘画已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内涵和品评体系,在这背后产生支撑作用的是中国人积淀延续的生活方式、哲思模式和审美观念。“高原雪山画派”创立者李兵在雪山下工作、生活十余年,用绘画语言将朝夕相伴的雪山之壮美、崇高和冰清玉洁的境界表现出来,如雪山在風雪中沉着坚定、在阳光下风姿卓越,冬日积蓄能量、春天滋润沧海桑田,以及冰肌玉颜春风化雨的风骨之气。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有相同关注点的四川山水画家汇聚在一起,将四川高原雪山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域环境为他们提供的,能够反映本土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的内在动因紧紧抓住,经过他们的审美再造,创作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原雪山审美对象。
如李兵这样将对甘孜雪山的深情厚谊转化为创作表达并取得艺术成就的例子,在美术史中不胜枚举。例如这次巡展的第一站陕西西安,就是“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孕育的摇篮,其中石鲁先生于延安、刘文西先生于陕北的真挚感情是两大画派中浓厚的地域情感的体现。“长安画派”以赵望云、石鲁为领军者,继承和发扬延安革命文艺传统,衍生出厚重豪放的现实主义山水画风格;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将对黄土地的深厚感情化作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将人民群众形象塑造于纸上,形成阳刚豪放和蓬勃向上的艺术风格。以李兵为代表的“高原雪山画派”长年深入藏区,扎根雪域高原,将创作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把对雪山的崇敬融入画面,塑造出巍峨挺拔的高原雪山形象,形成崇高宏大、正大凛然的艺术风格。以此三人为例所体现出的地缘、情感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地域审美观念和文艺创作的内在联系。在西方美学史上,对地域审美观念与文艺创作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的,以孟德斯鸠为领路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情感气质有着重要作用。”从孟德斯鸠和高原雪山画派所体现的地域性艺术风格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明确的地域审美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画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
每一个创作者都与他所成长、生活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描绘出本土的文化精神,这就要求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具备地域审美观念。“高原雪山画派”创始人李兵在画派开创之初就具备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看,地域审美观是包括高原雪山画派在内任何一个画派确立的基础,是它具备自身艺术性质和风格的先决条件,是它走向发展面向世界的重要条件。从更深层次来讲,地域审美特征是构成民族特征的基础,艺术创作中若没有地域审美特征便无从谈民族特征,在普遍趋同下,“民族的”便因失去自身的特色与定位而逐渐模糊。这也是我们为何说“越是地域性的就越是民族性的,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性的”。
高原雪山画派在多年的实际探索中,凝练出本土文化中未曾表现过的雪山具象图式和文化精神特质,具备了艺术创作中明确的地域审美观念,展示出代表民族走向世界的姿态。
二、画派形成: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载体
从十九世纪的中国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到二十世纪的王伯敏、薛永年等史论家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归纳出中国绘画流派判定的三个标准,即:一定的师承关系(创始人和继承者)、相近的笔墨风格和相似的画学思想。高原雪山画派在创立者李兵的带领下,广泛吸纳它的创作群体,带着以西部高原雪山为主要创作对象的优秀作品连续两年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巡展,使高原雪山画派和“水墨雪山”的学术命题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由此可见,高原雪山画派以其艺术表现特点而得名,且具备了一个绘画流派须有的三个条件。
在探讨高原雪山画派所具备的地域性审美观念时,地理和自然环境对画派形成的影响似乎要呼之欲出。但为何不能简单地将地域性作为画派形成的仅有原因去套用,那是因为画派的含义包括但超过了地域观念,特别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高原雪山画派,更是在画派界定的专业场域中囊括了画派的尽有含义,若仅仅在地域性中去谈,则窄化了它的特性。

薛永年曾将中国绘画史中的画派进行定义,他认为画派有两种:“一种是历时性的画家传派,由创造新风格的画家及其追随者构成;另一种是共时性的地方画派,由同一地区的画家群体组成,当然也包括开创者和传人。”二者相通之处在于都有创造风格的开派人物和继承者,不同之处在于“历时性的画家传派”是跨越时代、贯穿各个时期的,强调总体风格和共性的追随,如文人画派和院体画派,同时地理因素对其也有着直接影响,如南宗董源、巨然和北宗荆浩、关仝。“共时性的地方画派”多指在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成长起来的开派人物和传承者共同形成的群体。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高原雪山画派完全符合“共时性地方画派”所列的几大特点。其次,要谈一谈这一画派的“历时性”传承。在山东站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四川处于我国的西南,但是高原雪山画派的作品画出了北派山水的气魄”。回溯历史,潘天寿在《潘天寿美术文集》中用“严明刚劲”“水墨苍劲”来形容北方山石轮廓和北派山水画两大系统,用“柔和婉约”“水墨淡彩”来形容南派,并提出“黄河以北”或“长江以南”的地理区分。高原雪山画派笔下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延展至四川西部,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和巴颜喀拉山的长江、黄河自西向东流经青海或西藏自治区后,都首先来到四川。此时川西北高原雪山的区位划分是不能从“黄河以北”或“长江以南”来界定的,高原雪山画派的创作对象也已经不能以简单的南北地域来区分。研讨会上还有学者产生直观的审美感受,品评作品“特别强调山的骨力”,并认为“范宽的作品为‘得山之骨,这个说法也可以用来形容李兵的冰雪山水画。”回望历史,清代画家戴熙在《习苦斋画絮》中道:“董、巨尚气,荆、关尚骨”。荆浩、关仝作为北派山水的开创者,他们的画风对“得山之骨”的范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原雪山画派在“历时性”的总体风格和共性延续上是可以溯源并有所倾向的。荆、关作品中“尚骨”的艺术表现方式与高原雪山画派“雪中有骨、云中有志”的阳刚大气之美相呼应,使雪山画派的作品经历了时空,打破了狭义的地域,与五代时期的绘画风格相碰触。
高原雪山画派具备了画派形成的三大要素,它跨越了时代,立足但已超越了地域性,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呈现出一个画派应具备的理论与创作逻辑。
三、审美形态:崇高中的正大与无限
在两站的研讨会发言中,不少理论家提及高原雪山画派绘画风格时指出,画面具有“圣”“大”的观感,“作品的表现力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包含着对“壮美”“雄伟”和“高大”的表达。当站在现代美学体系的理论构架中,以上对雪山画派绘画风格所进行的诸多描述,都应属于对其审美形态的概括,具体来讲是对“崇高感”的描述。
英国的博赖特在《大地礼赞》中,用“庞大的自然对象”“赞叹的愉悦”等说法对崇高进行了概括,但此时“崇高”一词并未真正脱颖而出。到了18世纪,英国美学家博克将崇高的“大、坚实、朦胧”等特征做出界定,直至康德,“崇高”被上升至哲学高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崇高对象应表现为体积和数量的无限巨大以及力量的无限强大。那么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崇高的释与注颇丰,如《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中,称“崇”为“万物得其高大也”,《国语·周语》中说,“容貌有崇,威仪有则”,更有《诗经·大雅·崧高》中,将人格的崇高与山岳的“俊极”相联系。

以上关于“崇高”的审美客体外形及观感的分析,从中、西方美学角度出发,映射在高原雪山画派的作品上显得尤为合理与贴切。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中将崇高形容为“审美感兴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种类型”“主体心灵始终处在一种强烈的摇撼和震荡之中”。在高原雪山画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雪域高山的神圣之气,画面中大山大水的境界之意,笔下山体凛然的坚实之感,都在丈尺之间经营得游刃有余,对崇高进行了诠释。画面中雪山的力度和气势,使审美主体感受到庄严与肃穆,受到极大震撼。至此,若从雪山的坚实厚重与庞大庄严引人赞颂这一点来分析,对雪山画派作品在崇高感的体现上的论述都已经说明。我们不妨立足理论史料,更加深入透彻一些。
“无限”是崇高的背景与美学底色。对于画面中的雪山来说,或者对于任何一个审美对象来说,它自身是有限的存在体,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前景单纯地去感性地体现。当“有限”要向“无限”去延伸以达到崇高的审美形态,就要摸索并借助“形式語言”。例如李兵的作品《春光唤醒沉睡土》中,地平线由雪山下茵茵绿草的前景过渡至朦胧雾霭以产生视觉上的推移,与雪域山体相连接。冰雪峰峦之间,视线延展至远方连绵不绝,使观者的视点由近至远,层层推出直至目极的天际,最终使画面成为无限意境的象征。将空间的无限拓展至时间的无限,成为历史、精神的无限,这是高原雪山画派作品中崇高理想的不断超越与实现。

由此可见,审美客体高原雪山所展现的坚实、正大,画面整体中雪域山川透露的凛然、无限,二者由表及里,由相至意,共同塑造出雪山画派作品中“崇高”的审美形态。
四、笔墨意境: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关联
回溯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进程,从魏晋南北朝山水游赏兴起,到隋唐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的审美并存,从五代两宋山水画中的哲学表现,到元朝的写意倾向和明清的继承延续,这都是传统中国山水画的自律性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山水雪景图的创作是有的,比如王维、赵松雪、黄公望、沈周的江南山水雪景。到了北方中原,有山西荆浩的太行山雪景图,陕西关仝的中原雪景,长期在终南山隐居的陕西铜川人范宽,擅长创作以秦岭终南山为题材的雪景图。但这个时候,由于高寒缺氧气候和交通无法达到的因素,以西部高原雪山为题材的创作是未曾见的。
时至近代,中国绘画艺术未能像欧洲绘画艺术那样,在类似启蒙运动中产生自发的文化革新,而是带着被迫性、抑制性和移植性开始现代转型之路。此时关于中国画如何取得进步的分歧是比较大的——西化派、融合派、传统派,各自有着艺术主张与实践。傅抱石的《雪山行旅途》,张大千的《瑞士雪山》等,都是山水画雪山创作在现代性转型中持续进步的表现。吴作人、吴冠中、常书鸿等创作的雪山雪景图也各具风格。巴蜀地区冯建吴、吴一峰、嘉州画派李琼久,都在传统雪景山水画上做出过新的探索与尝试。
在长久的时光里,山水经过一代代的更迭,披上了一层层文学和艺术的嫁衣,这是山水的历史记忆和审美痕迹。赏析今日的山水画,从历史延续而来的绘画风格与技法,就成为我们认识当下中国山水的重要方式。在研讨会中有学者认为,以李兵为代表的高原雪山画派在创作中融入了传统的山水画精神,特别是宋代绘画的艺术境界。结合美术史中山水画风格的承变,我们不难发现,李兵作品中的宋代绘画艺术境界,正是五代两宋绘画“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高度融合。他在作品《神巅横空来》中,用山体和生灵自然本真的存在方式去理解描绘,身为观者,却在视觉定位上营造出静观的超越视角,置身自然、体验自然、化入自然,使主客观和谐统一,使画面脱离世俗之我,达到“无我之境”。作品《祥云伴我还》中,他“以我观物”,用饱含热情的眼光注情于雪域山川,选取适应于画者心境的雪山、祥云以及严酷自然环境下令人敬畏的生命力量,创造出鲜明的“待到春回日”的希望之感,达到表现主观情意的“有我之境”。学者们所提到的李兵作品中“理性的浪漫气氛”“克制稳定”“非激情式”,都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基因。
意境的营造同时离不开笔墨的支撑。李兵为了寻找到最能表现雪山形象和雪山神韵的笔法,投入到中国美术史中去探究国画技法,研究水墨山水的绘画语言。经过长达10年的探索与实践,他发现没有某一种传统的皴法能够把他眼中的雪山景象和心中的雪山神韵表现出来。就好像《石涛画语录·皴法章第九》中说的那样:“笔之于皴也,开生面也。山之为形万状,则其开面非一端。”山的形状有千万种,块面呈现方式和山体质感都是不同的,如何在传统水墨的继承下,把雪山特殊的质感、生动的体面关系和肌理效果自然地表现出来,这非一两种皴法可以解决,需要继往开来者的发现与创造。李兵正是在发现问题中开始对皴法的探索。
山水画技法中的“斧劈皴”有大小斧劈之分,“大斧劈皴”用笔苍劲宽阔,方中带圆,墨气浑厚,适合表现大块面积的山石,李兵在关注到这一点的同时,也发现这种传统皴法还不能够最好地呈现雪山山体。他于是尝试把大小、长短不同的“皴”糅合,以“块”的方式来表现高山雪线和岩石裸露的关系,处理山势走向和积雪冰封的关系,这才基本把雪巅神彩展现在宣纸上,至此,创立了“块斧劈皴”的新皴法。在对水墨雪山画法的研究中,李兵曾阐述过自己“皴随物定”的观点,认为深入生活观察自然,用心体味所要表现的“物”,根据物之特点使用恰当的皴法,才能更准确地表达物象的形和神。这一观点,是他作为画家本身能够创立“块斧劈皴”新皴法的思想基础,与石涛的“山之为形万状,则其开面非一端”这一观点不谋而合,是绘画中法则与自由相呼应的体现。

高原雪山画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雪山的雄伟磅礴,亦可以看到云雾的层次变化与雪山的光色辉映。中国画自古以来非常重视画面中的空白,认为空白在意境构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笪重光在《画筌》中提到“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在解決了水墨雪山绘画技法表现“实景”与“真境”的问题后,创始人李兵将目光投向了“空景”与“神境”。他开始思考山水画意境创造过程中的虚实相生,如何在水墨雪山的创作中达到写实与写意的高度融合,使“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在探索中,他寻找到“挤白”“衬白”和“冷暖对比”等染雪方法,通过笔触和色墨在纸上留下的痕迹与之相互映衬,使观者看到画面的实体雪山时能感觉到雪的存在,以“空白”作载体渲染出“画雪山,未画雪,雪已现”的意境。
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名誉主席冯远先生所言:国画家李兵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探索,探究出了“块斧劈皴”笔墨技法和“挤白”“衬白”等染雪法,通过笔触和色墨在纸上留下的痕迹,将高原地区因冰川冻土而形成的肃穆刚劲感、将高寒积雪因风吹而形成的流动感,以及将高原雪山因太阳运动而带来的光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拓展了中国水墨雪景山水画的创作题材,不仅推动了雪景绘画艺术在体现物象质感和动感上的进步,而且推动了中国画的程式发展,这是对中国美术史在笔墨创新和审美意趣时代化方面的重大贡献!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大国崛起的新时代下,如何回望和继承传统,如何迎接和追求创新,这是新时代给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一道思考题。高原雪山画派以当代的广阔视野,实现从雪景绘画图式到雪山绘画图式的变化,实现从寒山寒林萧疏寂寥到雪域山川崇高壮美的审美转变。他们也在挖掘和探索笔墨的妙用与意境的传神,思考着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进程当中“水墨雪山”命题的当下延续。在这样继古开今的尝试之中,高原雪山画派的群体风格日渐清晰,既具备发展延续的现代精神,又具备了中华民族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性和文化特点,对新时期中国画以及艺术流派的诞生、发展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