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电影”:一种纪录片的先锋异端样式
按:自新千年以降,“影像”作为媒体艺术的基本样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主流的表现形态之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其自身亦形成了一部模糊的非线性历史,而这部历史因为其羸弱的发展轨迹和驳杂的血缘谱系,使得许多词源概念、语言逻辑、资料史实、陈述文体等都缺乏翔实性与可考性。
“映验场”(EX-CINEMA)作为一个意象性的专栏名词,穿越了从电影(Film)到录像(Video)、从新媒体(New Media)到动态影像(Moving Images)一系列历史语汇,以穷究于理、正本清源为栏目的既定目标,以达成一次媒体考古学的文本预演。(曹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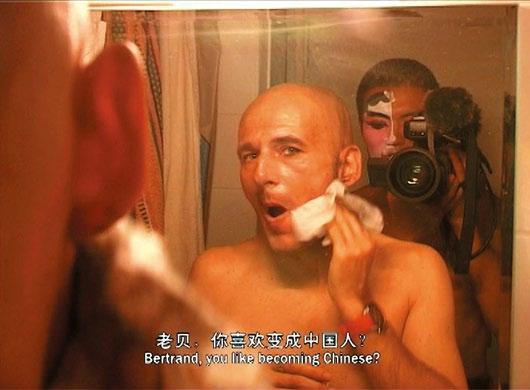
一
什么是“坏电影”?直接反应的答案很简单——与“好电影”相悖的电影,就是“坏电影”;至于“好电影”的概念,那是毋庸赘言的。
在某种语境里,“坏电影”的概念与当代艺术中的“坏画”相类似——“它表示更专注于差异性风格,是对所谓‘好画的嘲讽,它表现为变形扭曲的图像、混搭艺术与非艺术的风格,以及荒诞不经的内容。”如果把“坏电影”局限到纪录片的范畴,那么,作品的思想表达与观念文本之良莠姑且不论,在世俗语义里定义一部纪录片的“好”与“坏”,主要是针对其美学语言的匹配度和完成度而言。一部“坏电影”,可能是一种具有反主流样态的纪录片语言实验,也可能是一种观念化的纪录片图像构成方式。
一般来说,纪录片中的“坏电影”在反主流风格的倾向上会很明显,画面与图像的血统驳杂而不纯正、来源混乱而不统一;许多素材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譬如画面的跟焦不实、曝光不足、增益过度、构图残缺等;而在制作上显得语法逻辑生硬、跳跃、失配,缺乏程序与关联。拼贴与硬接这类经典纪录片中比较边缘和极端的手段,却成为“坏电影”常用的方法。

“坏电影”的纪录片样本来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因为生产技术的不足,无法达到基本运作要求,而造成的作品先天缺陷性。这里的生产技术一方面指作者自身的能力因素,另一方面指技术设备等外部条件。第二类是作者出于某种对既定风格样式的背叛,从而生产出一种与既有美学标准大相径庭的作品。在这里,前者的定位,来自外部标准的认定;后者却是作者的某种主观意念的达成,系刻意为之。但在某种时候,面对一部“坏电影”,通常是无法认定其生产的主客观因素的,对研究者来说,需要通过具体个案分析,按照作者个人创作史的线性梳理来做出判断。
从中国独立纪录片主体建构的历史过程来看,因为资讯匮乏和范本缺失而造成的某种“野蛮”工作,是导致“坏电影”出现的根本原因——表达的欲望远远超过了表达的方法,这使得一部分作品充斥着各种违背纪录片经典样式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工作方法错误和呈现样式错误,其中既有对模仿范式的误读,也有随机即兴的杜撰,更多是一知半解的想当然耳。
但对研究者而言,如何看待这些“错误”? 如何评判这些“错误”?如何归置这些“错误”?这些“错误”的存在是否具有另一种价值?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系列问题的构成,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某种语言更新与重建的价值判断。
二
沿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时间轴反向行进,“坏电影”的出现可以追及诗人唐丹鸿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当时中国独立纪录片正以“直接电影”为基本立足点,对抗既往通行的专题纪录片模式,但是唐的这部作品却在当时就明显地偏离了“直接电影”的经典轨道。这或许与作者在摄制过程中一次巨大的心态落差有关,作者内在的变化,使得其对客体内部世界的深度探究终于出现反转,而对准了主体自身(身体与内心)。由此造成了一种杂驳式的语言表述——其中既有即时性的旁观,也有介入式的访谈;既有再现式的摆拍,也有镜像式的自拍;甚至包括面对镜头的呓语独白。影片结构上更是一种硬性的拼贴式接驳,场景画面之间的转换不讲究内在的语言逻辑,而是通过作者主体的观念逻辑来达到其统一性。
此类语言混乱、结构杂驳、具有“私电影”特质的纪录片,完全可以归结为“坏电影”的类型。在后来的一些创作者身上可以看到许多“坏电影”的相似性,譬如李凝创作于2010—2015年之间的“自画像系列”纪录片,这个系列由3部相对独立而又关联的纪录片组成——《胶带》《冰冻期/卫星》《身体的归途》。在这一系列中,李凝作为一个肢体舞蹈表演者在工作与私生活之间不停地转换身份,所记录的大都是某种日记式的零碎片段:某次街头肢体表演前后,作者所面临的生活与工作的各种压力与窘迫;同时发生在欧、亚两个不同时区的繁复人物的纠葛;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与表演现场夸张肢体动作的超现实性交错组接;乃至对已逝家族成员的追忆。以上这些梦呓式的自白,造成了一种对自我身体的拷问。
李凝的“自画像系列”作品充分显示了“壞电影”的诸多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影片章节的转场,许多都以硬切的方式打断,包括强行植入的行为艺术表演现场,莫名添加的类似MV式的意象性剪辑,以及突然插入的自拍式FaceTime视频对话,这些都造成了一种杂乱语言的搅拌式表述。最终支撑起作品整体结构的依托,可能只有归结到作者自身内在的心理发生过程。
三
对新千年以降崛起的独立纪录片作者群而言,其身份来源十分驳杂。在成为纪录片工作者之前,大多数人经历了一次或两次身份转移——从其他领域跨界进入纪录片群落,他们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各不相同,对纪录片的理解程度更是五花八门。对他们来说,创作的过程即为实验的过程,故有相当数量的作者是在摸索中探究出一条自我创作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其中很多人依照自己的理解对纪录片样式进行了形式主义的改造。

作为人类学民俗志纪录片的工作者,毛晨雨一直以家乡湖南洞庭湖流域的“细毛家屋场”作为拍摄和研究的对象。他一直试图“通过诗学和政治学行动”来重构其家族及原生地的历史神话谱系,而这种思想的野心和企图的目标远非纪录片这种艺术形态所能完全承载的。为此,他需要通过“几类物件”来印证“在族群生存语境中释放出的特殊意味及与之对应的独特宇宙观”,这种“物件”并非通常概念中的道具,而是加持了他的观念的某种装置,比如在《猪脚/葡萄酒/死亡迅速》一片中所展现的实物样本。
在早期,毛晨雨还更多借助直接电影的工作方法,但从总体结构上讲,他的创作是观念引导形式、主观驾驭客体,为凸显其观念的传达,越往后越来越不择手段。如果说早期的《秘密人》尚具有更多乡村民俗志式的人类学纪录片特质,那么,到《拥有》出现,他已经彻底走向了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式的观念图解模式,大量的文字符号、示意图形、摄影图片以二维动画及平面转场的方式被整合在作品中,解说式和口述式的主客体角度频繁交错,且几乎不再顾忌段落之间的蒙太奇逻辑衔接,经常是以生硬的跳转模式直接切入下一章节。
21世纪初后半期,毛晨雨在克鲁格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在克鲁格晚期的作品中,其“谜语电影”的语言特质已经逐步走向了文本至上的形式异端,以图像拼贴作为文本阐释的表象,甚至以满屏文本的直接书写,辅之以图示、表格、引言、注解等“非电影”范式。类似的方法被大量运用在毛晨雨的另一部作品《云爆,洞庭及符号死亡》中。他的這部作品从历史语境切入当今现实,以一个动物保护组织者的个人微博为客体对象,在核战争的“云爆”意象背景下,将“洞庭”作为一个抽象符号置入现实中进行分析式的论证。在这一过程中,毛似乎并不在意论证的结果,而是更多沉溺于论证的形式表达的快感上,包括色彩鲜艳刺激的满屏字幕和画质颗粒粗粝的网络视频,无一不显现出典型的克鲁格主义的异端语言倾向。
四
以纪录片的通行概念来定义文海在2010年之后的工作,一直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在离开故土之后,文海的纪录片创作在观念上明显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不再注重纪录片作品的结构完整性和语言经典性,而更在意一种反逻辑叙事的诗性表达,以意象的、隐喻的、内在的段落书写来构成整部作品,其构成的方式经常采用一种无征兆的硬性黏接,而这种方式的结果呈现在作品的外观上,就出现了许多“坏电影”的美学特征。
《喊叫与耳语》几乎就是一部把影像碎片再度黏合的作品,这些碎片不再仅仅限于视频,也包括动画,甚至素描、水彩、静照都成为可以粘贴的素材。即便是视频素材,也包含了许多对影像现成品片段的挪用,片中驳杂的语言程式与跳跃的图式转场,都是为展现对声音的凸现——“耳语”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呐喊”是女性民工的群体发声,而更多不同事件犹如多个声部穿插其中,成为某种即兴SOLO。
毫无疑问,要黏合如此多血缘驳杂、性质混乱的图像(动态与静态)和图形(矢量与点阵)于一条时间轴上,面对画种特性、风格样式等迥异的画面特征,基本上不可能做到无缝衔接的单纯叠化或复杂转场。在这样的境况下,“硬接”这种“坏电影”的工作方法,成为一种简单粗暴却行之有效的可能。然而,这种非逻辑性的生硬的衔接一旦达成,一种内在的诗性却意外地生成在全片的结构中。
其实,在文海的早期纪录片工作中,粗粝与生硬一直是被忽略的一种“坏电影”作品气质。《梦游》的图像噪点满屏到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黑白影调处理上的过度对比显得通篇鬼影幢幢。而《我们》的生硬转场和不讲理的衔接,几乎让人觉得无须胶水就可以黏合胶片。只是因为作品内在的诗化和观念化,使得叙事逻辑在某种尺度上奇异地达到了融合和统一。
在文海的另一部作品《在流放地》中,历史与现实的片段被粘贴为一幅巨大的影像地图:离群索居港台的第三代诗人、声嘶力竭朗诵的纽约老诗人、在希腊爱琴海边行吟与思索的艺术家、重访故土的历史研究者与书写者,以及众多身份不一的异地流亡者。为了强化某种情绪,文海会将更为生硬的意象性画面直接生硬插入,仅仅是为了强化一种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类似的有日本先锋舞蹈团在九龙城寨的肢体表演等。
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文海在剪辑成片时,内心深处激烈巨大的震荡,在很多时候他已经完全无法顾及叙事逻辑与形式转场等纪录片语言的基本方式,而是以一种信念支撑的蛮力强行推进着时间轴的向前延伸。
五
把纪录片中所有不讲理的“坏电影”工作方法归结在一起的时候,“先锋”与“实验”这样的词汇在不经意间就已经距离很近了。具有先锋性、实验性的非常规纪录片,在“内”与“外”两个方面都表现出异端倾向,其“内”是一种语言内质的“先锋性”,更多涉及哲学及其诗性的表达;其“外”是一种语言形式的“异质化”,主要是美学层面的多种尝试。某些纪录片具有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有些纪录片同时具备了两个方面。
“坏电影”的异端倾向,更多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指征,对于其“内”在观念的解析,往往要依赖于第三方的知识文本阐释。但是,很多时候,纪录片中的“坏电影” 被阐释时会出现一种谱系缺失的状态。事实上,无论其先锋属性如何匪夷所思、骇人听闻,无论其异端倾向如何离经叛道、越界出位,任何作品都是可以在谱系内找到自己位置的,关键是要被归入准确而恰当的谱系。对纪录片中“坏电影”的困难解读,最主要是体现在解析的角度和定位上,其次是对相关知识谱系的通读与通识,其中不仅仅体现在纪录片本体理论知识上,也包括更为广泛的整体的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知识上,21世纪以来,更扩展到古典电影发展的支脉——“延展电影”(Expanding Cinema)系统,以及来自当代艺术领域与媒体艺术领域的“动态影像”(Moving Image)系统。
另外一种对“坏电影”的认定方法,必须将此类作品完全从“纪录片”系统内部剥离,即便这类作品已经具有了显著的纪录片的外部形态。一旦失去了先入为主的“纪录片”身份的认证,其隐形的先锋性与实验性必将得到彰显,寻找更适合其身份的标签的可能性出现了!这种十分容易被疏忽的方法,可以称之为“谱系置换”,即将此种“坏电影”从纪录片谱系中移除,在其他谱系中重新为其寻找新的归置。一般而言,在电影史系统内可以更换到“实验电影谱系”寻找其位置,更远的可以走到更广泛的当代艺术史系统内——从古典的“录像艺术”到当代的“新媒体艺术”中都可以找到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某种具有先锋异端性质的纪录片进行归类,识别并寻找到其在相似谱系下的位置,很多时候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工作。说到底,快速定义一部“坏电影”,其实是一次对自我知识系统的极速扫描,需要在瞬间做出判别、解析、推论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思想过程。由此可见,最终定位一部“坏电影”,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跨界性、交集性、复合性都是一种难得的考量。
归根到底,“坏电影”仅仅是对生产者与研究者具有意义的一个指代名词,对观众来说,能否在“坏电影”中体验到某种受虐式的快感或厌恶感,或许才是一个关键。“坏电影”并非是关于纪录片“好”与“坏”的标准界定,而是其先锋异端的特性在电影或艺术谱系中的某个定位。
责任编辑:孟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