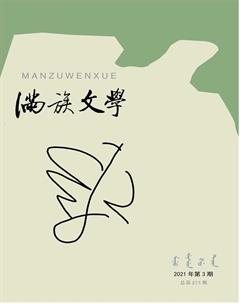大师兄
孙鹏飞
我拿了个对于我这个段位的作者来说很有分量的嘉奖,要飞去南方那个纸醉金迷的城市领。正好大师兄陈宇也在。微信上问他,他说过来接我,貌似他也在关注着这个奖。因为时间、地点我都没有告诉他,他就找来了。仪式结束之后,照例有老人鼓励我好好写,说着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哪个行业里都是有老人的。
我们的师父就是个老人。师父在晚年收了两个徒弟,陈宇和我。当然师父一生也只收了两个徒弟。
师父是个长篇小说作家,他大概两三年才写一个长篇。写完发在纯文学刊物上。或者,得不到发表。在他的晚年,精力明显跟不上,写作时间和发表周期都在无限延长着。
在当时,跟着师父学写作,一年只要两袋白面。
陈宇是大师兄,我是小师弟。师父曾叮嘱我,凡事都要听大师兄的。很多年以后,师父说,记住我的话,你远离陈宇,永远不要再跟他来往。
散场之前我终于看见了陈宇。还有不少出版人认识他这个80后新秀,他同几个人同时周旋着,我走到陈宇身边,他最后跟他们握了遍手,说着后会有期。
陈宇变化很大,梳着油头,我都有点认不出他了。
一
陈宇是我邻居,比我大五个月。我自小爱跟他玩。夏日在门口乘凉,我妈把我推到陈宇跟前,要我喊他哥哥。我不想喊他哥哥,但我妈推我,我才不情愿喊哥哥。陈宇一听,从嘴里抠出半节湿漉漉的奶糖,这是要吐给我。彼时,陈宇的爸爸因为严打进去没几个月。他家有棵石榴树,最大的那个石榴他总要留给我。我把石榴皮撕开,想跟他一起吃。我说,吃完我就叫你陈宇,不叫哥哥了。他说,不,这是哥哥给你留的,就你一个人吃。
我家里煮了玉米,我妈也叫我拿给陈宇。陈宇收到吃的,就特别大度,说,你叫我陈宇也行。他嘴上是这样说,心里还是想我喊他哥哥。隔天结伴去村口上幼儿园,他还说,叫不叫我哥哥无所谓,反正也不是亲哥哥,但是你要是叫我哥哥的话,我会当你是亲弟弟。
陈宇爸爸放出来时,村口的肉火烧铺子正在开张,陈宇爸爸给了五块钱,陈宇带我去买肉火烧。肉火烧一块钱三个,滋滋往外流着油,陈宇还从没吃过,我们拎着满满当当一塑料袋肉火烧回来时,他突然递给我,要我吃。见我犹豫他说,你吃吧,火烧买了就是吃的。我常吃肉火烧,只是看见火烧的样子,心里便知道这东西有多好吃。咬了没几口,陈宇叫我快点吃完,我说烫嘴,陈宇说,那你扔掉,快点。
村口小卖部旁边摆着台球桌子,大孩子打台球的间隙正在望着我们。
见我不扔,陈宇一把夺过来扔掉了。
大孩子走过来问我们拿的什么,陈宇说,肉火烧。大孩子不信,他问陈宇哪里拿的,陈宇说买来的。大孩子说,你爸你妈都在饭店端盘子,你们家一年到头就吃别人的剩饭剩菜,你以为我不知道。
大孩子伸手要拿,街上正好走着扛锹下地的大人,陈宇喊,你不会抢我们小孩子吃的吧。
大人往我们这边看,大孩子又把手缩了回去。
马路牙子有另一个大孩子在撒尿。
前一个大孩子冲着我眉心戳了一指头,他说,你跟我瞪眼睛呢。陈宇把我护在身后说,你别打我弟弟。撒完尿的孩子也过来了,他说,往他俩脸上吐唾沫,快点。我们没跑掉,让两个大孩子按到了地上。
二
上學那会儿陈宇嫌每天写作业麻烦,干脆不写。但是成绩却比我们写作业的要好。我爸爸很喜欢他,碰上赶集,买了包子、油条,把陈宇请到我们家里。要陈宇给我辅导功课,晚上再盛情地款待陈宇。除了我们款待他,他依然每顿吃饭店里的剩饭剩菜。都是端盘子的妈妈打包回家的。
后来学校里办了校报,老师把陈宇一篇习作推荐到校报。是一个老虎和熊战斗的小故事。印出来之后学校给了陈宇五块钱。陈宇买了甘蔗,骑着自行车载我到了报社门口。我在门口吃甘蔗,陈宇自己进了玻璃门。我隔门看里面,前台也有值班的正好站起来看我。
不到一周,稿子就发在了日报上,稿费变成了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能买好多吃的,巧克力、果冻、酸奶、麻花,陈宇见我不吃,又说那句话,你吃吧,买了就是吃的。我刚要吃,他又说,你叫我哥哥行吗?
一年后,我爸爸把我和陈宇送到了隔壁村师父家里。
师父这漫长的一生只收了两个徒弟,一个陈宇,一个我。
师父不教任何写作技巧,叫我们写了东西拿给他看。我们每次写好拿给他,他都招呼我和陈宇嗑瓜子。等我们走的时候再把稿子还给我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我们照此改。
师父爱抽烟,我和陈宇不管谁又拿了稿费,总要买两包烟送给师父。师父写作抽,阅读抽,洗碗筷也抽,跟我们说话嘴里总是翘翘地斜插着一根烟。一根刚抽完,就点起另一支。
师父家里很简单,就他自己过日子,没有太多家具,一个没门的大衣柜,一个我在电视上看见的,酷似民国那会儿的碗橱,床上、地上堆满了书。书都太老太久了,许多没有封面,页码卷了角。院子里一口土灶,一口大铁锅,临着门口一辆自行车。到了夏天暴雨季节,茅坑里的水总是往外漾。
我和陈宇就给师父刮过茅坑。
师父喜欢陈宇多过我。师父说,陈宇是灵性写作,这种人世间少有。因此,陈宇写作少,但是每一篇都是能发表的。
我写的大多数作品没办法修改。师父说,像是踏入禾苗地里,哪里都不敢踩。
后来陈宇考上了市里重点中学,我还是我爸爸交了委培费才上去的,跟陈宇分在了一个班。有一年夏天我们一人打磨一篇青春小说,投给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社。暑假里,作品发表了,杂志社出了两张动车票,请我和陈宇去北京玩玩。
那晚师父喝了好多酒,他拍拍陈宇肩膀说,你要抓住机会。又拍拍我的肩膀说,抓不住机会,就会像我一样。师父喝了大酒,又吐又拉难受了一夜,隔天起了个大清早坚持要把我们送上动车,师父眼中含着热泪。
只是文学上投入多了,功课就完全垫了底。
陈宇倒是不一样,他总是同我不一样。
三
实际上我和陈宇的生活,还有交际圈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从前我未察觉。我做功课很用功,成绩却总不理想,属于脑子不灵光的那一类人。平时和我玩的也都是一些努力保持在中上游的苦哈哈。可是陈宇不同,往来的有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也有沉到底的差生,还有常来找他玩的,几个流浪在社会的差生的哥哥。
陈宇和差生玩主要是因为网游。大概从陈宇妈妈改嫁之后,陈宇有了钱就要上网吧。多数是和差生一起去。刷地图、爆装备、打怪、升级。我也跟着陈宇去,我跟不上节奏,都是陈宇给我开个号,让我自己玩射击类的游戏,“半条命”啥的。
陈宇上网吧也不光白天,有时是睡一觉起来,叫上宿舍里几个孩子一道过去。班长并不查人,因为他自己就是班长。东窗事发是因为周一全校升国旗,我们班的大多数男生不在操场。之后,年级主任把刚从网吧回来,还趴在教室睡觉的陈宇叫到了办公室。
陈宇背着手说,我没上网。
年级主任说,不打自招,谁说你上网了?
上课铃响。陈宇说,我回去上课了。
年级主任拍了桌子,说,你跟我表演呢,你等着。他把同去网吧的陈宇同桌叫来。主任问同桌,同桌说,陈宇去网吧了,我们凌晨一起去的,早饭一起买的肉火烧,吃完回来的,大概上午八点。
陈宇对同桌的表现失望极了,像是对他妈妈的改嫁,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但陈宇只是笑。
主任问陈宇,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陈宇问同桌,你怎么不说看见我杀人了,你怎么污蔑我呢?
同桌说,我没有说谎,你承认吧。
陈宇说,是因为我成绩比你优秀,你就污蔑我吗?
年级主任说,我昨晚查夜,宿舍少了那么多人,我去网吧一看,都在网吧里呢。我都看到了,你还抵赖。
陈宇又笑,笑了好长时间,主任心里发毛。陈宇笑完说,我不是说了嘛,我没上网。您去网吧看了最好,您能证明我清白。
年级主任看着这个唇角才长出第一层绒毛的少年,愣了半晌,说,你走吧。
年级主任把事情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让陈宇把家长叫来,陈宇迟迟不叫。年级主任开学生大会的时候说,大家不要學陈宇,这种撒谎溜屁嘴里没一句实话的人,老师最讨厌啦。年纪这么小,就这么邪恶。明明去网吧了,嘴硬,不承认,以为不承认老师就拿他没办法。
那天之后,陈宇很少再正儿八经写东西。逃课成了家常便饭。他到网吧写一个玄幻小说,在国内最大的文学网站上连载。尽管师父知道陈宇写烂大街的东西很生气,陈宇依然把几十万字的玄幻故事连载了下去。有时,我买了吃的送去,他已经熬了一夜,正给粉丝发小纸条,他建了自己的小读者群,很多人给他打赏。
我给他捎来了师父的话,他说,才华放在哪里都是才华,你说呢。我也不知道他和师父谁对。他问我,你说,知道师父的人多,还是知道我的人多?
我说,你的名气比师父大。
他说,你不要学师父那么顽固。
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散步,沿着街道一直走,我们不说话就一直走,走到了市中心,又往回走。最近的路要穿过漫长的铁轨,这时候运煤的火车呼啸着驶过,灯光照亮了陈宇尚显稚嫩的面孔,他拉着我跳下轨道。火车一节一节过去,煤灰四散,我们变得灰头土脸。
四
陈宇有个不知道哪里结交的老铁,开了家书吧,他常常带我去喝咖啡。陈宇个子已经比我高整整一头,又留着长头发,安静地坐在落地窗前,用修长的手指轻轻点在书页上,桌上摆着只喝了几口,从来不见喝完的咖啡。我感觉他在摆造型,免不了有女孩子羞答答过来问他索要联系方式,他都会以挑剔的目光看看她们的脸再决定给不给。那个下午,大街上通下水道,远远近近的井盖都掀在地上,像是城市的窟窿,半个县城弥漫的都是放荡不羁的味道。陈宇叫我看一个与此情此景格格不入的女孩。
女孩留着披肩发,白净极了,身边围拢着一堆男孩。女孩大概也是高中生,也是逃课出来的。女孩见我看她,冲我们点点头。
她是从文学作品里走出来的,比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形容她就极为贴切。
陈宇说,你去,把她联系方式要来。
我犹豫,说,我可不敢。
陈宇不死心地望着那个女孩,他这一次把咖啡喝完了,重重地把杯子蹾上桌面。
下水道通完,井盖盖回去,放荡不羁的味道还未完全消散,行人掩住口鼻在其中穿行,车辆陆陆续续经过。一个男孩走了过来,走到我们桌边,他是要说什么,我看着男孩,感觉我比他还急躁。陈宇的目光不在男孩身上,还看着那个披肩发女孩,女孩也看他。男孩只是憋红了脸,僵尸一样站了会儿,又走了。
陈宇跟我说,叫你去要,你不去,现在女孩都派同学来了。
我这才回头看那个男孩,现在他同女孩坐在一张桌上。
又隔了会儿,男孩又过来了,男孩问陈宇,请问,你的联系方式可以给我吗?陈宇说,不是你要,是她要吧?男孩回看女孩,老老实实说是。陈宇说,叫她自己过来,男孩为难地笑笑,又悻悻然回去了。
女孩始终没有过来。后面的几天都没有看见女孩。高考前一个月的雨夜,我和陈宇在常去的一家大排档打牌。桌椅板凳都是矮脚的,街道很挤,饭点人很多。店前摆着小电视,在播一场篮球赛。有时是放武打录像,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我觉得陈宇恋爱了,同谁恋爱不知道,我问他,他否认了。打了几把牌,他说了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球队的名字,电视里正好在重播这场比赛。他说,你说这次比赛结果是双数还是单数,我们打赌好不好。
我看看他,说,好啊。
他说,你生活费是多少?
我说两百。
他说,赌两百,我赌双数。然后他拿出两百块钱,把钱交到一同打牌的一个朋友手上。
本来我是开玩笑,见他是认真的,现在倒进退两难了,我也只好拿出钱。
结果我输了。
五
高三下半年,陈宇都很忙,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几乎见不到人。毕业前几周,陈宇接了个私活,替企业搞一台十周年夏日晚会。他一个高中生,包揽了策划、编导、制片,出彩的几个语言类节目也都是他自己写的。
他挣了钱,同我带着两条烟去看师父。师父不喜欢他弄这些小打小闹的东西,问他,多久没写正经作品了,我在你身上怎么完全看不到灵性了。陈宇只赔着笑。但是从陈宇那里,你完全感受不到他在把师父当回事,像是年级主任开大会批判他,他在底下听时做出的样子。
师父看着他的眼睛,说是长时间凝视也不为过,最终叹了口气,说,你太聪明了,轻而易举就在俗世里获得好处,也就注定了不会把精力放在钻研上。陈宇说,师父您倒是爱钻研,后半辈子就守着两间土屋子。
我和陈宇出门的时候,师父把那两条烟扔了出来。
大学,我和陈宇考去了南方一个纸醉金迷的城市。陈宇二十岁生日那天,师父叫我们吃饭。陈宇电话里说,人在南方,没回来。其实,我们已经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骗师父。
还有就是,当时只见过一面的披肩发女孩,真的成了陈宇的女朋友。我们庆祝完陈宇生日,醉醺醺的陈宇就带着女孩走了。
陈宇出了一本书,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说是小说集,其实是迎合市场的段子同心灵鸡汤拼凑而成的故事集。他去几个大学里办了讲座。他自己还是大学生,但是他以作家的身份去大学里办讲座。
他也因为这一本段子同心灵鸡汤的故事集,当上了他们学校文学团的团长,在校外租了房子,还包了学校附近的两层棋牌室。有晚我去找他,碰到他很多朋友,有他们文学团的几个女孩,一个年轻的韩国籍导演,一个红酒供应商,一个搞装修的穿皮衣的男人。
吃完饭我们玩狼人杀。我第一次玩这种费脑筋的游戏。陈宇教我几次,我都没有掌握动脑筋的核心。后来穿皮衣的男人把牌一摔,问我,你是不是没脑子?
大家都在看我,我不说话。他说,操,我没问你话是不是!
陈宇搂搂皮衣的肩膀,又搂搂我,摸摸我的头发。陈宇说,你不要欺负我的小师弟好吗。“小师弟”三个字让我想起年代久远的“哥哥弟弟”,消失了多年的称呼。皮衣又嘟囔了一句,陈宇把烟掐灭,猛地抽了皮衣一个嘴巴。在座的都吓到了,我第一次觉得陈宇好可怕。
后来我就放下牌,不玩这个了。我说困了,陈宇叫我去睡,我回了他租的房。卧室里还有个人,我吓一跳,床上坐着个女孩子,我看清楚后说着不好意思,女孩说,你别走,应该是我走。
女孩并没有走,我只是站在门口,也没有真的要出去。
她说,我叫詹子欣。她大概刚哭过,说话囔声囔气。
她同我握手。问我,陈宇是你大师兄吧,他有女朋友了对吗?
我说有了,是一个披肩发女孩。
然后她就走了。
六
大四那会儿建新校区,陈宇联系学校后勤,包办了快递,成了新校区的快递总代理。之后陈宇推说忙着工作,把文学团团长的位置让给了詹子欣。后来很多次,我都在陈宇的房间里看到过詹子欣。那时候陈宇应该是同詹子欣在一起了,床头柜上摆着他们的合照。
詹子欣约我散步,我们沿着乌江边走边说。夏日的南方都市,气温超过三十度就要降一阵雨。雨后空气清新舒适,散步累了,坐进半山腰的茶室里,临江远眺。詹子欣问我,陈宇的前女友什么样子,你见过吗?我描述着披肩发女孩,好多与事实不相符的赞美之词都是我随意添加的。关于陈宇和她是否相爱,我不得而知。但是在我嘴里,这两个人是你侬我侬,相依为命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詹子欣失望、绝望、痛哭。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残忍念头。我只盼望一件事,就是詹子欣快点离开陈宇。
我坐在对面的靠背椅上,面前摆着夏日畅销的冰奶茶。我也像当年的陈宇,一杯饮料只喝一小口。余下的时间,便是目不转睛看着詹子欣。回去的时候,我问詹子欣,我可以抱抱你吗?她同意了。
后来还有几次,为了个中细节,詹子欣找我核实,说到陈宇和披肩发第一次开房,我慎重想了想。然后说,在家乡,我和陈宇常去打牌的那家大排档里,店前放着电视机,在播一场篮球赛。陈宇恋爱了,同谁恋爱我不知道,从坐下他就不怎么同我说话,一直忙着发短信。我问他恋爱了,他还否认了。打了几把牌,他說想同我赌球,赌单双数。他知道这边的电视节目都是重播,好像放武打片,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可是他不知道这些我也知道。我说好啊,然后他拿出两百块钱,并把钱交到了一同打牌的一个朋友手上。我只好也拿出钱。
最终陈宇拿了我的钱,同那个披肩发女孩开房了。
詹子欣对于某些细节近乎偏执,某些我不在场的环节,更是不停地追问。尽管问一次哭一次,也要问下去,直到我露出破绽为止。她是包容我的破绽的,不然不会在问出破绽之后,还要问。
她没有不信任我,反而是感激我。
毕业的头一年,陈宇出国。陈宇走后,我向詹子欣表白,她拒绝了我。
七
一年后陈宇从英国拿了研究生学位回来。
那天我同詹子欣吃火锅,又说到陈宇。越是说陈宇,我发现自己越是说不清陈宇。我说,英国读研究生只需一年,这次陈宇又比我们快。詹子欣说是啊,样子很是失落。
陈宇走的时候我帮他装的行李,他带上了他和詹子欣的照片,我告诉了詹子欣这些。我也帮着詹子欣收拾好了行李箱,送她到地铁站。之后,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好像也跟着她走了。
陈宇回来后,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有一天陈宇打来电话问我手里有多少钱。我手里那点钱交了房租,剩下的也就够过日子的。我说,你要多少。他说,我不要,师父打来电话问我要,还是我解决这事吧,师父问你要的话,你不要给他了。我问他师父怎么了,他说,师父肺部出了点问题,要做个手术。
陈宇自己出了师父的手术费。但是陈宇同时联系了师父的儿子。我一直以为师父是孤身一人呢,没想到师父是很多年前离家出走的。师父的儿子已经结婚了。陈宇让师父儿子写下了欠条,按上了手印。我回去看师父,形销骨立的师父跟我一字一句说,远离陈宇,不要再跟他来往,你听见没有,远离陈宇,远离他。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小城,师父最后一个长篇是在病床上结的尾,他要我念给他听。念了开头几句,师父打断我说,还得大改。走前,我把几千块钱压在师父枕头底下,师父醒了,拍拍我的手背。他说,你好好写吧,那将是你的一切。陈宇已经失去灵性了,他不可能有更大作为了。
像是暗暗同师父较劲儿,师父说陈宇不会有更大作为了,他年底就当上了南方林业局的一个正科级部门负责人。那晚大家聚在一起庆贺,饭桌上陈宇话很少,只忙着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女领导夹菜。大家走后,陈宇跟我说,我这次玩大了,把自己陷进去了。我问他怎么了,他哭了,像是每一个为他哭泣过的姑娘那样痛哭。
不到半年我收到了陈宇结婚的请帖。再半年,师父去世,陈宇回来献花。陈宇胖了,圆润了。我们吃饭时,我总感觉他提不起精神。他的电话一直在响,接起来几乎是歇斯底里对着电话吼。我们劝他,有了家庭就不一样了,忙的话就先撤吧。他眼睛红了一圈,等了会儿又打回电话去细雨呢喃地解释。我们都傻了眼。
酒越喝越多,他举着吃光了的菜盘,问一个面容姣好的女服务员,可不可以给我們续一盘。
服务员没明白他的话,他说,就跟咖啡续杯一样,吃完了菜,你给我们续上,续盘。
服务员只是笑,他摸摸服务员的手背,服务员笑得更厉害。他说,你笑啥,做不了主,就叫你们经理来。
他和服务员一同出去了,也没告别,之后就没再回来。
八
有两年陈宇什么动静都没有。直到我拿了这个奖,他来接我。他梳了个油头,开着兰博基尼来的。看得出来他很看重这个奖,在路上他问我能不能买我的奖杯,我说送你吧。他说,奖杯上有字,我要把字销去。回去我转账给你。
本来我要住酒店的,他说家里有地方。他家里确实有地方,住的是三层小别墅,车库比我刚买的房子还大。车库角落里堆满了没拆包装的书,用一张不够大的帆布盖着。看我感兴趣,他说你能拿走都是你的。我挑挑拣拣,里面还有他当年出的段子同心灵鸡汤故事集,还有一张蒙了灰尘的合照,这也是他和詹子欣唯一的一张吧。我把合照放回去。
他家里也比我想象中的奢华,他得到的,是我再拿十个奖再乘以十,都难以企及的。他妻子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们并没有站起来,像我以为地跟我问好,点点头或者握握手,之后拿拖鞋给我换。她只是坐着,像个木偶。
她抬头看陈宇,说,你什么意思,合着要我守活寡呢。
陈宇看了看她,没搭理。
我跟着陈宇进了卧室。
他说,你洗澡吧。他把浴袍、毛巾递给我。
我觉得他妻子面熟,这会儿想起来了,就是在他的升职宴上,他一直给夹菜的那位女领导。
他说,我最近也要写点东西,我要捡起来,真的。你快去洗澡吧,洗完我们好好聊聊。
他妻子推门进来,暖黄灯光下,依然感受得到他妻子的老态,泪水湿过的妆容依然精致着,大我们十五岁或者二十岁的样子。她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回,我们谈谈。
陈宇说,谈个屁呀。
我要去洗手间,他妻子抢在我前头挡住门。
她说,这是你朋友吧,当着你朋友不太好,但是我得让他知道,让全世界的人知道陈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宇像是满怀期望地看着妻子,问她,说呀,我是什么人。
她呸了陈宇一口。
陈宇扶扶眼镜说,说吧,愿闻其详。
她说,你真是无耻,真是恶心,你是最恶心的人。不是想离婚吗,有本事就跟我离婚,到时候看看谁求谁。
陈宇朝我笑笑,厚底眼镜里面的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如今藏进了密密麻麻的鱼尾纹里面。
陈宇也老了,和年龄不相称的衰老。
我又想起詹子欣,如果现在是她出现在这个家里,又会是怎样。
隔天我醒了个大早,陈宇在给我煮咖啡,油头比昨晚要油亮。那个大我们十五或者二十岁的妻子心情好了很多,还把咖啡碟端到我面前,请我慢用。之后她娇哒哒地拦腰环抱着陈宇,真的像是一对模范夫妻。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陈宇累了。他应该是很累了。
我想起上学时常常错的一道题,一百度的水和一百度的水蒸气哪个更烫人。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百度的水。但是,错了,答案是一百度的水蒸气。水蒸气会液化成为水再烫你一次。
我要说什么呢?好多事情看着像一百度的水,实际上是一百度的水蒸气。因为它更烫。
离开他家之后我才想起奖杯还放在他家客厅的茶几上。
【责任编辑】李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