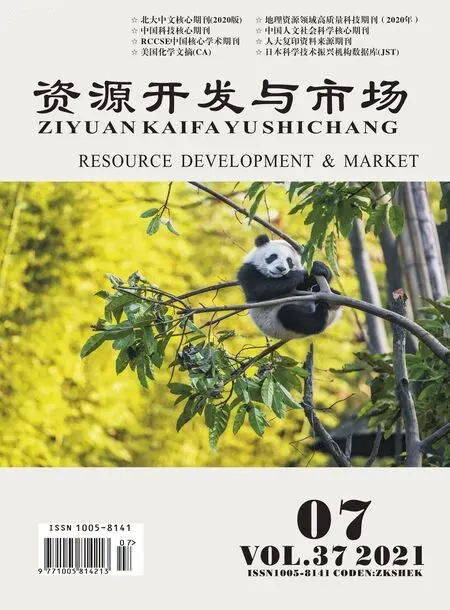人地关系视域下山地户外旅游地“三生”空间演变研究
——以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为例
谭静,明庆忠,李佩聪,龚剑,刘勇
(1.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0100;2.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昆明650221;3.四川旅游学院运动与休闲学院,四川成都610100)
随着旅游业市场的不断细分,2020 年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鼓励各地全面推进体育旅游、山地旅游、户外旅游等旅游业态开辟新的发展模式。目前,山西、陕西、四川[1]等山地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始打造以山地户外运动为核心的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山地户外旅游作为国内新兴产业,与传统观光旅游相比,要求参与者对其参与的项目具备最基本的技能基础、理论基础和一定的身心素质,更侧重于运动探险类型,具有体验性和一定风险性[2]。与此同时,山地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规划以山地户外运动为核心的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时,迎来人与地方环境、人与经济、人与资源三层关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过程。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空间”和“地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与“环境”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载体[3],而这类旅游目的地带来的空间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发生了变化。同时,“地”由原来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要素变为生产—生活—生态交融复合功能的统一体,“人”和“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人地关系是指一定生产和社会背景下的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4,5]。国外较早地开展了人地关系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基础理论的认识,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物质流模型、生态足迹、能值分析、生态效率、数理统计、综合集成评价等模型和方法的定量研究方法[6]。国内研究在借鉴国外人地关系思想演变和理论的基础上,对人地关系思想内涵发展[7]、旅游人地关系理论[8,9]、从空间维度对不同地域人地关系演变的分析与评价[10,11]、资源地可持续发展[12]等展开。当前人地关系研究侧重于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一定地域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状态及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估[8]。“三生”空间指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国内关于“三生”空间的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是乡村聚落[11]、城镇旅游[13]、国土[14]等研究内容,以及“三生”空间的格局演变与优化、空间功能的转化[15]、空间重构[16]等方面。
结合人地关系与“三生空间”演变的研究范围,目前对于海岛、城市景区、乡村旅游聚落等地的研究较多,但已有学者提出展开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实现山地旅游与人山关系地域系统、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17,18]。因此,本文以山地户外运动为核心内容打造的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区为例,结合人与地方环境、人与经济、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对案例地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以期丰富人地关系研究领域,并为未来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区“三生”空间打造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山地户外旅游地空间演变的影响过程
人地关系对山地户外旅游地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演化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在人地关系中,地域内人与地互动的过程促进了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的形成与演化。基于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的出现、演变与未来空间重构发展的过程,其影响主要通过产生、进化和多样化塑造3 个方面的作用形成:①产生作用。山地户外旅游空间产生的本质是人地关系中人主观能动性与综合需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山地资源丰富地区,传统畜牧业、农业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通过对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不断利用,人类生存需求需要的集聚性空间逐渐形成。②进化效应。输入性人口数量和集约型生活空间的组成,对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的需求在增加,生产力水平反映了综合利用和转化自然资源的能力。人地要素的属性中,“人”与“地”之间的动态变化改变了人地互动的方式和深度,影响了山地户外旅游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推动山地户外旅游空间演化。③多样性塑造。从“人”与“地”互动过程与协调发展出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生态自然环境中的地域性特征和影响的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人地关系下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的多样性。受人类社会、文化、信息和其他因素影响,人们选择适当或过度的方法来规划和改造自然环境,以形成山地户外旅游的规模结构、资源利用和内部生活的多样性。
2 四姑娘山概况及户外旅游发展
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境内,属邛崃山脉,地理座标为102°42′30″—102°58′40″E、30°54′16″—31°16′21″之间,属于第二阶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区内山势陡峭,现代冰川发育。四姑娘山总面积约1375.85km2,其中对外开放面积450km2,最高峰海拔6250m,最大高差为3500m,有61 个雪峰海拔在5000m,有120 多个瀑布和多个超过3800m 的小湖泊。四姑娘山是一个集旅游,登山,远征,穿越,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山岳型自然旅游资源地(表1)[19],海子沟、双桥沟、长坪沟现已开发了许多户外活动产品与徒步线路(表2)。在地理交通上,成都至四姑娘山的整个行程约为220km,随着2016 年巴郎山隧道全面贯通,两地之间出行时间已缩短至3h,极大地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20]。

表1 20 世纪90年代以来四姑娘山所获荣誉称号

表2 四姑娘山山地资源开发现状
在过去的20 年中,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区吸引了约150 万人次游客,门票收入超过7500 万元。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四姑娘山现已成为川西地区众多旅游环路的重要节点和集旅游、商贸、山地户外运动体验式参与为一体的四川省重点旅游区。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推动下,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资源得到了持续性的开发与利用,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专项客源市场,但这个过程中人与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使得四姑娘山传统单一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生了一定变化,如何科学合理的对空间进行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和未来需要重视的问题。当前,四姑娘山的发展和变化因其地域上和资源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山地户外旅游空间发展的一般阶段,因此选择四姑娘山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探索人地关系视域下山地户外旅游地空间演变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3 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空间演变
3.1 生产空间由农业型转向旅游服务型
四姑娘山生产空间经历了从原始畜牧业、农业主导型向旅游服务第三产业主导型空间转型。20世纪90 年代以前,四姑娘山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与外界接触较少,生产活动主要是以采集狩猎、畜牧业、农业自给自足为主要形式。由于四姑娘山属于高原地区,该地区以养殖牛和羊为主,农业以种植青稞、小麦等作物为主,单一的传统畜牧业、农业生产空间一直延续到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进入才逐渐发生变化。1982 年,国务院指定四姑娘山为全球十大高级攀岩运动场馆之一。随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登山队在四姑娘山进行了相应的山地户外活动,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发展雏形开始形成。2007 年成立四姑娘山登山培训学校,2008 年成立四姑娘山户外运动管理中心,其户外运动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为整体空间布局带来了巨大变化。首先受益的是四姑娘山镇的村民,村民可以直接参与部分常规和非常规的山地户外旅游服务工作,使当地村民生计方式逐渐发生了转变。目前已有较多的持证高山向导和高山协作人员,这类职业作为非常规就业的主要群体,他们可以直接与外来游客接触并受益。伴随着游客量的增大和外来经营者的不断参与,农业用地减少,本地村民就业模式呈现出从旅游服务者向旅游经营者的转变,生产方式也逐步从农业和畜牧业转变为旅游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2016 年至今,四姑娘山着力打造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发挥旅游主导作用和充分利用山地自然资源的同时,对户外活动项目的空间结构规划在逐层推进。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四姑娘山风景区管理局对山地户外运动项目进行了分级,根据运动强度与难度的不同打造“一心、一带、三区、两线、多节点”的活动空间(表3)[21],这个阶段的山地户外旅游生产活动空间特征呈现出由单一的登山观光旅游向综合服务的深度体验式模式发展趋势。

表3 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结构转变过程
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四姑娘山的餐饮、停车场、商店和旅游配套设施等商业活动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村落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弱化,依托山地户外运动打造的山地户外旅游生产空间的效益更加突出(表4)。据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统计,2019年四姑娘山共接待游客19.98 万人次,门票收入1152.11 万元,分别较2018 年同期增长了10.53%和5.68%。山地户外旅游区中,大部分村民均在从事山地户外旅游相关工作,生产空间演变中第三产业服务功能态势较为明显,从而导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迎来变化。
3.2 生活空间由传统集散型转向集聚型
20世纪90 年代以前,四姑娘山镇因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的制约,聚落空间形态变化稳定,扩张缓慢,地域上总体人少地多,实现了居住、农业、放牧和森林空间的统一,形成了原始藏族村庄定居空间的原型。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山地旅游业的发展,四姑娘山旅游区居住方式、生活空间、社会关系等由传统集散型转向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集聚型生活空间。
居住方式上,四姑娘山广泛分布的石砌碉楼是极具藏族特色的传统建筑。20 世纪80 年代,四姑娘山生活条件与交通方面相对落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渐提高,私人生活住宅、水厕、太阳能热水器等现代化生活用具逐渐普及。本地人为了更好的收益,将房屋和土地对外来人进行租赁,外来人口则对宅屋进行改造成半传统半现代化形式的民宿酒店等居住场所,在打造时保留了部分藏族传统风格。随着混合式藏式民俗和家庭旅馆之类的住宿方式出现,传统的住房功能逐渐被旅游服务接待功能取代,其居住功能更加丰富,住宅功能由生活居住功能向旅居复合功能转变。

表4 四姑娘山旅游产业集聚区生产功能
生活空间上,大多数人的私人居住空间减少,半私人或半公共空间增加。传统的石砌碉楼是四姑娘山传统聚落的私人空间,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在旅游业介入之前,房屋只是居民生活和邻里交往的载体。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输入性游客数量增加,四姑娘山居民积极参与山地户外旅游服务业相关工作。随着生活空间多样化,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的户外旅游购物超市、餐馆、民宿等出现,为了提升四姑娘山镇整体山地户外旅游风貌与特色和解决旅游旺季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宅屋主人在政府的指导下对房屋生活空间进行了改造,增加了空间供给,以此提高游客居住区的旅游接受能力和整体结构,生活空间从原来的私人居住空间转向生活—消费空间。
社会关系上,随着四姑娘山镇山地户外旅游的发展,商务活动频繁,当地居民参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四姑娘山自身山地资源的优势和众多山地旅游产品的打造,助推了游客和外来经营者数量的增加,社会关系从封闭和内向型关系转变为更加开放包容型关系;交往环境也从以邻居为主导的熟人环境为基础,增加了游客和外来从事旅游业工作的多元交往环境;交往空间由当地和邻近社区扩展到周边城市,提供了更多开放和多样化的交流空间。
3.3 生态空间由单一型转向多元复合型
四姑娘山镇位于高原干旱河谷地带,四周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生态较为敏感。据统计,四姑娘山镇林地、牧草地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70%,其次为自然保留地。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四姑娘山为了满足外来的人口承载力和一定的生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动植物、冰川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小金县四姑娘山镇总体规划(2014—2030)》,对于生态环境在旅游开发中呈现的问题,景区对生态空间进行分级保护,全镇有大部分土地都处于受保护等级较高的保护范围之中,可用于适度建设的土地资源较少,主要表现在山区村落聚居空间扩展和景区开发(表5)。

表5 四姑娘山旅游区生态保护分区
因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扩张,生态用地不仅承担着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基本生态功能,还因发展山地户外旅游的开发需要,成为旅游活动的载体,形成生产—生态复合空间。
4 山地户外旅游空间演变的综合分析
从人地关系驱动过程分析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空间演变,更能反映出旅游发展与山地户外资源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现有资料整理出四姑娘山旅游发展和山地户外资源开发的发展历程(表6),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基本形成4 个阶段。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下,以人类活动为中心展开与“地”的互动方式在空间发展中越来越密切,呈环境—经济—资源3 个层面的发展特征。

表6 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空间发展历程
4.1 农旅结合下生产活动协同发展
四姑娘山多元化的自然生态资源为山地户外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山地户外项目主要体现在陆域、水域、空域三大空间结构。20 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游客进入四姑娘山,居民不仅可以依靠传统的畜牧业和农业产生经济收益以外,还可以利用山地户外旅游所提供的非常规就业或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来丰富经济来源。据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统计,2020 年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区可提供直接就业岗位约1000 个、间接岗位2000 个,大大缓解了小金县和四姑娘山的就业压力。基于旅游服务的第三产业将继续成为该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并决定着四姑娘山镇乃至日隆—达维—美兴城镇带的发展。
目前在四姑娘山主要沿线村落中,长坪村位于四姑娘山镇和景区集散型游客接待的核心位置,对比其他4 个村寨在地理位置上、经济生产水平、空间接待力上具有突出的优势。未来在四姑娘山及周边交通布局的改善下,参与山地户外旅游人数将面临激增的趋势,人口聚居规模如何达到一定规模承载力,这就需要逐步协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地”的科学利用与开发,逐步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以此实现山地户外旅游空间发展的产业形成,保持经济生产活动的活力,促进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
4.2 协调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治理模式
随着四姑娘山农牧业生产向第三产业的转变,人与地方环境在空间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人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和排污对旅游地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并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早期的山地户外旅游游客和从业者的素质层次不齐,对“无痕山野”的环保意识未形成,导致经济生产过程与生态过程深深交织在一起,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预测,综合考虑极限户外活动项目的特殊性和停留时间,2021 年四姑娘山户外活动游人容量为49.47 万人次,预计游客人数达到5.06 万人次以上,项目地户外活动游人年环境容量49.47 万人次>预计户外游客人数5.06 万人次。容量与参与人次之间呈现正向趋势,在考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获得的机遇条件及需求的同时,还需考虑保持现有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确定及使用用地容量,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待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在完善基础设施时还需对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以提高居民和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3 未来山地户外旅游空间发展趋势
人地关系的协调和优化最终需落实在具体地区实施。不同地区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经济和社会条件各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优化人地关系。重视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山地户外旅游空间有序生产与重构,以更好地应对与平衡未来空间演变所带来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击与压力[22]。对于四姑娘山现有的山地资源与旅游业开放程度,其山地户外旅游生活、生产、生态空间会随着游客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为了实现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的可持续利用,生产空间可形成以农牧业和山地户外旅游结合下的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融合空间。而以旅游为主的生产空间会随着需求的增长而不断扩展,呈现产品多样化分级明显、服务标准化明显、非常规就业人群减少等趋势。生活空间除四姑娘山镇的几个主要村落居住以外,可适当向海拔更高、道路沿线相对便利的村落延伸发展。同时,可在完善人居环境的基础上提升基础公共设施建设质量,加强具有四姑娘山嘉绒藏族特色的居住环境和民族风貌为导向。对于生态空间需注重对生态承载力的合理评估和规划,应加强对各级层自然区的生态修复,环境的综合治理,实现四姑娘山生态空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整体的生态保护。
5 结论、建议与讨论
5.1 结论与建议
山地户外旅游地域内人地要素的互动促进了其空间的形成和演化,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区的“三生”空间实际上是由于生产空间变化,带来了生活空间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生态空间。主要结论:①“三生”空间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演变。其中,生产空间由原始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向旅游服务第三产业空间转型;生活空间在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下,从原始高原村落的集散分布向现代集聚型空间转变,主要体现在旅居混合的居住模式、居住空间的开放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生态空间则由单一生态空间向“生产—生态”复合型空间发展。②空间形成阶段,四姑娘山以山地户外运动为核心项目发展,在主客体的参与下持续性从事第三产业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其山地户外旅游空间形成可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基本形成4 个重要阶段。③未来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空间应朝规划高效的生产空间、极具特色的旅居融合生活空间、综合治理的生态空间方向全面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生产空间遵循发展规律,产品服务优化升级。扩大不同人群的体验活动区域,优化不同级别的山地户外运动产品,完善山地户外旅游服务标准,重视山地户外运动从业人员培养和梯度建设,实现高效集约的生产空间。②提高生活空间质量,主客互动展现地方特色。注重山地户外旅游接待过程中主题民宿、餐饮等与嘉绒藏族文化的融合;主客互动交流的公共空间中加强对地方民族文化的输出,实现旅居融合的生活空间。③生态空间注重修复与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对不同级别的保护区进行有效的平衡与保护,加大对居民、游客“无痕山野”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构建适用于山地户外旅游发展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开发有度、保护有效的生态空间。
5.2 讨论
伴随旅游经济的介入,打破了四姑娘山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地理状态,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不断促进山地户外旅游演变与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处理好山地户外资源开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推进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可根据四姑娘山聚落的地理区域特征、人文历史背景、资源差异性等,因地制宜采取实施策略。本文对于研究人地关系视域的山地户外旅游空间演变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价值,是对山地户外旅游空间的多元化协调发展的初步探索。在人地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如何对空间结构的重建方法和机理,以及未来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与影响将在下一步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