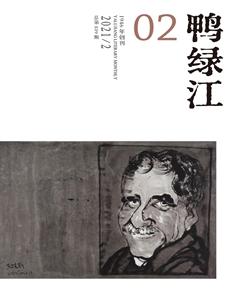桃花引(短篇)
井得水和韩常萍的相识很偶然,朝阳镇请井得水去讲课,给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讲一讲诗歌。为什么请他呢?原因很简单,井得水自己写诗写了很多年,在圈内小有名气。另外他爱人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家族产业,董事长是她的亲哥哥,家里不缺钱,深知自己的丈夫有“这口累”,便出资在出版社办了一个“套书号”,让丈夫办一个叫《八风阁》的诗歌季刊。在此说明两点,一是“这口累”属东北方言,“累”字读三声,意思是“这个瘾”;二是“季刊”,也就是一个书号,用不了多少钱。出四本《八风阁》,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的CIP数据是独立的。说是季刊,其实在出版社那里体现的就是四本名字有关联的书而已。至于《八风阁》,有点诗歌常识的人都知道,出自苏子的诗,所谓“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井得水去朝阳镇讲课,所讲内容早已轻车熟路。他最喜欢讲的就是两点:一个是诗歌的“造境”,在他的体会,也就是意境的本质存在,这在诗人本身是最需要主观性和绝对自觉性的;还有一个,他喜欢说,好的诗歌一定是“意”“表”结合,过于“表象”的诗歌是顺口溜,过于“意象”的诗歌是胡说八道。按说他的这套理论,在朝阳镇已经讲过不下七八回了,几乎年年去讲,有时一年还讲两次或者三次,但每次去讲,仍然有许多以前听过课的文学爱好者向他提出许多以前就提过的问题,他认真回答,提问题的人也认认真真地记在同一个小本子上,就像一个公式,人有了公式,也就形成了惰性和惯性。
韩常萍是第一次来听课。
六月是北方最美的时节,满目青绿,生机盎然,井得水一点儿也不否认,他的心情很好。新一期的《八风阁》刚刚出版,此时“春季卷”就放在他车的后备箱里。在这一期刊物里,有一个“朝阳镇诗歌小辑”。朝阳镇的许多诗歌爱好者的作品位列其上,这也是朝阳镇又一次热情邀请他“莅临”的主要原因。井得水讲课,喜欢背书,所取内容在他看来便是佐证。每每有学生提问,这些佐证便是最好的回答。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有一点年纪的人了,记忆力大减,不如当年那样“一目一行、一目三行、一目十行”之后便口若悬河。
为了这次讲课,他新背了两段文字。井得水讲诗歌,但他所援引的“佐证”皆出自小说,就是一种癖。至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别人更无从得知。有时“学生”或朋友问急了,他便顾左右而言他地解释,说自己潜意识里可能是一个写小说的,可是小说太难写了,所以改成诗歌,不承想一写而成名,博得诗坛留姓名。这于他是鬼话,但对于发问的人却深信不疑。
他新背诵的这两段文字是针对一个叫“名落孙山”的作者的,这个作者就是韩常萍。《八风阁》的“朝阳镇诗歌小辑”里没有选韩常萍的作品,韩常萍为此打电话询问他,口气当然是有点生硬的,甚至有点气恼,更甚至有点气急败坏。
韩常萍问他:“井老师,你能和我说一说不选我的理由吗?我感觉你所选的人当中还有不如我的呢。”
说实话,井得水有点尴尬,因为在一个有“职业操守”的编辑的解题库里,这类问题真的不好回答。他在电话里沉默很长时间,说:“是这样,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会给出最标准的答案。”
井得水以为韩常萍会有更激烈的质问井喷而出,谁知韩常萍在电话那端“扑哧”一声笑了,语气无比客气而温柔地说:“井老师,我服了,您真是个诗人,什么时候来朝阳镇,我请您吃饭。”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此事不大,歷时不长,前后不过几分钟,但井得水感到自己受到了挑战和侮辱。
朝阳镇请他去讲课,他第一个想到了韩常萍,他不知道这个韩常萍会不会来听课,但不管她来不来,井得水都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复仇机会。他要把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案例,既可以丰富一下课堂的内容,又可以光明正大地报一箭之仇。于是,在“备课”的过程中,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他翻检他杂乱无章的藏书,从中找到一本日本“泛80”作家森见登美彦的小说集《奔跑吧,梅洛斯:新解》,拆了塑封——买了很长时间,一直未读——胡乱读起来。先读首篇《山月记》,开篇文字如下——
“京都吉田一带有一孤傲学生,他的盛名只有部分相关人士知晓。
“其名曰斋藤秀太郎。
“他住大文字山脚下的法然院附近的一处木结构廉价公寓里。兴起时便会顺着哲学之道散步,日日醉心思辨。他以香烟、咖啡和卧游为乐,也研究过厕所窗户上壁虎脚底板的奥秘,还尝试过蜈蚣泡酒,为此差一点一命呜呼。他嗜秋刀鱼为命,为品尝秋刀鱼的美味,曾在阳台上架起炉火炭烤,险些将租来的房子付之一炬。
哪怕冒着烧毁房屋的风险,秋刀鱼也非吃不可。除此之外,能让他慷慨倾注热情的就只有文章了。杯盘狼藉之事在他身上少有发生,恋爱游戏修取学分这等俗事他也不屑一顾,写出一部妥斯托耶夫斯基那样的大型长篇小说,这才是他的目标。他写了揉揉了写,心无旁骛。至于读者,尚无一人。”
这篇小说他并未读完,“至于读者,尚无一人”八个字让他极度兴奋,他有点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读这个短篇,如果早点读了,那天回答韩常萍的问题一定会游刃有余。不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此次去朝阳镇,在讲课开端,他要不点名地提他和韩常萍的这段公案,然后声情并茂地背诵《山月记》的开篇。再然后,非常宽宏大量地以诗者兼长者的身份及气度告知在座的每一位,说:“给生活以时间,纺出你们看不见的生命金线。”
春风得意马蹄疾。
心情好是必然的。
在去往朝阳镇的路上,为了表述无误,他特意用百度查了一下《山月记》的作者——中岛敦,日本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山月记》等。
他因为自己的“严谨”,又添了一份对自我的信任和尊重。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儿,他的这次讲座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开篇的备受欢迎显而易见,全场爆发出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他也礼貌地站起来,向下边一行行、一列列期盼的目光频频致意。
讲座之后是例行的招待宴,在镇上最好的饭店,不大的包房里挨挨挤挤坐满了一桌男男女女。主办者介绍当地作者,特意介绍了一位美女——应当是美女,个子不高,梳短发;皮肤有点黑,但润滑而泛亮;眼睛不大,弯弯的,一笑像下弦月;唇痕饱满而清晰,说话的声音略哑,初听有点像某明星,但细听要比她更加瓷实,略带一点金属音。
主办者说:“韩常萍,我们镇的文学新兵。”
说实话,井得水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为此他的脸未酒而热,汗珠从额角滚滚而下。
韩常萍幽默地说:“井老师也脸红啊,真是一个可爱的大叔。”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大家抢着互相倒酒,彼此布菜,推杯换盏,一派欢颜。酒过三巡,主办方打趣,把自己的位置与韩常萍交换,口中一连声地叫着:“美女,美女,你来,我坐在这儿老师喝不进去酒,你过来,过来陪老师多喝几杯。”
韩常萍也不客气,大大方方地站起身,挨个儿从众人的后背挤过来,一扭腰就坐到了井得水的旁边。这种颇为暧昧的玩笑让现场的气氛更加轻松。一圈儿酒已经敬完了,酒局进入到单打独斗的阶段。韩常萍给井得水敬酒,井得水痛快地喝了一杯。敬第二杯的时候,井得水有点犹豫,不想韩常萍在桌子下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攥着。第二杯酒给喝了,接着是第三杯。从这一刻,俩人的手几乎一直握在一起,井得水感觉韩常萍的小手柔软而温热。
那天井得水喝多了,在回程的车里,他沉沉地睡了一路。
第二天酒醒,他就接到了韩常萍的微信,先是问好,之后是问身体情况,是不是进入了“一日饮,一日醉,一日病酒,三日不朝”的状态。井得水有点头疼,起身动作大了还犯呕,但他坚持着用尽量幽默的语气给韩常萍回了一条微信,说:“廉颇虽老,尚能饭,且一日一遗。”韩常萍回了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他回赠了三朵玫瑰花。
他爱人的公司今天有例会,要求穿正装。他去卫生间,看见爱人一身严肃地在照镜子,左扭右闪的,颇有几分风情。爱人的正装是黑色的,白衬衣,小翻领的西服,下身是一步裙,高跟鞋,让她腰身比平时显得更纤细了一些。最主要的是长筒袜,肉色的,把爱人的肌肤修饰得格外诱人。井得水突然有了冲动,卫生间也不去了,像个小伙子似的,说白了更像个强奸犯似的,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粗暴地扒去爱人的衣服,强按在沙发上尽情地疯狂了一把。
这在他们夫妻之间已是两三年没有的事儿了,爱人娇嗔地——这个年纪的娇嗔实在不美——捶打他,说他弄皱了她的衣服,耽误了她开会,但眉眼间还是湿润的。从沙发上起来,井得水去了卫生间,他失去力气一般地坐在马桶上,长长地撒了一泡尿,心底泛起巨大的无聊和忧伤,同时还有一点自责和恶心。他承认,在他和爱人的最后一刻,他的脑海里出现的是韩常萍的影子,心里默念的是韩常萍的名字。
井得水写诗之后有过几次婚外情。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对方也是一个诗人,在他的“道德史”上,这一次刻骨铭心。那时他三十几岁,刚结婚没几年,孩子很小,应该是在幼儿园大班。那时最流行的一个词叫“七年之痒”,他大致明白是什么意思,但骨子里不愿意更深刻地去承认它、理解它、感悟它。女诗人比他大两岁,和他是同乡,当时正在邻近城市的一家文学院进修。他鬼使神差地去看她,一个人坐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每当火车穿过隧洞,他就会想起女诗人写的一句诗:火车一进入山洞,我的欲望就开始骨质增生。他视这句诗为神来之笔,特别想知道“骨质增生”能给欲望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欢乐,或痛并快乐着。他按捺不住自己,被这隐喻迷惑,他双手颤抖地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想去拜访她。现在想来可笑,為什么选择“拜访”一词呢?弄得双方都很高尚似的。那个女诗人姓房,叫房芳。房芳听了他的电话,很诗意地,也很哲学地回答:“蓝天依旧是蓝天,江河依旧是江河,出发依然是出发,死亡依然是死亡。出发是死亡的护照,死亡是出发的证明。”他瞬间凝固了,像一尊风蚀的塑像,他磕磕巴巴地和爱人撒了一个谎,马不停蹄地登上火车。他和房芳见面了,也在一起喝酒了。说实话,迄今为止,如果让他在他现有的生命旅程中,找出一个比房芳更丑的女人,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当时,他不可救药地被她迷住了,她身上的光环笼罩着他,他把她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圣旨,是女王的命令,女王让他吃一坨狗屎,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吞咽下去。房芳显然是在酒后接待的他,头发散乱,睡衣的外边披了一件军大衣,光脚穿着一双皮鞋。她手里拿着一支钢笔,不时地把它叼在嘴上,说话的时候,一边的嘴角往上扯,仿佛要和眼角的皱纹连成一线。他猜想,她是知道自己这点缺陷的,因为她照镜子的时候,总是努力微笑着,说:“这是一道无解的几何命题。”于是,他们又喝酒,喝完酒去骑摩托车——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拥有一辆摩托车,他们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在近郊的大路上飞驰,像两只收拢了翅膀的鸟儿。然后,他们跌倒了,跌倒在路边的壕沟里,摩托车的车轮在那里兀自空转,他们两个人却叠加在一起,一个出示护照,一个开具证明。当他们彼此抽离了自己的身体时,灾难一般的恐惧包围着他,他衣衫不整地走到火车站,用了整整七个小时。事后,他长时间拒绝和爱人行房事,并几次在深夜爱人熟睡的时候,跪在爱人的脚下向她忏悔,又几次想以书面的方式向爱人坦陈此事,但最终魔鬼的自尊和侥幸的心理让他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小心地以常态的善良装饰自己的生活,但有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是一个有污点的人,而他的污点的证人就是他自己。房芳自杀了,自杀之前焚烧了自己所有的手稿和笔记,她只留下了那支钢笔,压在一张纸条上,纸条上写的是她的遗书,只有一行字——“这曾是我的自慰工具,但我并不想带走它。”
井得水有点悲伤。
他第二次往自己的污点上涂墨又是什么时候呢?
他自己记不清楚了。
除了房芳,他记不住那两三个人的名字,但有一点可以记清,那就是每一次经历同一类事之后,他都会陷入巨大的无聊和忧伤,相伴左右的还是自责和恶心,就像刚刚和爱人完事之后一样,这种情绪让他一遍遍发誓,一定要把自己洗干净,否则近乎抑郁症的自虐使他绝望,并使他卑微的灵魂在欲念面前瑟瑟发抖。
但是比绝望更绝望的是——他又有了下一次。
比卑微更卑微的是——他没有勇气拒绝“它”,并且乐于屈服“它”带给他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以及短暂的幸福感。
“啊!这是多么微妙的一种心理啊!”
他自嘲地又一次原谅了自己。
和韩常萍有了联系之后,每天早晨问候形成了例行的礼节。渐渐地问候里边带了内容,韩常萍不时地会把日常的生活照发给他,并且向他索要他的生活照——更多的时候是工作照,韩常萍说他工作的时候有一种格外的魅力。韩常萍的赞美总会让他不自觉地调整一下坐姿,竭尽全力地维护这种赞美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韩常萍给他来发了一组诗歌,他着重看了一遍。韩常萍在微信里告诉他,这组诗里包括她从前寄来但未被发表的那两首,但井得水分辨不出来是哪两首。井得水突然觉得韩常萍的诗歌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在朝阳镇那一帮写诗的人里边,她的诗歌也是很有特点的。
他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韩常萍。
韩常萍的笑脸变成了一排。
当然,他的玫瑰花也变成了一排。
有一天,韩常萍发微信说:“听说你喜欢吃果儿,什么时候来吧,我带你去乡下采摘。先是杏,然后是李子,然后是海棠,老秋了还有香水梨和小山桃。”
他说:“那不得去好几趟。”
韩常萍说:“来呗,我又不嫌麻烦。”
他说:“哎呀妈呀,那帮鬼还不得把我喝死。”
韩常萍说:“你不会不告诉他们,就咱俩。”
这话里就藏了话了,井得水想了半天,没敢直接应,只回这两个字:“哈哈。”
对方回的是:“呵呵。”
井得水准备在《八风阁》的“秋季号”上给韩常萍发一个小辑,照片、简介,加上至少三十首诗歌,然后再配上他亲手写的一篇评论,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根基并不扎实,就有意开始恶补。他去图书馆、书店找来大量的诗歌评论家的种种文字,从中寻找灵感和一些彰显文章力度的词,比如吊诡、蹈雪、灵魂缺失、向度、维度、精神层面、物质对调……这些词汇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他觉得自己对诗歌的认知和释解上升了一个空间,而且这个空间与时间是并行的。
七月初,韩常萍告诉他,杏子下来了,再不来就落了。
但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七月末,李子下来了,韩常萍告诉他,李子尖儿红了,甜酸适度,等都熟透了就不好吃了。
但他觉得他还是没有准备好。
其间,他们微信往来颇为密集,有时半夜也会发了一条。内容无外乎:“你睡了吗,有点想你了。”要么就是“么么哒!”“抱抱!”话已然说到这种地步,两个人想达到的关系以及关系的程度可谓一目了然、心照不宣。所以不必再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至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那简直是真真切切的故弄玄虚、自相矛盾了。
八月中旬,韩常萍说:“我们山里最好的季节来了,而且海棠到了最好吃的时季,我盼着你来,去山里的小屋住,我陪你好好喝点,往死里弄。”
显然“往死里弄”是双关语。
至少在井得水听来如此!
井得水去朝阳镇了,他不是第一次去朝阳镇,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去朝阳镇,而且今后去朝阳镇的频率也许会比以前更高。他没有给朝阳镇的朋友们打电话,而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韩常萍在约好的地点等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戴着一个大散檐儿的帽子,手腕上缠了一块装饰用的小纱巾,因为没穿高跟鞋,她又显得矮了一点,但玲珑感顿生。她笑靥如花,看见井得水之后,还踮起脚后跟儿远远地冲着他招手。
井得水五十岁了,但此时他忘记了年龄,他也伸出有些肥胖的手,小跑着向韩常萍逼近。他想拥抱一下韩常萍,韩常萍巧妙地侧身躲开了,人是躲过了,眼眸却顾盼流离地看着他。人在笑,笑容里有对他的到来的接纳,也有对他“注意公共场合,人言可畏”的提示。井得水一下就明白了,为自己的莽撞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心虚。
他们打了一辆车,大包小裹地向韩常萍所说的山里进发,路上的风景并不能引起井得水的注意,他现在的心里只盼着目的地快点到达,到达之后他们想办的事情就都顺理成章了。
那真是一间山里的小屋啊!
井得水这么想。
他们是下午三点多到的,此时阳光正好,身在山林之中,暑热没有那么重,又因小屋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水的流动又给人平添了凉爽的暗示。小河上有桥,由两根原木并搭而成,一根木头入地略深,一端的枝丫上生出新的嫩芽。小屋的柴門半掩着,一只鸟伫停在上边,但是他们的突至打扰了它的清静,它歪着头看看这些陌生的访客,“啾啾”两声表示疑问之后,一振翅,扑棱棱地飞走了。
韩常萍说:“买了有几年了,才花了一千多块钱。平时不怎么来,有时心太烦,就自己来住两天。”
井得水问:“你一个人?”
韩常萍点点头,说:“一个人。”
井得水左右看看,又问:“荒郊野岭的,不害怕吗?”
韩常萍说:“心里又没鬼,怕什么。”
井得水想想也是。
他定下心神,又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才发现离这间小屋二里之遥,有一个人口不多的村落,偶尔有一两声马嘶狗吠传来,让人明晰地感觉到烟火气的存在。再转身看眼前的这间小屋,前面有园子,里边种了各种菜蔬,绕房四周种了各种各样的果树,数一数有几十棵之多,棵棵硕果累累,枝条垂地,不得不用木棍支着。
井得水自言自语:“世外桃源。”
韩常萍没答他的话,一个人拎着东西去开门,井得水见状也急忙行动起来,不消一刻钟的时间,包裹被运至室内,各种吃食也安放在相应的地方。在这些吃食中,以熟食为多,一个最沉的包袱里是四瓶白酒和几十罐啤酒。需要现做的食材有排骨、苞米、土豆,应该是做“一锅出”用的。韩常萍干活麻利,进了屋就开始收拾,她扎了围裙,带着套袖去井里打水,倒入洗衣盆中,那些啤酒被“叮叮咚咚”地倒在里边,看一眼牙根儿都会发凉。之后,她提了一个筐去园子里摘了豆角、茄子、黄瓜和辣椒,哗啦哗啦地洗净,端在灶台上,各备所用。
看韩常萍干活,井得水身上的燥气减了不少,他承认自己现在的口欲大于性欲,肚子里的酒虫子一拱一拱的,把他的口水都拱出来了。
这间小屋不大,按照老式的说法是两间房,土木结构的,进屋就是灶间,再进去就是正屋,靠南窗是土炕,炕上摆着一个木制的炕桌。靠北是老式的大柜,柜上的老式花样都有些模糊了。柜上有一个胆瓶,里边插了一个大大的鸡毛掸子,再有就是散落的几本杂志和书,还有一个干瘪的葫芦。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显然是女人住过的屋,除了泥土及苫草的陈腐味儿,还有一丝女人弥漫于此的馨香。
韩常萍在灶间喊:“井老师,你看看喜欢什么熟食,往桌子上捡,饭菜说好就好,一会儿咱就开喝。”
这句话让井得水有点激动,他忙不迭地找盘子,拿碗筷,往桌子上放了一盘鸡爪子、一盘猪头肉,转身看看灶间冒出的蒸汽,又摸摸自己的肚子,衡量着够了,便去拿白酒,拧开一瓶,“咚咚咚”地倒满两碗。韩常萍那边也快,急火硬功,黄瓜、鸡蛋酱、排骨炖茄子、土豆、豆角,满满当当装了一盆。
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韩常萍净了手,盘腿上炕坐好,端起酒碗猛地喝了一大口之后,笑眯眯地看着井得水,让井得水不由得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情景。他伸出一只手,放肆地和韩常萍隔空握着,另一只手端起酒碗,一仰脖儿全干了。
韩常萍问他:“井老师,曾看过你的一首叙事诗,说你的表哥得了癌症,临死之前你带他去洗澡,想给他找个按摩师,让他享受一下。”
井得水感慨说:“是的,可是他不敢。”
韩常萍说:“后来他死了。”
井得水突然想哭。
韩常萍说:“后来,你带那个女孩去了江边,你想代替你表哥完成一个仪式,一个关乎死亡又与死亡无关的仪式。可是……”
井得水擦了一下眼睛,说:“我出现了幻觉,我发现那个女孩是透明的,骨骼和神经清晰可见……”
韩常萍执瓶倒酒,一瓶酒两下就倒空了。
他们又起了第三瓶。
一瓶酒只能倒两碗。
第二瓶酒在碗里,第三瓶酒在那里伫立着,像一个卫士,也像一个监酒员。
韩常萍问井得水:“那天你来讲课提到了《山月记》。”
井得水头脑不浑,他有点兴奋。他拉着韩常萍的手,让她坐到自己的这一侧。坐在她身边,他没松开她的手,就像那天她没松开他的手一样。
他说:“是啊,中岛敦开篇即说,‘京都吉田一带有一孤傲学生,他的盛名只有部分相关人士知晓。”停顿一下,又说:“其名曰斋藤秀太郎。”说完,用手刮了一下韩常萍的鼻子,十分亲昵的样子。
他们开心地喝完了第二碗酒。
第三瓶酒倒满。
韩常萍问:“井老师……”
井得水打断她,强调说:“叫老井。”
韩常萍妩媚地笑了一下,叫了一声“老井”就接着说:“那《山月记》的结尾,你还记得吗?”
井得水皱了下眉头,做沉思状,半晌,摇摇头说:“实在记不起来了。”
韩常萍笑得更加妩媚了,她亲了一下井得水,说:“我记得,你想不想听?”
井得水也亲了她一下,说:“想听。”
于是韩常萍也背诵起来,文字如下:
“这时候李征又恢复了先前自嘲的语气,说道:‘如果我是个人的话,其实理应先央求你这件事才对。可是比起饥寒之中的妻儿,我首先牵记的居然是自己微不足道的诗名,所以我这种人才会堕落为兽身啊!
“李征接着又叮嘱道:‘袁傪,你从岭南返程途中千萬不要走这条路,因为那时我说不定会错乱到连老友都认不出来而加害于你。分手后,你走到前边约百步的那座山丘时,请朝这里回望一眼,我会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模样,这不是想向你夸示我的勇猛,而是希望你看到我丑陋的形象之后,再也不想路过这里看到我。”
井得水深感疑惑,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叫斋藤秀太郎吗?怎么到了结尾又叫李征了?
他一时语塞。
第四碗酒斟上的时候,井得水微微有点醉态,他于学问之类也已不感兴趣,他只想把先前那件事情完成。他的手放开了韩常萍,继而放在了她的大腿上。她的大腿上有很多毛,像一只猫科动物。
韩常萍问他:“你真的想那样吗?”
井得水说:“想,非常想。”
韩常萍看了他一眼,站起身后,退到炕头的墙壁上,她的背依着那些糊墙用的旧报纸,如一则待发的新闻。她开始慢慢地除去上衣,裸露了自己的上体。本来,井得水是端起酒碗准备冲刺的,但当他看到韩常萍的胴体的一部分时,惊得嘴大张起来。
韩常萍的胸被切除了,代之的是疤痕和缝合疤痕的蜈蚣一样密密的针脚。
“这,这……”
井得水的酒蓦地全醒了。
韩常萍说:“我也一样,希望你看到我丑恶的形象之后,再也不想路过这里看到我。”
井得水“啊”的一声一跃而起,继而破窗而出,他手脚着地,迅疾地奔跑,一蹿蹿过了木桥,再一蹿隐入林木。他就这样急速逃遁,尾巴直直的像一根提防韩常萍追赶而来的哨棒。井得水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他后来只记得,他从山中小屋奔至朝阳镇客运站的时间,正好也是七个小时。
韩常萍的“小辑”流产了,因为《八风阁》已自动停刊。
井得水也决定不再写诗而改写小说。
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叫《面包》,开篇是这样的:
“1985年12月的最后一天,再有几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对旧年的无限依赖和自责,对新年的殷殷渴望和自省。胡安·鲁尔福努力地坐起身子,伸出手臂,把台灯调到更暗一些。‘你还好吗?他自言自语,‘我希望你耻辱地活着。他说的是安纳克莱托,他自己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被一群妇女似狂若痴般地拥戴并请求册封为圣徒的人。他实际上是一个灵魂的罪犯,乱伦的无赖,奸淫的老手。‘你也是,令我恶心的人!他又说。这一回,他说的是佩德罗·巴勒莫,克马拉村的统治者,一个庄园主和酋长,在他的欺诈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走了,妇女们谁都难逃他的蹂躏,他的私生子多到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了。”
作者简介:
于德北,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吉林德惠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吉林省作协全委、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长春市作协副主席。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在《十月》《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散文》《小小说选刊》《鸭绿江》等几百家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零点开始》,长篇随笔《我和端端》,散文集《自然笔记》《一个人的春天》,散文诗集《渡口集》,短篇小说集《少年菊花刀》《没有门窗的房间》,小小说集《青春比鸟自由》《杭州路10号》《秋夜》《美丽的梦》《百合花布》《世界的那端》等60余部。其中《杭州路10号》获中国首届海燕杯全国征文一等奖; 2007年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2009年《美丽的梦》获冰心图书奖;2018年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另获得过长白山文艺奖、君子兰文艺奖、吉林文学奖等奖项。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