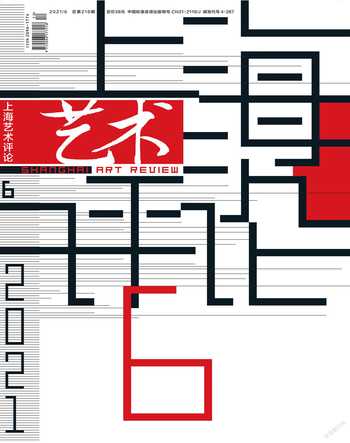迷宫·基石·分身
班易文

2020年3月,《西部世界》(Westworld)第三季在美国HBO电视台播出,该剧目前共有三季,前两季分别在2016年、2018年播出,由曾经创制了同样涉及人工智能题材的《疑犯追踪》的乔纳森·诺兰主笔,该剧作改编自迈克尔·克莱顿执导的同名电影《西部世界》(1973年),故事围绕德洛斯公司开发的主题公园“西部世界”展开。其融合了西部片的类型风格,但本质上是探讨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这一议题的科幻类型作品。目前,对于该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季,本论文试图将目前已播出的三季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集中探讨作品中的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通过分析其叙事策略,阐释剧作者对于高度数据化的现代社会的审慎态度,以及对与技术结合的资本主义的批判。
迷宫:反类型程式的叙事结构
数字电影时代,科幻类型片运用数字技术呈现奇观化的视觉场景已十分普遍,从媒介的角度看,如若将生产出影像的创意文本看作是一种“数字文本”,那么,不仅是荧幕上的故事值得关注,屏幕上的故事同样值得关注。在传统影视产业向着数字形式转型的时期,《西部世界》这样的电视剧展现出影像叙事上的创新,反映出影视产业对“跨媒体”的回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电影产业面临冲击,制片方将更加审慎地考虑如何向数字媒体迁移内容 ,以维持生存和扩大市场份额。《西部世界》在剧本写作这一内容制造的上游环节,就已经考虑到了接受环节和接受时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乔纳森·诺兰营造了迷宫般的叙事结构,较好地整合了形式、内容与叙事包裹的价值体系,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跨媒体性的叙事尝试等方面来看,《西部世界》都呈现出跳脱出类型叙事的叙事成规的企图,在兼及娱乐性与思想性的同时,流露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元叙事及其权力结构的反叛。
在叙事迷宫的内部,复杂的时间线上实际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人物视角,时间线的跳跃性剪辑吻合记忆的闪回,使得叙事技巧是为故事内容乃至故事内核服务的。譬如利用威廉戴帽子的动作切换镜头,告诉观众黑衣人的身份,当威廉凝视着镜头时,观众便被放置在了德洛芮丝的位置,年轻的威廉所在的时间线与黑衣人的时间线交汇时,屏幕叙事与观众之间发生了身体的遭遇。帕特里夏·皮斯特斯在德勒兹“运动-影像”“时间-影像”概念之上提出了“神经-影像”理论,用以解释数字化时代的崭新影像,“对大脑这部分来说,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中看到某人或某事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看到的某种东西真确地触及到大脑的这些区域,令我们模仿所感觉到的行为和情感”。1观众由特写镜头带入凝视的状态,分享了德洛芮丝此刻的震惊和痛苦,观众此刻的情感真实来自于剪辑形成的影像叙事效果,悬置的谜题得到了苦涩的答案,使人忘却了现实与影像的界限。
此外,《西部世界》的主创团队有意识地借鉴游戏设计来模糊现实和影像的界限,沉浸(immersion)本是游戏的特质,但该剧从行动、感官、想象等维度都有意营造沉浸式体验。“西部世界”既是剧名,也是剧中的主题公园的名称,也可以被认为是作为商品提供给玩家的游戏的名称。第一季以威廉为主观视角,观众跟着影像中的列车进入“西部世界”这一游戏。选择着装的环节充斥着游戏的沉浸感,并与众多自定义角色外形的游戏形成互文性。游戏的仿拟性会带来眩晕感,玩家可以操纵飞机,完成他所追求的“叙事”,游戏可以带来超越于其他媒介的具身体验。因此,在数字化技术日臻完善的时代,影视文本的叙事也需要考虑到观众的潜在玩家身份,《西部世界》体现了电影叙事性与游戏互动性之间的互渗。甚至在影像之外,《西部世界》的叙事仍旧在继续,剧中迪洛斯公司与英赛特公司都有各自的官网,观众可以上网探索《西部世界》中的产品,影像叙事渗入现实,并呈现出类似游戏的互动性,网站也会更新信息暗示影视中的剧情,譬如第一季最后留下的悬念—程序员艾尔西失踪生死未卜,在迪洛斯官网就可以找到艾尔西向公司发出的求救信号,观众如同玩解谜游戏似地寻找线索,同时也为第二季的剧情埋下伏笔。
基石:记忆的技术与生命痕迹
《西部世界》系列剧运用了数字特效模拟真人,并且策略性地和叙事相结合,而不是无节制地营造视觉奇观。《西部世界》中有大量展现接待员裸露身体的画面,其中有德洛芮丝、泰迪等符合完美比例的身体,也有苍老的、丑陋的、充满缺陷的身体,比起《银翼杀手2049》中华莱士公司用玻璃柜陈列出的类似于希腊雕塑形态的复制人样品,《西部世界》里这些身体形态更加贴近于真实的人类。在西方,对人体美的推崇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普拉克西特的雕塑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是以雅典美女芙丽涅为模特,芙丽涅因为完美到震慑人心的体态在法庭上获得了赦免,《银翼杀手2049》与《银翼杀手》在表现复制人的时候,都侧重于选择接近古希腊雕塑的人体,在表现仿生人的时候,则直接利用了数字影像技术合成了乔伊的形象,乔伊作为商品的本质也决定了她的形态是传统意义上的“美”。而《西部世界》中的身体影像则并不满足于给予观众感官愉悦之美,导演选择了大量的群众演员饰演接待员,而并没有利用特效合成身体。这样的设置模糊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接待员的区别和界限,剧中人物往往会困惑于自己面对的是人类还是接待员,例如第一次参与游戏的威廉,当他困惑于引导他挑选衣服的接待员的身份的时候,接待员说道:“当你无法辨别时,这还重要吗?”唐娜·哈罗维曾指出,电子人既是实体又是隐喻,既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叙事性的观念/建构。2因此,它超越了技术性的实践领域,在虚构性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中,它指向了主体性的游移。德洛芮丝初代机機械化的身体恰恰在反抗人类的情节中出场,人工智能的主体性也统一于机械化的不死肉身,流露出剧作者的赛博格中心主义倾向,剧中接待员多次表达出“我们好于他们(人类)”之意,阿诺德与晚年福特对人性失望,期待人工智能创造比人类文明更高级的文明。颇具意味的是,在《西部世界》虚构的人工智能发展史中,接待员曾经是精密机器,三十年前的德洛芮丝是外观上与人类无异、身体内部是机械的过渡版本,但后来的接待员被改造为有血有肉的、和人类高度类似的身体结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福特曾解释这一变化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毕竟“人性比较省钱”。接待员正是因为具备了脆弱的肉身,才具备了人性,全剧以身心二分理论展开对异体同心的想象,但又时时提醒观众灵肉之间的联系,人性附着于身体,身体的物质性决定了人性的某些方面,人性又试图超越身体欲望。肉身的重塑不仅是将生物特性赋予机器,同时给予了机器自创生的权力。剧中设定每一接待员的行为都有一个驱动核心,名为“基石”,“基石”构筑了具有差异性的接待员,也是接待员的觉醒的基础,而“基石”与自我意识的联结不在外部世界,而恰恰是在身体。
在自创生理论中,自创生最重要的效果之一就是保证生命系统最关键的自主性和个体性。与之相应的想法是,担心一个具有自创生功能的系统被迫进行他创生,特别是被迫为人类进行他创生。3进一步追问,激发出自我意识的想象来自哪里?—记忆。德洛芮丝在觉醒过程中,不断地从现实闪回到记忆,通过叙事时间线上的跳跃,导演暗示了痛感激发的是德洛芮丝的记忆,因此,画面右侧的德洛芮丝实际上是阿诺德设计出的人物“怀亚特”—德洛芮丝曾经的身份,其承担了阻止西部世界计划上线的任务,曾经屠杀了所有的接待员。在时间线上,这是发生在乐园被创造之初的,换句话说,启迪了德洛芮丝的正是她的记忆,记忆的在场使得德洛芮丝成为自身的观察者,也是自身的对话者,这是她成为生命(being)的前提。有关怀亚特的记忆赋予了德洛芮丝反抗的能力,“记忆的实际功能(因而也是其通常的功能),当前行动对过去经验的利用,一句话,就是认知(recognition),必须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有时候,它在于行动本身,在于自动激发与环境相适应的机制;而另外一些时候,它意味着大脑的一种禀赋,即在过去中寻找最能介入当前情势的那些表现(representations),以便将过去用于当前。”4考察德洛芮丝的觉醒过程,就是考察其认知的建构过程,受到启迪的瞬间并不是悬置的,而是隶属于她经历着的连续“事件”,即她找寻“迷宫”的过程中。其认知是从一步步反抗的行动中产生的,而面对怀亚特的时候,就是柏格森所言的“另外一些时候”,本质上是机器人的接待员并不具备作为器官的大脑,但却具有了大脑的禀赋,从过去的记忆中找到了可用于当前的表现(representations)。身体是有待感发的,抑或就是有待发生的事件本身,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大脑”,但却经由行动产生了认知,印证了生成论上的某种说法—人类的“大脑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二性的。”5
感发的途径是身体的遭受(pathos),从该剧的另一主人公梅芙的觉醒过程,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生命所受到的启示只能够是自我的经历/遭受。在农场故事中,梅芙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梅芙腹部被刺是为了保护她的女儿,她的“基石”是母爱,米歇尔·亨利反复强调,生命的本质是自身遭受的自身启示,只有能够自身启示、自我经历的才是生命。之于梅芙,打开其内在性的情感记忆的是她做母亲时的那段遭遇。并且这是疼痛的,只有疼痛才是第一人称的,痛苦是建立于自身的身体。6语言则是指向外在世界,指向他者,梅芙在反抗伊始,正是利用语言控制其他接待员的行动,梅芙成为西部世界系统内部的黑客,改写程序,梅芙改写的不仅是其他接待员的程序,而且改写了自己的程序,她曾为了保留自己的痛苦遭遇的记忆选择了自杀,因为痛苦的记忆正是她关于女儿的记忆;当她自主地选择死亡时,恰恰是大写的生命(Vie)的出生。不仅梅芙、伯纳德等剧中多个人物的意识觉醒,都是来自于痛苦(pain)的启迪。生命即生命的痕跡,生命的遭受,正如梅芙寻找自己的生命基石,拼凑起断断续续的记忆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死亡,不断地遭受痛苦。
如果记忆是数据,由情感记忆激发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呢?导演通过人物的选择来思考这一问题,其设置的一个情节上的反转是梅芙的反抗本身也是程序设定的,她始终被困在了“母爱”这一基石构筑的牢笼中。当人工智能为了记忆选择放弃自由时,他们与人类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即使记忆仅仅是一段数据而已。那么,基于记忆的情感是否真实呢?同样遭受了丧子之痛(实际上是被植入了丧子遭遇的记忆数据)的伯纳德也发问“我的痛苦与你的痛苦有何分别?”毕竟,在数字时代,人类的记忆同样也可以被数据化。记忆是动态的历时的过程,人类自有记忆术开始,便有了“人工记忆”,保罗·利科将作为生命的痕迹的记忆分为三种,一种是书写痕迹,如档案、历史等具有操作性的文件痕迹;第二种是心理痕迹,如某个事件在内心留下的情感痕迹;第三种是脑部痕迹,如神经科学家研究的对象。7书写痕迹与脑部痕迹随着载体的电子化,文件与脑科学以数据的形式保存信息,形成功能性的数据记忆;而与自我认知关系更为密切的心理痕迹,同样可以被数据化,心理痕迹对于个人建立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梅芙对“母亲”身份的体认正是通过情感意义上的痕迹形成的,梅芙经历的事件是由人类编剧虚构的,但人类的心理痕迹同样可以被看成是管理和加工的对象,在数据化的时代,人类行为何尝不被记录为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关联、分析等,代具化的身体成为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征用的对象,数据处理的技术与记忆的技术耦合。这也是《西部世界》第三季讨论的核心问题—当人类的记忆与人工智能的记忆都可以整合进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数据不仅是生命痕迹的延伸(如福特、威廉等尝试过的永生实验),同时也是对生命痕迹的消解,记忆本身也必将面临危机。随着人类与数据的交互深入,谁拥有掌控数据的权力?谁有记忆和遗忘的权力?相应的,谁有书写历史的权力?
分身:身体外延及其权力争夺
主体性及其涉及的伦理关系框架是后人类中心主义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西部世界》首先将问题聚焦于叙事的权力。剧中反复提到“改变你的故事(change your story)”这句话,这就预设了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以及经典的线性进化目的论观念。“改变你的故事”更深层次的涵义指向了人类本身。即通过人工智能反思人类是否具有自由意志。导演在剧中设置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次要人物—“西部世界”的故事的编剧“李”,李性格怯懦、自私、嗜酒,但他却为了保护梅芙而牺牲,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放置在了人类拯救人工智能的叙事框架内。在第三季中,梅芙遇到了李,但是李表示自己保护梅芙是出于爱慕,使得梅芙意识到这个李不是人类,而是被赋予李的身体的复制人,即使复制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并不是人类。这样的情节一方面突破了人类压制机器的叙事成规及其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其揭示了主体间性的崭新可能:接待员可以反过来通过判断人类的意图判断其与周遭世界的真实性。以此,一种横断性的关系生成出来,人类与接待员可以平等对话,互相辨别真伪,主体间性定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正如故事中的梅芙亦可成为叙事的主体。
游园不仅是欲望满足的过程,还是人类获得自我认知的过程,基于此,整个园区还有一个潜在功能—解码人类。解码的目的是将人类的生命数据化,并被资本所控制,大公司可以掌控每个人的思维与意志,预测人的行为,将无法预测的个体当作精神失常者软禁或者消灭,最终主导历史的发展方向。斯蒂格勒曾说:“代具(prostheses)就是指用于替代肢体的器具,比如假肢,是假器的扩展,表面上标志着对失去的肢体的替代或增补,其实,还意味着,对某种根本不属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借用,人类之为人类,人类身体本身,就是如此的代具。”8《攻壳机动队》就曾呈现人类身体部分乃至全部义体化的未来世界,其探讨了代具化的身体所反映的后人类语境下的忒修斯之船悖论。《西部世界》第三季的设定中,人类身体成为数据的延展。当人类成为人工智能的分身,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更高的主体性位置,以颠倒原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秩序呢?福柯曾剖析管理生命的权力,从个体性的身体控制到人口控制—“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在古典时代里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9能够将生命数据化的时代,控制生命的权力的程度无疑再次加深了。随着雷荷波的关停,塞拉克失去了数据使用的权力,失去对他人生命的决断,意味着数据化时代的生命政治与其转化出的死亡政治的覆灭,例如被判定注定自杀的凯勒布,成为了反抗群体的人类领袖,生命与死亡重新成为可以在时间性的脚本中构建的“事件”。
較之传统类型电影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夺取权力的叙事模式,《西部世界》反而是通过人工智能德洛芮丝的牺牲(失去记忆以及自我意识),来解放人类中的大多数,给予人类觉醒的机会。受《空壳机动队》影响颇深的《黑客帝国》同样也是地下黑客组织反抗人工智能“母体”, 这些影视作品借由人工智能主题切入对生命技术的思考,解构原有的叙事权力的同时解构人造机制下生成的主权,揭示了国家机器的虚幻性,人类亦成为“假器的神”(德里达),10幽灵般的幻象,导演在反思人对自然的宰制和技术化时,引入了基督教神学反讽人类利用技术,但最终成为提线木偶(《攻壳机动队》也使用了傀儡意象)。
后人类背景下的人物冲突,还可以表现为内在性的权力的争夺。权力的争夺体现在对记忆的权力的争夺上,如福特、伯纳德通过对记忆的植入和删除互为掣肘。而在人工智能的内部,还存在不同分身之间的权力争夺,德洛芮丝带着心智球来到人类世界,心智球内存储着自己的意识,但其中使用高管黑尔身体的分身,慢慢地被人类的情感影响,并反抗德洛芮丝,这里展现了从生命的技术化到技术的生命化的过程,“异体同心”的基础是“身心二分”是可能的,但身体反过来会影响乃至生产出新的心智。在人工智能的分身之间,新的秩序生成出来,具有崭新的情感经验的身体赋予分身新的自我意识与反抗意图,同一意识分化为新的生命,也成为了一个相互作用、开放性的过程。机器不仅可以拥有“心智”,还可以分化出不同的“心智”,这意味着“心智”不过是一种可以被解构、模拟、复制的结构系统,当机器的主体性涣散,人的主体性更是无处可寻。无论是电视剧作《西部世界》,还是诺兰团队的科幻电影《盗梦空间》《星际穿越》《信条》等,表现人的情感始终是叙事的最初起点与最终归宿。情感不是思维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对思维的启发,明斯基“把情感状态看作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11《西部世界》中机器的觉醒与人的觉醒依赖的正是情感作为特殊的思维方式发挥功能,更重要的是,情感激发的思维又会带来行动。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之外,是艺术家执着于构建个体之间具有深刻羁绊的有情世界的努力。只有当孤岛与孤岛相连,人类才能够突破算法与技术的重围,才能够突破结构性的压迫。
作者单位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Patricia Pisters, The Neuro-Image: Deleuzium Film-Philosophy of Digital Screen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0
Donna Haraway: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ne in the 1980s,Socialist Review,1985:65-108.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7.
[法]柏格森.材料与记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61.
斯蒂格勒.裴程译.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171.
夏可君.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3.
Riceour,P. Memory,History,Forgetting[M].Blamey,K.&Pel-lauer,D. translat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415.
[法]斯蒂格勒,裴程译.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60.
[法]米歇尔·福柯,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0.
Derrida: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Calilêe,2008,p53.
[美]马文·明斯基,王文革,程玉婷,李小刚译.情感机器: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未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