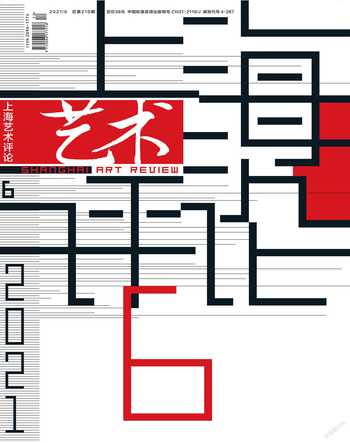功勋人物的“平民化”审视与“凡人化”塑造
龚金平

中国的传记片数量不少,传主基本上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志士、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雄模范或革命领袖。这些传主带有传奇性色彩,更具有英雄化的人格魅力,他们在不同领域做出了令人感动、惊叹、敬佩的业绩,值得后人敬仰和膜拜。
中国的传记片大都可以归入“主旋律片”的范畴,创作者带有“树碑立传”和“鼓舞后人”的双重目的。这也使中国的传记片天然有着“神圣”的光晕,观众很难在平视中感受主人公身上的烟火气息与平民底色。因为这种仰视的视角,当主人公选择某项事业或者某条道路时,观众会认为这是天命所在,是历史的必然,却难以追索人物行动的心理逻辑和性格逻辑。这就使观众难以对人物的处境和心境有切肤之感,也不可能激发“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的情绪共鸣,从而削弱了影片的“教育”意义。
同时,中国传记片中的传主一般已有了历史定性或者政治定性,创作者不可能像一般的故事片那样,去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更不要说揭示人物内心的犹豫、动摇、退缩心理。这就不奇怪,当人物身处矛盾的旋涡中,陷于两难情境或绝境中,观众会默认为他们无所不能,无所畏惧,根本不会为他们担心,这无疑会消解情节的张力和人物形象的感染力。
在这种背景下,电视剧《功勋》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剧作所选择的8位传主全部是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英雄人物,“功勋”的片名地定好了叙事的情感基调。我们似乎可以预料,上述中国传记片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会在这部剧中得到放大。事实上,《功勋》在披露人物动机的深层逻辑时确实有力有不逮的迹象,对于人物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修炼过程”也未作足够的先期铺垫,关于如何用更具现实质感的情境来还原人物内心的情绪起伏方面也处理得有些潦草。但是,《功勋》以“曲径通幽”的方式,回避以恢弘书写壮阔的高起点,而是用平实的叙事手法,以更为细腻、更富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细节,向观众展示了这些“共和国英雄”身上平易近人又感人至深的一面,从而对观众产生了深切的情绪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尤其是《功勋》中有关于敏、屠呦呦的篇章,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秉持开放的创作理念,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就有目共睹。
“平民化”的审视
于敏在设计中国的氢弹时,相当于面对一片中国人未踏足的沼泽,只凭理论层面的复杂推理与计算,要找出一条最佳路径,而不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一一实地探路。这种工作方式的开创性与挑战性是难以想象的,它随时会陷入茫然与困顿中,还要受到外界不同声音的干扰,若没有强大的意志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必然一事无成。屠呦呦在发明青蒿素的过程中,则类似于面对一座险峻奇崛的山峰,前人留下了许多似有若无的探索踪迹,一些路人也讲述了许多貌似可行的路径,面对这种千头万绪、莫衷一是的局面,屠呦呦需要对各种可能性遍挨遍尝,中间要历经许多歧路、险路、绝路,没有向导,也没有灵光乍现的奇迹,只有一次次跋涉之后的遍体鳞伤和自我反思、总结,最后步步艰辛地找到一条最为稳妥,最具效率的路。
面对这种“开路先锋”式的主人公,观众会下意识地把他们视为“神祇”一般的偶像,想当然地认为人物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成功,都带有命定般的“神迹”意味,进而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些丰碑一般的人物,只是供我们景仰而已,普通人与他们的能力、境界和品格相差太大,并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与成就中得到有价值的人生启示。
因此,《功勋》的创作者必须为这些英雄人物“祛魅”,即在一种日常化的氛围中,将人物置身于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中,让观众看到人物那些具体可感的焦虑、困惑、迷茫、无力,以及人物在逆境中所凸显的从容、坚定、淡泊与超脱。唯有如此,观众才有可能与人物心意相通,情绪共振。
《无名英雄于敏》中,于敏出场时,身上没有任何“光环”,反而显得神情沮丧、情绪低落,因为他正在为出国接受组织审查而忙得焦头烂额。在日常生活中,于敏更是显得有些木讷。与玉芹恋爱时,于敏的示爱方式真诚又笨拙,他只想着为玉芹买袜子,却因此付不起两碗面的钱,也没有留下买车票回去的钱。在生活能力方面,于敏不会生炉子,不会做饭,不会给孩子换尿布,像一个“四体不勤”的富贵闲人。
正因为剧作富有情趣地表现了于敏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弱点”,观众反而看到了他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的执着与专注,同时也感念于玉芹在家庭中的牺牲与承担。尤其当玉芹临产时一人艰难地走去医院时,当孩子们说不清自己的爸爸做什么工作时,当儿子眼巴巴地渴望父亲陪他放风筝而不得时,我们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共和国的功勋们在为国奉献时,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亲情,也使家人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和伦理缺憾。
在屠呦呦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不通世故”之处。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对于旁人“不屑一顾”,她直直地与军代表相撞而过却毫无知觉。军代表当着他人的面请屠呦呦坐下说话时,屠呦呦生硬地回答,“我不累,我只是不想坐着”。当丈夫要外出,向她交代家里的财产及各项事务时,屠呦呦完全像在听天书,根本无力应付。于是,她只买大白菜,因为买其他的都要排队,她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屠呦呦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又心酸动容的“轶事”:她为女儿买了两只都是右脚的鞋子,她经常忘记带钥匙,她晚上10点才想起来要去幼儿园接女儿。
《屠呦呦的礼物》这个片名中,“礼物”明显是双关语。当屠呦呦把青蒿素视为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指的是屠呦呦给全世界带来的福祉。在剧作中,屠呦呦还经手了几件具体的礼物,例如给小女儿买的鞋子,给父亲买的果脯。这些礼物折射了屠呦呦身为一位母亲和女儿对于家人的牵挂与关心,也体現了她用这些礼物弥补伦理亏欠的一种努力。
在于敏、屠呦呦身上,我们见证了他们对于工作的专注,也看到他们因这种专注而在生活中显得另类或迟钝的一面。剧作试图为观众呈现于敏、屠呦呦在工作和生活两个领域里不同的精神面貌,进而打破观众对于“科学家”的刻板而抽象的想象,让他们走进锅碗瓢盆的世俗生活中,让人物更接地气,更有亲和力。
“凡人化”的塑造
《功勋》将主人公进行“平民化”审视,以便和观众建立更为亲近的情感联系,这固然值得赞赏,但是,这些人物之所以伟大,终究不是因为他们亲切,而是他们在某个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业绩。因此,《功勋》必须立足于“人”的刻画,让观众体味人物在攀登科学高峰时所经历的痛苦与欢欣,进而使观众领会,这些人物的成功不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天分,而是依靠他们的胸怀、境界、毅力、担当。观众也许无法与一个“天才”心有灵犀,却可以和一个品格高尚的“凡人”感同身受。
于敏面对科技攻关的重重障碍,也有手忙腳乱、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刻,但他更多时候是从容而坚定的。他会在众人热烈讨论时表现出冷静、谦逊但又自信、乐观的气度,也会在同事对他提出质疑时豪爽地许下赌注,在受到他人误解时泰然处之。
屠呦呦虽然对身边的世界有点心不在焉,但她在专业领域,又是那样地忘我。她在政治运动中两边都不站队,只想在实验室平静而潜心地从事科学研究;她细心地在各种古代典籍中汲取前人的智慧,并加以综合、消化;她在四川出差时,不辞辛劳地奔波于乡间田野,搜罗各种民间偏方。
对于任何一项科学研究而言,必然伴随着无数的挫折、失败,必然无数次陷入沮丧与崩溃之中。那么,于敏和屠呦呦等人为何能够锲而不舍、荣辱不惊?他们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在于敏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崇高的家国情怀,他对郝国志说:“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他还不断用《后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勉励自己。在屠呦呦身上,我们看到她对群众疾苦的关心,对于中国医药的信心。正因为这些主人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他们才能将个人的力量投身于国家进步的事业中,才能在使命的驱使中找到不竭的力量源泉。
于敏、屠呦呦身为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对于每一次决策所导致的失败及其严重后果,都是第一责任人。尤其是于敏,他的一个错误判断,可能就意味着国家无数时间与金钱的损失。这时,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明哲保身。但是,于敏却常常在面对旁人的质疑与担忧时,语气平淡却又掷地有声地说,“我来负责”。屠呦呦在实验室着火,在提取新药不顺利时,面对军代表的不满,从来没有推卸责任或者颓唐悲观。正是这种积极的担当意识与永不退缩的坚韧,才使主人公身上“熠熠发光”。
这些主人公从事的是“高精尖”的前沿领域工作,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和具体感受这些工作的难度与挑战性,更无法设想人物在攻克一个个难关时,他们所要具备的非凡创造力和无以伦比的睿智。但是,剧作却很少突出主人公远超常人的智商与才华,而是不断强调他们在一次次艰难的抉择中所闪现的从容心态、坚定意志、恢弘担当。这才是人物的“制胜法宝”,这些“法宝”对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活化”的艺术手法
《功勋》中,创作者特别善于在生活化的细节中融入“微言大义”,使一些高深的科学问题世俗化,使一些庄严的主题通俗化。屠呦呦在试验青蒿的药效陷入困境时,丈夫关于酒糟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香甜可口的观点,一语惊醒了屠呦呦,让她察觉温度过高可能破坏了青蒿素的活性成分。屠呦呦和丈夫挑出绿豆中的小石子时,也让她触类旁通,顿悟必须过滤青蒿素中的杂质才能保证最佳药效。还有《无名英雄于敏》中,郝国志与于敏都喜欢用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来类比各种话题。郝国志要为于敏请功时,于敏谦虚地说,我做的工作又不是打乒乓球,而是踢足球。言下之意是他只是团队中的一员,不能忽略其他人的功劳。郝国志赶紧说,“那你就是教练”。这样,既肯定了团队的作用,又强调了于敏在这个团队中是主心骨和战略决策者的地位。
作为电视剧,《功勋》在场景的设置上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物的对话会占据大量的篇幅。在有限的场景中,“家庭”多次出场,让观众看到了特定的时代风情,更看到了特殊的家庭关系。屠呦呦的家简朴而逼仄,但是,这个家因为有丈夫的精心打理,显得温馨舒适,整洁有序。这个家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这个阳台在剧作中承担了重要的剧情意义和主题意义。屠呦呦在内心疲惫时,常常在这个阳台上仰望星空,星空中似乎出现许多中草药的名字。屠呦呦与丈夫偎依在一起,看着天空的星座时,他们之间的默契与融洽尽在不言中,天地之间的永恒与个人的渺小形成一种奇特的对话关系。在无尽的时空中,个体似乎微不足道,有人可能浑浑噩噩地度过,有人却努力在生命的长河中,在人类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迹,甚至成为一颗恒星永远照耀着中国乃至世界。
《功勋》中,创作者还设置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抒情时刻,尽情渲染天地之苍茫,山水之秀美,人情之淳厚。剧作没有回避特殊的时代环境对于个体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为了对抗这种外在的阻碍,个体除了要有超越性的情怀和坚定的志向,有时也需要用心中的诗意来抵消外界的纷扰。这种诗意,也是人物内心超脱与从容的艺术化呈现。正如于敏在深夜骑着自行车去办公室时,雪花飘舞,天地静谧,人与自然似乎融为一体,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屠呦呦去四川找药方时,剧作用大量镜头展现了当地的人心淳朴,山川河流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种诗情画意的环境,无疑可以抚慰屠呦呦身心的劳顿,可能也会激发屠呦呦攻克疟疾的决心。因为,她不能容忍疟疾对祖国大好河山、对善良百姓的摧残与毁灭。
《功勋》在片头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这些获得共和国勋章的主人公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劈波斩浪地前进的先锋。剧作既要呈现这些人物身上的英雄光环,又要提炼他们对于普通人的启示意义。为此,剧作一方面对这些主人公进行“平民化”审视,让观众看到他们作为“凡人”的烦恼与纠结,另一方面又带领观众在这些人物的“平凡处”见证他们过人的勇气、坚定的意志、非凡的担当,从而得到精神的鼓舞与感召。
也许,观众很难抵达这些功勋人物的人生成就,但是,剧作在细致地铺展这些人物的奋斗之路时,实际上也在不断调低叙述的调门,以平实的声调告诉观众,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是天才(虽然于敏、黄旭华等人确实是天才),而是因为他们怀着一颗朴素的报国心,他们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大爱精神,他们有着对事业的静心笃志,他们敢于在前人未开垦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他们能在众人困惑、迷茫、颓唐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这些才是他们成功的真正原因和动力,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样,剧作的“纪念”“致敬”“教育”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作者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
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