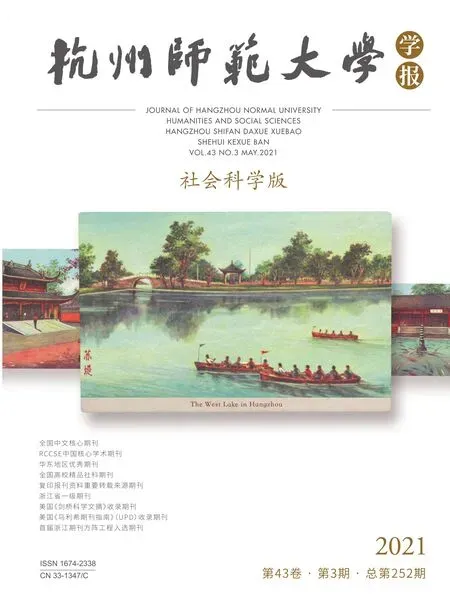是否有一条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①
刘民权
(北京大学 1.经济学院2.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一、引言
本文关注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所用的经济发展概念来自Lewis,即劳动力从传统的低生产力部门(如农业)转移到其他新兴的扩张部门(如工业和服务业),这些部门拥有比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PP.139-191)然而,尽管Lewis准确地抓住了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但他疏忽了强调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要成功地开展跨部门劳动力转移,一个重要条件是在转移之前,将被转移的工人首先获得合适的人力资本,而在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中,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Liu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发展由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特别是由教育投资推动。通过对教育进行投资,来自传统部门的人员(或其子女)可以离开这些部门(如农业),迁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等其他正在发展的部门。理论上,通过这种转移而可期望得到的更高收入应该能充分激励潜在的转移者事先投资于教育。然而,常常存在各种障碍导致个人教育投资市场严重失灵。Liu讨论了政府可如何通过提供必要的愿景、领导和规划来进行干预,以一方面引导个人和私营部门对教育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动用必要的公共资源补充私人投资。该文认为,只要政府积极发挥其作用,或许可以使教育投资和教育发展步入一种正向循环,一种类似于 “萨伊定律”的效应,即通过造就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工人,且达到一定规模,便有可能同时为利用这些工人创造足够的需求。在此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就同时得到了发展。[2](PP.37-53)
本文围绕是否存在一条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继续展开讨论。首先回顾和分析教育市场所经常出现的缺陷,以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然后对可能存在的“萨伊定律”作进一步界定。一个真实的由政府主导的教育投资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是新加坡。自其独立之日起,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干预措施有效地主导了该国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其经验似乎恰好印证了本文的假说,即存在一条关于教育的 “萨伊定律”。然而,这一“定律”是有条件的,本文指出几条重要的限定条件。下文第二节回顾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教育市场进行强有力干预的理由,同时进一步诠释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的含义。第三节介绍新加坡案例。第四节归纳总结新加坡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指出所存在的“萨伊定律”的有条件性。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教育市场上国家的作用
在以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下,政策关注的首要领域,或者说这一战略的最核心部分,是对教育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在不同程度上,市场也确实是这类投资的主要组织方式。然而,仅仅依靠市场往往无法提供一国所必需的教育投资,需要政府在这一关键领域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干预。
(一)教育市场及其失灵
理论上,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如果人们对教育的未来回报有完美的预期,如果教育投资无外部性,个人应该能够对教育投资做出对其个人(或家庭)和社会都最优的决策。然而,众所周知,教育的外部性是存在的,而且对教育未来回报的预期不可能是完美的(因而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即使个人做出了规避风险的最优决策,对社会来说也不可能是最优的选择。此外,资本市场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即使教育领域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个人也无法充分利用其未来的收入来获取贷款,除非他们已有足够的资产来充当抵押品。这也意味着贫穷的个人或家庭最终可能无法利用这些投资机会。(1)但从扶贫的角度看,这部分人群正是发展所应该首先惠及的。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包含了许多关于市场和政府失灵的讨论。许多教科书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列了一套严格的标准,不满足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实际上,很少有市场满足所有这些标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项行动:1.不采取任何行动(放任自由);2.规范和改善有关市场的运作(市场强化);3.与市场建立伙伴关系(公私伙伴或公私合营);4.直接接管全部或部分市场职能(市场替代)。积极的公共政策可涉及后三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但从最佳改善市场配置的和成本效益而言,哪一个方案是最好的则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不一定要选择可以有效改善现有市场配置但成本高昂的解决方案。而且,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有时采用一系列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的政策措施以解决一组相互关联的市场失灵,可能比单一进击其中任何一个失灵都更为有效。
鉴于其在推动发展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教育方面采取积极的公共行动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不采取任何行动绝不是一个选项)。比如,在提供助学贷款方面,可以努力改善资本市场的运作。可以结合私人和公共资源在供给方面进行投资,以改善和提高各类教育设施(学校、学院、大学)及其教学质量,并在需求方面提供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以使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从中获益。也可以直接动用独立的公共投资分别在供需两方补充次优的私人投资。为了确保这些投资不会“挤掉”私人投资,可优先考虑配置公共投资于那些特别缺乏私人投资的领域,或者那些出于外部性和公平性考量需要特别加以提升的领域。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普及基础教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部分人口已经享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但仍有一些人甚至没有接受到基础教育。如果要让这些人成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接受基础教育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随着世界各地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虽然这种基础教育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熟练工人,但它可能是该个人成为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连这种基础教育都没有,他或许会完全失业)。
(二)政府的作用:愿景、领导和规划
但是,国家的作用不应仅仅限于一切以市场为主、由市场来主导相关过程,而只在其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在教育这一关键的领域,国家的作用必须包括绘制愿景、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制定具体规划,而且这些都必须充分地提前做。在教育上,一个很现实问题是:培养一名熟练工人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最好在他/她还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年龄时就开始培养。因此,如果要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就需要有一些长期的前瞻性规划。
而且,愿景和规划不应仅仅限于满足未来对熟练工人的某些已知需求。毕竟,关于这些未来需求的明确信号有哪些呢,来自哪里呢?愿景、计划和领导还必须与塑造期望和促使情况发展有关!不用说,从消除任何不确定性的意义上来说,对未来的任何期望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从政府那里获得关于未来愿景的具体目标及规划,以及由政府提供坚定不移的承诺和领导,可以帮助个人在教育其自身以及子女方面做出更好、更明智的决定,尤其是针对那些或许需通过借款来进行相关投资的个人或家庭。在放贷方方面,政府的这种愿景、承诺和领导力也将有助于他们在贷款方面做出更好、更明智的决策。
政府在扩大教育方面给出明确的愿景、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制定相关的战略规划,对于一个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也不能认为政府只需要提供这样的愿景、领导和规划。即使政府对方向和目标提供了明确的信号,也不可能指望市场来完成所有工作。政府还需自己卷起袖子,与市场合作以共同实现其愿景。如前所述,这很大可能需要政府直接对教育进行投资,包括在需方和供方。政府还可以与私营部门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同时,政府还必须发挥其不可或缺的监管作用,严格监控公立和私营教育部门的教学质量和标准。
(三)萨伊定律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古老的定律——“萨伊定律”。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e Say在其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写道:“一产品刚刚诞生,它就为其他产品提供了一个市场,其价值就是该产品的价值。”[3](P.138)这一“定律”常被简单地概括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名言。但需要重申,萨伊实际上并没有断言在一个给定价值的产品A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同等价值的对该产品的需求就诞生了。实际上,等同于该产品价值的需求是针对所有产品的:A、B、C等等。但如果每个产品都这样做,那么对产品A的需求也就会等同于其自身的价值。
这条定律遭到了严厉的质疑,尤其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中。质疑的核心问题是商品和服务的普遍过剩是否可能。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2)不用说,商品和服务的普遍过剩决不是现代经济史上罕见的现象,它与经济的宏观管理有关。但是,即使没有普遍的供过于求,任何特定商品和服务品的供过于求也很常见。如果在反映其总要素收入的价格下该商品或服务品的总供应量超过了在此价格下对该商品或服务品的总需求量,则供过于求就发生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去追循萨伊或其他持有相同观点的古典经济学家以重申这条定律的有效性,而是通过它去指出存在关于教育投资的一种可能的良性效应。这一良性效应恰恰类似于一种“萨伊定律”——但这并不是字面上的,而是意境上的。这种良性效应可表述为:
当教育的初始投资达到某个临界点,以至于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支达到某一临界规模的熟练工人群体时,该群体的存在将有助于吸引大量需要雇用这些熟练工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或者可以说,当教育投资在造就这样的熟练工人时达到了一定规模,就有可能同时吸引针对这批熟练工人的需求,而且有时该需求甚至可以超过这支队伍的现有人数。
在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平衡时,当然还需说到工资,并区别短期与长期。图1给出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其中横轴代表经过教育投资的劳动力人数。与传统劳动力市场模型不同,图1中的横轴还考虑到各工人、职员的加班工时,也即在某个时间段(天、周、月)内超出某个标准小时数的工作时间。在任何一个社会,通过法律或约定俗成,都对这样的标准工时数有严格的规定,超出的部分即为超时数或加班工时数。由于所考虑的是经过一定教育投资的工人,在短期该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供给人数是给定的。但通过把工人们的超出标准工时数的工作时间按这些标准工时数折算成额外工人人数,则短期劳动力的供给量还是可变动的。长期来看,通过教育投资,实际工人人数当然是可变的。
通常把一个参与劳动的工人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叫做保留工资。图1中,存在两种这样的保留工资:WAR和WIR。WAR为未经教育投资的工人(或低技术工人)的保留工资,可由其“劳动主观成本”决定,或由其客观“最低生活成本”决定。前者为由收入边际效用调整过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水平,后者则指为维持一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在可见的未来正常运作所需的成本。不必纠结于选取哪种解释——对本文来说,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WIR则为经教育投资的工人的保留工资。如图所示,它是WAR外加一个追加项,代表一经过教育投资的工人为获取其教育而付出的成本,再分摊到其生命过程中的各工作时间单位的成本。(3)关于图1劳动力市场模型的进一步解释,见M. Liu, Educ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n Poverty Eradication, In Twin Challenges of Reducing Poverty and Creating Employment, UNDESA, New York,2013。
图1假定已有ON个工人经过教育投资。供需平衡取决于需求曲线。图中标出三种可能的情况。(A)如需求曲线为D1,则有部分经教育投资的工人没有在WIR工资水平上被需求单位雇用,相关教育投资的市场效果欠佳;(B)如需求曲线为D2,则需求和供给在WIR工资水平上恰好相等;(C)如需求曲线为D3,则经教育投资的工人人数少于用人单位所需人数。在长期,市场均衡只在情况(B)中出现。然而,在短期,如出现情况(C),加班工时可以是一种解决办法。为鼓励工人们超常工作,用人单位需为加班工时提供高于通常的单位小时工资的报酬。在图1,把这些增加部分(加班费)分摊到一工人的所有工时,则短期供需均衡会在W*工资水平上实现。在长期,这些超出平常保留工资WIR的高收入会起到鼓励更多工人投资于教育,成为经过教育的工人中的一员。

图1 教育投资与劳动力市场
依据图1,有几点需要澄清:首先,本文所说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效应,是指在长期,一国的教育投资,当达到一定规模时,会对需求曲线D所起的外移作用。这种外移,或者可使得需求充分跟上供给的步伐,并在WIR工资水平上与新的增加了的供给恰好相等,或者可使需求在该工资水平上超出新供给数。当然,不排除新需求仍然少于新的供给量的可能性,但我们重视的是前两种情况。
新需求没有跟上新供给的情况最近得到了世行等研究单位和学者的注意,通常指在一些国家,一些大学或得到过其他类似教育的毕业生没有能够很快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4)参见Tazeen Fasih,Linking Education Policy to Labor Market Outcomes,Washington DC: World Bank,2008;World Bank, Putting Higher Education to Work: Skills and Research for Growth in East Asia,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Report,2012;Roseth, iviana V.,Alexandria Valerio,Marcela Gutiérrez,Education, Skill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sults from Large-Scale Adult Skills Surveys in Urban Areas in 12 Countries,Washington DC: World Bank,2016。原因大都被归结于所在国相关教育的质量欠佳、课程设置不合理,等等。这些或许确实是问题,表明一国不但需要有规模地进行教育投资,而且还需全力改进教育质量、改善课程设置,等等。但根据本文的分析,或许还需甄别以上现象是否是长期的还是仅仅是短期的,教育投资规模又是否已达到了某个规模或临界水平。从长期来说,完美的教育质量、完全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很难一蹴而就的,甚至事前都无法准确知晓,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这些不构成一国教育投资中的大问题,则真正的挑战往往与教育投资的规模有关,以及给予相关教育投资足够的时间去发挥其功效。
其次,处在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中,要抽象准确地确定前述教育投资的临界规模是几乎不可能的。下文新加坡的例子将说明,关键是一国善于从全球经济的变迁中找到根据自身条件能够抓住的机会,并且果断行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及时展开相关教育投资。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一国所需的教育投资内容将是不同的,或者说其教育战略是需要不断变化的。在发展初期,重点可以是基础教育,之后则转到高等教育,再之后或许应有更高的目标。这些与本文提出的“萨伊定律”效应并不矛盾,只不过是该效应在不同阶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第三,虽然强调教育投资及其规模,但也必须指出,其他条件同样重要。很显然,一个开放的国内经济和全球贸易及投资体系,深度的生产碎片化以及广泛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与供应链,也包括支撑这些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各种物质条件,如快捷、高效的交通和通讯设施等,都将有助于一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成熟时充分吸收海外投资。在图1中,这些均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外移。因此,如同下文将指出的,本文提出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可被看作是一条“有条件的”萨伊定律。
第四,图1中主要考虑的是教育的私人投资,而本文倡导的是国家的作用。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首先,如上文已强调的,充分的私人投资迫切需要国家地引领和支持。另外,即使由国家主导相关的教育投资,投资的主体一般仍是私人部门。
最后须指出,我们提出的针对教育的“萨伊定律”,在一个关键方面不同于原来的萨伊定律:借用“后向联系”概念,可把原有萨伊定律描绘为“向后看的”,因为关于它的解释是完全根据一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应计的要素收入的;而本文提出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则是“向前看的”(如同在“前向关联”概念中那样),因为它完全取决于所创造的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力。
三、教育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上世纪东亚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1965年至1995年期间,新加坡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4%。[4]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功,促使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并思考是否可在其他国家复制新加坡的增长模式。研究人员将新加坡快速的经济增长归因于多个因素,如国家干预、地理位置、教育,甚至包括灌输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国家价值观。
本节旨在分析新加坡经济发展背后的原因,并讨论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新加坡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的解析表明教育虽然不是新加坡经济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前瞻性的教育政策与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相结合,使得新加坡始终拥有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合适劳动力。事实上,正如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多次重申的那样,新加坡的发展战略即是“开发新加坡唯一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即人民”。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拥有一个确保教育与经济需求协同作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5)这句话被广泛认为出自李光耀,尽管其确切来源很难追查。见 O Tan,E Low,and D Hung,Lee Kuan Yew’s Educational Legacy,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2017,p.7。
本节首先简要概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轨迹,然后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介绍,之后分析教育是如何与新加坡多年来实施的不同发展战略相互作用的。本节所说的新加坡教育是指旨在提高人口技能水平的正规教育或培训,以所达到的正规教育水平为基准。
(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虽然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挑战,但新加坡不必克服这一初始阶段,而直接跃升为制造业密集型经济。该国处于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的战略要道上,使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运输和通讯中心。这为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非常重要的优势”。[5](P.1)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1980)可被描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后殖民主义初期,不少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减少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新加坡也不例外。与马来西亚分离后,新加坡国内市场规模急剧缩小,其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初,面向出口市场的制造业贡献了28%的GDP和34%的就业。(6)见Rachel van Elken,Singapore’s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Bercuson, Kenneth (ed.), Singapore: A Case Study in Rapi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5,pp.4-5,p.16。
经过二十年的制造业扩张,新加坡被迫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1980-1990),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来自邻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逐渐侵蚀了新加坡的比较优势,迫使其重组经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开展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和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是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微芯片和半导体制造商受到了积极地鼓励和追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知识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快速的技术进步促使新加坡进入了当前的发展阶段,重点是在创新和创造力中应用知识,使经济重心偏离传统生产和传统工业生产要素。
在以上三个发展阶段中,正如Huff所观察到的,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外部依赖”于服务业和制成品出口,强调了“外向化的重要性”[6](P.735)。与出口导向战略相一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旨在吸引跨国公司和外资在新加坡投资,其中包括退税、低工资政策和建立一支合格的劳动力队伍。这些外国投资被认为能为新加坡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技术转让,并促进新加坡的整体发展。
(二)一些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现有理论
1.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要素解释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开放型经济、低税收政策、外国投资、宽松的劳动法是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因为它们为该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从而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将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区位优势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作为重要航运和运输线路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新加坡迅速成为了制造业企业理想的地理位置。其他地理优势,如缩小了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之间的时区差,使新加坡迈向了服务型经济,并跻身于世界主要外汇市场行列。
2.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像Huff和Low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将新加坡的成功归因于“外部自由贸易和强有力的内部控制的结合”[5](P.301)。他们认为,政府对部分经济部门的广泛干预,如低工资和高公共储蓄,使新加坡保持了竞争力,吸引了大量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与此同时,政府能够调动已积累的国内资本,对住房和交通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一些“政府关联公司”的实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导因素。与新加坡证交所10家最盈利的公司相比,这些政府关联公司获得了更高的利润。Low很好地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是1959年以来在连续的人民行动党治理下由政府制造的产物[7](PP.411-441)。
3.文化解释
Chang等社会学家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8](P.101)得益于该国的一些国家价值观,如新社会达尔文主义、关系主义、理性中庸主义、实用主义、社群主义和精英主义等。总的来说,这些价值观强调了卓越的重要性、雄心壮志和对最佳的追求。使新加坡长期保持领先于全球竞争的竞争文化可以被视为这些“国家价值观的产物”[8](P.101)。这些目标导向的价值观还有助于新加坡政府有效管控一些利益集团和工会的政治倾向,规范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跨国公司顺利开发业务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7)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原因,最著名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归因于一种强调获取、个人主义、理性和效率等特征的文化。从上世纪后期四个亚洲新工业化经济体(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的经验出发,东方主义者则认为东方文化可能对这些经济体的现代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讨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大背景。
(三)教育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以上种种解释,在强调各因素的同时,忽视了教育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教育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经济重组。成功而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使新加坡在半个世纪内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国家经济增长各阶段中促进技能形成的政策与对技能的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了新加坡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本促进增长。[9](P.191)如前所述,新加坡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阶段,以下将探讨教育在这三个阶段中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教育对于建立一支得力的劳动力队伍至关重要,以适应包含更高技能要求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在与马来西亚分离后,新加坡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当时有效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持续的。鉴于新加坡经济规模微乎其微,加之缺乏马来西亚腹地,向外向型工业化战略转变是唯一的前进道路,因此政府加紧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到新加坡投资。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需要从以前主要依靠不熟练劳动力和低技术要求的小规模生产转向依靠充分培训过的技术工人的行业。Goh和Gopinanthan认为,独立后,新加坡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最为重要的”。[10](P.83)Goh和Gopinanthan还谈到了“为生存所需的教育”战略。[10](P.87)在对以往技术和职业教育进行充分回顾的基础上,该战略制定了升级方案,包括设立培训设施,培训焊工、机械师等熟练工人,以服务于造船、炼油、电化、精密工程等重要行业。教育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可以通过1967年至1973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超过23亿新元和创造了147500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来证明。[4](P.13)在这个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足够的熟练劳动力的存在,以及诸如低工资和低税率等市场政策,使新加坡吸引了大量新的外资企业。很明显,早期的工业导向型教育战略使得新加坡足以为快速工业化造就了足够多的人力资源,以至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已从一个低工资剩余劳动力经济过渡到了一个高工资充分就业经济。
随着新加坡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由此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为经济升级提供先决条件。这一阶段初期,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承受实际工资上涨的压力,导致其与外国市场的竞争优势被逐步侵蚀。因此,新加坡必须“依靠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增值”[11](P.13),而这需要一支能胜任更高层次技能的劳动力队伍。因此,新加坡对教育体系进行了调整,目标转为培养具有额外科学和技术知识能力的劳动力队伍。此时建立了各种工业培训中心,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水平。这些保证了新加坡能为跨国公司稳定地提供训练有素的生产工人。由此新加坡的人均产值增长了31%[11](P.14)。对零部件和精密工程、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行业的投资逐步取代了对纺织品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政府在人力资本开发和劳动力技能提升方面的投资,为成功重组新加坡经济,使之步入更先进的产业链上游技术活动铺平了道路。由于此前通过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建立了相对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这种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型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从而变得相对容易。[10]处在被较不发达的国家包围之中,劳动力人数又少,新加坡的高技能劳动力队伍使得新加坡经济能够摆脱与周边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并以其较小的劳动力队伍,成功地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8)认识到需要提高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力后,新加坡对其教育体系进行了结构和课程方面的调整。结构上,高校招生率提高了200%,由此扩大了科技人才队伍。课程方面,新的重点放在了科学、数学、技术教育和发展计算机素养上。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学科是在高水平上引进的,学校甚至建立了计算机鉴赏俱乐部,还鼓励教师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教学。
在新加坡经济向更高级知识经济进军的第三阶段,教育对于确保劳动力始终与时俱进以及前瞻性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小型外向型经济体,新加坡尤其受到了国际经济变幻莫测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不断识别新增长部门,也强调了教育在保持劳动力更新方面的重要性。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促使新加坡经济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向知识经济转变。这一新的全球经济动向意味着一种从传统的工业生产和生产要素向依靠知识开展技术创新和原创性科技发现的转变。生物技术及航空航天的研发成为一些新的发展领域。为此,新加坡政府对有关教育课程再次进行了修改,以确保未来的受业者掌握相关技能和技术素养,并拥有充分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探险精神。显然,教育为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9)以知识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最好的代表是于1997年引入的新的教育范式:“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此时,新加坡对其原有课程和评估体系进行了审查,以减少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知识”。相反地,“项目”则作为一种学习和评估形式被更多引入,以发展学生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信息技术也被引入以用来培养学员的沟通技巧和建立独立学习的习惯。
除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帮助应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外,教育也是一些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得以灌输的主要渠道。尽管Chang认为通过不断的技能提升来追求卓越的动力来自诸如精英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目标导向的国家价值观[8](PP.85-10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观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例如,精英教育体系,以及强调科学和技术等实践学科而非“软”的艺术和人文学科,强化了新加坡的国家价值观。这种积极的国家价值观和存在一支技术上胜任的劳动力队伍共同作用,为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经营创造了有利的商业环境。不用说,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远远超出技能的形成,而将同时有助于向工人灌输相关的国家价值观,后者也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动力。
四、讨论
从以上对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叙述和对其原因的分析中,特别是对教育的作用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均与我们上文关于教育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以及政府在推动教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的观点相吻合。
(一)市场和国家
新加坡快速的教育发展显然既不是完全由市场主导,也不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虽然市场在推动其教育发展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教育的需求方,但教育市场的供给方在很大程度上则处于国家的指导之下。国家不仅在各个阶段为加强和升级供应方提供了财政支持,而且还负责直接启动、组织、领导和监督了许多发展规划。
事实上,新加坡的所有以上行动似乎都是由一个明确的愿景指导的,即由教育引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当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发展战略是依靠“开发新加坡唯一拥有的自然资源,即人民”时,他最清楚、最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愿景。从一开始,这一愿景就指导着新加坡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实际上,它推动和凝聚了新加坡政府随后在该国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开展的各项教育计划。
根据Low的说法[1],新加坡独特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教育从国家中剥离。国家通过调控人力发展规划在经济发展中起了战略指导作用,教育体系不仅是国家重建的载体,而且其作用直接波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过程。
(二)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
如果没有教育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紧密“耦合”,教育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前文叙述详细说明了新加坡经济和教育规划之间的直接联系。新加坡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优先项的每一次转变都由教育政策上的类似转变相匹配。如果没有这种紧密耦合,特定技能的供给和需求很有可能不匹配,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机会的丧失。因此,除了愿景和领导力外,能够根据国家发展机遇的新趋势,具体制定良好的教育发展规划并全力付诸行动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正如Goh等所指出的[10](P.91),“国家成功管理教育和技能的需求以及供给的能力,曾经是并将继续是新加坡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10)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其技能发展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Kuruvilla和Chua描述了该国是如何制定国家人力资源政策以为各发展阶段提供必要的技能的。见S Kuruvilla,& R. Chua,How Do Nations Develop Skills? 2000, Lessons from the skil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Singapore.Retrieved from Cornell University,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site: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bpubs/8。
成功地协调、管理教育和经济发展优先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及时、敏锐地认识到国民经济相对于全球经济变化的性质和特点的能力,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及时发现和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其对人力资本的新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规划国家教育战略。从上文可以看到,新加坡在对国内外情况进行评估和制定相应的政策优先项方面发生了几轮这样的转变,似乎都是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及时反应。对这些转变的任何管理不善都可能代价高昂。
新加坡成功协调和管理教育与经济发展机遇并及时制定合适的教育发展规划的故事,充分反映了该国对其人口教育标准的不断提高。在其最初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阶段,扩大基础教育是一项关键政策。此后,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经济型发展期,根据其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及时提高了对其人口的教育标准。应该说,类似的教育发展模式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人们都会预期其国家的教育标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关键是选准合适的时机进行合适的调整。
(三)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
新加坡高度成功的发展故事,是以一系列及时的教育发展规划为主导和基础的。它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国家如适时开展教育投资,并达到一定规模,便能产生一种良性效应,具体地说是它能刺激针对由这些教育投资培养起来的技术工人的需求。这种良性效应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一种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把其冠名为“定律”,并不意味着它有任何必然性。事实上,该“定律”的有效性只取决于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条件,包括:一个外向型国内经济和高度开放的全球贸易及投资体系,深度生产碎片化以及广泛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与供应链,快捷、高效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支持相关生产链和供应链进入并植根一国。很显然,所有这些条件都将极大地帮助一国在拥有相关人力资本的条件下充分地吸收海外投资。相反,如这些条件不具备,则即使一国通过教育投资拥有了所需的人力资本,也不能大量吸引海外投资进入。在图1中,这将表现为虽然需求曲线有所外移,但外移程度极其微小,起不到充分吸收一国所拥有的合适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正因为此,我们或可把本文提出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看作是一条有条件的定律。
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上列出的条件似乎都得到了满足。自独立之日起,建立一个外向型经济便成为该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其早期发展中,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还远非像现在这样高度开放,但新加坡还是充分利用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保证了其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自由化变革浪潮,更是使得新加坡获利匪浅。另外,由于其处在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上,便捷快速的交通和通讯成为了其固有的优势,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无法与其相比。但其他国家也有它们特有的比较优势,再说了,目前大为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也为许多后发国家提供了新加坡在其早期发展中所不享有的发展条件。
最后,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加坡的经济和人口规模都是属于较小的。显然,本文不是全面分析一国经济与人口规模对其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地方,但有一点值得指出,新加坡较小的人口规模,客观上使得其教育投资是较易覆盖全人口的,而不须顾及相关人力资本过剩的问题(教育投资过多)。针对新加坡,倒是应该考虑前文提到的临界教育投资规模的问题,主要指其本国人口是否能支撑起足够多的人力资本以吸引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投资。考虑到新加坡在最近几十年中不断引进海外高技术人才,它似乎早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对于经济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临界教育投资规模的问题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相关投资需要覆盖多少本国人口才能达到临界要求?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处在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中,一国需要做的就是从全球经济的变迁中敏锐地找到合乎自身条件的机会,并果断行动。
五、结论
发展的实质在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对教育的投资。新加坡的经验证明,教育可以促进和引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一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真正应该首先关注的事项。本文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即,适时造就一批达到一定规模的、受过先进教育的技术工人群体,以吸引需要雇用这些工人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投资,其中包括甚至主要依靠国际投资。也就是说,在造就这样的一支技术工人队伍的同时,或有可能也就造就了对这支队伍的需求。在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日趋密布、全球直接投资大幅攀升的今天,预见这样一种劳动力供方对需方的良性效应只会日趋显著。即便在面临贸易战威胁的今天,这一良性效应也不会过时,因为任何贸易战将无法阻挡已经兴起而且日趋强劲的贸易、投资和生产上的全球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