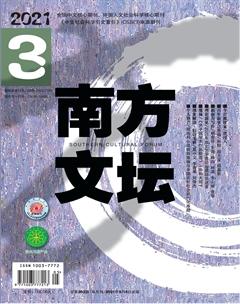从民俗到文化意象:20世纪前半叶舞狮习俗文献研究
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舞狮习俗获得现代学术记录的启始时期。彼时正是现代民俗研究崛起的时期,舞狮习俗得益于这一历史契机而进入学者视线并且得到较为详细的记录和研究。而且在彼时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舞狮作为一种传统民俗和民间体育运动,在当时语境下也被赋予了唤醒国民的时代意义,这种“睡狮当醒来”的思潮也深深影响到彼时的舞狮活动和相关记录之中。
我们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应将其对象定义为作为“过去式”的“遗产”(Heritage),而应将之视为活态的“资产”(Properties),“活化态”地运用在民俗实践过程中,不断为现时代的文化发展创造出新的价值。可以说,舞狮习俗从近代以来一直参与到了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进程中,是构造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同時它也以其浓郁“中国风”的文化符号意味,作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意象走入世界大舞台,参与到中华文化对域外的传播之中。
一、20世纪前半叶舞狮习俗
文献记录的整体面貌
作为一项具有浓郁节庆色彩的民俗,舞狮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自其兴起后与之相关的记录也屡见于官方文献和私人笔记小说,但这些传统方法与现代学术研究还有相当差距。今日舞狮习俗已获得了学科化的系统研究,相关研究论著颇为丰富,但对作为启始时期的20世纪前半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论文还较少,故而对这段时期的文献进行系统地追溯和梳理非常有必要①。梳理这一时期关于舞狮习俗的相关文献,不但有利于提升今日舞狮习俗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能通过对其“内在理路”的把握而理解这些文献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
目前留存下来的20世纪前半叶舞狮习俗文献记录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舞狮习俗的新闻和随笔,另一类是针对舞狮习俗展开研究的专题文献。从整体上看,彼时关于舞狮习俗的新闻和随笔并不少,目前笔者搜集到的就有近百篇,但能从学科化视角开展研究的专题文献却不多。这其实也反映了特定学术选题的起始阶段的普遍特征:一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选题的重要性,但参与研究的人数偏少且零散,彼此之间是缺乏联系的“学术孤岛”,没能构成可以彼此呼应互补的群体,亦尚未能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性研究。
此外,历史上舞狮是一种普遍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习俗活动,不过从20世纪早期开始,舞狮这项习俗流行的范围开始逐步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集中在广东、广西、四川、江西这一带区域。而且这一时期关于舞龙舞狮的记录还主要是关于两广地区的。舞狮习俗的这一流传特征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地域性和“超地域性”共存的独特状态,它本已从一种全国性的习俗活动逐步收缩到两广地区,但在文化认同上依旧保有其作为一种“超地域性”的全国性民俗活动的地位。这有似于今天的京剧,京剧的受众虽主要集中于京津地区,但并不妨碍它以“国粹”的面貌出现。只不过京剧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造成的,而舞狮的地位却跟它本身的大众性有着深刻联系,在大众当中的影响力更为广大而深远。
在近代中国人通过民俗信仰等民间意识形态确立自己属于中华民族的国族“文化身份”过程中,舞狮习俗无疑扮演着颇为重要的重要角色。这种“文化身份”的确立,对内是围绕习俗而凝聚的文化记忆及认同,而对外展示的则是形象性的中华文化身份形态,甚至构造起能获得域外人群的体认和接受的所谓“跨文化认同”②。
关于舞狮的文章中,一部分是关于舞狮习俗的随笔,如张亦菴的《元旦所见舞狮子》(《文华》1930年第7期)、笔名“大华烈士”的简又文的《广东人过新年记》(《逸经》1936年第1期)、冯节的《广东人过新年记“补订”》(《逸经》1937年第21期)等。一部分则是报道舞狮的新闻,如行云的《舞龙跳狮之国民二军》(《晶报》1926年1月27日)、新闻社所刊《舞狮比赛:桂省当局通令筹办提倡武化唤醒国魂》(《浙江民众教育》1936年第4卷第1期)、新闻社所刊《师区模范队舞狮募欵慰劳新兵》(《肇清兵役》1942年创刊号)等。此外,在1935年娄子匡编著的《新年风俗志》,以及1937年的《南宁社会调查》这两本书中也片段性谈及南宁的舞狮活动。此外还有几篇关于舞狮的诗歌,从中亦可片段性了解彼时舞狮的状况,如署名“锡金”的诗歌《舞狮》(《当代诗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署名“焦桐”的诗歌《舞狮歌》(《永安月刊》1943年第53期)等。
《良友画报》对舞狮有过零星的报道,且皆为图配字的新闻,如1929年第34期的新闻《舞狮》,1929年第41期的新闻《国庆纪念:吡能华侨国庆节舞狮之热闹》,1931年第59期的新闻《醒狮》,包括“美国旧金山华侨国技团之舞狮”和“华侨舞狮时声震远近之鼓乐”两张照片。《良友画报》以《舞狮》这一则新闻配以对舞狮活动的俯拍照片,还是黑白照片,而且未能正面拍摄狮头。但毕竟是关于此俗图配文的开篇之作。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这一照片实际上来自《纽约时报》记者,所拍摄的也不是国内的舞狮,而是纽约华侨在当地的表演。另外几篇也都是华侨的舞狮活动照片而非中国本土的,但这些新闻照片至少说明中国人在远赴重洋后把舞狮习俗也随之带去,以具体的民俗表演在美国展现了中国精神。而简又文的《广东人过新年记》配有舞狮的正面照片,正好弥补了《良友画报》的缺憾。其他新闻里也有舞狮的照片,如《广义童子军团舞狮》(《上海童子军会汇刊》1927年第1期)等,但这些刊物照片多不够清晰,加上采用的是远景拍摄,所以看起来就更模糊了,整体质量都逊于《良友画报》。
任何叙述都是基于某种视角而发出的,故而文本本身就内含着某种期待视野和意识形态,我们如果细致考究这些社会新闻和随笔在谈及舞狮习俗时所聚焦的问题,就会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一条值得注意的文化线索:在时代剧烈转化的大背景下,原本是一种普通的、大众化的与民俗的舞狮习俗,开始跟时代政治搭上关系。它的现实作用使之能够在参与慰问、募捐等社会活动中以作为“中国精神”的文化意象走入强调“社会动员”的新语境之中,虽是传统民俗却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新的时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舞狮习俗在国家、民族亟须救亡图存、重整复兴之际,在对外传播方面扮演了文化外交使者的角色,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历史先进性③。当这种习俗漂洋过海到国外演出时,它热闹奔放的表演过程就是一种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风范的过程,这种特别具有感染力的表演对位传播构建出了一个积极精进的正面形象,让西方国家的民众看到中国人时不再只是联想到“吸鸦片”“猪尾巴辫子”“裹脚”等所谓“东亚病夫”的负面形象,而是中国人民努力奋进、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尽管如此,针对舞狮习俗展开研究的专题文献仍然偏少,笔者目前只觅得共计九篇。包括:张亦菴的《狮舞》(《文华》1930年第7期)、曾维慎的《舞狮之意义》(《北洋画报》1932年第18卷第862期)、黄芝冈的《谈两广人的舞狮》(《中流》1936年第1卷4期)、廖苹庵的《舞狮的艺术》(《逸经》1936年第7期)、双石山人的《舞狮》(《民间旬报》1936年第12期)、周天骥辑录的《桂省年节中的舞狮会》(《边疆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3—4期,此文末尾标注“节录自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日《大美晚报》怡怡著《点缀新年的桂省的‘烧狮风俗》”,笔者目前尚未寻觅到《大美晚报》原文,故暂以周天骥此文为准)、珊的《舞狮:歙县新年游戏之一》(《礼拜日周报》1938年第1卷第3期)、绍虞的《广州之舞狮》(《民意周刊》1941年第15卷第185期)、靜观的《谈高跷与舞狮》(《湘桂黔旬刊》1948年第3卷第5期)。这显示出彼时作为现代学术记录的启始时期的某种准备不足,毕竟,虽舞狮习俗在古代一直被零星记录,但这种记录属于“前学科化”时期的产物。而所谓现代学术记录中的“现代”范畴,不是单指年代已从古代进入现代,而更关键的是指开始以现代的科学、规范、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开展记录工作。
当然,虽存在各种不足且数量偏少,但这8篇启始时期的早期文献仍然显得弥足珍贵。诚如学者高小康所言:“每个独特文化群体及其传统所传承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认同,都是通过象征符号体系的构建和意象表达,从而成为特定文化群体的感知、体验与叙述等审美经验。”④这9篇关于舞狮习俗的史料既是对舞狮民俗的记录,是彼时文化现象的重要记录,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的珍贵文本,具有历史和学术的双重价值。
二、20世纪前半叶时黄芝冈等
学者的舞狮习俗专题研究
如前所述,20世纪前半叶时针对舞狮习俗展开研究的专题文献偏少,而且其中真正具备学术底蕴的又更少了。其中民俗学家黄芝冈1936年所撰的《谈两广人的舞狮》一文是当时关于舞狮习俗文献中最具有现代学科视野和系统性的一篇。此文与其他文章偏重于随笔式记录不同,黄芝冈以其专业底蕴出发撰写的此文,不但包括对当时两广地区具体舞狮习俗的记录,而且以史学逻辑为脉络,上究此俗的历史沿革,下录表演的具体流程。
黄芝冈依据其对文献的考证,将舞狮习俗追溯到唐代。中国古代因为开垦农田的缘故,有虎豹犀象等兽类被从北方赶到了南方,但狮子并非中国本土兽类,据《后汉书》记载,这种西域猛兽直到汉章帝章和元年才由安息国作为贡品献到中国。而舞狮也并非彼时中国本土民俗,据白居易《西凉伎》一诗所述内容,当来自西凉国:“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黄芝冈认为中国的舞狮形式和由此产生的习惯习俗,应当是古代西凉舞狮在漫长岁月中在中国境内不断传播和改良的结果。⑤实际上,跟黄芝冈同时代的学者邓之诚更早从《西凉伎》中考证舞狮习俗,在他民国十五年(1926年)交由北京富文斋、佩文斋印刷的《古董琐记》卷二中提到此诗,并补充说:“今世俗有舞狮子者,其制与乐天所咏者同予在蜀粤屡见之。”⑥但邓之诚仅寥寥数语就收笔,考证远未有黄芝冈详细,不过邓之诚所述也可侧证彼时的舞狮习俗已呈现出集中在岭南、西南地区一带的态势。
两广地区在舞狮活动中,用以引狮的角色有两种,一为“猴子”,二为“大头和尚”,黄芝冈认为这实际上跟白居易《西凉伎》提到的引导舞狮者(“假狮子”)的“胡儿”有着继承关系。今日的引狮者(“胡头”)的角色,实际上就是源于西凉舞狮表演中的“紫髯深目两胡儿”。西凉舞狮在中国本土的演化过程中,跟中国巫术仪式发生联系,比如南北朝梁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记录了胡头面具在巫术活动中所起到的“逐疫”仪式功能。由于西域胡人多“紫髯深目”,所以“胡头”演变为“猢狲”,再变成两广地区的“猴子”,也是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的。黄芝冈为增强自己论述的文献可考性,提到了《友会谈薮》所记录的宋时舞狮情况:“京师货药者多假弄狮子猢狲为戏,聚集旁人。供俸者形质么麽(“么麽”,小吏之谓也——笔者按),颐颊尖薄、克肖猢狲,复委质于戏场焉。韦绳贯颈,跳踯不已。”不过黄芝冈此处的论述还有可以商榷之处,如“大头和尚”不一定跟西凉舞狮的“胡儿”角色有继承关系,此角色可能还有其他起源,因为浙江宁波民俗中有“大头和尚”跳“哑舞”的表演形式,在此表演形式中,只有“大头和尚”表演而并无舞狮。两广地区舞狮活动中的“大头和尚”角色可能有多重源头,这正如“瑞狮”实际上是狮子、麒麟等诸多动物、神兽的集合体一样,“猴子”和“大头和尚”也可能是各种民俗原型在历史演变中最后汇集而成当下的形式。
此外娄子匡编著的《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作为民俗史志类书籍也记录了若干广东彼时的舞狮状况。该书首先提到“了新年”习俗:新年闲着不做工,叫作“了新年”。而民众在新年期间的娱乐就包括“舞狮凤”,这些表演者开始着手到各村户去揾钱(“揾钱”即“挣钱”之意——笔者按)。而舞狮凤的时间段大约从大年初四起到十五止。“十五过后,‘大正(“大正”指元宵节——笔者按)已开,谁也没有心来看,自然挣不到钱了,如果远地来的江西狮,当作例外。”他还提到:“舞狮的,是些学拳棒之人,人数自七人至十四人,穿一样的衫鞋帽,束一样的带,很是威风,刀、棒等都齐备。还有一个纸糊的‘狮头,因其形不同,而有‘猫头狮‘鸡公狮‘斗牛狮之分。眼鼻口舌具备,画着彩色,饰着绒线鸡尾兽毛等,煞是好看。另有四个假面具,二个猴形,叫‘孙猴子,二个笨伯;一个是唐僧,一个是沙僧。舞时,随着滚动跳走,饶有兴趣。舞罢,演习拳棒,至汗流浃背才止。‘拜帖”上写‘狮报兴隆‘狮报宏发等吉利语。还有人家赏给的红旗子,一手擎去闹威风。什么‘勇冠三军,‘披甲全球,‘武艺救国,‘唤醒黄魂。”⑦
娄子匡这里的记录比较奇特的地方是,他提到舞狮表演加入了西游记的人物,但没有猪八戒形象,而是两个“猴形”。不知是他所目睹的的确如此,还是记录有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娄子匡提到韶关翁源这些舞狮队伍的构成时,特别指出他们是从江西来的。娄子匡此处的记录缺少完整性,没有详细说明是指当地舞狮队伍主要是由江西人构成,抑或指其中“打江西狮的”演技最为精湛,只是现象性地谈及这些江西舞狮队伍“人数较少,技术较精,能挟孩登十数张台子的上面”,他们以表演的高难度和危险性取胜,“演种种戏法,以人命为儿戏”,“虽过于残酷,但是民众却对他很表欢迎,所以搵钱亦易”。由于迎合了彼时两广人的尚武好斗风气,所以这种高危表演相当受欢迎。
除了舞狮之外,还有今已少见的“舞凤”和“夜鼓狮”。娄子匡记录道:“也有两个纸糊的纸凤头,使小孩蒙着,成寻食,挺翼,生卵的状态,孩子们看了,也很觉有趣。可是他们到底主要耍技术,却是打八音,弄弦索(胡琴,二弦,三弦,月弦,管子,笛……)唱调子搵钱。”不过舞凤的受众比舞狮的要少,“不会欣赏的老百姓们,老是不欢喜舞凤的,而爱那舞狮”,依照乡间的受众欣赏口味,尚武的表演远比尚文的更受欢迎,这或许也是舞凤式微的原因。而所谓“夜鼓狮”,其实类似于花灯出游,“舞牛舞马,舞龙,舞鹤,舞鲤鱼等各操所糊的牛马等,伴着锣鼓旗帜灯笼,多于夜间出行舞弄”,又云,“舞时,有的扮女子,有的扮丑脚,互相向难歌唱,以锣鼓相和,恒使人满意的失笑。歌词多为四句一首,或以十二月为题,或以立春、雨水等节期为题,或以牛马为题,说到人世的辛苦女人的难做,着实是声调委婉凄楚耐人寻味”。依据他这里的描述,“夜鼓狮”跟原生态的秧歌巡走仪式亦有形式上的一致性。这些关于舞狮的文献存在的一个遗憾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从舞狮外观上加以描述,但其实舞狮的鼓点等听觉性的内容则基本不涉及,殊不知,舞狮表演作为开阔地带的表演艺术,除了视觉元素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将四面八方的人群聚集而来的声音,这种声音构造的氛围甚至可以从场域的角度来称为所谓“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⑧。这个空间不但构造了作为文化意象的舞狮表演本身,也构造了观众与扮演者共同存在的文化空间,从而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塑造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
三、20世纪前半叶舞狮风俗
流传地发生变迁的社会动因
如前所述,涉及舞狮活动的文章中,无论是新闻、散文、诗歌还是专题论述,其所提到的舞狮活动虽涉及全国,但最繁盛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华南特别是两广。其中《良友画报》所转载的纽约华侨或也是广东移民。
黄芝冈等作者的文章已注意到清末民国时期的舞狮活动集中在两广地区,但没能进一步解释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一状况。倒是有一位笔名“绍虞”的作者在其文《广州之舞狮》里尝试追溯其中原因,但他依据的并非文献,而只以口述史的形式叙述。他注意到舞龙舞狮这种表演形式具有“寓武术于游戏”的重要特征,然后他叙述说,舞狮习俗原本盛行于湘鄂,旁及于江浙赣皖川黔等省。不过由此引发的斗殴争夺事件太多,特别是光绪二年(1876年)时武汉因为舞龙之事死数十人,导致官府下令于正月十八日后不准舞狮,这导致“湘鄂之间舞龙之风乃渐衰”。而且作者对此说法也不敢确证,只是录此作待考之用,所以他在叙述完之后,在这段开头的末尾以一句“此为余闻之于先慈者”作为总结,言下之意为:这些都是我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具体是否如此我就不敢确定了。⑨
此处“绍虞”认为中国南方的舞狮习俗流行的版图逐步缩减,跟官府禁止有关,此说虽可作为其唯一原因,但关于舞狮习俗为何最终集中在两广地区,笔者认为还与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因素有关。
第一,与地方政府出于特定目的去推动有关。正所谓“社会记忆”是一种被“选择性唤起”的被建构起来的认同政治⑩,舞狮习俗就是一種以“社会记忆”形式凝聚人心的极佳形式。这在彼时的广西新桂系政府方面最为突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当时《大公报》的“南宁通讯”所提:“桂省当局,素重尚武,最近又决定实行一种新的政策,通令全省村庄,每村组织舞狮队一队,每队约三十人,有人造狮子一条,并将废历元宵节,改称‘舞狮节,借以提倡武化,唤醒国魂,一雪东亚睡狮之谓。”11
第二,契合了当地民风,故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最重要的。与广西新桂系政府试图让舞狮习俗为己所用而刻意提倡不同,广东方面却对该习俗有所忌惮,各地一度对之发布禁令,如广州市公安局于1923年以局长那其仁的名义发布公告,强调“禁止耍狮舞龙,如违拘罚不贷”12。然而这一禁令在民众汹涌的舞狮需求勉强维持不了多久就废弛了。
根据关于两广地区的史料和现实风情,粤文化地区不但喜欢舞狮,而且把舞狮当成本土重要民俗内容。而且两广地区的民众也确有强烈的尚武精神,由于历代各种族裔的移民不断聚集于此,所以彼此之间在交融的过程中也伴生着剧烈的冲突。在过去,械斗是发生冲突时“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有能表达尚武精神的表演才能生存乃至生根下来。在戏剧方面,早期粤剧中武戏比例颇大,再又以下四府粤剧的形式传导给广西的邕剧,使得邕剧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南派武功”。舞龙和舞狮在两广地区以包含打斗内容的舞狮为最盛,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粤人“双石山人”在1936年的《舞狮》一文中提到他所目睹的乡中舞狮场景,他说,那一个个“舞狮的朋友”都是“乡中的好汉”,平时就喜欢舞刀弄棍,如今有机会出场献艺,更是兴奋不已。排场练习时,“赤着肩脖露出一身铜筋铁骨,粗皮蛮肉”。所以他感慨在民间提倡这种“务求得胜,务求博彩”的舞狮奋斗精神是值得赞许的。13另外,《北洋画报》新闻里也提到,旅津广东音乐会专门设置舞狮专项活动,为的就是“发奋尚武精神”。作者还以激越而悲愤的心情写道:“狮为兽中之王,一鸣而百兽惧;但当其睡也,虽蝼蚁之小,亦敢撄之。吾国物博地大,文化垂数千年,实无愧乎为狮;然受人欺凌,是正犹狮之鼾然酣睡也。若欲使其雄震天下,歼彼丑虏,则必待吾民族之觉醒。予观某影片,曾见十九路军于杀敌之际,尝高舞纸制之狮,殆亦欲借其以唤起民众,鼓励士卒,俾免受睡狮之讥耳。”14此话当中包含着一个显著的信息:当时的舞狮活动并非单纯的民俗这么简单,而是在其之中寄予了发自内心的“唤醒睡狮,振我国威”的深切愿望。
当然,舞狮习俗虽以两广地区为盛,但它同时也以“超地域性”的形态获得着全国民众普遍认同。如果说高雅的文学启蒙是在“诉诸理性”,那么舞狮等民俗活动就是渗入乡民社会毛细血管的“诉诸感性”15。舞狮习俗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但通过舞狮而构建文化认同却是20世纪前半叶的新兴文化实践。该时段正是所谓“启蒙民俗思潮”涌起之时,民俗理念被知识分子用以作为武器来向民众开展启蒙教育16。与此同时,在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下,如何凝聚人心去创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彼时知识分子努力思考的关键问题17。毕竟,我们需要通过“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意识去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于是就在这种氛围下,舞狮习俗被用作为彼时时代精神的独特载体就成了某种历史的必然。
回顾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国内报纸,常有将中国以“睡狮”为喻,力图唤醒国人,让中华复兴做“狮子吼”的热切期待。如1926年时作者“春伯”在《哀睡狮》一诗中疾呼:“我可爱的睡狮啊!霹雳一声!几千年不曾开过的门栏,一朝被人冲破!无数如狼似虎的妖魔,一齐涌进来了。……你也该痛极了呵!怎么还在酣睡不醒?”181931年时还有作者“佛缘”以《睡狮》为题,写诗呼唤:“睡狮!睡狮!现在有人来唤你,你快些醒来哩!努力!努力!”19用词虽浅稚而缺少诗歌的韵味,但渴望唤醒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在诗歌中洋溢。另有不少文章,也是以“睡狮”为文化符号,表达自己面对国家危亡的焦虑和痛心,以及呼吁大众觉醒以救亡图存。如1932年时上海《中华周报》的社评《睡狮之国》20、1933年时作者“章寅”的《睡狮到底醒不醒》21、1934年时作者“问笔”的《醒狮还是睡狮》22等。
清末民国时期正是国内面临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清末报纸多以“睡狮”形容中国,而舞狮活动在彼时语境下就带有激励和鼓舞国人当自强的文化政治的象征意味。借用学者曾军的话来说即是仁人志士们亟须“在以中西关系为主导的‘世界中的中国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位置”23,从而作为奋起直追西方先进列强的精神坐标,以最终将中国从“睡狮”唤醒为“吼狮”,实现民族复兴的终极目标。由于希望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早日醒来,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国人的共同心愿,故而在象征意义上符合彼时民众的心理诉求的舞狮活动也就顺势具备了其他民俗活动所不具备的所谓“精神势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舞狮习俗在20世纪前半叶走入其获得现代学术记录的启始时期,这些记录不仅以文献形式叙述了彼时舞狮习俗的具体样貌,而且本身包含着关于那个时期的文化政治的丰富信息。于是这一段时期的舞狮民俗研究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知识范畴,展现出承载着那个年代的风云际会的文化意象。
我们今日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传统时,需要在理念和表达上关注这些具有锚定意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24。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就需要让传统与现实态的、有温度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让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25。舞狮习俗不但包含了易于接受的情感认同,而且也内在包含了中国民众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认同,以一种文化意象的方式持续指引和确证着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内在身份认同,需要我们从实践和学术等各个维度上加以细致探究。■
【注释】
①笔者曾经就20世纪前半叶舞狮习俗中具体的舞狮形貌、队伍构成和舞狮表演步骤等相关问题进行过探究,文章见《民国时期舞狮习俗谈》(《文史知识》2018年第10期)。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立足于整个民国时期相关的文献对舞狮习俗进行综合研究。另,舞龙舞狮活动具有相似性,不过舞狮相对于舞龙而言,直接表演人数更少,尚武精神更重,舞狮在表演过程中加入诸多武术的内容,场面更加热闹和“火爆”,发展出的流派和习俗细节也更多,故而这一时期对于舞龙舞狮的记录,实则集中在舞狮方面,至于舞龙则往往是一笔带过。
②贾文山、冯凡:《跨文化认同的流变与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再释》,《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③王丽君:《“五四”百年中国从救亡图存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④高小康:《非遗美学:传承、创意与互享》,《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⑤黄芝冈:《谈两广人的舞狮》,《中流》1936年第1卷第4期。
⑥邓之诚:《骨董琐记》,邓珂点校,北京出版社,1996,第296页。
⑦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第90-103、128页。
⑧张聪:《走向听觉的格式塔——谢弗自然主义声音理论及其现象学方法》,《东岳论丛》2020年第12期。
⑨绍虞:《广州之舞狮》,《民意周刊》1941年第15卷第185期。
⑩刘玉堂、张帅奇:《社会记忆与方志的文本书写——以明清时期〈汉阳府志〉编纂为中心的考察》,《江汉学术》2020年第6期。
11本刊记者:《舞狮比赛:桂省当局通令筹办提倡武化唤醒国》,《浙江民众教育》1936年第4卷第1期。
12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布告(中华民国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广州市市政公报》1923年第69期。
13双石山人:《舞狮》,《民间旬报》1936年第12期。
14曾维慎:《舞狮之意义》,《北洋画报》1932年第18卷第862期。
15刘清平:《文字、理性和正义:三期启蒙辨析》,《关东学刊》2020年第1期。
16刘颖:《晚清民初启蒙民俗思潮的形成与传播》,《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7朱锦、李征、詹小美:《民族共同体建构视域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价值》,《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8春伯:《哀睡狮》,《自强》1926年第1卷第3期。
19佛缘:《睡獅》,《大众医刊》1931年第9期。
20社评:《睡狮之国》,《中华周报》1932年第9期。
21章寅:《睡狮到底醒不醒》,《晨光》1933年第1卷第41期。
22问笔:《醒狮还是睡狮》,《论语》1934年第59期。
23曾军:《古今中西视野下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的演变(1949—2019)》,《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4刘海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儒家伦理底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5刘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简圣宇,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现代阐释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BZX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