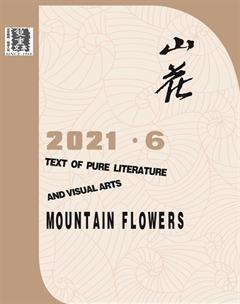打针观察者
玉珍
打针观察者
我生下来是个八九斤的胖子,但不虚胖,小时候我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嚼着花生地瓜跟在我妈屁股后面,带妹妹去卫生院打针。
傍晚时风中有桔梗和草叶的香气,夹杂一部分牛粪和泥土的气味。太阳刚落那会儿天空会有些红,紫红,火红或带点灰的红。最美的是黄里透红的蔷薇色,我们在路上慢慢地走着,我妈背着我妹,她俩都很瘦。我爸也瘦,家里就我胖。
通常情況下我的乡村医生姑姑从盒子里拿出消毒后的针我妹就开始哭,要是哭得厉害了想逃出去我妈会对我说:过来,摁住她。
这句话还会在另一种情形下出现,杀鸡宰鸭时奶奶会跟我说,过来,捉它的腿。场面有些严峻,像在执行什么,我清秀好看的姑姑一边安慰她一边瞄准,像个正在做实验的科学家。
这件事持续时间不长,但她的哭声仿佛在受刑,我望着她,觉得她像个瘦弱的小羊羔子,看她哭得扭曲的小脸蛋,觉得有些心疼。
在这四人组成的小社会里,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妹无疑是反抗者,也是受害与受益者,打针使她的脸第一次有了逃避与抗争的神情,她用哭声与针头做斗争,甚至捏紧了拳头,绷紧了屁股和神经。
我姑说:放松,别怕,不要生气噢。
她哭起来小脸涨红,嗓门尖细直冲屋顶,虽然哭声很烈,性子很倔,但针还是非扎不可。在这场决斗中,病人不存在赢面。
一开始她大哭我会心疼,希望那尖尖的玩意儿来扎我,我愿意为她承受病痛。毕竟针头扎进肉里面这件事实在是莫名叫人害怕,后来次数太多,我也就麻木了。
这件事谁也帮不了她,我可以替她做事,甚至替她去死,但不能替她打针吃药,替她吃饭上厕所。我能做的仅仅是看,盯着看,认真看,望着,记住,回忆或祈祷,我站在那儿,瞪着两只大眼睛,像只可怜又冷漠的大眼田鸡。
我俨然成为了世上最麻木不仁的打针观察者,极其熟练,冷血,镇定自若甚至目不转睛。观察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面对恐惧之好奇,面对哭嚎之冷漠,消化痛苦之彻底,神情神经之麻木,实在难以形容。
我妈胡乱地用衣袖给我妹擦擦眼泪,背着她走出去,我的乡村医生表姑跟在后头重复过去那些叮嘱,并在我妹的瘦脸蛋子上轻轻捏一下,有时给她一颗糖,朝她甜美地笑一笑。我妹的哭声通常要到田间小路上才会停,她被驮在背上,衣服和呼吸里隐约飘荡着药味。有时哭着哭着她嘴里的糖果掉下来,她望我一眼,我就说,已经脏了,不能吃。她就又接着哭。
只有时间能破译孩子眼中的秘密,她哭了,但她不需要手帕,她只要糖。
可能糖会使人开心,她嗜甜,无论米果还是粽子,白粥甚至米饭,放糖就对了,拿调羹大把大把地放。我记得她举着一只用筷子插着的粽子开心地跑来跑去,那粽子浑身晶莹雪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因为裹满了白砂糖,就像个镶了钻的糖三角。
她吃糖时表现出最大的奢侈和快乐,恨不得嘴里全是甜蜜;而我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也爱甜,但我喝粥放盐,炒饭放酱油,凉拌什么的也不要糖,粽子米饺蘸酸水或辣椒面就行,从小吃得辣,也绝不挑食。指天椒、酸菜、苦瓜,压根难不倒我,小时候跟我爸比赛吃辣椒,场面热火朝天。
给我什么就吃什么,我胃口很好,而我妹是给什么都不爱吃(除了甜的)。他们都说我大概在娘胎里面就很会抢吃的,所以妈生下我之后面黄肌瘦,身子很弱,谁知紧接着又怀上了妹妹。
出生前的颠簸,以及苦难晦暗时辰的长期洗礼,让妹妹生下来就瘦小、虚弱,样子难看,气色不水灵,一副营养不良有气无力的样子。老实说,她来到我们身边并不容易,吃尽了千辛万苦,打娘胎里开始,她就是伴随危机和羸弱的,所以我们得呵护她,像保护一个小天使那样。
也许她出生前就累着了,生下后都不爱动,我有时背着她去上学,不觉得特别费劲,其实我不愿意这样,我希望她走走路,但她不愿意,大概是身体虚弱,不爱走路。
放学后我把她带回家,让她一个人玩儿,我去放牛,或者去田里面奔跑,打滚,跟伙伴们玩游戏。我是好动的,没什么能拦得住我,我到宽阔的荒原上狂奔,翻跟头,学大侠,唱歌,狂笑狂吼,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怎么过瘾怎么来。但她不一样,她不爱动,说话小声小气儿,也不太爱笑和说话,她是内向的,像那种天才的沉闷自闭的小孩子。
爸妈和奶奶说我,别四处疯,好好带着妹妹,别到处乱跑乱跳,她会学,万一摔断了腿酿得清(母亲老家客家方言,怎么办的意思)?
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睁着无知天真的大眼睛,不知在想什么。有时她让我想起电影《铁皮鼓》里面的小奥斯卡,因为太瘦,脸小,使得那眼睛显得更大,在小小脸庞上极其突出,但她的神情又没有奥斯卡的那种倔强,她毕竟有些羸弱;她的神情又让我想到了《迦百农》里面的小男孩,随时随地笼罩着无奈的淡淡忧伤,里面也没多少小孩的霸气和顽皮;而她那美丽忧愁的眉眼,又让我想起电影《马戏之家》里面的那个阿格拉娅,那孩子的眼神太美了。
我在山坡上玩,将她放在干净的石头上或草堆上,给她摘些小花之类的。她往远处看着,不知在观察什么。我远远看着她,观察周围的一切,免得她磕着碰着。
在她还小的时候我是很少让她一个人出门的,虽然村里的孩子个个像牛羊一样四处乱跑,但我妹不行。她胆小,身体也不够壮。
村里到处是狗,家家户户都有,多少不一,性情也大不相同。最凶的是我七爷家的白狗,在他家门前经过,见一回吠一回,吠完还撵,龇牙大眼凶神恶煞,就我这样厉害的小孩子,也给它咬过几回,真是逃命般的经历。至于其他的狗,普普通通防着就行,稍微警惕的暴躁的,几十米之外就开始吠,蠢蠢欲动往前冲来,多少会让孩子受点惊吓;但大多习惯了,时间久了,谁家的狗几分危险,已经了如指掌。
不过人们都挺提防,平时还带个打狗棒什么的,我带过,但嫌麻烦,经常会忘记。你要是遇到了疯狗和比疯狗好些的凶狗,你就得稳住,稳不住就得跑,跑不赢就得战斗,战斗不赢就得被咬。被咬是谁也不愿意的,一旦被狗咬了,针是铁定要扎的,打针还得花钱,处理迟了弄不好会得狂犬病。
虽然孩子们怕打针,但死显然更可怕。所以大家都得十分注意,能少一事就少一事。我就曾吃过狗的亏,前前后后打针数次,让我厌烦。
一般的狗只是样子凶,刀子嘴豆腐心,纯属过嘴瘾,狂吠几下看不见人了就消停了,但有一部分狗是没完没了,吠就算了,还得龇牙往前冲,前爪不安分,好像要把人衣襟子给撕下来。对付这个我是有方法的,狗虽然忠诚老實,但难说也有些势利,也怕比它厉害的,这个时候我就会让自己看起来比它更凶,怒目而瞪,或者大声吼叫。
有一次我居然站在路中间与一条狗对峙了几分钟,我们都瞪大了眼睛,作凶狠状,谁也不让着谁,但谁也不往前一些,最后,我见我妹站在旁边有些无聊了,便更凶地往前迈了几步,那狗子居然怕了,被我的气势吓回家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小小年纪便懂得从一条狗的眼睛里去观察狗的内心,或者并不足以涉及到内心那么复杂,仅仅是观察它是否会发动攻击,以及凶残程度能达到几级。从它的眼睛中我能判断它扑向我时我能否迅捷躲开。大多数时候我有把握完全躲过它,而且有把握在我做出比它更凶狠愤怒的神情时,它会有退却的意思,它的前爪,它的眼睛、脸和耳朵尾巴全在传达一种信息,我通过观察这些,可以看到一条狗的想法。这是我与它对峙之前就已做好的事情,我的视力和胆量都非常棒,这基于长久以来对大量狗的观察和了解,还有一部分来自我的无聊。我曾把自己当成一条狗去想象遭遇人类对手时的心情。
我知道它对我并不具有威胁,并且在实验当我真正挑衅它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反应。如我所想,很有意思,狗退回到它的领域去了。它们毕竟不是疯狗,就算我七爷家那条最凶的狗,也仅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咬了我。它是唯一的特例。怪我那时年幼无知太鲁莽,想要跟它大战一场,刚好碰上它心情不太好的一天。有一回我跑得太快冒犯了它和它刚生下的孩子,刚做母亲的它便警惕暴躁地报复了我,其实多年来无数次的经过与见面,它也并没有拿我怎样,它仅仅是一条忠心的狗而已。
我与狗对峙过很多回,因为贪玩好奇和无聊,并次次取得预料中的小胜利,若有必要,我指不定会与野狗打架。而我妈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她说拎着打狗棒可以随便在任何狗群中大摇大摆地过去。
无论任何时候你都能在村子里看到人的脚边站着一条狗,屋子旁边站着一条狗,马路上站着一条狗,黑夜中站着一条狗,任意一道门前也会站着一条狗,所有的狗都是那么善良,具有同样单纯的眼睛。它们唯一会做的凶巴巴的事情仅仅是在感到危险的时候龇牙吠叫,那是它们的职责。
我妹就从来不像我这样顽皮和狂妄。在她和狗中间总是隔着一个我,有我在,可以少打几针狂犬疫苗。我就是她不用扎针的狂犬疫苗。我将她与狗隔绝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当中。她虽然比我小,但遇到什么都波澜不惊。
有时看到她突然往一个地方走,问她去哪,她回头,也不说话,略有沉思地往前,仅仅是去摘个小野花啥的。她有时在田里走来走去,也许是跟着一只蜻蜓蝴蝶,也许是因为兔子和鸟的叫声,她就循着那些玩意儿慢慢走过去。为了不让她掉下田埂或水沟沼泽,也为了让自己不必在她突然的哭声中去全世界寻找一颗糖与彩色纸小玩具之类的,我得时刻保持警惕,像个保镖那样,不时地观察。
我观察她就像观察别的某些让人哀伤的事物一样,比如观察打针,这的确是有些让人警惕和悲伤的事情,但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心不知道哀伤。
当时乡下爱给孩子取些乱七八糟土掉渣的小名,什么猪狗牛羊铁蛋冬瓜之类的,名字贱,好养,接地气又好玩。不过我没有土掉渣的绰号。但我其实是有绰号的,我们班上男同学曾叫我母老虎。就因为我脾气有些暴,嗓门有些大,体格强而且大耳大眼大额大脸,是女孩里气势最猛的。
我爸是个文雅之人,也没给我妹取小名,因为瘦小,就叫她小不点。我们全家都很呵护小不点。我后来想,如果给她取名狗蛋牛娃猪屎甚至大滚坨子之类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除了打针时的哭声,她的嗓门从没有特别强有力的表现,我既希望她忍住嚎哭省省力气,又觉得她很快便会好起来,因为一个特别虚弱的人是发不出那种穿透屋顶的尖利哭声的。
我知道疾病长在她的身上,那是个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对疾病没有办法,对贫穷也没有办法,一切都需要慢慢克服。我能体会到羸弱和悲伤的滋味,不仅因为我多病的妹妹,那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敏感。我对可怕的东西有种残忍的好奇心和感受力,也许是哭声听得太多,心肠变硬了,我能很好地忍耐这种残忍。
我很少在她面前表现出不快乐,也不跟她讲烦恼的事情,我怕她累。我希望她所有的力气拿来长个儿,长肉,长力气,她只要开心就好;我希望她那美丽清秀的黑褐色眼珠里不要有不像孩童的无趣和疲累,我宁愿对着牛说话也不会打扰她。我将全部的语言的负累扫进了垃圾桶,她现在很快乐,比我快乐。虽然小时候有些病怏怏的样子,但五官极其好看,那种美貌在十几年后展现出来,她也在调养下恢复了不错的体质。生活仍往返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困难和灰心中,与此同在的是大大小小的幽默与自得自乐。
而我们的性格也朝与儿时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
一切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现在比她小时候更不爱动,也不爱说话,讨厌与人打交道,讨厌说话,甚至讨厌出门,而她相反,我们的位置互换了。现在我是羸弱者。
有一回冬天深夜我突然不舒服,难受得不得了,她从床上爬起来开车送我去医院。车子里很暗,也没有声音,半路上突然听到她在哽咽,偷偷拿手擦眼泪,我问你干嘛,她不作声。另一回我低血糖犯晕进医院,同事将她喊来,在医院我醒来就看到她眼珠哭红了。她长大之后就哭过那么几回,平时遇到困难从来不哭。
只有极少的事能让她流眼泪。她得了一次肠炎,前后扎了四五回针,回回哭,屁股针那下子她死活不同意,怕,二十多岁的人,吓得在医院大哭,我突然就想起二十多年前她也是这样哭,好像我们都还没长大。
来打针的小伙子站在那儿,看着她哭,我耳边不住地回响着我妈的二十多年前的声音:过来,摁住她。好,别哭了,不疼。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我对那小伙子说,你来,我摁住她。
小伙子腼腆,见她还在哭,站着没动,我跟她讲了一堆道理,然后说:不打也要打。
她知道逃不过了,只好别过去咬牙把头埋在病床上。跟二十多年前不同,我也把头别过去,我成了最敏感的打针观察者,不敢看别人打针,自己也怕。
我仍然是观察者,仍然有麻木的时候,仍然会瞪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看某些事情,但不是从前那样。
不会有那样的时辰了,蔷薇色的晚霞,熟悉的哭声笑声。草叶泥土的味道,药房的味道,背着布包的学生,天空下河流的颜色,河边上圆形或三角形的树,树上剧烈的蝉鸣,油亮清香的树叶……
我跟在我妈屁股后面慢慢走着,那时我没有痛苦。
驼背者
这儿的男人女人,到了老年大多将头往大地上垂去,驼背这种悲伤的仪式,居然要在脖子上持续十几甚至几十年。
傍晚时我站在房檐下发呆,夕光中驼背老人们一个个出来,干净的青石小路,被踩得透亮,纯洁。老人们走向原野,一天中最后一次去地里收集枯草拿回家引火做饭,或召唤家禽,喊在外头顽皮的孙儿归家。我跟着他们走出去,我那时还小,就像个跟屁虫,喜欢跟在驼背的老人后面,驼背让我看不见他们的后脑勺。
他们跟我说话,说,孩子,回家去,别跟着。
但我没有。
村里面很多老人,都是老人带孩子,大人在外面打拼。在那种峦雾漫天丛林莽莽的山村,森林草木中渗透大量湿气,多数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犯风湿,驼背。
我的外婆六十岁就背驼得厉害,走起路来很累。当她忙完自己的事情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在那种静止中缓气歇息。我们都让她不要出门做事情,但她总是不听,也许一个人静静待着久了也觉得孤寂无聊,要出去走动走动。一个人驼背了老了,大概连坐着躺着也是累的,无论怎样,苍老和沉疴还是很快将她召唤去了,在天上,她不要再受沉重之苦了。
山里面像我奶奶这样,八十多岁仍然腰背挺直的老人不多了。崇山峻岭里的老人几乎都在跟风湿抗争,我的三婆善谈而勤劳,一生在群山、溪沟、丛林里穿梭,去山沟里采猪草,种菜种地跋山涉水,几乎全年都与冷水打交道。疼痛慢慢进入到她的骨髓,最后这缓慢的疼痛带走了她。后来三爷也难逃厄运,有一次我放假回家,看到他坐在竹椅上鼻青脸肿,额上还有伤痕血污,很心疼;他说走在路上突然摔了一跤,因为膝盖不能用力,完全走不了了。我想这就是风湿,长年累月到现在,根治是不可能了,只能去医院开药调养,治一治就会好很多,顶多承受点风湿骨痛。他说好,他也觉得只是膝盖不给力了,人还是好的,然而我回单位上班不足一个月,他竟然去世了。
他们之前的人生总在苦难中度过,肩负家庭的重担。到了晚年,很多事情已经没法去做了,健康也恢复不了了。
我见过一个很穷很穷的老人,晚年背驼得厉害,但因为生活穷困,仍然要去地里干活,她将一个背篓背在身上,驼背使那背篓像背在一个拱形的小山坡上,因为篓子够深,所以走在她后面的人只看到了背篓,看不到她的头,仿佛是一个没有头的背篓在走路。
当一个人的背驼成骆驼身上的一个驼峰,因为累他们的头都不爱抬起来了。声音从那儿发出但不知道他们的神情,即使有神情也被皱纹遮盖,消化了。后来他们大多严肃,再后来,寡言,苦涩,警觉。他们已真正朝最低处望去,直到看穿生死。
我儿时见到过太多驼背的慈祥老人,他们走在路上,只能迫使自己抬起头来。如果个子很矮,驼背会让他们看不清对面高个的人。最后近处的看不清,远处的也看不清。有时他们点燃了原野的荒草或一堆垃圾,身躯像个符号在那儿悬着,腿脚小小的,细细的,身子弯弯的,矮小。火焰晃动着他们的影子,有些悲壮。
驼背者看到的会更少,听到的却会更清楚,但他们又不是完全看不到。当我看到驼背者站在风中和夕阳下,仿佛从他们那弓向大地的嘴里面会发出什么声音,我会悄悄地站在离他们不远处,等着他们做出什么动作或发出什么声音来。有时候他们会讲要变天了,我怎么会相信呢?我是一个孩子,我对一切看上去神气庄重的东西带着孩子气的轻视,但后来我发现气候真的变了,甚至会有一些灾难,比如洪水或火灾。我甚至一度想要低下头去看看那驼背者几乎低到了大地上去的脸庞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眼睛究竟从大地之上看到了什么?他的耳朵究竟从风中发现了什么秘密?
驼背像一种证明,苦难的羞辱或表扬。在它上面是时间、日子、哭泣、荣耀、劳累、屈辱、付出、恐惧、忙碌。像一粒种子长回到它的原点,无限弯曲着接近开始的地方。
我常能看到驼背老人们前前后后走着,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伙伴,亲人般活在这个地方,儿时一起长大,年轻时都是好兄弟,个个腰杆挺拔一表人才,身体强健生龙活虎,去过外面的世界闯荡但一一回来,一起去漫漫的山路上運过货,一起在命运的打击下发过誓,在黑暗中一起奋斗过。
年少时大多血性轻狂,为些小事都要争斗一番,他们会在河滩上打架,有时候他赢了,有时候他输了,但总会分出个高低。不论如何他们总归热烈地年轻过,像一把骄傲暴躁的火,被时间往下按,直到现在,弯下腰去,慈祥又沉默。现在好了,老年是一切的和解。无奈的命运,默认的顺从。
大家都要低头,全体低头,朝向泥土,然后钻进泥土。
十分得体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