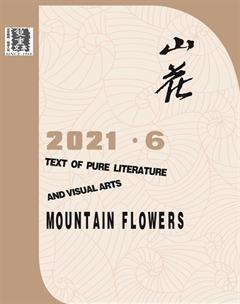头上天空,脚下泥巴
李晁
最初是谢挺老师在编辑部里提到一个人,自然,我们说人,就一定是作家,因那是带着发现的喜悦被讲述出来的。彼时,我刚来编辑部,以我的眼生对发现一个新作家还很有些茫然,喜悦即使经过前辈的渲染,也很难感同身受。我所知道的作家都是我曾明确知道的,这建立在阅读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文学刊物与图书是一个可供无尽挑选的内容库,我以为可以这样一劳永逸地开展工作,时间却很快证明,我太天真了,那是一份难以获取的目标。而今回头看,每一次的发现有多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谢挺老师口中的那个人,就是尹文武,当时居安顺,在银行工作。简短的介绍换来的还是茫然。一个作家毕竟是与作品关联起来的,一旦不掌握作品,即使那人的简历长达一百页,我们也不会知道得更多。更因为编辑与编辑(同事)的作者有一种微妙关系,这几乎是一种友好的隔膜,也许不少行业都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但在编辑行当,这几乎是一种秘而不宣的規定动作,即我们可以漫不经心到对彼此的作者不闻不问。
我想当然地以为尹文武是写职场小说的。
事实证明,我又错了。印象的作用正是这样,要么加深,要么递减,这印象是指作品。从早期的一系列小说,到眼下,作家的变化已被刊物所证实,这是实证的,倒不是说刊物有多么权威,而是指刊物背后的眼光。
提到尹文武的作品,就不得不提及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和其间的人物。地理环境当然是指本乡本土,人物也在城与乡之间,他们要么是久居山间的人,要么是进城混生活者,而唯独没有尹文武置身其中的专业职场氛围。我曾就这一问题咨询过他,银行里会诞生多少故事多少人物,那些金融内幕(我们以为的内幕),为什么不可以化身写出来?这正是我们陌生的呀。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过于简单,从实际来说,作家面有难色,似乎一言难尽,这里的难度自然可以理解。人类酷爱对号入座,这传统由来有之,经久不衰便是明证。多少作家回到故里或置身熟悉氛围,总会被人指责是故乡或某一氛围的破坏者,当人们怀着抑制不住的好奇去阅读一位作家以人们熟悉的背景展开的作品后,无一不会恼羞成怒,他们会以为这个那个人物就是“我”,一旦涉及“我”,涉及人性里的那份难堪乃至丑恶,他们前一天还引以为傲的作家瞬间就会沦为恶棍或者恶妇。从杜鲁门·卡波特到门罗,无一例外。此外,作家的写作离童年不会太遥远,这是基因一类的顽固遗存,童年生活的烙印之深,是一生难以消磨的,大家从不同的原点辐射出去,不论一个人能走多远,都会被这原点所牵绊。迪迪埃·埃里蓬从故乡兰斯出走三十年,仍摆脱不掉故乡笼罩的阴影,不论他用多少谎言掩盖、模糊自己的过去与家庭,最终他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成长之所。羞耻,是他真正的出发地。但对小说家来讲,这样的忧虑与障碍恰是自我得以树立精神坐标的基础,作家的叙述倾向和对象,是不被后天的身份所动摇的,后天身份带来的落差实则是一种断裂,无法填补,它属于顽强的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讲到这里,尹文武为什么回避自己的从业环境,就可以理解了。要我说,这也是最为质朴最不投机的写作,事实上,这更是一条显眼的有着广阔背景的窄路,因他会发现自己一出手,就要和那么多作家那么多作品去搏斗。传统路径的路最难走,因要走出新意。
通过对作家作品的集中阅读,我试图在尹文武的小说中寻找几个关键词,但我发现这是徒劳的——人物的生存场域自然有其独特性,但放在更广泛的范围来考量,它仍是不同地区千千万万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由此看,地球仍嫌太小,人类到底是单一和孤独的族群。我说的小说场域是指那些山寨、乡镇和城市,它们来自小说的人物视野,在他们的感受中生发。
《王熙凤》里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处建筑工地,一个叫幸福小区的地方,怀有进取之志的打工青年因对“迎春楼”某一扇窗隙的眺望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说的侧重点显然不是这个叫王登峰的青年的命运,生命的突然终结也从来不是一种有效的呈现方式,这一点仍可以与作者商榷,只有小说中透出来的工地上野心勃勃的运转法则才是令我们毛骨悚然的存在。尹老板的精明布局正是世相的浓缩,他梦想开办的“银行”不过是另一台更大的压榨器,而窗帘的缝隙那么窄,窄到无法容纳一个青年紊乱的偷窥目光,多少蓬勃的生命在面对尹老板的老谋深算时纷纷夭折,王登峰是唯一的例外。这例外也带来了撕扯,这正是发现那一道暧昧的光芒并被它持续吸引的时候,这是青春最难以被制服的悸动,然而对于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来说,这一切又可以被抵制,因而“大红花”的奖励之于王登峰便是无效的。另一头,工友的生活仍处于紧迫之中,紧迫到没有人愿意睡懒觉,因“老家那边的人不允许”,短短的一句话,触及了小说后面的生活……凡此种种,小说的言外之意与巧妙便这般联合起来。如果换我来责编这篇小说,我也许会建议让王登峰活下去,未来的目标并不因死亡而终结,但也并不会因为肉身的存在而变得可以实现,或者说变得更容易实现。
《石房子》写的是一对老人,这样顽固的老头在乡间为数不少,两者的微妙敌对转化为攀比,你起高楼,我便要多起一层,这是心理层面的压制与胜利,狭隘到可笑,可它带来的是对生命的确认(亦即现在说的“存在感”),又是一个人得以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这理由来得简单直观乃至粗暴。曾是村长的王山民要修石房子(坟墓),曾经的对手马培林岂能落后,王山民修两座,马培林便要修三座,一个孤独的老人,为何需要三座气派的石砌坟墓?简直毫无道理可讲,这是小说超离现实的地方。马培林说,“我死后,一把土埋了就行了,修三个石房子,也不是我想用。大丫、二丫迟早会出嫁,就算了,你们兄弟正好三个,以后就留给你们用吧。”这是令人瞠目的安排,“马培林说的也是实话,谁住石房子他无所谓,反正王山民要修,他也要修。”这是一个人的心气,不论狭隘疯狂与否,人物的性格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至于随后接连的死亡,已不再重要,这只是让小说得以继续的手段与交代。最后看,石房子的气派与金丝楠木的棺木不过是用于炫耀的存在,就这一点来说,王山民的执着仍处于下风,马培林的看似跟风,绝不落人后,其实并不是为了身后的自己,而只是为着一口气,在他眼里,眼下就是唯一的意义。
两篇小说对现实的贴近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之处,对于人物命运的安排,多少有些强行与随意,但这过程里作者流露出的却是关切,是对人物如何存在或何以存在的指向,是对处境的表达,又因粗粝的叙述,让小说有种未经打磨的生涩。我以为粗粝感是一个作家原生的写作天赋,当然也可视作一种方式。在《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里,安妮·普鲁正展现了一个小说家难得的粗粝之气,在《脚下泥巴》《荒草天涯尽头》《身居地狱但求杯水》《工作史》里,那种强烈粗狂的气息犹如西部荒原上的狂风,狠狠地拍打着读者的心。那是暴烈到不容细腻心思来展现人物的时刻,只有通过不断的行动,才能安放那些人物的躁动。安妮·普鲁曾自道,“我多少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地理、地质、气候、天气、悠远的过去和时下的事物塑造了人物,并且部分地决定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这一点,正是我在泛意义上的西部,具体来说是贵州,想要从作家笔下看到的东西,我想我看到了。
就作家的这一系列作品来说,如《拯救王家坝》《最快的行驶》《王胜利造梦》等等,如果能少一点作者的小小机锋,磨砺出更为粗粝而又明快的风格,那将是极为可观的事情。
在这之后的小说《枪声》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跳出熟悉的当下氛围,稍稍眺望了过去,这是一个发生在乌江边的故事,它涉及财主的生活,江上生涯,神秘的弹棉花客,他们彼此的交锋让小说透着历史的迷思,也显出历史的转折对这一处封闭生活的改变。这个小说的出现,在作者原有的创作版图上开创了新的领域,它甚至细腻了,看上去机锋也变得更加微妙深藏了,有着“谍”的味道,这是作家的一变,也是难以隐藏的趣味。
有一年,尹文武去了一个县的支行做行长,那是他屁股不落座的时期。既然难得遇到,逮住他我就会问几个关心的问题,比如城市发展与金融的关联等等。我记得的回答,没有我自以为的焦虑,以我的短浅目光是无法看透这一切了,因而他的回答于我相当于一针镇定剂。
尹文武任职的地方是紫云,一个梦幻般的名字,它是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有着我们熟知的格凸河穿洞风景区,长达两万六千行的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魯王》也是在这里被发现的。有一年我们前去采风,那是我第一次到紫云,我顿时了然,山水因文学作品留下的印象是奇特的,风景的直观也不过是一种感官印象,文学作品的难度在于将人事完美地融入其中。那时,我哪想到有一天会读到尹文武的又一篇小说——《飞翔的亚鲁》。
我至今也没有问过《飞翔的亚鲁》的诞生是否与那一时期尹文武在紫云的任职有关,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2020年第2期,作为短篇小说栏目的头条被重点刊出。小说的责编刘汀对我说,这是篇好小说。有这么一句话就足够了。我读《飞翔的亚鲁》是在发表之前,还是初稿阶段——尹文武不常拿小说给我看,一旦他说有个新作要让我看看时,一定是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记得对初稿提过几个意见,就这篇小说我们做过简短的交流,等它再出现时,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版本了。
我很喜欢这个标题,《飞翔的亚鲁》。提到这篇小说的背景,我们不一定要对《亚鲁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该说到的,小说里都浅浅地提到了,苗族的迁徙与征战,正是通过口口相传被语言而非文字保留了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事业。“在高溪,每家小孩的背扇带上都绣有象形符号,圆代表太阳,椭圆代表月亮,一横代表黄河,二横代表长江,那是祖辈迁徙的记录,再以歌的形式传唱,一辈传给一辈,源远流长。”已经足够了,这简短的描述,已是流传的另一种形式,现在我们赋予它艺术之名,实在是浅陋了。
小说从这么一个即将被扶贫搬迁的苗族山寨说起,豹子岩、月亮河、高溪、法那……这一系列地名串联起来的正是远古与当下的遇合,这遇合到了现在,又面临全新的情况,即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小说里有一句“高溪的困境是什么?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困境”,人对故土的依恋,对现状的坦然,都蕴含其中,这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权利,因而当“贫困”这样字眼出现时,便显得过于刺眼。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考量,这是现实一种,可对灵魂与肉身的安放来说就是另一种,两者的遭遇正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生涩的刘干事出现时,大家的目光是不信任的。可,还是要走。正如祖先的一次次迁徙,这是一种基因,也是当代的迁徙史,而这一次并非躲避战乱与逃离不可预计的危险,而是要摘掉贫困的帽子。青马跟随着阿公来到了热闹的法那,阿公的存在是一个象征,由他接连起过去和当下,他是孩子们对祖先与历史的认知导师,可这又是一个“不安分”的角色,他在法那无所适从,他的眼中也没有生死,一切的死亡都是朝向东方的旅程,是回归祖先魂灵居所的必然之途。我不知道现代文明在试图解释生死时,会不会想到还有这么一处群落,有着这样超脱的视野?我最近阅读的安妮·普鲁的长篇小说《树民》恰让我想到了《飞翔的亚鲁》。原始的开发,印第安人的迁徙,乃至环境的败亡,给人心留下了多么大的漏洞。对于外来人来讲,这是文明的进程,可对自然生存的一方来说,它是带着破坏力的介入,它扰乱了自然与人的平衡,所以北美的发现、开发史,实则是带着浓重的血腥与原罪完成的。这一点又与《飞翔的亚鲁》不同,这是美好的愿景,搬迁的目的有多种,不仅为着消除贫困,它或许还是让不宜居住之地的人将自然还给自然。阿公的命运与挫折正是肉身与心灵归属的挣扎。真要仔细推敲,何为故乡?这便是很难推导的难题,故乡的前面难道没有另一个故乡?我们到底要遵从哪一个?故乡正是无数故乡的叠加才对呀。但人又是现实的,往前一步与退后一步,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抉择,因而小说里的故土显而易见,但心中的故乡却遥不可及,所以阿公在高溪种下那些幼小的柏木,正是他对故土最为质朴的留恋与告别。小说的精神向度在此完成,诗性的跳跃将我们从简单的故事层面抽离,让我们得以以仰望的姿态活着,去面对此在此身的变化,这是小说带给我的触动。
让我们来看看阿公的吟唱,这是经作者整理加工后的歌声:
我们乘着岩鹰飞翔
我们乘着马匹飞翔
我们乘着鱼儿飞翔
亚鲁,我们都是飞翔的亚鲁……
布朗肖在写塞壬之歌的那篇《遇见想象》里有如此一笔:“在这真实、普通、神秘、简单、寻常的歌中,是有点那么不可思议之处,人类一下子就能看出这点不可思议,无须真实,这歌凭着陌生的力量就能唱出来,那陌生的力量,说出来就是想象的力量,这歌,是深渊之歌,一旦流入人的耳朵,每个字都似深渊大敞,强烈地诱人消失。”这是极为精准的概括。可被传唱的《亚鲁王》却与塞壬之歌不同,它是飞翔之歌,是高山之歌,它不诱人消失,它只是召唤,对一个人身后灵魂的召唤。若没有这召唤,那些先祖的磨砺、开创的历史便会日益苍白;没有这歌,回归的路途无从说起,它会消失在千头万绪的生活中。
对于尹文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小说,为他的小说写作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我知道这有多难,每次要写一个新作品,往常的经验、教训通通变得软弱无力,你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话,有人不认可,以为创作总是连续的,他们不会想到新维度的发生要经历多么大的煎熬。极端自信的克洛代尔写完《人质》后致信纪德,“过去的经历没用,每一部新作都在提出新问题,让人自感新人一般,满是不确定和焦虑,另外还容易叛变……”同样的话通过克洛代尔之口,我相信要让人信服得多。
《飞翔的亚鲁》还有续篇,就是《阿公失踪》。刘干事依旧风风火火地出场,这犹如李向阳挎着盒子炮的出场让人莞尔。阿公的顽固在这里变得更为强烈,可他看待世界的眼光又那么洒脱高拔。这个倔强的老头在新的地方开始了全新的事业,经历了熬柏油、养马蜂,最终他成为退守高溪、住在树上的人。阿公的秉性我们在前一篇里已瞧出端倪,只是没想到会来得如此决绝,可我要說,这不光是让人哀叹的,因为老头将他的智慧与顽强传给了后代子孙,犹如他曾经在高溪山上种下的那些柏木苗。
到了《巴诺王》,仍是以扶贫为时代背景,展现的是这一背景下的新生活,古老的苗寨搬迁带来的人事变化。老阿公的儿媳妇嫁入城里,迎来的新生活并非如意,但女人隐忍坚持下来,并创出自己的生活,而留下来的老阿公则进入牛奶场工作,饲养本地黄牛和进口奶牛,与奶牛之间的情感,逐渐转化了苗族古英雄“巴诺王”的称号,这是老阿公的情感投射。远古的召唤,让他异想天开地想放奶牛一条生路,奶牛的进入与孙辈阿郎的境遇也形成一种比照,我们会看到人物的当下处境与远古血液里的对英雄的崇拜仍然铭刻在人物的行止之间,忧伤的氛围里,见出人世的复杂与多态。
尹文武最初是写诗,可从他的小说里见不到多少诗歌的影响,直到《飞翔的亚鲁》出现,一个小说家的“诗人附身”在这里得以完成,这不仅指向语言层面的表现,更是指精神上的贯通,对短篇小说的理解,他在紧盯现实的小说里完成了一个难度系数谁也说不好的动作。目光的抬升,必然带来视野的宽广,这是值得欣喜的变化。可还有一路小说,在现实里,也完成了一种跨度,那是对时间、对事物变化的掌控,这就是《军马》。
《军马》的丰沛信息含量犹如一个中篇小说,这是我阅读后的印象。我也曾问过尹文武,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中篇,这是一个值得用中篇篇幅表现的作品。这观点和作者本人不谋而合。不过后来再想,这也只是一种幻象,小说的内容在紧凑中已经表达完成,何须再填充延伸?这篇小说的复杂度在作家的创作序列里是最高的,可以说是最不好写的一个,它考验了作家对叙事的把握,对时代变化的体察。
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一种见证与落差,在这不短的时间进程里,生产队对军马场军马的紧迫念想,换来的只是一次次落空,为此生产队派出了一个个的人:知青教师王宝才,赵牛馆,赵牛馆的女儿大槐。可以说为了接近军马,为了一次可怜的交配权,生产队简直用尽了办法,直到军马场改制,转为畜牧场,西屯生产队才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让雄壮的军马来到生产队助力生产。可谁也不会想到,军马的到来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会迎来更大的挫折。畜牧场一下将四十九匹军马卖给了费尽心机的生产队,生产队组织了隆重的唢呐班去迎接……故事看到这里,似乎皆大欢喜,看到张队长了却夙愿,我们也很振奋,甚至替他长松了一口气。但时代的迅猛变化降临了,包产到户的实施很快让军马进入每家的户头,可这些漂亮的军马根本无法胜任农活,于是故事翻转,没人想要这些马儿了。所以,刚刚开怀的张队长又一次火烧火燎地奔向畜牧场,想换回自己的土马……
对不同时代的观察,对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描述,告诉我们他们曾怎样生活,还将如何继续,这不仅仅是小说家面对世界的好奇,更是一种沉潜,这是审视后“穿越历史的运动”;从接受层面,一些小说(如《飞翔的亚鲁》《巴诺王》等)具有了这样一种指向,在身处变化的时代,在信息庞杂汹涌的潮流中,修复心灵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功课。
注:标题来自汤姆·罗素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