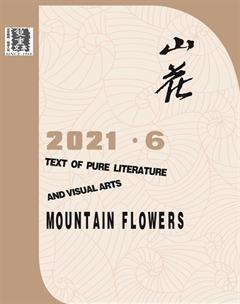死者
严彬
一个人临死前会有什么感受?
他(她)会看到一些什么?
有人说那个正在死去的人会感到自己变轻,他慢慢上升,竟离开了自己的身体——那是他的灵魂。从前一个人只能偶尔感受到灵魂从身体中飘散出去,这一次人看到自己的身体下沉,远离了自己——他正在成为一个单独的灵魂。理性的人会希望记录和理解自己的死,那是他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最后一次机会,他要好好把握。如果有可能,他还希望说出那最后一天关于他的一切,而不只是感到恐惧和痛苦。有很多神奇的传说留下来,告诉世人某某人亲身经历了死亡,他回光返照说出临终前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后才真正死去。这样的传说无法得到任何验证,因为那样的人也早已作古。
在乡下,一个人如果生病,或者年纪很大了,他(她)往往提前就能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如果他那时重病住在医院,就会请求家人为他办理出院手续,用车将他拖回家里——我爷爷当年就是那样做的,他和他两个女儿说,要给他从镇上的医院办理出院手续,他要回家。如果他有力气,可能会自己走路回去,就像电视中常有的那样,他会伸出一只手,示意他的子女都来身边……
大多数人都有面对死者的经验,亲眼见过身边亲人和邻居的离世,参加过他们的葬礼。我的经验也是如此。他们曾生活在我周围,给过我长辈、邻居和亲人的关心、仁慈和爱。那时候他们在浏阳河岸走来走去,如今都已泯灭,身体被埋进泥土里先后腐败掉。我提到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活过,还有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深浅不一的情感。
施爱华
施爱华,我的奶奶(外婆)。
我们那里管奶奶叫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的称呼,可泛指熟悉的年老女性;也可狭义地特指自己的亲奶奶,爷爷的妻子。我的娭毑施爱华大概生于一九三零年,比我爷爷严定洋小三岁。她死于一九九零年,那时她的丈夫严定洋六十三岁,皮肤白净,身体健康,自己种两块菜地,常常挑菜上街去卖。
施爱华去世的时候是在夏天,天气很热,那时我已经九岁,对这件事情大致还记得。但我已经忘了我奶奶施爱华的长相,她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记得后来请人根据我们亲人和邻居的回忆性描述画了一张像,曾经悬挂在我家堂屋朝南的墙上,后来也不知何年何月没了踪影。在我们那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通常会给自己准备好一张高约一尺的照片作为自己老了(去世)以后的遗像,黑白色的,大部分是相机照的,也有讲究一些的人家,就请人提前为老人画像。这是为那位老人离世的提前准备,并不是做什么不吉利的事——几乎每位老人都会提前拥有自己的棺材,那棺材一般放在侧屋或楼上,早早刷了几遍红色油漆,在暗处停放着,发出少许幽暗而令人惊恐的光。我爷爷的棺材曾经放在我家楼上,那是我奶奶去世以后他给自己准备的,漆着红色油漆,久而久之,油漆的紅色也褪色了,等到我爷爷去世时,又重新漆了一次。我娭毑却没有能够提前做好棺材,因为她走得突然,我们都没有料到她老人家的死。
施爱华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八岁。她是一位身材矮小但并不瘦弱的女人。我没有见过她的照片,自然也不知道她年轻时候的长相,我爷爷和我妈妈、我姑姑也都没有给我说过。我记得我娭毑似乎长着一张圆脸,比她的亲妹妹——我姨娭毑——要胖一点点。我姨娭毑现在还在世,住在离我家约七八里路的平达岭上,小时候我爷爷常常带我去走亲戚,走路去,走路回,有时还在姨娭毑家留宿一两晚。如果我还想要回忆我娭毑的样子,可以去姨娭毑家看看她老人家。我姨娭毑年纪很大了,也有八十几岁了,她已经比她亲姐姐多活了快三十年。很多年来我都没有去看望她,有几次她来我家而我不凑巧又没有回家。想起这些,我总是心里隐隐难过。
我对我娭毑施爱华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她活在我的童年时代。记得她喜欢拿着竹制的丛嘎(音,第一声)耙子到河边树底下去耙柴。一年四季都会有树枝和树叶子落到地上,秋天和冬天多些,春天和夏天少一些。落在地上的树枝和树叶子很快就干枯掉,我娭毑把它们耙到一起,成为一堆一堆的,隔几天再自己或叫爷爷帮着装到竹篮子里提回家做柴烧。因为耙柴,据说我娭毑还和我邻居付伯娭毑起过争吵,闹过小矛盾。也许这是真有其事的,因为乡下人忙的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时常为一些看起来没有必要的小事争吵怄气,有时候结怨多年,有时很快又消释了。
我娭毑是在一九九零年夏日的某天傍晚,吃了一顿狗肉后,拉肚子不止去世的。那时我还小,很多细节记得不清楚,只知道她临终前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吃狗肉,很开心。晚上我奶奶也照常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她已去世了。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我娭毑是怎样难受地过去的——而我印象中为什么不记得我爷爷在?我爷爷在的话不会发觉并送我娭毑去医院吗?或者已经送了医院,只是我不记得了?……那中间的事我全忘记了,接下来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奶奶的葬礼,就在那之后的几天。
后来我们才知道,狗肉是大补之物,并不适合体质不好的人突然大量食用,就像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一次食用大量人参便会鼻孔流血。我奶奶体质不好,大概肠胃也不好,我们没有在意,一家人吃了狗肉,她就那样去世了。她肠胃不好的体质也遗传给了我妈妈,我妈妈又遗传给了我。
她的老家是施家冲,也是镇头人,离她出嫁的地方大约十几里路。她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德老舅,还有她的亲侄子,也就是我的施今春叔叔,后来多年我们还经常互相走亲戚。去年过年前我爸爸和我说起老舅,说应该去施家冲看看他老人家。德老舅人很好,很乐观,又很高大而英气,年轻时候一定是很迷人的。他很喜欢来我家,在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常常过年来了都要住上几天才回去,后来我爷爷去世了,他也常常来走动。施家冲在浏阳东边的山里。“冲”在我们那里就是山里住人的地方,与冲类似的还有某某坳,某某塅,也相当于北方的某某屯,某某庄,某某沟,都是中国乡村小村民聚居地的意思,和村子相当,但不是严格的行政单位。从前施家冲的人家到了冬天,家家堂屋或灶屋中都会有一个火塘,火塘中烧着柴火,上面吊着开水壶或各种腊肉。人们围着火塘烤火,非常暖和。
施爱华没有留下什么传奇故事,后来也很少有人提起她,和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人一样就那样消逝了。但她是我亲娭毑,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妈妈也是在对自己肠胃不好的一片惊恐中去世的,她死的时候才四十九岁。
家叔娭毑
家叔娭毑就是我叔公(严定湘)的老婆,严波和严小春姑姑的妈妈。她就在我家隔壁,只有一墙之隔,是我十八岁之前经常见到的人,可我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直就不知道,好像她根本不需要名字。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叫她“家叔娭毑”。她长得高大,比她丈夫要高些,人也很壮实。
家叔娭毑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具体的原因去世的,我也忘了。她的葬礼我没有参加,那时我不在家,应该已经到了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我知道在去世之前的很多年,她的精神已经不大正常了,时好时坏,但也还可以控制。
一个人精神不好,神志不清,很容易离家出走成为流浪汉。在镇头,我记得那时街上总有几个疯了的流浪汉在街上游荡,晚上睡在街上。当人们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一位从前常见的疯子,那大概就是他已经死掉了,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那些疯了的人,我们叫做癫子,疯癫的癫。疯性很强的癫子行为极不受控制,很有危险性,他们可能打人,可能抢小孩东西。因此大人们也常常说“你不要淘气啊——再淘气把你扔到街上去,让癫子来打你!”,孩子们就怕了。癫子们也常常在乡间游荡。他们各人又似乎有各人待的地方,比如某个癫子习惯待在某条街上,某个癫子总是在街口塘坐着……
家叔娭毑的神志不清是阵发性的。我知道的那些年她发过几次病,但不总是失常的,情况还不算太坏。她好的时候喜欢打牌,牌技很好。她不是十分热心的人,并不像一般的邻居那么热心于见面打招呼——但人总还是不错的,没有听过什么关于她的不好的传言。我记得她和我姑姑、上面涂家的几个年轻媳妇,还有我亮哥哥的老婆,她们几个女人常常聚在一块打牌,纸牌和麻将都打。有时候她们就在家叔娭毑家左边的卧室里打牌。那间房子很大又很黑,当时有一盏从屋顶吊着下来的灯泡,通常是四十瓦或者六十瓦,发出黄色的灯光。因为房子很大,有大概七八米深,又只有一扇朝南的窗户,一天到晚,如果她们打牌,就得开着那盏发出黄色灯光的灯。家叔娭毑常常能赢到钱,这大概也是她喜欢打牌的原因。她的面部轮廓清晰,眼睛和牙齿都有些前突,因此等到她打牌高兴了笑起来,总露出她那大大的前突的牙齿,看上去并不那么好看。
家叔娭毑是个真正的家庭妇女,一般不出远门。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嫁过来的,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干活很麻利,插秧和割稻子都很快,干这些农活她都是一把好手,和一个男性劳力没有多少区别。没有活干的时候,她不是那么勤快的人,就在家里待着,很多时候是靠打牌来打发时间。她嫁给家叔公,她的女儿比我大三四岁,儿子比我小一歲。她老公和我姑姑的丈夫是亲兄弟,也姓严,就叫做严定湘。严定湘和我爷爷是同一辈分,都是定字辈。我姑姑属于近亲结婚,嫁给了严定湘的亲弟弟严树海,也就是我树叔叔。这样一来就乱了辈分,树叔叔原本是我叔公,因为娶了我亲姑姑,就成了我叔叔。
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姑姑唯一的儿子严静出生的那年,我姑姑和我树叔叔同他哥哥严定湘还住在一起,两兄弟一人一个大房间,共用堂屋和灶屋,日子并不宽裕。而我姑姑、叔叔那间房子就邻着我家。所以也可以说,我姑姑是带着不多的嫁妆住到了隔壁,就结束了她的姑娘生活,成为我叔叔的妻子的。我姑姑生严静就是在他们那间房子里,由请来的乡村接生婆接生的。记得我和我弟弟还有严波他们还趴在窗户边往里头偷看。严静出生在一九八六年,那年我五岁,我弟弟三岁,严波四岁。
很长一段时间,我同时叫严静的爸爸树叔叔,又叫我树叔叔的亲哥哥严定湘家为叔公。直到后来,经我爸爸多次提醒,我才改口和严静一起叫家叔公为家伯伯,他也都应着。我叫家伯的时候,他的老婆家叔娭毑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从未对家叔娭毑改口,她嫁到我们严家,就和我爷爷同辈。我见她发过两三次病,具体什么时候我忘记了。
记得有一年,家叔娭毑又发了病,正是夏天,浏阳河发着洪水。那些天我常常看到家叔娭毑站在已经涨到了牛叔公家地坪前的洪水边上,朝着南方的洪水大声喊着谁的名字。
银伯娭毑
前年过年时我还同我爸爸、我弟弟一起去看望过银伯娭毑。她家离我家大概有一里路,门前靠着一条公路,沿着公路往南边走一百米的样子就是我们那里的土地庙——庙虽然小,香火常年不断。那时她老人家已经九十七岁了,躺在自己床上。她听到我们来了,就扶着床坐了起来,笑眯眯看着我们。我记得以前过年时我们去看望她,她还会找出糖果拿给我们吃。
去年秋天,她就去世了。我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他说银伯娭毑去世了,他去帮了两天忙。
银伯娭毑还是没有活到一百岁。自我懂事开始,她好像就行动不那么方便了。在我小的时候我爷爷也常去她家走动。那时我走进她家大门,当时还能走动的银伯娭毑会从房间里慢慢走出来,招呼我们坐。我们坐下来,她的媳妇,也就是我的伯母会给我们泡茶喝。爷爷就坐下来和他们聊天,我和他家的两个孩子不怎么熟悉,往往坐在那里无事可做。我爷爷是一九二七年生人,如果活到现在是九十二岁。银伯娭毑活到今年有九十九岁,那就离一百岁不远了。一百岁的老人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器官日渐衰老,加上腿脚不便,晚年大半时间她是在床上度过的。但她是一位爱干净的老人,我每次见到她老人家,她银色的头发总是梳得很妥帖,衣服也干干净净。这一定是她自己的个性和年轻时候的教养,还有她有一位体贴好相处的媳妇的缘故。我记得银伯伯的名字是严昌其,他是昌字辈,和我付伯伯严昌富一个辈份,大约年长我四十岁的样子。我好像听人说我银伯伯是过继而来的儿子,他的老婆,我银伯母名字好像叫做严明秀,她也姓严。我现在没有去问我爸爸,但我推断严明秀伯母是我银伯娭毑的亲女儿,而不是儿媳妇,我上面的叫法应该是弄错的了。不论怎样,银伯母是个很好的人,我几乎没听说她跟谁有过什么矛盾。她很早就掉了两颗门牙,又总是见人就笑,她那空洞洞的牙缝就露出来了。
我爸爸和我说过,银伯娭毑去世前不久,我们生产队上那位吴奶奶也去世了。银伯娭毑和吴奶奶去世以后,我们那里现在就再也没有一位年老的女性了……当然,也不准确,因为银伯母也老了,银伯伯看上去都比我爷爷以前更老了。
银伯娭毑是民国初年的人,应该生于一九二零前后。
严海龙
我们一大群年纪相仿的孩子,一起从四五岁左右玩到各自都慢慢大了。这些常在一起玩的孩子有我和我弟弟严威,我邻居家叔娭毑的儿子严波和他的姐姐严小春,我姑姑的儿子严静,严静他秋伯伯的儿子严涛,我付伯伯的孙女严芬,我付伯伯的孙子、也是我发哥哥严明亮的儿子严浩文,可叔叔的两个女儿,二爷的女儿严小兰;还有涂正根、吴晴、吴刚,以及涂正根和吴晴几位年纪更小的弟弟;还有严松。
严松的爸爸就是严海龙,一位样子很勇猛,却在中年生病去世的男人。
严海龙好像是得了癌症去世的。他去世时我也没有在家,只是听说。那时他的父亲也不在了,他的儿子严松就继承了家业,后来做花木生意,还在外面跑车,自己买了一二十米长的重型卡车运货、运花木。严松在我们这帮孩子中几乎是最懂事的,在我看来他最像一个大人,而我和我弟弟倒还不怎么成熟,做事情也不大像个成年人那样让人觉得可以信赖。记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总是觉得我爸爸还有别的老人们都是无所不能的。
严松虽然做事情很好,继承了家业做了一家之主,却没有继承他爷爷和他爸爸的那门手艺:杀猪。
严松的爸爸严海龙是杀猪匠,严海龙的爸爸也是一位杀猪匠。至于严海龙的爷爷是不是同样是杀猪匠我不知道,因为严松的爷爷我见过,严海龙的爷爷我却没有见过。我猜这门手艺他家可能是祖传的。一个人能做好什么,确实也和他的体格、个性等等自然因素都有关系。杀猪匠这门手艺要求人胆子大,有力气,这是最基本的。一头成年的猪总有两百来斤,力气远比一个成年人要大,杀死后竖起来立在架子上也有一人来高。一个人如果胆小,比如怕血,不敢杀生,而他力气又小,像我这般,肯定就无法从事这个行当。
严海龙和他父亲都生得孔武有力,人高马大。严海龙的父亲看样子有一米八以上,而严海龙据说还有一位伯伯高达一米九,我没有亲眼见过,他在外面去了。作为杀猪匠的严海龙不独过年过节或遇到红白喜事,给邻里杀猪,他还要带着杀猪的行头,各种道具、刮毛的铁刮子、手梯、棕绳子等等,去外地给人家杀猪。说杀猪是门行当便是这样,杀猪匠可以通過杀猪的劳作获得收入,养活家里人,还总能让家里的饭桌上有肉吃。因为不管给谁家杀猪,不论是帮忙还是专门请去的,除了正式的工钱,主人家还总要在猪杀完后将那头杀掉的猪割几斤肉,再将一些猪血和猪的内脏等等,一并拿了赠给杀猪匠。这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习俗,也是对手艺人的尊重。但这样的手艺,包括杀猪匠这样的手艺人,随着现代工具和规模化与标准化生产迅速推广后,就像铁匠、剃头匠、补锅匠一般,都慢慢地少了,几乎要消失掉了。我记得严海龙叔叔去世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并且早已不杀猪了。
他家离我家有一百来米距离,中间隔了严波家和我牛叔公家。严海龙家西边曾有块水泥地,水泥地前放着杀猪用的大木桶、绳子,如果是在家里,他们一般就在那里杀猪。他们杀猪时,我们大人小孩总有人去围观,帮一点小忙。在杀猪用的水泥地旁边是他家的两株枣树。枣树很能结果,年年都结满枣子。在枣树的西边,紧挨着两株很大的柿子树,树冠都有一个房子那么大。那两株柿子树也很能结果,每年秋天都挂满了红透的柿子,一株是严松家的,另一株好像是统叔公家的,或者我记错了,全是严松家的也说不定。
严海龙的老婆是我们那里那些妇女中长相颇好的一位。这话实际上也只能悄悄说,因为我可叔叔的老婆,我另外一位术叔叔的老婆,都是蛮漂亮的人。在严海龙去世前,他老婆好像和他离过婚,改嫁过一次,后来她又回来了,重新和他过日子。每年我回家过年或者别的时候回去,也往往能够见到她。她似乎不大出门。我见她曾翻土整理过屋门口的地,开出一条很宽的路来,据说是打算再种菜,或者为了方便屋后面待售的高大的花木以后运出去。和我家一样,严海龙家也临着浏阳河。
以前他家还有条船。他们家河对岸也有亲戚,严海龙的两位妹妹就嫁到了河对岸。那条船载着他们在浏阳河中穿行,我们这些邻居要到对岸去,为了少走路、方便,也总是借用他家的木船。有时候我和弟弟还有我爷爷在河对岸我三位姑娭毑家走亲戚回来,就在西满仓那边的河岸边朝严松家这边大喊:
“哎——来人啊——开船过来啊……”
然后就会有人划着严松家的木船过来接我们。
后来我爷爷也做了一条木船,大小和严松家的差不多,我也学会了划船。
伯 伯
我爷爷(我妈妈的爸爸。我爸爸是上门女婿,他姓陈)以前说过,我曾有一个伯伯,是他的长子,我妈妈和我叔叔的哥哥。那位伯伯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我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好奇心,就没有刨根问底,不知道我那位没能成年的伯伯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他那么年轻又是怎样死掉的。
我妈妈是一九六零年生人,我那位伯伯应该是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他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什么原因,我都不知道。也许是一九五四年,因为那年浏阳河发了大洪水,将我爷爷的房子淹了一米多深,又或者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我爷爷是什么时候和我奶奶结婚的,回头我要去问问我姑姑,不知道她记得不记得。这些事情如果小孩子不问,大人们是不会主动去说的。我也没有听我爸爸妈妈说起过多少他们结婚时的事情。如果我姑姑不知道,那我只好去问牛叔公,牛叔公管事很多,是个百宝箱,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我爷爷是个普通的农民,现在他已经去世十九年了。他青年时候的事情我已经几乎无从知晓,不知道他从前做过什么。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去,我会多多央求我爷爷,讲一讲他过去经历的事,包括他的一儿两女三个孩子。
我那位死去的伯伯大概没有留下坟墓。在过年和清明时节我们去扫墓,我也只在我爷爷的父亲、我爷爷的爷爷奶奶、我爷爷和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坟前磕过头,从来没听说过伯伯埋在了哪里。
又或者,我也想过,这位伯伯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他原本就从未降生,从来也没有存在过。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有了那个想象,就认为我有那样一位伯伯,我妈妈还有一个哥哥。我伯伯的存在颇像一个传说。
在每个人有限的生命中不断看到别人出生和死亡,关于人的故事是说也说不完的。死是严肃的哲学命题,对死亡的恐惧悬在每一个人头顶,是终究都会来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死亡怀有深深的恐惧。这种关于死的启蒙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也许是在我见了我奶奶的死、参加了她的葬礼过后的几年,或者是我从电视上慢慢看来的。
当我知道包括我爷爷、我妈妈和我爸爸,我自己和我弟弟,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所有人都难逃一死的时候,我就幻想自己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死去,随之而来的就是恐惧。我想过死的时候会有多痛——可能比被刀割伤一个口子要痛上一万倍。我也无数次和自己说过:既然这事情如此公平又无法逃避,就把它忘掉吧。忘掉自己会死,要尽力在这世上好好活。
死亡的方式无奇不有,有的人出门死于车祸,有人死于谋杀,更多的人因衰老和疾病而死。我的另外一个爷爷——我爸爸的爸爸——陈春林,他活着时每天都在喝酒,常常醉倒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同村的人见到了醉倒在路边的他,就想办法通知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有时是我的两个叔叔,有时是我爸爸,儿子们会过去将他扶起来,搭过路的顺风车接回家。我爷爷死在某一年除夕夜和大年初一凌晨之间。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喝多了酒,后来便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叔叔去他房里叫他起床吃饭,迎接新年,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因此没有人知道我爷爷死亡的具体时间,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死是“喜丧”,他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他去世时已经八十二岁,无病无灾,就那么在醉酒的沉睡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既然死亡无法避免,我就以一首小诗结束这场关于我那些浏阳河岸故人们的回忆和对自我死亡的想象吧:
死后,我又回来了。
推开门,
跳进自己的身体,
参观他的地下室,
带走几件旧衣服。
——《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