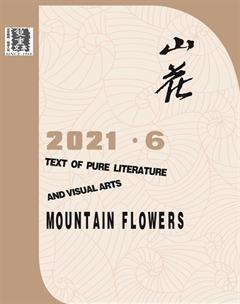靡草,靡草
唐丽妮
大清早,打开第一封电子邮件,看到陈建格的名字,小晴愣怔了半天。
每天,小晴的工作都是从处理邮件开始的。每天,未读的邮件就像整齐的士兵方队,处理一批,又冒出一批,源源不断。但小晴很从容,十几年了,业务上的那些事难不倒她。
陈建格。小晴内心深处一个晃荡。这个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或许他就是她的一个节气吧。她想。
小满快过去了,接下来就是芒种。近年,小晴着魔似的对二十四节气敏感起来。俊智不一样,他始终习惯新历,某年某月某日,像一个个小格子,今天与昨天很分明,今天与明天也很分明,似乎那里头没有丝毫瓜葛。俊智讲,节气跟你有关系吗?似乎真没关系。囿于小城之内,终日坐在亮堂堂的办公楼里,中央空调吹着,红枣枸杞姜茶喝着,不过,节气之类看似无用的事物仿佛更能牵动她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也许我曾经是一株草。小晴自嘲一笑。
俊智又出差了。小晴一个人走路上班。昨晚上,老厂大院里,玉兰一夜糜香。果然落了满地花瓣。她见路边白花菜绿得很浓,就摘了一把。晚饭打一个白花菜鸡蛋汤,黄的白的绿的水汪汪一碗,多好看。但小晴最贪恋的,还是喝汤过后,身体深处那股甘甜,清润,妥帖。
邮件是李燕发来的,说陈建格的资料她审过了,还说是急事,让她抓紧办。按一般程序,每一份资料李燕都需附一张审批表,请各级领导一一审核签字。但有些常规业务,再跑繁文缛节,就太古板啦。小晴和李燕就把一些常规业务归拢合办,一月一签。领导也觉得好。不破规矩,小小溢出,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小晴的责任会略有增加。但她不在意,也不深思。她喜欢简单,何况这是与人方便的事。陈建格的事就属于可删繁就简的范围。也就是一个简单的证明,证明他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家庭怎么样。小晴不明白的是,他为何要办这样的证明?
说实在的,小晴与陈建格没见过几次面。
第一次。很久了,1998年还是1999年?记不清。一帮差不多都是第一批双向选择自谋职业的大中专毕业生,逃离农村,落脚紫荆城。偏逢国企改革,一进厂,就面临被裁员的境遇。所幸,老厂挣扎几年,竟又活了。小晴俊智他们因年轻有知识而幸存,但一个个亦是面色发蓝,形销骨立。用俊智的话说就是,一群有知识的农民工。那几年,好几对纷纷结婚了。好像是过小年吧?也有点贺贺劫后余生的意思,有人提议聚一聚。夜市,大排档,烧烤,冰啤,雪碧。半轮弯弯的月亮神色模糊地挂在天上。十几个人乱哄哄拼几张小桌烤炉,挤挤挨挨坐了狭长一圈。小晴挨着俊智坐,那时她脸嫩,害羞,老低着头,不敢看人。她与俊智领证半年不到,但这是城里,又不是山里没见过世面的小媳妇,按理不应该。夜风闹哄哄的,一忽儿从前面吹,扇来烧烤摊的热烟熏得人眼发胀;一忽儿从旁边吹,把她的披肩长发胡扯乱抛。她捏着半杯雪碧,浅浅笑,浅浅酌。坐她身边的李燕要么吭吭吭地大声咳嗽,要么隔了桌子与对面几个男生猜码,大甩胳膊,吆五喝六。不知玩了多久,好多人醉了。俊智也有了几份醉意,与旁边的人大声争论着什么。小晴就有些孤单,有些落寞,有些恍惚。眼前灯光昏黄,人影绰绰,仿佛都已飘离地面,而泛着灰光的白烟则像河水一样向夜空流去。弯月悄然消失,夜色苍茫,不晓得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忽然有人大喊小晴的名字。
小晴小晴,那时候,我们都想追你!
几张桌子的那一头,突然直挺挺地站起来一个人,笑吟吟地粗着嗓子说。这人说完,又笑吟吟地坐下,直挺挺地盯着桌子上的烤串微笑,一副在梦中喝足了美酒的样子。
小晴记得,当时十几个人刹时静了,灯光似乎暗了一下,烟仿佛凝滞在半空。小晴心头顿时一阵惶恐,掉头就去寻找俊智的表情。她看到俊智一愣,她的心不由得跟着一沉。紧接着,周围的人呼啦一下,又闹开了。李燕举着一次性塑料酒杯吼得特别卖力。俊智也随即复又投入被中断的高谈阔论中,他在那方面一向较为愚钝。小晴再看桌子那头,几个晃悠悠的黑脑袋挤一堆猜码,喊三喊五,好不欢腾。眼前一切恢复如前,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那人是谁呢?她不认识他呀!他说的“我们”又都是谁呢?他拿自己开涮吗?小晴又好奇又忐忑。事实上,小晴进老厂没多久就被俊智拿下了——她还没考虑清楚,他就已让所有人相信他们好上了。现在想来,俊智其实还是很有些手段的。这样,小晴就没什么机会认识别的人了。一起宵夜的十几个人,有一半小晴不认识。
陈建格。小晴记住了这个名字。
当时,小晴心里有些恨恨的,她担心俊智会生气,误会她在外面招蜂作妖。她也不全是恨,她还有些欢喜。她把这份欢喜藏得很深。她甚至连恨恨的表情也没露出来。她装作没听见。陈建格那晚不再提她,也不再跟她说话。后来他们一直也没碰面。老厂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办公楼有三四栋,厂房十几栋,员工两三千,班次也不尽相同。虽说大多数职工都住在大院里头,可大院住着一万多人呢,小镇子似的。医院,学校,幼儿園,银行,超市,球馆,市场里就更不用说了,鱼肉米面,干货生蔬,活宰鸡鸭,粉店快餐豆浆油条,补衣修鞋的,修锅的,卖烟丝的,还有五金店杂货店茶麸养发馆,搓背的,泡脚的……哎,要什么有什么。实在没有的,就网购呗。总之呢,老厂建厂九十多年,一直盘踞于紫荆城的一隅,城不城,村不村的,有点闭塞,有点独特。人家说,你们跟街边的人不一样。意思是说老厂人不太热衷于交际,不灵活,像木头,像机械,像钉在墙上的一条条规章制度。小晴想,这里的人呢,的确不爱胡搅,只把如火的煎熬放在心里。他们既热烈,又疏淡;既亲近,又保有一定的距离;既抱成一团,又各有各的小心思。若非业务往来,若非有意拜访,两个人几年不打照面是很正常的。总之,就是俊智,也绝口不提那晚之事。
可能真是梦。小晴想。
她甚至怀疑陈建格此人是否存在。她偶尔又会想起他。比如说,在俊智面前受了委屈,一腔幽怨时,那晚的情景就会浮现:陈建格高高瘦瘦,站在苍穹下,一双大眼睛迸出灼亮的光,毫无顾忌地盯着她,就好像两支咬准了猎物的箭。而他浓密的三七分头发竖起来一小撮,在风中摇曳,仿佛春天里一棵蓬勃的靡草。他结婚了吗?他新婚的妻子有没有跟他闹?小晴心上偶尔会掠过几丝担忧。她记得那时陈建格的身边坐着一个女孩,低眉顺眼。不过,小晴想起陈建格的时候很少很少,只是墙上挂钟秒针的偶然一嘀,只是那绵密漫长旅程中某一个小小的点。其余的光阴,小晴都忙着柴米油盐去了。毕竟,每个人都得过着各自甩不掉的浓稠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小晴怀孕,生子,操心尿片,奶粉,遛娃,预防针,幼儿园,兴趣班,沉溺于孩子的一颦一笑一粥一饭,热衷于与别的妈妈交流育儿心得。就连俊智她也疏于关注了。渐渐地,陈建格这个名字就彻底消失,被掩埋到生活的最底层了。
唉——小晴长长一声叹息,忽然发现,陈建格并没来办材料。李燕在一楼,她在二楼,两步台阶的事。又说是急事,这算什么嘛?她本要在微信里问问李燕,仿佛又过于郑重,就又作罢。他或许回去补充资料了吧。小晴想。她感觉肩胛骨被中央空调吹得凉嗖嗖的,寒气小蛇一样往骨头里钻,就赶紧披上披肩,偎到走廊窗前的阳光中暖一暖。厚厚的隔热玻璃虑过的阳光,仍是温热的,可知此时的太阳有多泼辣。窗外一排假槟榔,它们最不怕晒,越晒就越旺盛,灰白细长的树杆又高又直,叶子又大又硬,无畏无惧地向热辣辣的高处奔去。这叶子只在树顶上撑出一簇,虽形如伞,叶子亦绿得深,却遥遥于半空,对栖身在树下的靡草来说,并无遮盖作用。青草们在夏阳下耷拉着脑袋。在整个春天,它们都致力于贮存水份,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而此时芒种未到,它们身体的水份就已被阳光抽得差不多了。
干枯,衰老,是不由分说的。小晴叹息,还没进入最热的夏伏呢。她想起了上班路上摘的那把不再娇嫩的野菜——中年的白花菜,老绿了,卷缩,枯瘦,吸不进多少水份了。一般人都不爱吃这个,说嚼起来味道又硬又柴。
小晴第二次碰见陈建格是在路上。她记得,那时节,更年轻的八零后晨光一样涌进了老厂,而他们七零后老生则渐见凋零,有人离开了老厂,有人从这个岗调整到那个岗,有人被封在固定的位置。俊智盯了几年的职位被一位刚毕业的八零后黄毛丫头越位而上,他心里忿忿的,回到家就摔摔打打借机发泄。她还记得,那是一个有阳光的周日上午,俊智又跟她闹了。为什么闹?记不太清了。三十出头的小夫妻,头发丝一点事也能闹一场。总之,闹得小晴心里乱,把孩子送去画画班后,就乱逛。走过九曲桥,鱼塘泛起阵阵鱼腥气;转到菜市,菜市里死去了的鸡鸭鱼狗等各式禽类畜类混合的腥臭气味,比鱼塘更甚。小晴赌气不给俊智买肉,只给孩子买一条塘角鱼。清蒸塘角鱼,放几片金钱草,很香,助消化的,孩子爱吃。只要是孩子喜欢的,小晴都乐意做。宠!宠!宠!你就知道宠!俊智恼怒地骂她。对了,小晴忽然想起来,那天早上就是因为小晴答应孩子给他买遥控汽车,俊智就大发脾气,骂她把孩子宠坏了。可她乐意,她宠,她开心她满足。就宠了,怎么的!小晴恨恨地想,但没有讲出来。腔子里,一股说不出的惆怅。在菜市口,一个阿婆挑来满满两篮刚摘下的南瓜花,黄灿灿的。小晴就喜欢这花啊草啊叶啊什么的。拎着一条小小的鱼,捧着一大把南瓜花走在阳光里,小晴的心情仿佛好了许多,几乎忘记了俊智拉长了的胖脸。她脚步轻快了,闲闲悠悠,把那水灵灵的花举在阳光里美美地瞅着。
陈建格就是在此时突然出现的。
他站在她的面前,低头望她,眼里满含笑意。
嗨,我们又见面了。他轻轻地说。
小晴记得,她当时愣了愣,好像还说了一句,是的呢。话出口,她又感觉好像口气过于亲热。事实上他们连真正的认识都还算不上呢。她还记得,她仰起头冲他笑了一笑。他长得很高,可能有一米八,也可能是一米七八,而小晴只是一米五五的小个子。她看到他的脸上铺满亮堂堂的阳光,浓密的黑头发依然是三七分,整齐,服帖,有那么几缕特别长一些,微风拂过,就在额前微微飞动。他的眼睛黑亮,有光,有笑意,满含着宠溺。宠溺。这个词让小晴受了惊吓。怎么可能?她在俊智的眼里都从未见过。俊智看她的眼神有时也会放光,之前是赞美,喜欢,爱慕,渴求……近来她却常常迎来他的怒目之光。她从未得到过俊智的宠溺。这突然的发现,让人受伤了。宠溺。小晴感觉身子发软。她想那可能是她的想象,因为她缺乏,所以产生了幻觉。她慢慢地抬头想再看看那双眼睛,他却已从她身边走过,挺拔的背影很快转入熙熙攘攘的菜市,不见了。这人怎么这么怪?小晴又恍惚了,刚才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然而,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就挺好。小晴想。
但她又后悔刚才没有问他在哪个部门。老厂惯例,大学毕业生在车间实习一年,即可调到职能部门。中专毕业生则要看情况,有些抽调上部门了,有些仍留在车间当工人。她曾经猜想过他的职务,销售员,采购员,质检员,工人。因为这些人员是小晴较为陌生的,大多数她都不认识,而其他部门的同事她基本都过过眼了。
也许不知道更好。小晴想。
每个人都应该保留一点小小的秘密。她接着想。
想到这,小晴心里微微一动,仿佛凉凉的风掠过,心似乎平静了,舒缓了,妥帖了,又好像变宽了,变通透了。她在阳光里晃了晃手中的南瓜花,微微一笑,沉静地转身,返回菜市,稱了一大块五花肉。她想好了,今晚就做一顿香香的回锅肉,放点冰糖,放点葱姜蒜爆香,再放香叶八角桂皮翻炒,再依次加入料酒老抽生抽,然后用小火慢慢炖,直至汁液浓稠,肉质糜烂入口即化。这是俊智的最爱。平常她不太做。她觉得俊智越来越胖,就是吃肉太多的缘故。为这个,俊智常常不痛快,认为她在敷衍他。
白花花的时光河水一样流淌,到了三个月后的那个晚上。
小晴记得,快到霜降了,那晚月亮不是很圆,但很亮,银色的光,有些晃人眼。孩子半夜突然捂着肚子喊疼,满床滚。俊智出差未回,小晴又不会开车,只好拨出租车公司的电话。车子来得竟快,几分钟就到了。这很少有的,老厂偏僻,出租车若不是刚好送客进来,一般不肯费油跑这一趟。车子麻利地停在小晴的脚边,驾驶室里钻出瘦高的司机,打开后座车门,接过了小晴背上的孩子。小晴愣愣地看着,树影幽暗,看不清五官,但那身材,那轮廓,还有额前那撮在风中拂动的头发,是她眼熟的。
不认识了?司机说。
陈建格!真是你?!你怎么……
上中班。下了班出来找两块酒钱。陈建格回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问孩子哪里不舒服。
肚子疼,估计又偷吃辣条了。小晴说这孩子经常这样,又要吃,又要喊疼,可常常医生一摸肚子,臭小子又讲不疼了,叫人又恼又心疼。可今晚他好像疼得特别厉害!小晴忧心得很。孩子在她怀里哼哼唧唧的。
呵,孩子哪有不贪嘴的?再说了,男孩子连辣条都不敢吃,能叫男孩子吗?能长成男子汉吗?是吧?臭小子?阿叔告诉你啊,吃辣条之后,一定要喝一大杯暖暖的开水,保证肚子不疼。
嗯。孩子乖乖地答应了。
还有,如果你能吃一包,你就吃半包;如果你能吃两包,你就吃一包,剩下的给你阿妈。
嗯。臭小子竟又乖乖地答应了。不可思议。小晴与俊智平常怎么讲他都不听的。但小晴又觉得这人鼓励孩子吃垃圾食品,总归是不好的。
车上有温开水,给他喝一杯。陈建格对小晴说。
说来也奇怪,孩子喝了温开水后,渐渐地不哼唧了,到了医院门口,他竟说好了,不疼了,不看医生,不打针了,要回家了。
于是,就又回转,好像三人是出来遛弯的。
还没回到半路,闹了半宿的孩子就困得咻咻睡去了。
车子一下安静下来,气氛就有点怪。车里的空间仿佛变小了,有点挤,让人都不敢自由呼吸了。小晴只好转脸望窗外。月亮已偏西,仍然很亮,远天有寥寥几颗星。陈建格也不再说话,默默开车。此时,似乎人的形色已消失,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占领了这狭小时空。小晴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她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又感觉太俗。
他怎么也不说话呢?不是应该男的主动打破这种尴尬的吗?他不是很会说话的吗?小晴心里竟有些恨了。旋即又想心中坦荡,不该尴尬。仿佛为了掩饰那复杂的心思,她轻轻抚着孩子的背,细声说,你对孩子,竟很有一套。
前面哧一声轻笑,道,食色,性也。你越不让他吃,他越要吃。人性本是如此。宜疏,不宜堵。
小晴一时不晓得如何答话了。
你,不认得我。陈建格突然降低声调说。小晴有点懵,她搞不懂他说的“认得”指哪一层的认得。
那年,大洪水,芒果树,铲车。他的声更低了,一截一截的。
是你!小晴几乎要惊叫了。
恍惚间,小晴仿佛又看到洪水汤汤,泡沫片,塑料袋,枯枝,落叶……她仿佛又挂在了多年前围墙边的芒果树枝上,半截腿浸于快两米深的浊水中。惊慌的小腿,踢不走水中的白沫,灰黑的油污漂在水上像蛇一样……那时她刚毕业,报到第三天。她的宿舍却已被洪水淹去半米,舍友纷纷找住在楼房的相熟同事避灾去了。她刚来,不认识人,听说办公楼可以避难,又听说围墙边有一架梯子,顺着梯子爬到货车顶上,就可以抵达办公室大楼二楼平台。于是,她独自涉水,爬上芒果树,翻上墙头,用脚去撩木梯,没踩住,木梯晃悠一下向水中滑去。她慌忙抓紧树枝,几番努力,没能回到树上,也没能攀上墙头。她能望见办公楼高耸的后墙,却没人看见她,也没人听见她的呼救。她绝望地想她大概会死的了。忽闻有轰轰之声,暮色中,一辆桔红色的铲车摇摇摆摆开过来……她软软地跌落于巨大坚实的大铲子之中,仿佛落入一张温暖的大鸟嘴巴。大鸟嘴巴衔着她,轻轻把她送到办公楼前的高台上。铲车随即又摇摇摆摆开走了。暮色朦胧,看不清司机的长相,她只看到车窗里半边瘦削的侧影一晃而过,长度刚好的额发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一条长长的手臂伸出车窗外,朝她晃了晃。洪水过后,她曾经问过很多人。都说没有这样的铲车司机,仿佛她说的是一个梦。
孩子睡得太香,一头微汗。小晴轻轻抹了抹孩子被洇湿了的额发。她看看前面,低头咬咬唇,轻声说:
做好事不留名。我还真以为是神仙搭救呢。
哈,那时我根本不会开车,没证。趁师傅去休息,偷偷过一把瘾。没人知道这事。我不认,谁敢认这英雄?
那你干嘛不认?
说话间,车子就回到了大院。
洪水一退,我就去南宁学习了。半年。停车后,他回头,深深地望她一眼。
原来如此。小晴愣在车里,怔忡半天。直到陈建格接过孩子,直到他把她請下车,直到他把孩子抱回家中,直到他问,孩子睡哪间?她才惊醒,耽误他出车接单了。
那劳烦请杯茶吧。陈建格微微一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刚下中班就忙活了这大半夜,能不累么?他坐的是俊智常坐的座位——正面对着电视机——家长的座位。她心里,忽地一阵甜,一阵惆怅,又不知为何甜,为何惆怅。她去沏茶。看见玻璃杯里蜷缩的茶叶缓缓舒展,复活一般恢复了嫩芽的模样,她就有些恍惚。她心里一些说不清的东西绕来绕去绕成一团,仿佛只有为他做点什么,才能化解。冰箱里,有两盒周日包好冻好的香菇鸡肉饺子——本是为这一周准备的早餐。她想他应该还没来得及吃晚饭的。就是吃了,再吃碗夜宵也未尝不可。她就没问他,直接拧开煤气灶,把两盒饺子全倒进锅里煮了。端上桌,满满一盘。陈建格看一眼饺子,又深深地望她一眼,也不说话,坐在餐桌旁,就呼哧呼哧吃了起来。小晴饮茶相陪。在心里,她感激他的不问,不谢,不客气。不知怎么的,氤氲的茶香熏上来,她竟有点想流泪。接着她看到桌上有一瓶酒,她就有点慌。他埋头咽下半盆饺子后,果然一把抓起酒瓶就往口里灌。喝酒这事,她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怎么都不妥了。他一向爱喝几口,她能猜得到。可这夜深深的,悄静静的,是喝酒的时辰么?再说了,喝了酒,等会怎么开出租车?不出车,岂不白白扔了几百块租金管理费?不出车,拿不出钱来给家里人,他该怎么说?她心里千回百转,想不出个道理来。
小晴小晴,你就是一只——青芒。
他有些醉了,两只眼睛亮得有些吓人。她的心就突突地弹。月光从窗外斜照进来,白底灰格,床单似的,铺在地上。她不由得张了张胳膊——一片月光,她竟想拿件什么东西去遮盖一下。
小晴——他又大灌一口酒,眼里流转出水光,仿佛是他把酒灌到眼睛里了。
小晴,我——
他突然一把抓住她的手。滚烫的手掌宽大,强劲,硬硬的茧紧贴着她的手背。俊智的手不这样,太软,甚至比小晴的手还要软,像两团棉花。这突如其来的粗砺的包裹,使小晴一阵情迷意乱。她感觉到他渐渐使用了力气,由轻到重,感受到他手心里的脉息火苗似的东扑西扑。她想起少女时代常做的白日梦,突然被骑马的男子一把掳到马背上,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风一样飞驰。所期盼的,不就是这样的感觉吗?紧张,惧怕,惊喜,自由。哦,像风那样自在,不着形迹,不受拘束,无所畏惧,过山过水,上天入地,谁管得了她?谁管得了她?!她就像风迷失在广漠的草原上——她已然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然而,她还是恍若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阿妈……
阿妈……
是孩子在房里叫她。梦呓中的含糊,其实并不微弱。她听清楚了,也就瞬间明白,自己陷得深了。她推他。他却箍得更紧了。越推就越箍紧。他大概以为她在扭捏,在害羞。他眼里闪烁一种陌生的光,并不是之前那种宠溺,而更像是一种油腻的侵犯。她奋力挣脱。他仍不肯罢休。她就怒了,啪一声脆响,她的巴掌甩了过去。
打过之后,她脑袋里瞬间一阵空,屋子里陷入寂静。
他慢慢放开了她。他们相对呆立。她感觉手掌在发麻,发酸,发痛。她忽然发现,原来她要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一种幻梦的感觉。她突然恨起自己来。她再一次举起了手掌,又是一声脆响——她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不知道。
怎么离开的?她也不知道。
她甚至不知道他离开时的表情。她一直捂着脸,泪水滴落,深深陷入自责,羞愧,悔恨。从此,他们彼此陌路,不再相见。
直到这一天,该死的芒种到来之前的这一天。
陈建格来找小晴,已是第二天即将下班时分。当他走进来时,下班的钟声刚好咣啷咣啷被敲响。同事们拎起包一个接一个鱼一样游出了办公室。他们都是九零后小同事,早早就计划好了下班约火锅,或是约奶茶,或是电影,KTV。他们认为,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潇洒而随性,令人羡慕。那时,小晴刚刚写完一个邮件,准备发送出去。一抬头,她就看到了他。
他或许在外面已经站了一段时间了,或许昨天就站了老半天。小晴不晓得自己为何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脸上忽然一阵热,赶紧骂一句自己,啐!自作多情!而心底又涌上一团淡淡的水雾。离上一次见面,又过去了十三四个年头了。想起那把在阳光里闪闪发光的南瓜花,那脸上铺满阳光的高个子青年男子,仿佛已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此时,小晴已下班,没回家,独自缓缓拐向厂后一条偏僻小道。斜阳将歇,寂静无人,只有淡淡的影子跟在她的身后。路过一棵高大的玉兰树,小晴几乎走不动了——刚才那一幕,太伤感。
他是陈建格吗?不是。他不像他。不像陈建格。
腊黄,消瘦,眼眶深陷,头发不再浓密,剪平了,腰背不再挺拔,佝偻着,仿佛连个头都变矮了,变小了。他望着她,轻声说,嗨。有点颤。眼里仍然含笑,仍然有光。可那是什么光啊?怯惧,躲闪,一点点向眼睛深处退缩。他的脚步也在向后退去。当她抬头看他,他就踉跄后退,一步,两步,三步。他好像故意要避开她,不敢靠近她,好像小晴的眼睛里发出的不是目光,而是浪涛,这浪涛在推他后退似的。不,也不是。而是他好像害怕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会沾染到小晴,就好像他自己是一瓶正在破碎的墨水,他害怕那飞溅的星星点点会溅到小晴的乔治白的衬衫上,所以他要离她远远的,远远的。他局促,不安,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卡座隔板,避开她的桌子,避开她的手指,也避开她写满疑问却又不敢暴露悲怜的眼神。他神情复杂,小心翼翼地接过材料,退一步,再退一步。然后,转身,离去了。
离异,一孩,年收入两万元。他的材料上这样写着。
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今后怎么打算?小晴不敢问。她给李燕打电话。东拉西扯,不晓得讲了什么,只是在最后问:
他……的腿,怎么啦?
噢,陈建格啊!十几年啦。酒驾,大晚上的,撞到电线杆……
小晴依稀记得,他喝酒那晚不久,李燕曾约她,说去看看陈建格。当时她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立即推托了。
是……快霜降……月亮很亮的晚上吗?小晴努力控制着抖动的嘴唇。
好像是!我们还纳闷,月亮那么亮,那么粗的电线杆,怎么就看不清?后来听说是喝蒙了。李燕说。她忽然又惊奇地问,咦,你原来也知道啊?
小晴没回答。她软软地靠着玉兰树,闭上眼睛,泪水直流。
在她的脚下,落花掉了一地,鲜见有完整一朵的,几乎全是些細长的白花瓣。她知道,从开花的第一夜开始,这些玉兰就开始了凋零,一瓣,两瓣……缓缓撕裂,松脱,坠落,直到一瓣不剩,直到下一个花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