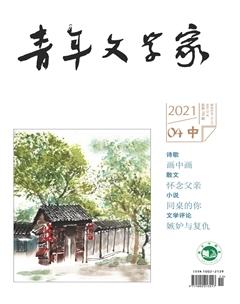孔夫子是个漩涡派
刘冠成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美国著名诗人与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英美意象派和新诗运动的领导者,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至深。漩涡主义是埃兹拉·庞德所创立的未来主义艺术流派。漩涡主义将“漩涡”作为极力之点,融合各种因素进行文学创作,这种创作原则深刻地影响了庞德的诗歌创作,以及对于世界的理解。本文以漩涡主义诗学为基础,分析庞德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对于创新的推崇,以及将各种艺术手段综合起来进行文学创作,这与孔子的诗教观也是一致的。
上世纪初,东方与西方都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现代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摆在了每个艺术家的面前,处于这场漩涡之中的庞德也未能置身事外。在这个阶段,欧美文坛所流行的仍然是上个世纪无病呻吟的后维多利亚诗风,青年时期的庞德对这种诗风嗤之以鼻,他想要效仿自己的偶像但丁以及导师叶芝,成为真正的大师级别的艺术家。然而,上个世纪初的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商业化程度极高,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喧嚣的状态,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正如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所经历的“美国梦”一样最终走向幻灭,或者用马克·吐温的那部作品的名称来表达更合适,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只能是——“镀金时代”。庞德和他同时期的年轻人一样,对这个时代充满了困惑与不安,他与曾被他提携的后辈海明威一样,都属于那个时代的“迷惘的一代”。如何做?大部分青年选择了拥抱过去,去寻找欧洲文学传统。就如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流放者的归来》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三十岁之前,大多数人在地理上所遵循的生活模式可以用两个城市和一个州的名字来扼要地表达:纽约、巴黎和康涅狄格州。他們离开格林威治村之后,居住在蒙帕纳斯(或其在诺曼底和里维埃拉的郊区),他们中有些人将年复一年地留在那里,看来是一种永久的流放。”庞德也不能免俗,去国经年,流连于意大利、巴黎、伦敦以及格林威治村,甘愿自我流放。但庞德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和领导能力,以及显而易见的野心,迅速成为了那批“迷惘的一代”的领军人物。“在现代派文学的高峰时期,庞德扮演了示范作家、评论家、编辑、青年作家的联络人和宣传家的角色。庞德为英美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起摇旗呐喊,并在短期内将美国和英国的作家联结在一起,故被称为‘伦敦和格林威治的桥梁。所以说,就庞德时代而言,即英美现代派文学的鼎盛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50年代,庞德是执其牛耳之人”。
在欧洲的庞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先辈们的文学传统,同时与同时代的文学青年们共同策划着各种文学活动,希望领导一场“文学革命”,给象征着旧时代的维多利亚诗风以最后一击。1908年,在他写给威廉斯的信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按照诗人所见的事物来写;语言美;禁止说教;语言简洁。”这已经有了“意象派”诗风的雏形。庞德在1912年的《回击》(Ripostes)一文中第一次使用“意象派”(imagism)一词,并对T·E·休姆的五首诗进行注释时使用了“意象派诗人”(imagiste)的称谓。在1913年,庞德发表了那首著名的《在地铁站》,这首诗歌迅速成为了意象派的代表作品,引领了英美新诗运动。
无论是“意象派”的宣言还是庞德自己的创作,都不难看出,庞德所坚持的诗学原则是用诗歌中的“意象”来明确表现这个世界,对于诗歌语言来说就是“用词精确”。这极大地影响了庞德早期的诗歌创作。但庞德不满足于“意象”静止的状态,他希望“意象”能从瞬间变成永恒的力。在这时,机缘巧合之下,庞德与原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馆馆长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遗孀会面,从而得到了费诺罗萨先前研究日本汉诗、能剧的手稿,以及一篇题为《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the Medium for Poetry)的演讲稿。这篇文章对于庞德的启发非常大,其中谈论了汉语和英语在表情达意上的不同,尤其强调了汉语在诗歌创作上的优势,叶维廉在《庞德与潇湘八景》中评论到:“《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一文有关文字结构的讨论与分析,尤其是会意字的分析,加深了他利用两个象形元素的并置,放射出来多重互玩意味的蒙太奇(montage)效果,成为庞德后来在他始终高度发挥并大力推展,大大影响了后来美国诗人的重要美学题旨与策略。”
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一文中,费诺罗萨(或是庞德)提出:“但是汉字的表记却远非任意的符号。它的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这思维图画既由符号唤起,又由词语唤起,但生动具体得多。每个字中都有腿,它们都是活的。这一组字有连续的电影的性质。绘画或照片虽具体但不真实,因为失去了自然的连贯这要素。”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留下来的手稿中的指示,重新发现了汉字有别于拉丁字母别样的意蕴,同时也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奥秘。这使他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庞德和一些意象派诗人关系不睦,导致他离开意象派,创立了更为激进的“漩涡派”。
1914年,庞德与温德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克里斯托弗·内文森(Christopher Nevinson)、爱德华·沃兹沃思(Edward Wadsworth)等人合办了漩涡主义的核心刊物《轰炸》(Blast),在创刊号中,庞德发表了题为《漩涡》(Vortex)的文章,成为了漩涡主义的宣言书。在文中庞德提到“漩涡是极力之点,它代表着机械上的最大功率”,“漩涡主义者只使用其艺术的基本媒介。诗歌的基本色素是意象。漩涡主义者决不允许任何概念或情感的基本表达沦为模拟”等等。庞德此举是想要打破意象所保持的平衡和静止的状态,使其变成所有力的集合点的“漩涡”,成为意象的集聚,多种关系的交叉集合。虽然“漩涡派”作为文学团体只是短暂存在了一段时间便解散了,而且庞德本人也没有写出漩涡主义的代表作,但是“漩涡”这个整体意象却刻在了庞德整体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诗章》中,到处都有“漩涡”的影子。而这不仅有着深刻的西方文化传统影响,还与庞德所受的儒家思想分不开。
庞德在评论漩涡主义运动时曾经说道:“孔夫子是个漩涡派。这样的人有福了,能从自己的所处开始,并能有所成就。”这句话不仅是指孔子在当时时代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当然这是庞德所认为的),而且是因为庞德所想象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满足了他对于“漩涡主义”的要求。儒家思想与漩涡主义诗学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日日新”
庞德在接触儒家思想之后,将《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day by day make it new)作为自己的座右銘,在《诗章》中,经常引用此句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且还直接将汉字“求新”放进《诗章》之中。这也就说明了庞德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不论是发起意象派或者是漩涡主义运动,还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追求,甚至到后来痴迷于纳西族文化,都证明了庞德一生都在追求“新”。这与庞德发起漩涡主义运动的初衷也是密不可分的。
漩涡主义强调在艺术中的运动,是一种表现的动力,这与当时兴起的未来主义运动密不可分。漩涡主义对于“机械”和“动力”的追求与未来主义如出一辙,并且两者都是在追求“创新”,不过截然不同的是漩涡主义和未来主义对于传统的态度上。未来主义者们大多数都在宣扬摒弃故有的一切传统,通过对于科技文明的歌颂,建立新时代自己的文化。而漩涡主义者们却十分重视古代文明,庞德虽然是为了求新,表面上看他却是一个文化复古主义者,而这种复古,却是一种“创古”,复古便是从文化源头上求新。但这种新到底与之前的古存在多大关系,那就得另当别论了。比如庞德所歌颂的东方漩涡派的孔夫子,他认为孔夫子这样的人有福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真正的孔子却“累累若丧家之狗”。庞德思想成分极其复杂,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只要符合自己对于世界的想象便拿来为我所用,但很多时候只顾得表面相似,却疏忽了本质的不同,最后只落得貌合神离的结果。
然而,对于创新的强调,又使得庞德对以孔夫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极为推崇。在《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句话不仅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强调了思想上求新的重要性。时间的顺序更加印证了动态过程的重要性,这也与漩涡主义所追求的动力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一种呈螺旋型上升的过程。庞德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价值,庞德曾说“当权力的漩涡与文化的漩涡巧合时,你们就有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艺术家们应当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集合起来,共同创建一种动力强劲、永葆活力的艺术,以此去改造这个社会。这与孔子“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等诗教观也是一致的。
二、各种艺术的融合
在漩涡主义的宣言书《漩涡》之中,庞德说:“一幅画等于一百首诗,一支曲子等于一百幅画,能量最高度集中的陈述,这种陈述尚未在表达中竭尽自我,然而却是最富于表达潜能力”,“每一个概念,每一种情感,均以某种基本的形式把自己呈现给清晰的意识。它从属于这种形式的艺术。若是声音,则属音乐;若是成形的字词,则属文学;意象,则属诗歌;形式,则属设计;平面的色彩,则属绘画;三维的形式及设计,则属雕塑,随舞蹈或音乐或诗的节奏而动”。庞德将自己所信奉的漩涡主义看作是各种艺术手段的聚合体,而漩涡主义这个团体也是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们的集合,绘画、雕塑、诗歌等各种形式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漩涡主义。
与其他漩涡主义艺术家们不同的是,庞德则更多的是从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来凸显漩涡主义。比如上面的那段话,这就体现了庞德的“主调”(primary pigment)原则:各种艺术自有其独特属性与特性,即“主调”,每种艺术的佳作就是将该艺术特性以最集中或强烈的方式展现出来。故以“主调”创作完成的作品,即“抵得上一百首诗的画作,抵得上一百幅画的音乐,是最高赋能的观点陈述,这种观点陈述虽尚未穷尽其表达方式,但却是最有表达能力的”。而对于漩涡主义者而言,他“只依赖他自己艺术的主调,别无它物”。对于漩涡主义来说,便是以文学为基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参与其中。由此可见,漩涡主义就是庞德所说的“关联美学”。这与孔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发出“尽善尽美”的感慨,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也是一致的。孔夫子论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他的审美标准就是“和”,“和”就是性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和”这个汉字在《诗章》中也多次出现,对于庞德的漩涡主义而言,“和”便是漩涡的中心点,是极力之点,能够将各种艺术手段吸纳其中,产生最大的能量,以此去形成完美的作品,从而改造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