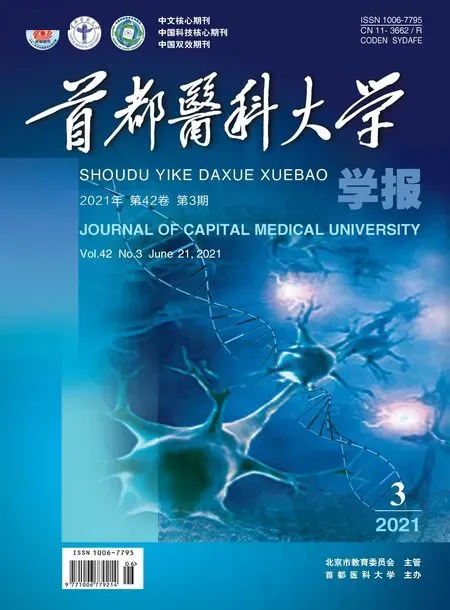神经系统损伤的ANCA相关性血管炎患者14例临床特点分析
赵莹莹 孙金梅 张拥波 许春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 北京 100050)
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AAV)是一种少见的以小血管受累为主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包括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tis, MPA),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GPA)[原称为韦格纳肉芽肿(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G)]和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EGPA)(原称为Churg-Strauss 综合征)3种类型[1-2]。AAV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在欧洲其患病率为每年每百万人20~25例。AAV可影响全身各个部位,最常见的是上呼吸道、肺脏、肾脏、眼以及周围神经[3],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并不多见(<15%)[4]。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复杂多变,影响了AAV患者的早期诊断,延误治疗,造成患者的不良预后、疾病复发甚至是死亡[4]。本研究总结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近年来AAV合并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和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的14例AAV患者,通过对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资料的分析,提高临床医生对AAV的认知,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1 临床资料
14例出现神经系统临床表现的确诊AAV患者,诊断均符合1990年美国风湿病学会诊断标准[5]及2012年Chapel Hill血管炎共识会议分类标准[6]。
14例患者中男性7例(50%),女性7例(50%),男女比例1 ∶1。就诊年龄53~74岁,平均年龄(64.9±7.31)岁。病程5个月到8年不等,大部分患者病程2~5年。4例患者既往体健; 4例既往患有高血压病,其中1例同时患有2型糖尿病, 1例同时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心房纤颤,1例同时患有高尿酸血症,1例同时患有高脂血症和精神分裂症; 1例既往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十二指肠溃疡;1例既往患有骨质疏松;1例既往患有慢性胰腺炎;1例既往患有肺纤维化;1例既往患有高脂血症和糖耐量异常;1例既往患有肺结核和腰椎间盘突出。所有患者均无相关疾病家族史。2例患者同时合并继发性干燥综合征,其中1例同时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
14例患者中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患者8例(57.1%)(病例1~8);出现周围神经系统受累10例(71.4%)(病例5~14);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同时受累4例(28.6%)(病例5~8)。14例患者中MPA 12例(85.7%),GPA 2例(14.3%)。12例MPA患者中累及中枢神经系统6例(50.0%),累及周围神经系统9例(75.0%),同时累及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3例(25.0%),除神经系统以外不同程度累及肺脏和/或肾脏。2例GPA患者均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其中1例同时累及周围神经系统。2例GPA患者均存在广泛全身系统受累,包括肺脏、肾脏、五官(病例4累及耳,病例7累及眼)和关节肌肉。除1例GPA患者为胞质型-ANCA(cytoplasmic pattern-ANCA, c-ANCA)阳性(7.1%),其余13例患者均为核周型-ANCA(perinuclear pattern-ANCA, p-ANCA)阳性(92.9%)。髓过氧化物酶-IgG(myeloperoxidase, MPO-IgG)阳性12例(85.7%), 蛋白酶3-IgG(proteinase 3, PR3-IgG)阳性2例(14.3%),其中MPO-IgG、PR3-IgG均阴性1例,MPO-IgG、PR3-IgG均阳性1例。所有患者均完善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抗可溶性抗原抗体(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antibodies, ENA)、类风湿因子、抗链“O”及免疫球蛋白+补体,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检查,其中2例患者抗干燥综合征抗原(Sjögren syndrome antigen,SSA)抗体阳性,1例抗核糖核蛋白(ribonucleoprotein, RNP)抗体阳性,1例抗链“O” 升高,7例患者类风湿因子升高,7例患者IgG升高,其中合并IgA升高3例,所有患者均出现CRP升高和ESR增快,详见表1和2。

表1 出现神经系统表现的AAV患者临床特点概况

表2 出现神经系统表现的AAV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

续表2
8例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患者中,脑梗死7例(87.5%),脑出血2例(25.0%),蛛网膜下腔出血1例(12.5%),脑膜炎1例(12.5%)。其中3例(37.5%)患者反复发作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病例1首先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诊断AAV后拒绝治疗,1个月内出现脑出血(图1),病例4先后出现2次脑梗死和2次脑出血,病例8先后出现2次脑梗死(图2)。病例3同时出现脑梗死和脑膜炎改变。临床表现主要包括肢体无力、肢体麻木、癫痫发作、记忆力减退和精神障碍。头颅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或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显示2例患者的颅内病变分布在单侧大脑半球;其余6例患者的颅内病变分布在双侧大脑半球不同区域及脑干,非单一血管供血范围。2例患者未完善脑血管相关检查,1例患者头颈部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提示轻微脑动脉狭窄,其余5例患者均未发现与颅内病变部位相关的责任血管病变,详见表3。

图1 病例1,女性,60岁,头颅影像学

表3 8例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AAV患者的临床特点

图2 病例8,男性,66岁,头颅影像学
周围神经系统受累的患者多表现为肢体麻木、疼痛。10例累及周围神经系统的患者中9例为肌电图证实的周围神经受损,1例仅表现为四肢麻木,未完善肌电图检查。肌电图检查提示患者存在多发性单神经病、单神经病、多发性神经病三种表现形式,其中大部分患者以多发性单神经病为主要表现,运动感觉均有受累,髓鞘和轴索均有损伤,以轴索为主,详见表4。病例5肌电图呈动态变化,最初仅为单神经损害,随着疾病进展,逐渐发展为多发性单神经病,损伤程度亦不断加重。病例13肌电图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呈长度依赖性,但同时合并糖尿病。病例9完善了腰椎穿刺脑脊液化验、神经活检和肾脏活检。腰椎穿刺压力160 mmH2O(1 mmH2O=9.8 Pa),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 2×106/L,蛋白47.16 mg/dl(正常15~45 mg/dl),免疫球蛋白G 82.6 mg/L(正常0~34 mg/L),寡克隆区带阴性,脑脊液的IgG鞘内合成率9.06mg/24 h(正常<7.0 mg/24 h),脑脊液髓鞘碱性蛋白 9.09 μg/L(正常<3.5 μg/L),血髓鞘碱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 MBP)9.39 μg/L(正常<2.5 μg/L)。血和脑脊液副肿瘤相关抗体、神经节苷脂谱抗体均阴性。神经病理提示:周围神经的主要病理改变是出现有髓神经纤维中重度丢失,较多轴索变性,个别再生簇结构,伴随神经内衣水肿改变,符合急性轴索性周围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特点,不同束间病变分布不均;肾脏病理提示:肾穿刺组织可见30个肾小球,6个小球缺血性硬化,1个小球细胞纤维性新月体形成,其余小球系膜细胞和基质轻度节段增生,肾小管上皮细胞颗粒变性,约25%肾小管萎缩,约25%肾间质纤维化,小动脉壁增厚伴玻璃样变性。符合肾小球轻微病变(图3)。

表4 10例周围神经受累的AAV患者的临床特点

图3 病例9,男性,53岁,神经活检和肾脏活检
14例患者中有3例(病例1、9和10)是以神经系统表现为首发症状就诊于神经内科,经检查发现已合并出现肺脏和/或肾脏受累。其中病例1为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病例9和10为周围神经系统受累。
除1例发现胸腺瘤患者仅给予对症营养神经治疗外,其余13例患者均给予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10例患者给予激素加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1例患者给予激素加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P),2例患者仅给予激素治疗。经治疗后9例(64.3%)患者临床症状有所好转,2例(14.3%)患者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2例(14.3%)患者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包括肌无力、肌萎缩、肢体麻木疼痛。1例(7.1%)GPA患者呈反复发作,多次住院治疗。所有患者随访截至2020年12月31日,无患者死亡。
2 讨论
AAV的发病无性别倾向,大部分研究[7]显示男性发病较女性稍有增多,男女比率1.07~1.48。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有所增加,近年来发病年龄峰值呈逐渐上升趋势,由55~64岁上升至84岁,可能与检查技术手段和对疾病的认识水平提高相关[7]。本研究显示在出现神经系统临床症状的AAV患者当中男女比例相当,平均年龄(64.9±7.31)岁。神经系统受累在AAV患者当中并不少见,可发生在疾病的任何阶段,GPA患者中的发生率为22%~54%,MPA患者中的发生率为34%~72%。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占所有AAV患者不到15%[4],周围神经损伤更多见。本研究中14例出现神经系统表现的患者占同期医院确诊的146例AAV患者的9.6%(14/146),中枢神经系统受累5.5%(8/146),周围神经受累6.8%(10/146),由此可见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神经损伤比例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AAV患者由于呼吸系统、肾脏受累就诊于呼吸科、感染科和肾内科而被确诊,且既往研究[4]显示,中枢神经损伤通常发生在疾病的晚期,本研究显示个别患者可以中枢或周围神经系统损伤作为首发症状起病,并且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容易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相混淆。且该研究者[4]认为“局限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AAV”可能是AAV的一种特殊亚型。
AAV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可能机制为:(1)炎症反应增加了颅内小血管的通透性或引起血管阻塞;(2)临近结构肉芽肿病变的侵犯或压迫;(3)中枢神经系统内产生的肉芽肿性病变[4]。临床上可出现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肥厚性硬脑膜炎、肉芽肿样占位性病变、脊髓病变等等[8-13]。本研究显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AAV患者中脑梗死最常见,其次为出血性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膜炎最少,与既往文献[14]报道一致。脑梗死临床表现无特异,多为肢体无力、麻木,部分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精神障碍,个别患者可出现癫痫发作。影像学检查显示病灶呈腔隙性梗死灶,多数患者梗死灶分布范围较广,同时累及双侧前循环,个别同时伴有后循环梗死,不符合单一血管分布区,且血管检查未发现严重大动脉狭窄的证据,符合AAV广泛小血管损伤的特点。另有报道[8]显示,AAV患者也可表现为大面积梗死并出血转化。尸检显示患者病理改变为坏死性小血管炎[15]。此外,还有研究者[4]发现有头颅MRI T2加权像广泛分布的非特异性白质高信号,包括侧脑室旁、皮质下、基底节区、中脑和脑桥,通常与患者认知损害相关。AAV患者发生脑梗死后给予抗血栓治疗需谨慎,因小血管炎性改变导致通透性增加,患者出血风险也相应增加。有报道[16]给予1例伴有低热、肌痛、盗汗、皮疹的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tPA静脉溶栓后出现出血转化,患者病情进展加重,最终检查确诊为AAV。出血性脑血管病临床表现及影像多无特异性,需完善全面检查,排除其他疾病。文献[11]报道,AAV可导致肥厚性硬脑膜炎,而本研究中1例患者头颅MRI显示软脑膜强化,完善腰椎穿刺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推测与软脑膜血管炎症相关。由于中枢神经系统活检病理较难获得,因此患者颅内病变缺乏病理诊断的支持,但患者给予传统脑血管病治疗效果欠佳,给予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好转可协助临床医生评判诊断的正确性。
AAV周围神经损伤最初表现为急性起病的远端肢体麻木疼痛,常多见于下肢。病初感觉异常分布区符合多发性单神经病,也有小部分患者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随着病情进展,多发性单神经病最终演变为对称性或非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肌无力程度和对称性各异,可能主要累及感觉受累肢体的远端。病初无明显肌萎缩,随着病情进展可出现肌萎缩。脑脊液化验显示细胞数和蛋白正常。病理改变主要是因血管炎导致缺血而产生的轴索变性,有髓纤维的减少或丧失,神经纤维密度减低,脱髓鞘改变相对较轻,偶见再生簇。尽管血管壁炎症损伤是鉴别血管炎性神经病的主要表现,但实际检出率并不高[17-18]。本研究中周围神经损伤患者临床特点与既往文献[18]报道相似。临床上以肢体麻木疼痛,肌无力、肌萎缩为主要表现,肌电图检查提示患者主要表现为多发性单神经病,运动及感觉均有受累,髓鞘和轴索均有损伤,以轴索为主。动态监测肌电图可发现患者从单神经病发展至多发性单神经病的过程,提示病程初期患者可能仅表现为单神经病。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病的患者如合并糖尿病则较难鉴别。脑脊液细胞数正常,蛋白、免疫球蛋白、鞘内合成率稍有升高,血和脑脊液副肿瘤相关抗体、神经节苷脂谱抗体均阴性,提示存在非特异性神经损伤。神经病理提示炎性细胞浸润不明显,有髓神经纤维中重度丢失,较多轴索变性,个别再生簇结构,伴随神经内衣水肿改变。
本研究14例患者中,12例(85.7%)患者诊断为MPA,无论在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还是在周围神经系统受累患者中MPA均占大多数,与既往报道[14]相一致。MPA和GPA患者中既有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也可以存在周围神经损伤。GPA患者累及全身系统范围相对更广泛。有研究者[14,19]认为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并不影响AAV患者的生存率,合并周围神经损伤的MPA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58%,并非不良预后的预测因素。本研究中大部分患者经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有所好转,少部分患者遗留后遗症,个别患者临床上反复发作。
总之,AAV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亦可累及周围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受累略多见,而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亦不少见。中枢神经系统可表现为脑梗死或出血性脑血管病等,脑梗死最多见,多为腔隙性梗死灶,分布范围较广,不符合单一血管分布区,且多无大动脉严重狭窄。由于影像难以显示小血管病变,活检病理可明确诊断,但较难获得。周围神经损伤主要表现为多发性单神经病,以轴索损伤为主,亦可出现多发性神经病,炎性细胞浸润检出率并不高。中枢神经受损和周围神经受损均可作为AAV首发症状出现,而全身其他脏器损伤经详细检查后才被发现。因此,临床医生需提高对AAV的认识,以免延误治疗,AAV患者经积极治疗后多数临床症状可明显改善,神经系统受累并不影响患者预期生存率,患者不良结局多由于肺、肾功能受损,继发感染以及心血管事件引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