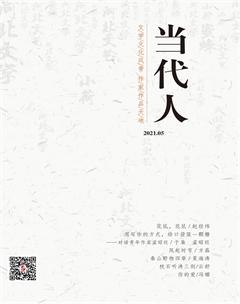一九七零年代的冬天
一
一九七零年代的冬天,准确地说是一九七零年代下半叶的冬天。老天似乎总是阴雨绵绵,不曾体体面面地出过几次红火太阳。杀年猪,过大年,饱吃一顿猪肉,添一件新棉袄等等,一些美好事情,在我无数次急不可耐地等待中,隐隐约约地来,又隐隐约约地去了。
那些年的冬天真是漫长呵。沉寂和忧虑,并未消磨村庄的意志。大人们的脸终于有了起色,笑容徐徐展开。
几个姐姐相继远嫁到了山外。少了几个熟悉的亲人,加上母亲的病痛一天甚比一天,老屋显得有些空落了。这并不影响接下来的动静。冬天快要到头的时候,家里破天荒分得好几块庄稼地。一个濒临贫困边缘的山里人家,忧郁的背后,是跃跃欲试的兴奋。
真的是跃跃欲试!
一九七零年代的冬天,我上完了五年小学。
二
我的母校是夹江县麻柳公社红旗小学。据说,那所小学是夹江县最偏远的一所学校,且是可以验证的。
准确地说,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山里的天气难得的好,现在还能回想起它的阳光灿烂。
某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就要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幕里粉墨登场了。
我的小学,从我的大姐提着我的书包,陪我去学堂报名开始。
学堂是三间瓦房,据说原来是一座庙宇,叫回龙庙,后来改作了村里的学堂。校门上分明写着“红旗小学”,完全跟那庙扯不到一块。这个名字不如现在的复古意好——回龙小学。
回龙庙为何叫那蹊跷的名字?问了几个大人,各人说一套。一种说法是,学堂周围汇聚几座山脊,我们这些学生娃其实是坐在几条龙的脑壳上念功课,占尽风水,似乎预示有大出息。龙脑壳一说尽管牵强,却让我对学堂日渐产生敬畏与好感。
学校一共三个老师,三人包三班,一杆子插到底——教到毕业。好在那时只开了很少的几门课,主要是语文、算术,到了高年级,每周又加了两节豆芽课——政治和自然。学生娃围着老师转,老师围着课堂转。我们不累,老师倒是转昏了头,没有三头六臂对付不过来。真佩服那些村小包班的老师呵。
包我们班的老师叫李长安。他的身份是代课老师,连民办也不是。公办是国家的人,民办是乡镇集体的人,代课算谁的,大隊的还是生产队的?不得而知。只是,每个学期末,李老师总是提着一个干瘪的麻袋,轮流到每个生产队里称玉米,我就纳闷,怎么先生不像个先生,倒像个要饭的?另外两个老师是公办,一个主任,一个后勤。李老师曾经是上过师范的,他的父亲叫他回家学木匠,耽误了一个学期,终是没有资格毕业。每次谈到他辍学的事,李老师总是习惯性地抿嘴一笑,嘿嘿,这样也好,粗通两门手艺,不至于饿饭了。
李老师常常穿一件洗得发糠的青布长衫,脸色也白净清秀,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旧年的书生气。听说他发蒙时上过私塾,古文古诗,张嘴就来,叫人羡慕得不行。老师那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曾经就我们学校的“地脉”传闻请教于他。李老师对风水一说,自然一脸不屑。祖坟里有啥弯弯木?学堂里有啥龙脉龙气?要出人头地,除却脚踏实地,大把小把汗水,别无他路。因为此话,奠定了李老师于我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后来,每每填写各种档案材料时,我都要在个人简历的小学学历证明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填上他的名字,尽管一个先生不像先生、农民不像农民的老男人的证明不值一提。
三
刘二狗是我小学印象最深的同桌。
二狗插到我们班的时候,我上三年级。听说成绩差得没底,他们班的周老师就把他降班了。降班是不需要家长和学生娃表态的,放在今天要视作“被降班”,会遭到家长和学生质疑投诉的。
李老师让二狗和我同桌,结对“一帮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如此格局。二狗贪玩,经常完不成作业,让我挨了不少批评。二狗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就常常带些小玩意到学校同我一道玩,还请我到他家里吃猪肉,我也不好说什么了。这也真应了一句老话: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口软。三年同桌,二狗的成绩不见有多大长进,我们俩倒是成了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就差没有同穿一条裤子了。
别看二狗书读不进去,却有一个要命的嗜好,看坝坝电影。跟在公社放影队屁股后头,这山追到那山,一部电影反复看好几遍还过不了瘾。有一回,大概也是在冬天,他和村里几个上初中的娃去很远的李山村看《平原游击队》。电影一完,那几个初中生一溜烟,把他给甩了。二狗胆子也大,甩了便甩了,索性耍赖,半路钻进一堆玉米秆里,不走了。周围黑黢黢一团,不时还传来几声野猫的诡叫。二狗睡不着,就想八路军和李向阳,数头上的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一直数到一千颗。这可是他亲口说的,虽然我不相信他有毅力从一数到一千!数到一千,还是睡不着。幸好有一堆玉米秆密密匝匝遮挡寒气,有满天的星斗忽闪忽闪打发时间。直到下半夜,二狗才提心吊胆地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二狗迷迷糊糊醒来,家也顾不上回,撒腿直奔学校。听他眉飞色舞讲述夜晚苞谷地的奇遇,都佩服得不行。
后来有一次,老师让我们用“要是,要是,就”造句。刘二狗造的句子大意是:要是那天晚上没有那一堆玉米秆呢,要是半夜里来了一只“娘”呢,我不就惨了?他竟然把“狼”写成了“娘”!刘二狗造的句子,差点让全班同学笑岔肠子,自然也成了李老师奚落的话柄,刘二狗啊刘二狗,你简直是一截烂穿了孔的朽木。
朽木不可雕也!李老师似乎还念叨了一句那时我们似懂非懂的古话。
立冬一过,寒意渐从四下里聚拢。刀子一样凛冽威猛的风,刮破了教室窗户上的黄纸,挤进课堂,再从领口、袖口和裤腿几处,往我们的背心里灌。随后,冷雨也进来了。我们几个穿得最单薄的娃,冻得上牙磕下牙,恍惚一听,还以为嘴里不停地念叨“g、k、h”哩。女同窗们的小手,开始生冻疮,有几个还用毛线织成手笼子,套在手上,还是冷,厉害点的手指头,俨然已成一棵棵红透的胡萝卜。她们的手也太娇气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学堂背后的鹰嘴山尖也戴上了动人的雪帽。大家冻得捱不住了,就把烘手篼提到学校。五花八门的烘手篼,小巧的,粗糙的,都是家里大人们亲手新编。上课,大家就把手放上去,边暖手边听老师讲。一下课,就得忙着添碳吹火,搞得满教室都是烟尘在飞。
当然,小烘手篼仍然不能解决全班的烤火问题,于是就趁天放晴时拾柴禾。记得学校旁边有一座小山叫癞子岭,林子里不时冒出些老坟塘,平时少有人至,柴禾四处是。我们每次进林子里去,闹哄哄折腾半天,抱回来的柴禾能堆满半间教室。在教室当中生起一堆大火。不用担心失火,地面是泥的。把柴禾横七竖八地架上去,一点燃,满教室都是暖烘烘的光彩了。火燃旺,就把小烘手篼的碳火灭了,围坐在火塘周围,烘烤潮衣潮鞋,读课文写作业,那感觉就像在自家屋里无二。
大雪终于下来了。纷纷扬扬的雪片,携带童话的趣味。堆雪人,打雪仗。女同窗也加入游戏,一玩便忘记手上已是九皴八裂,甚至连上课的铃声响也忘了。
现在能熟背一首打油诗,就是应雪景。“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真是一首绝妙的好诗,简直跟细娃眼见心想一模一样!谁作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其实,李老师还教我们背过许多雪花诗的,像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类,只是现在差不多都淡忘了。
从我家到学堂,大约有半个钟头的山路。出门几步,是一条小溪。小溪不宽,一根独木作桥,树脑壳搁在这头,树梢伸到那头。之后是一道山脊,一口气翻过去,再穿过一片竹林,前面就是学堂了。
山脊叫“白果树”,印象中原来有好几棵很威武的白果树的——山里不叫银杏,就叫白果,至于是“百果”还是“白果”,谁也不会去细究,反正比周围其他的树要高大,会结一种神秘的干果。我刚上一年级的那个秋天,还在下面捡过白果叶的。那些白果叶就像一面面金黄的圆扇。我用大姐给我的红丝线,把它们小心缀起来,插进书页,真是好看。后来,队里因为购买打米机、打麦机,建加工房,就把山岭两旁的几棵白果树砍了,卖给了山外来的生意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那叫“白果树”的山脊,可怜巴巴秃了。
白果树一砍,藏在树干背后一块很大的顽石,就露出一脸的丑相来。石上孔洞相连,坑洼一片。苍苔被风吹干,老去,脱落,现出许多花白斑痕。曾经在一个午后,仔细琢磨过石头上的那些“画”。有的像疯玩的猫狗,有的像大团小团的云朵,有的像灯戏里的将军,肩上还扛着一竿竿旗帜。“石画”似是而非,却饶有趣味。更多的像一窝窝眼睛窟窿,《大闹天宫》里妖魔鬼怪的那种。凶神恶煞的眼睛窟窿,自那个午后不止一次地在我的梦里出现。便不敢一个人与那些眼睛对峙。独自打那块石头前路过时,还未走近,那些鬼怪那些眼睛,似乎已聚在眼前,散发深邃的光彩,脚步不自觉地要快,三步也就并作两步,心也要跳出来了。
倘若有女同窗一道上学,我们就会拿那些眼睛做文章,制造恶作剧,吓唬吓唬她们。经过那石头前面时,几个男生突然阴阳怪气地唤,鬼来喽,鬼来喽……吓得女同窗们赶紧随我们惶跑,这一跑,摔跟头,就有得好看了。下山脊时,是一段泥泞路,没有铺石板,逢下雨又湿又滑,整整一个冬天几乎不会有什么改观。看着女同窗们摔得满嘴啃泥,我们会生出一种异样的报复快感,谁叫她们经常在老师面前说我们的坏话呢?我们其实也是沉不住气的,除了心虚老师收拾以外,也惧怕石头上的那些眼睛。就像阴森森贴在脑后一样,你跑一步,它跑一步,甩都甩不脱。
白果树砍后不久,我们已上五年级了,女同窗们已经不再畏惧男生装神闹鬼。那块石头,也渐渐有了個名字——“鬼眼睛石”,自然是我们的杰作了。村里的人很快习惯这个新地名。他们早已不再计较,山脊上是不是曾经有过三棵还是五棵大白果树了。
我小学五年的二十个同窗,毕业时教室里还坐有十五个,全部考上初中。后来听说,有当干部的,有当医生的,有发了小财的。还有几个当了老师,其中两个留在母校代课。一个是姓符的女同窗,职高幼师班毕业,回村一直在那所村小代课。另一个你猜是谁,是那个刘二狗。
因为同学们统考成绩出息,我们班一毕业,李老师顺理成章转成了公办老师,成了体面的国家干部,还调进了中心校。一九八六年秋天,是我走上讲台的第一个秋天,抽空去拜访了先生,向他讨教一些为人师的法宝,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至于我的母校,回龙小学,哦,应该叫红旗小学,我回老家时特意去看过两回。路虽然不再是那泥滑的石板路,木头房子也换成了镶嵌玻璃的砖房。但那座座山梁,阵阵书声,似曾相识。刘二狗已经不再代课,姓符的女同窗还在。娃也不多。女同窗领着山娃子们大声诵读课文的时候,我已然从那一张张新鲜陌生的笑脸上,找不见丁点儿一九七零年代的表情了。
(沈荣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思想及文艺史随笔作家。)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