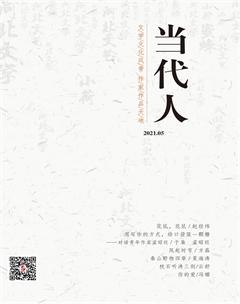“后视镜”里的众生相(评论)
大部分人进入社会、参与工作以后,多多少少都会丢失对周遭自然世界的感知力。人,是一种社会性的智慧生物,也许能够忍耐孤独、忍受存在绝境,但总还是需要陪伴,跨越种族和物种的亲密关系亦能在某些孤独时刻赋予人存在的慰藉,甚或存在的意义。依靠动物去描述这种绝境中的“慰藉”,或者通过动物视角叙述生存处境的文学作品非常多,赵经纬的短篇小说《花鼠,花鼠》正是这一庞大谱系中新生的佳作。
花鼠,南方的朋友可能并不多见。这一与松鼠近亲的小动物多见于长江以北草木繁茂的平原和盆地。由于有伤农事,偷吃储粮和种子,务农和经商的人家对这些“鼠类”没有好感。尽管它们在当代人的眼里有着宠物一般机灵又小巧的特性,但倘若在农事上和花鼠打过交道,恐怕总会随口骂一声“花栗棒子”。鼠类的恶名影响到了花鼠在人间的地位。北方民俗文化中常有“四大门”一说,狐狸(胡)、蛇(常)、黄鼠狼(黄)和刺猬(白)可通过修炼列为仙家(家仙),与人共存,可为圣灵。另外,还有“五大门”的说法流行,老鼠(灰)和兔子(白)有时能跻身其中。可怜此鼠非彼鼠,花鼠不仅要承受人们日常对鼠辈的仇恶,还会因为破坏庄稼的“劣迹”而被视为仇敌。“花栗棒子”与那些带有情色调侃、身体或性别歧视的骂法并不在一个逻辑里,这一骂名处于鄙视链的底端:贼眉鼠眼、好吃懒做、偷盗成性、损人利己。它还包含了另外的意思:贫瘠的生活里每个人都需要奋力求生,若是外形丑陋但能勤劳耕种就是好样的,可你偏偏不能付出劳动,还要乞食求生,寄人篱下,“从穷人嘴里抢口粮”,这不就是让人唾骂的“花栗棒子”吗?
小说中描述的,正是像花鼠一样“从穷人嘴里‘抢口粮”的小鹿一家。
主人公小鹿正值天真烂漫的年纪,但小时候生病不得医治,落下了侏儒之症。他身体停止发育,还需每日服药,好在父亲是中学教师,能维持一家子的生计。可是,某日父亲上班后再也没有回来,小鹿一家没了顶梁柱,就此陷入窘境。虽然还没到全家都寄人篱下的地步,但总得求人接济,向同样贫苦的乡邻讨生活。这一家子的处境对于旁人来说,是不是“可怜又讨厌”呢?小说开篇,父亲已经离家许久,小鹿还期盼着他像往常一样穿着雪白的衬衫、骑着锃亮的飞鸽自行车回家。小鹿没有意识到父亲毫无音信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很想念有父亲在的日子,想念无忧无虑,想念糖果。小鹿的身体因为疾病而停止发育,头脑和思想也没有变得更为警敏,似乎停留在父亲刚刚“离家”的那些时候。小说随着这一视角徐徐展开,小鹿用童心、奇思、委屈和思父等视角构建起的乡野生活,与小鹿一家人艰难尴尬的求生日常重叠在一起。
《花鼠,花鼠》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这叙述视角——将“天真儿童”和“求生日常”重叠在一起。用儿童视角来讲成人世界的不堪已造就不少好作品,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便是其中典型。《喧哗与骚动》以“复调”响彻现代小说界,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多人声部,此类小说假借儿童视野,限制作者和读者以成人的心思去揣测小说天机。《喧哗与骚动》和《花鼠,花鼠》的“天机”不在多声部的互相争辩,文本缝隙里的沉默难言更具意味。被视为心智发育不全的儿童,或者在小说中沦为侏儒、弱智、残障者的人更能还原事情的“真相”,直抵存在的残酷面相。
莫言、阎连科等名家也曾模仿福克纳的手法,以“儿童+残障”的人物为主角,用童真童趣的“后视镜”去看普通人的生活,从而照见日常里的不幸和不堪。除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外,莫言在《枯河》和《白狗秋千架》里也用了同样的手法,但其文笔之间弥漫着魔幻主义的气息,暴力和死亡的隐喻藏在文本风景之中,小说中童真的声音和残忍的“日常”像是黄口小儿与洪荒死神在二重唱,文本内蕴含的张力极大。反复读这些小说,阴郁寒冷的味道涌上读者心田,有时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相比之下,赵经纬这篇《花鼠,花鼠》却是真正把重心放在小鹿身上。小鹿对周遭环境的童真好奇,对人际关系的不明所以,对于善意和恶念混杂在一起时的即时反应,这些都是作者认认真真书写的内容。于是,风景和环境,物象和生活的细节,以及人物情态的缓慢变化等要素都被细心写出。赵经纬为此恐怕酝酿了许久,花了大心思去琢磨。白描手法与心理描写相配合是小说叙述成功与否的关隘,《花鼠,花鼠》攻克了这个难题,并没有向心理描写一边倒。而且,这篇小说的整体氛围得益于作者克制的文笔,阴郁绝望的气氛很好地被拿捏住了。道德评判也未曾展现在纸面,一切交由读者去回味和反思,留在小说里呼之欲出的是作者“悲悯”的眼神——小说里有些小鹿的话,更像是成熟的作者在为懵懂的小鹿陈情。
故事情节的高潮出现在父亲死讯传来时。有人在河滩边发现了小鹿父亲的尸体,一切童真的等待和委屈都要面对赤裸的现实。读到这里,不禁令人联想巴西作家罗萨在《河的第三条岸》里刻画的父亲,那位执意漂泊于江河之中的父亲倘若死掉会怎样?《花鼠,花鼠》的作者选择跳出童真的视野去看这一场景,用第三人的眼睛盯着小鹿有什么举动。小鹿将挖到的小老鼠杀死,希望它们能替父亲挡过此劫,替身换命。这一笔真是厉害极了,小说由此破题,原来花鼠不仅是宠物,不仅是小鹿寄予思念和希冀的对象,还是那“神圣的人”。
当代哲学家阿甘本有言,“神圣的人”(homo sacer),亦即“牲人”,乃是被驱逐出社会、不容于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的人。他被视为神灵的财产,任何人杀他都不构成犯罪。这一古罗马法律概念被阿甘本延伸至当代。那些无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中跻身的人,会被各种权力指为牲人,他们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反而被高度政治和经济化,成为随时可被夺取生命的物品。小说里的父亲为何而死我们无法知道,意外落水或被人所杀皆有可能。但自父亲“不歸”后,小鹿一家就陷入了极艰难的困境。尽管四周乡亲和亲戚并没有过分欺辱,还不时接济他们,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同那个消失了的父亲一样,都成了“牲人”,都成了“花栗棒子”,是当地的“花鼠”。虽然作者试图让残障但纯真的儿童去反抗被视为“神圣的人”,但终究是徒劳。
小说叙述到这里,已至尾声。第八节讲述了小鹿亲眼见证福婶心脏病发作,试图喂以药丸却告失败。小说的结尾召回意象派和魔幻主义,将小鹿送到一片美好的世界里。这样的写法,怕是作者无奈之笔,虽有急促收尾之嫌,但也算是不得已的留白之法,再写下去,就要扩充、丰富周围人的具体形象和行为,不断增加新的情节,这将给小说的叙述带来巨大压力。
《花鼠,花鼠》里对小花鼠的描述颇具温情,仿佛它无法感受痛苦一样。花鼠以替身的角色在小说中退场,而小鹿继续存留在文本中,不时让我们看见花鼠的影子。人与动物在小说中互为替身,将人间的残酷化解在其中。
(李屹,字修远,安徽黄山人。2015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17至20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习。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当代文学批评。近年来关注医学人文学,老年文化与老龄社会研究,性与性别文学文化研究。)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