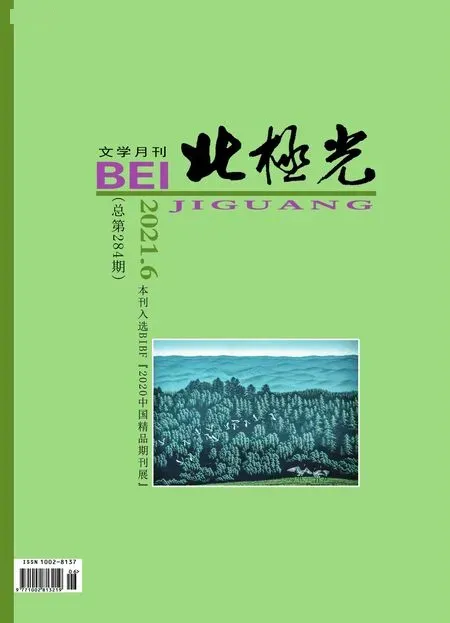长安诗酒胡姬花
□英子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天宝年间,白马白衫的李白跨进长安城时,他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这座城池的法地象天的帝王气度,而是一双挥舞着的绵软素手。城里的街道上,从世界各地涌来的商贾学子艺人僧侣缕缕行行,车水马龙,人口最多时已超过一百万。开放而宽容的、多民族混居的长安城,遂成了一个胡风滚滚、胡尘漫漫、胡乐飘飘的所在,在胡服、胡食、胡俗、胡歌之中,妖冶的胡姬伴着盛唐的诗酒欢歌,以狂野精怪喧嚣着长安城内的一百零八坊,此时,这位金发碧眼、腰肢纤软的胡姬的召唤正和着一缕缕春风,鼓荡着李白精致的绸衫,也鼓荡着李白狂放多情的心。
汉文古籍中所说的“胡”原意所指甚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华夏域外的异族。但据向达先生所著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考证,当时古籍中记载的流寓长安、擅长经商的“胡人”,主要是指波斯人和粟特人等。高鼻深目、曾书写过楔形文字的波斯人性喜饮酒,美酒与美色是波斯人生活的重要内容;粟特人祖居于茫茫葱岭以西,通过归附、人质、使节、技艺、商贾等多种渠道,粟特人的血脉之溪,沿着古雍州古凉州的河西走廊,数百年里一直无畏而坚定地向着长安、洛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主干城市渗透,至盛唐时,波斯人与栗特人早已成为长安城里重要的迁徙民族。
这些人数虽多、但仍被长安民众轻蔑地称之为“胡人”的商贾,多以贩卖丝绸与美酒为生,他们贩卖的酒类是高昌之“葡萄酒”、波斯之“三勒浆”、乌弋山离国的“龙膏酒”。“蒲桃”就是“葡萄”,据说,“唐太宗平定高昌后,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种源自于高昌国,又经唐太宗御手钦制的、酒性酷烈的“葡萄美酒”,成了豪华的李唐皇宴的标志性饮品。暗红色的美酒与碧绿色夜光杯色泽绝配,烈香彻骨,透过王昌龄“葡萄美酒夜光杯”给后人留下了精妙的遐想;“三勒浆”同“蒲桃酒”一样的皇家珍品,可能酒性不如“蒲桃酒”那般清冽,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这样记载:“唐代宗以“三勒浆”赐太学诸生,其光灼灼,如蒲桃桂酿,味则温馨甘滑”;“龙膏酒”既然称之为“膏”,外观一定粘腻似膏,唐代武功县的进士苏鹗一定是喝过这种美酒的,他在《杜阳杂编》里称“龙膏酒”为“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杜阳杂编》卷二又记云:上(指唐宪宗)因好神仙不老之术,一个名叫“玄解”的“气息高洁”的处士被密召入宫禁:“上知其异人,遂令密召入宫,处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龙膏酒色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至多,亦大国也”的“乌弋山离国”是班超打通的西域诸国之一,当指今之阿富汗的赫拉特一带。如此看来,蒲桃酒、三勒浆、龙膏酒等不仅是酒类,更兼是唐代的珍贵滋补品。时至今日,四川成都的三勒浆药业集团的广告单上仍然写着:“唐代的一本名叫《国史补》的古书上首次记载了一种神奇的配方,名为三勒浆。后来,三勒浆的主要药材均收入历代本草著作,包括《唐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药性论》和《本草纲目》等”。
这些带着西域诡谲香气的美酒一入长安,便引发了满城哗然的喧嚣。初唐诗人、生性贪酒的王绩肯定是最早的一批酒客,因手中常无沽酒之资,王绩只得赊酒而饮,后来干脆作《题酒店壁五首》以充酒钱:
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的长道贳,惭愧酒家胡。
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比西域名酒更让男人们惊艳的,是开酒店的胡人带来的粉嫩如花的“胡姬”。胡姬是指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是欧洲一带的女性,从诗人们夸赞她们“数钱怜皓腕”“胡姬招素手”的句子来看,她们应当是印欧人种的白种人,很可能源出中亚的索格底亚那地区。是被波斯或粟特的商人贩卖到长安的女奴。《新唐书·西域传》中“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的记载,说明西域一直存在着买卖女奴的“女肆”。长安地处于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西域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各地商人在贩卖丝绸美酒的同时,也轻车熟路地在长安做起了胡姬的买卖。纤腰胡姬身着广袖合欢袄,脚踩绣花丝靴,猫一般绵软地游走,她们碧绿发光的猫眼瞬间万变,她们的头发也如猫儿一样黄里透金。还说,她们摆动腰肢、踮起足尖的胡旋舞,疾如旋风,轻如飞雪,在声声惊心的羯鼓声里,高挑细削的胡姬那酥胸含雪环佩叮当的装束,那完全不同于汉族女子的热辣眼风,个个都是“胡姬醉舞筋骨柔”。于是,那头发蓬乱、身披渔阳战尘的骠骑男儿,是怎样在铮铮鼗鼓声中,摘下他腰间从沙场上带回的大秦珠,换得一坛美酒的啊!那策马而来、头簪红花的轻狂少年,是怎样卸下了他的玉勒雕鞍,买得胡姬的一宿春醉啊!那身着仙袂般软白的绸衫、常在酒肆中烂醉如泥的诗品般的李白,又是在怎样的寸寸结结之中,写下了“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的啊: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
为官清廉、却也时常参与诗友的风花雪月之会的杨巨源,又是在哪一处“绿柳才黄半未匀”的二月清风里,朦胧的醉眼里飘忽着十五岁的娇羞,才写下了这首丝丝缕缕的“胡姬词”的啊: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
“青绮门”即长安的春明门,在正东,兴庆坊与道政坊之间。开元十六年,唐玄宗移入兴庆宫听政,兴庆宫遂成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中心。唐代著名的宫殿南熏殿、大同殿、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和沉香亭等建筑物都在兴庆宫里,按照唐玄宗的授意,东郭墙内建造了“夹城”,供唐玄宗与皇亲们秘密通行。夹城的南北起点就在春明门,淡扫娥眉身着男装的虢国夫人,正拂开丝丝细柳,以天子之姨的华贵与慵懒,穿行于春明门的夹道之间呢。面白无须却得意弄权的高力士,说不定就扶辇于夹城中,匆匆接回在宁王宅第烂醉的李翰林,说皇上和贵妃娘娘正在牡丹亭等着他的新诗呢。而日日笙歌的教坊里,紫玉笛吹出的清平调和霓裳羽衣曲,正顺着春明门的夹城,传入勤政楼上唐玄宗的耳中。这声声召唤,引得酷爱丝竹的唐玄宗放下了手中的朱笔,偷偷抚摸着藏在龙袍里的玉笛,心思又飘忽到昨夜的新曲谱上了。
“江头”指的是曲江边,在东南角,“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的暮春,大唐的新科进士锣鼓喧天地在此摆下“闻喜宴”。这种连皇上都要“御紫云楼,垂帘观焉”的盛况,豪华的教坊乐队丝竹高亢,乐师雷海青的铮铮琵琶惊涛裂岸,宫伎第一女歌手念奴的高音破空而下,被玄宗誉为“每执行当席,声出朝霞之上,二十五人吹管也盖不过其歌喉”。王定保《唐摭言》有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所以,那高举着皇上赏赐的四百酒钱的青年才俊,今日不仅畅饮美酒,还会一日看尽长安花呢。
如此的富贵丽景之下,在铺着红毡地毯、摆满波斯风格的金银杯壶的酒肆内,胡地厨师精心烹制出的羊馔、脍鲤、胡炮肉、驼峰炙、驼蹄羹、鹅鸭炙、羊皮花丝已盛满高足银盘,三勒浆闪着华彩,已在夜光杯中层层荡漾。清越胡琴奏出的《乐世娘》丝丝入扣,俯在客人肩头轻摇小扇的妖媚胡姬,薄薄青衫中透出“胡姬若拟邀他宿”的暗香,怎不让多情公子意乱神迷啊。
花钱买得与胡姬春风一度,是当时的长安少年最得意、最乐意的事情。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推动了长安酒文化的女性群体,这些传播过西域歌舞的草根艺术家们,在长安的大街小巷鲜艳了数百年后却真真的“风吹芳兰折”了。今天,除了在诗人粉艳的诗笺上和斑驳的壁画上能看到她们妖冶的背影之外,史书里竟然没有关于她们的只言片语。
时至现代,却有许多现代的学者们开始研究胡姬的生活,甚至有学者认为留下一整本传奇戏文《西厢记》的崔莺莺就是一位胡姬。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大学者陈寅恪。陈先生在《读莺莺传》中推测说,崔莺莺原型是中亚粟特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并推出崔的原名为“曹九九”。近年来,《文物》主编葛承雍教授通过对《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山西永济唐代蒲州普救寺的一系列考察,非常肯定地断定崔莺莺的原型就是中亚“胡姬”。现将葛承雍教授发表于《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摘录于后,并致谢忱:
“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非常善于从实录笔法的小说中发现有根有据的历史,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写有《读莺莺传》一文,推测元稹塑造的崔莺莺原型是中亚粟特种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他参照胡姓、胡名和胡俗三项标准立说,首先,设想崔莺莺原名为曹九九,因为唐代中亚粟特人入居中原的很多,其中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G u b d a n)‘曹’国人,不仅在唐朝拜相做官,而且善弹琵琶,入居中国者很多,莺莺姓‘曹’而不姓‘崔’。极有可能,莺莺与古音‘九九’相近,双文复字在唐代女子取名中常见,故崔莺莺谐音曹九九。”

如今,隔着风隔着沙,长安城诗酒中的胡姬御风而去,竟无半点遗迹可寻。连年征战的大漠边关,裹在腐锈铁衣中的狼族枯骨,再不能带来半点异乡的消息。如果,崔莺莺真是一位胡姬的话,那遥远的边城,会不会有一位同样高鼻深目的少年,吹着羌笛,遥遥地寄来一份思念呢?这画卷般令人心碎的一幕,却早已出现在精灵诡谲的李贺的“龙夜吟”中:
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尽吹横竹。
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从曲中的副词分析崔莺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