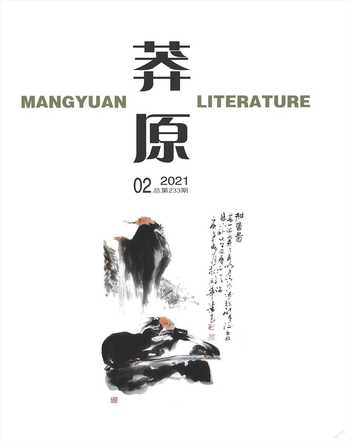在路上
1
站在寓所的落地窗前,女儿指着远处的山脉问我:爸,哪是什么山?
我想了一下说:应该是银山。
女儿查了资料,告诉我是慕田峪。
我怎么会不知道呀,慕田峪,居庸关,八达岭,燕山,白登山,恒山,沿着恒山山脉前行,会遇到翠屏山,三二岭,莲花山,虎头山,二龙山,奶奶庙山;会遇到四十年前的我,坐在奶奶庙山上不断向北凝视。
2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村庄,四周是山,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像一条大蟒蛇,与天上的流云相接,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山了。
小村南北有一条长街,长一里,宽半里,街的两边是各类店铺。我的祖上开马车店,在村南,由大爷继承;父亲在他们四个弟兄中最小,居小村北面,叫“马驿”,传说是南宋时战马休息的地方。
村头有个大庙,稍微改造,就成了学堂。东边与北边是城墙,再往外是树林,河流,大山。河流与小村之间,是石头垒成的大坝,坝里是防护林,我们叫它“大坝林”。林子里有一条石子路,是学生早上跑操的地方。早晨六点半开始跑,七点结束回学校上课。
我不跑,站在路边看别人跑。老师问:臧长风,你怎么不跑步?我说:我没有鞋。没有鞋就不能在石子路上跑步。很快小村就传开了:臧家的孩子因为没有鞋不能跑步。我娘脸红了,让我穿哥哥穿小了的鞋子。可我还是不跑。哥哥穿小了的鞋子,对我来说,还是太大。
但我偷着跑。
教室与城墙之间,有一条用于流水的窄狭甬道,仅有成人身体那么宽。我小,可以通过。城墙上有草,还有用三块砖头垒成的小庙,里面驻着大仙,有人上供,也有人点灯,夜晚会有烛火蹿动。我一个人到小甬道玩,边走边看,慢慢开始跑。仿佛这个小甬道有什么东西挡着我的道路一样,跑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东西在破碎。回到教室,坐在课桌前,心怦怦地跳,像是自己破坏了很多东西,有丝丝快感。
臧长风,你上讲台做题。老师点了我的名字。
我大大方方地走上去,转身,屁股对着同学们,放了个大响屁,又不动声色地走回座位。老师勃然大怒,让我从教室里滚出去。我毅然地走出了教室。
小村东边有座“奶奶庙”山,山上有林子,林子里有鸟,还有野兔和松鼠;林外有田,种着谷子、玉米、黍子、黄豆、土豆之类的杂粮。蝴蝶在土豆地里飞来飞去。我捉住一只蝴蝶,把蚂蚁放在它的翅膀上,再放飞。蝴蝶被蚂蚁咬得飞不动,落下来,我跑过去,看蝴蝶让蚂蚁咬得痛苦不堪,开心地笑。一只金黄色的松鼠偷食时被人打断了腿,我救了它,在树下给它做了一个小窝,每天给它送吃的,给它医腿。我們成了好朋友。它的活动范围就在学校外那块土豆地里,听到我的口哨声,它就会跑来陪我玩,在我身上跳来跳去。冬天来临的时候,小松鼠失踪了,而我,也很快离开了学校。
我上初中时有了一双鞋,而且是跑步鞋。
当时,我正在看一本武侠小说,看完后借给了另一个同学看,那个同学又借给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把书丢了。问我赔钱行不行?我说不行,我也是借别人的书,一定要还书。小村里怎么能买到这本书?女孩儿的娘找到我娘,哭诉开来。我下学后,我娘给了我十块钱,说不要赔书,赔钱。我说不行。我娘说小屁孩儿你还想翻天啊?赔钱就不错了。我后来没把钱给借书的人,自己留下来,只是告诉他书丢了。事实上,那时候人们经常借书,也经常丢书,大家都习惯了。这个事过去后,女孩儿的娘为了表示感谢,就送了我一双运动鞋。娘说这下好了,我孩儿有鞋了,跑步去吧。我说我不跑,这鞋是别人的,不是我的鞋。
我喜欢钻洞。
学校操场是新修的,怕被雨水冲坏,便修了下水洞。每次经过,我总会盯着下水道的洞口看。终于有一天,我偷偷地从洞口钻进去了。洞口很小,只能爬着进去。爬到半途我的身子被卡住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我用尽全身力量往里钻,呼吸越来越困难,在觉得自己快要死的那一刹那,我终于爬了过去——刻骨铭心,却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后来读 《仁王经》,看到“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知道刻在记忆里的是“生灭”。
后来,我跟同学说了这件事。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便决定把洞挖大一些。我没去。他们挖洞的时候,洞塌了,有一个孩子的腿因塌方被压住了,等大人把他弄出来,他的腿已经废掉了。我觉得他是替我被压成残废的,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每次遇到这个坐轮椅的人,都会产生亏欠感。
这种感觉在煤矿下井时也曾有过。一次矿难中死了好多人。那天我有事没有下井,跟一个工友换班,他恰恰就在死难名单中。我看过那次矿难的照片,有的人正举着铁锹清理巷道,有的正依在煤帮上睡觉,各式各样的焦骨,黑色的,轰隆一声,这些黑色的生命就固定在某一个动作中,浑然不觉。面对这些照片,我又有了亏欠之感。
后来读了很多书,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亏欠感觉,我发现很多人有过类似的体验。卡夫卡说:“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门前走过。”佩索阿说:“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高贵的蒙难,不会有日后的复活相随,我能做的就是承受它全部的下贱。”
3
一天夜里,风穿过白蚁蛀食过的窗格子,闯进屋里,屋里许多声响跟着嚷了起来。声音像活泼的生命,到处乱爬,耳朵里有众多的黑的碎的小脚在移动,它们惊慌失措,找不到光和出口。全家人睡在北方的大火炕上,亲人都睡着了,我害怕了,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胡思乱想。那天晚上之后,我对苦役般的学校生活失去了兴趣。
我娘养了很多鸡。娘把鸡蛋收集到桌子上黄色的瓷罐里,攒到一定的数量,然后卖掉,钱用来给我们交学费。我几个哥哥都考上大学离开了小村,在娘的心里,只要罐里的鸡蛋不被吃掉,迟早会换成钱的;而我考上大学也是早晚的事。娘没想到我会从罐里偷了鸡蛋离家出走。
我大哥大学毕业后在煤矿工作,我找他,让他帮我找了一份下井的工作。我从大山深处奔跑到地层深处,没想到地层深处还得跑。在井下工作需要穿棉衣,穿水靴。我脚小,没有适合我穿的水靴,只能穿大水靴。每到下班的时候,大家出井时快步如飞。我个头小,又穿着不合脚的大水靴,只能小跑着拼命跟上,如果跟不上,我就会找不到出井的路。有时候,跑到井口,遇到升井机还没有开动,我们会走着出井——八百米深的台阶,一个一个地爬上去。第一次爬长城时,我就当下了一次井。
我当矿工,是顶了表哥的指标。那个指标本来是他的,可他因为生病,没能参加招工。我在煤矿这十几年,一直用的是我表哥的名字。后来,我大哥又帮表哥办了个招工指标,表哥的名字让我用了,他只好用我的名字。表哥在煤矿上班没多久,便因为与人打架坐了牢。我固执地认为,表哥是替我坐了牢。
在煤矿时,我在大哥的护翼下生活,大哥向我发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拖累了大哥,如果不是我,大哥能做很多大事。没有人告诉过我凭什么要让大哥护翼,我寻不到答案,只能默默忍受他的责骂。我放不下更拿不起来,对大哥和表哥的亏欠感压了我整整三十年,当我能放下之时,他们都老了,我只能陪着他们说说东家长西家短。我终于明白,我内心里所有的亏欠感,源于用别人的生命预测自己的未来。
后来,我不再下井了,在区队打扫卫生,每天像个老人一样,挑水、扫地,服务于各个领导。我很享受这种等待肉身死亡的生活,有大量的时间自由支配。我完成本职工作之后,发发呆,抽抽烟,与一些闲散的人打牌。煤矿是一个更大的农村,却比农村好存活。所以矿区有很多懒惰的人,偷点炭,偷点铁,就能拿去换钱。勤劳的人可以养活很多闲人,吃吃饭,说说闲话,一天就过去了,很舒适。
我忽然意识到,如果再这样生活下去,我亏欠的将是自己的骨肉。
我决定离开煤矿,走进城市。进入城市需要办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在小村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的时候,突然想到为自己重新起个名字,以便重建自己对灵魂的热爱。“长风”这两个字从脑海里跳出来,我为自己选择了将来的生活:自由随性,漂泊万里。
二十年后,歌手王娟唱:“亲人们总是突然/或莫名地离开/他们都不生不死永久生活在大地上/是啊 我已到了/熟悉天空和星辰的年龄……”
我在歌声中放下了所有的亏欠。
4
我一路向北,最终选择了这个城市的北方,安营扎寨,赡养亲人与自己的肉身。他们说北方是故乡。我的儿时记忆没有故乡这个词汇,只是听从内心呼唤而来到北方。
这是一个大到不会同时下雨的城市,有着众多我不认识但熟知的灵魂,自然,自律,坦荡地生活。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经历不同,但拥有相同的儿时记忆。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与我同时来到这个世界的灵魂都是我的亲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生命是孤独的,孤独是灵魂能力缺失的体现。我与肉身相伴,用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城市,降低欲望,尊重万物生灵。我如鱼在水,如同花蕊藏在花瓣中。我居住在一個古代建筑的大院子里,周围有美术馆,有书店,这些都是我欢愉途中的最美风景。
女儿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老师,居住在城市中心,执意要我把工作室搬过去,以方便照顾。不忍拂了她一片孝心,便答应了。
搬家公司来了两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俩看了我工作室里的东西,一直说东西太多了,车上装不下的。我笑着说,那怎么办啊?要不,咱们分成两车来装吧。年轻人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哈哈大笑,说我们都是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赚钱的人,你俩好好搬,价钱可以根据表现来定。年轻人开始搬东西,老人却还与我讲装不下的理由。我指着他笑说,你让这个城市教坏了。
他们开始搬东西。我问朋友,如果我们到了六十岁,还能不能像他这样把东西搬到车上?朋友笑着说,现在我们都搬不动了。
出发时。老人让我自己开车或者打车,不能坐他的车。我硬是与他们挤到了一起,又笑着说,你真的是让这个城市教坏了。老人的脸红了,说,如果真变坏了,今天就真的一车装不下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城市,比煤矿还容易存活。初到这个城市时,我曾经计算过,只要这个城市里的每个饭店给我三天的打工机会,我终其一生也有干不完的活儿。
车到目的地后,年轻人认可了我这个农村人,理直气壮地指挥我干活儿,当然,都是些轻松的活儿,说,这个城市让你变老了!
好像女儿也觉得我老了,会和我讨论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我从来都是顺从她的意愿,我觉得只要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所有的生活都是美好的。直到女儿非要让我到医院做个全面体检,我才知道她与我交流养生的目的。我不愿意排队,她替我排队;我不想与医生交流,她替我与医生交流……折腾了很久,才做完了各种各样的检查。
医院真是给人希望、也让人绝望的地方。众多平日充满尊严的肉身让医生呼来喝去,摆来摆去,不由让人对“生命”这两个字产生怀疑。我很认真地对女儿说:如果有一天爸爸需要上手术台,一定要征求我的同意才可以。女儿问,如果你说不出话呢?我说,说不出话我就会将氧气管拔掉,你不要阻挡我。女儿问,如果你连拔管子的力量也没有怎么办?我傲然一笑:怎么会!
体检的各种指标出来之后,粉碎了我所有的骄傲。我问医生,我的身体一点也没感到不舒服,能不能不吃降脂药?医生说,如果身体有反应才吃药就迟了。我问医生怎么办?难道要一直吃药吗?医生说:跑步去。
又是跑。在乡下我赤脚在山上跑,进矿区我穿着大水靴在井下跑,然后,一路向北,跑到城市,本以为可以停下歇歇脚了,可还要跑。人生好像是一场永无终点的奔跑。
女儿买了个电子秤,让我每天跑完步称一下。我对女儿说,不用担心,肯定会瘦下来的,爸爸小时候就是个瘦子,现在胖是因为太懒了。女儿又问:爷爷胖吗?我愣了一下:他怎么会胖,瘦得像个竹竿儿。
此后,看到我去跑步,女儿总会说:老臧,拔管子去啊!我回答:嗯哪。
跑步的路上,我遇到过把自行车放在路边放声大哭的女人;遇到过送快递的恋人在奥体公园前相拥着,久久不愿分开;遇到过在雨夜里为老人递一把雨伞的少年;遇到过摔在路边的中年人,看到我询问的眼神,挥挥手,让我继续前行。
我将跑步的指标定在三公里与五公里之间。心情好,时间足,就跑五公里;没心情就跑三公里,很快就变得轻松起来。有一次跑完步在家里拉腿,女儿看到了,说:哎呀,老臧,你都有腰了,我梦寐以求的腰啊!我回答:嗯哪。
在跑步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香道。我的嗅觉很好,小时候,每到中秋节,娘总会买一些苦涩的小果子供奉月神。这种小果子还不太熟,需要放到冬天才变得好吃。三哥将小果子藏了起来,等冬天拿出来享用。三哥藏的小果子总会让我找到。三哥想不明白我是怎么找到的,长大后问我,我说是嗅着气味找到的。
我用崖柏制香。在我记忆里一直有一款香的味道,但我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味道。我采摘各种儿时记忆中的野花,带回来,铺一层野花,放一层崖柏,密封后开始蒸,我不断地调试,以为这样香料便能散发出记忆中的味道,可是不管我怎么做,还是找不到那个味道。某天夜里,跑步穿过树林的时候,突然就嗅到那个味道,才明白自己一直想调的是“草木香”。
不知不觉中,欲望侵袭灵魂,竟然让我忘了草木的味道,忘记了家乡。
5
在一个阴天的早晨,我没去跑步,骑自行车穿过六环,我看到了众多涌向地铁的人,仿佛与初到城市的自己相遇。一路向北,我来到了经常凝望的大山前面。
在穿过小镇集市时,遇到了大雨,我在公交候车厅下避雨,看到从集市里出来一个小老头儿,戴了一顶草帽,拖着拐杖,冒雨前行。雨停后,我继续朝前骑行,在前面的镇子里遇到第二场雨,只好到小卖铺屋檐下继续避雨,却看到那位老人依然在雨中前行,不同的是丢了拐杖,将草帽拿在手里。大雨滂沱,老人蹒跚而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避避雨再走,小镇的人可能对这个老人的倔强司空见惯,或者老人是外来的居民,大家都没有劝说什么。
我冒雨而行,到了大山下面的小村庄。这个村子叫桃林村,是我刚来时的住所。我走到317号院,打开锈迹斑驳的大门。
荒芜的小院里有一架葡萄,一棵蓝莓树,一棵柿子树,还有一棵香椿树,无数的荒草侵占了院子。我简单将院子收拾了一下,拉了把椅子,坐在门口听雨。恍恍惚惚看到父亲从田间归来,抚摸我的头,说:这个城市让你瘦成这样了啊,你是不是没有钱吃饭了?父亲掏出一沓钱,非要給我。我对父亲说:没事啊,臧衡现在当老师,每个月赚好多钱,你管好自己就行了。父亲叹息了一声,硬是把钱放在我手上,转身离去。我伸手想拉住他,却没能拉住,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雨中。
臧衡是我女儿的名字。我守着自己的女儿,却忘了自己的父亲。
此后不久,父亲便打电话让我回家,说我大爷殁了。
我大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识字,会画画儿,会唱曲儿,还会制作独门的“金创药”,药里有一味特殊的石头,我们叫它“刀解药”。这味药最大的功效是止血。
有一年冬天,三表姐盖新房子,我跟着大人在小村的河边上捡石头。河床结了冰,白茫茫一大片,大大小小的石头,有深褐色,有青蓝的,也有白色的,从高处望去,像卧在河滩的羊群。大人拉着平板车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推车。上坡的时候,有石头从车上滚下来,把我的手夹在石头与车厢中间,食指与中指上的皮全部脱下来。冬天,冷,血冻凝了,不流动,也不痛,我只记得红红的两个指头,没有了白的皮。洒“刀解药”的时候,开始流血,也开始痛,我裂开了嘴,准备哭,大爷把几颗果子递到我手上,说,别哭,给你好吃的。大爷家有一棵树,很大的树,结着小小的果子,红彤彤的,刚熟时有点酸,有点涩,冻了后才会甜,人们秋天采摘贮存下来,到冬天吃。
祖上的车马店由大爷继承,本来是不错的一份家业,可他沾上了鸦片,好好的一个家开始衰败。吸了鸦片,大爷的情绪很不稳定,怕自己的儿女抛弃他,总是骂人。我说大爷你别怕,我长大会养活你的,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大爷很开心,抚摸我的头,给我看“小人书”,还给我吃那棵大树结的小红果子。大爷的家离学校不远,他估摸我差不多下学的时间,就把冻果子放在炕与灶连接的地方,那地儿热乎,等我到了大爷家,果子就消冻了,正好吃。吃着果子,大爷还教我背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指着远处的大山,跟我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爷活了八十多岁,得了病,卧床不起,自己给自己配了点药,吃了就死了。听娘说,大爷吃药的时候,还劝大娘也吃。大娘不吃,还想活。大爷说:那你可要受罪哩。后来,大娘患了骨癌,不吃不喝,生生把自己饿死了。她的儿女们劝她吃点东西,她说吃了东西死后身体会发臭,拖累你们。
然后,是我父亲。父亲死得很干脆。如果不是我目睹了整个过程,会怀疑他是主动赴死。
那个早晨,父亲准备起床后到后山的田地干活,刚坐起来,就倒了,再也没有坐起。我们回去后,父亲望着我与大哥,连流泪也不会了,只是发呆。把父亲抬到车上,送往市医院。折腾了半夜,医生说没事了,我们才放下心来。我想把父亲的胡子刮了,父亲太瘦了,脸颊枯,胡子长,刮胡刀根本就刮不住,我是用剪刀把胡子剪断的。手术之后,医生说是脑出血,死不了,但也不会下床了。
父亲一直不能说话,总用手在空中抓,嘴里嗯嗯呀呀的,俯下耳听,好像是想抽烟。我故意对妹说:咱爹想打牌了,把麻将取来。妹真的取来麻将牌,对父亲说:您现在不能打牌了,摸一摸,过过瘾。父亲不要,手还在空中抓。我就问:您想做啥?父亲把手放在嘴上比画,妹也看出他想抽烟,说:医院不让抽烟,您摸摸麻将牌吧。父亲生气了,接过麻将,扬手,把牌扔在地上。妹说,病了,还这么大的火气啊。
父亲本来都可以说话了,问妹,你孩子谁管?妹说,他爸。又对我说:你回去上班吧,别误了公家的事。我便回家收拾好东西,准备第二天返回京城。没想到我前脚到家,姐夫后脚就到了,他跟我说爹没事了。我长出了口气,又问我姐姐呢?姐夫看了我一眼,说,爹没事了,你还没明白?我这才猛然想起,在我们家乡,“没事了”的意思就是死了。我的脸霎时变得很白,像张白纸。有风穿过阴阴的小屋,透骨冰凉。我低了头,匆匆向医院走去。
我在住院处三层的楼梯上遇到了姐姐和妹妹,她们俩手里拿着父亲住院的洗涮用具,正走下楼来。她们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她们,就那样对视了一下,她们就开始哭。我不理她们,跑到病房。父亲一个人躺在床上,医生正在收拾床头上的医用物件。我坐在父亲身边,抚摸他的脸庞,那么白,他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么白的皮肤。
父亲因为高烧引起别的病,一口气堵住憋死了。他不想拖累孩子,死得干干净净。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死人不让进村。我们将父亲伪装成没有去世的样子,带着输液的全套药具上路了。大哥把父亲抱到车后座上,我与妹妹坐在父亲两边,大哥坐在车的前端,车开出城市后,大哥把一串用麻纸做成的纸钱扔出车外,说,爹,跟着您的儿子回家吧。
途中,妹妹说,哥,怎么爹的身子老往我这边靠,压得不行。妹说一次我就紧抱一下父亲。妹说的次数多了,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去探父亲的怀,一手冰凉。我对大哥说,咱爹变硬了。大哥说,不能硬,硬了就穿不上老衣了。哥让妹坐到前面,他与我一起抱起父亲,让父亲躺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父亲的全身抚摸着,用我们的身体温暖着他的身子。我摆动着父亲的胳膊,说,动一下,你动一下,这就到家了……我们把父亲放到炕上的时候,可能是一直憋屈着身子,死去很久的父亲竟然长出了一口气。大哥一下坐在地上,痛哭,说爹回了家才把最后一口气咽下去,他不想死在外边。
村里人对死亡很看重,仪式非常隆重。人去世后,要根据生辰八字与死亡时间,计算在家里停多少时间,有的是三天,有的是七天,还有九天的,这段时间灵魂还会与肉身在一起,之后会慢慢离去;打墓,入棺,报丧,办丧事等,都有一系列的仪式;死者入坟的前一天,要沿街烧纸上香,办丧队伍有乐器,吹吹打打地上街,孝子们随在其后。
我父亲死得干干净净,谁也不欠,谁也不拖累。所以,父亲的葬礼一切从简。大哥站在坟头,我站在坟尾,将父亲埋在了黄土里。
有时候想想,人生就是一双鞋,该走的路走完了,这双鞋也就磨烂了——像 《仁王经》里的禅释——“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
责任编辑 吴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