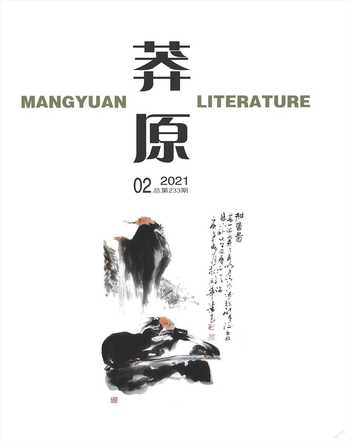一次“心灵的压模”
菡萏
写 《安》 时,疫情的阴霾已经散去,时间进入炎热夏季。所以这篇小说不是趁热打铁的抗疫题材创作,而是安这个人物,在疫情大背景下的一段生活——更重要的,她是一个失语者。
安并非凭空杜撰的人物,而是有其生活原型,她是个画家,身为聋哑人,取得的成绩比常人要辉煌。然而,此非重点,在小说里,我想表现的,是安的人生态度,她所散发的女性魅力——她的艺术气质、动手能力,对女儿的爱,对老人的眷顾,对学生的牵挂,对老师的哀悼,对生命的执着坚韧——是她面临重大变故时的从容镇定与善良宽容。她默不作声,只有诚挚的表情和绵密的行动,似哈莫修伊的画,低头缝纫或临窗而立,安静的黑白基调,流淌白色忧伤,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却能窥见其内心的高贵坚韧和温婉贤淑。在写安这个人物时,我的耳边一直萦绕着 《法兰西组曲》,战地黄花迎风摇曳。
疫情期间,我不时接到安的原型发来的图片:喂小猫吃饭,于金灿灿的阳光下给小猫剪指甲;夜深人静时,独自在灯下用玻璃瓶子擀饺子皮,用精致的小秤一克一克称佐料,烤鸡、烤饼干、做烧麦、包包子;给母亲煮中药水泡脚,用电动理发工具为父亲剃头;给女儿做西餐,摆水果拼盘;为学生录视频,用手语讲解防护知识;把切剩下的萝卜根,放在水盆里,种成萝卜花……等等。那时,她处在武汉重灾区,楼上楼下都有感染者,但她热爱生活,无所不能。她冒雨去为建方舱医院腾桌椅那天,留言说,终于可以为疫情做点事了。她对人世的爱,深沉厚重,又云淡风轻,不是岁月静好,而是笑对生活。
我之所以写这个人物,决非刻意,而是放不下。
给主人公起名“安”,有平安、安静之意。她从小就是个安静的孩子,给洋娃娃裁剪缝制衣服,独自去聋哑学校上学,与常人一起高考,一同坐在高等学府“听课”;她在国内外拿奖,无丝毫炫耀,只羞涩一笑;她生活朴素,骑踏板车上班,却听不到后面的喇叭声……她所克服的困难常人无法想象,她的苦,自知而无声。
安这个形象,一旦从原型剥离,便不再是她,而是我的附魂体。我借安的一双眼睛在各种环境里游走,为其骨骼添上血肉、脉络,为其动作配上“语言”、心理,让其丰满立体鲜活生动。我就是安,安就是我。所以很多場景是互融的,比如安用的绿檀发簪,安做饭时忙碌的身影,把菜叶子、果皮、蛋壳、骨头,放在渣滓机里绞碎冲走,洗碗用烂的海绵,扔进垃圾桶,又捡起,用洗洁精搓净再用,以及安和丈夫有关登山的对话,许许多多都是我虚构的,且有意注入主体意识和我对生活的理解。写的是安,更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安”是我们共同营造的胚胎,是故事真实与我思想真实的一次嫁接。小说不能完全用虚构定义,思想的真实更为真实,是作者崇敬美的一次“心灵压模”。借别人素材,抒自我之情感。
很多细节,我都有精心的设计。比如疫情期间的那场肃穆的大雪,山河一片白,城市却无行人。冰箱告急后,安瞅着窗外,勾起几十年前失聪后,父亲带她求医的雪天回忆。所不同的,那次是个体的苦难,这次是全体的灾难。怎样形容窗外的雪?晶莹、洁白这样的字眼肯定不够,故借用蹲在窗台的小米的双眼,大雪像细碎的纸花。雪非雪,是纸花,比冷更可怕的是死亡,亦是上天对亡灵的哀悼。
安的女儿有音乐天赋,安却听不见,所以安的女儿叫音子,表达一家人对声音的渴望;女儿养了两条小蛇,她不怕蛇是因为孤独惯了,人活着就是在对抗孤独;疫情期间,蛇也在冬眠,疫情结束,蛇也开始了新生。小说不是胡编乱造,也非个人梦呓,需有生活的根性,有内在逻辑。
父亲没烟了,这个信息是小猫传递的。此处,我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省了许多笔墨。真实的情况是父亲的烟,眼看着一包包没了,不得不限制一天只抽六根,直至两根,且有意留存烟蒂。“断粮”后,坐在月夜的暗影里,偷偷剥出烟丝,卷着抽。安发现后,千方百计通过志愿者买回两条烟,默默放在父亲的案旁。小说里,这种生活中的细小感动,在父亲临走时留给安的信里,一笔带过。父女之情,一目了然。
《安》 既是中国女性的缩影,也是两代文化人疫情中的生活写照。一根线上,用了穿插、回忆、倒叙的手法,使其丰满。父亲疫情期间创作的几幅画,《升腾空间》《春天》《窗外》《黄鹤归来》《葬花吟》《地平线的光》等,是艺术化的疫情曲线图。他们不是医护人员,也不是志愿者,却坚守着日常,坚守着希望,坚守着热爱生活的一扇窗口。
解封那天凌晨,安和女儿登上50层楼顶,璀璨的夜幕下,一条条车河在流动。女儿可以跑,可以欢呼;安张了张嘴,却泪流满面。为解封,更为卸下心头重任——女儿可以正常高考了,也不用再担心父母断药而突发疾病,多种滋味交织。她所有的坚强,都是那么脆弱,却又不得不坚强。
一个朋友发微信朋友圈,说同样的日光,他手机拍的照片,他夫人却拍不出来。因为他的镜头上有一滴水,所以能产生纵横迷离的光线。其实,疫情就是我们镜头上的一滴泪,有逝者之痛,也有阳光灿烂的折射。
谢谢朋友无意间给了《莽原》 的邮箱,谢谢 《莽原》 给予一个普通写作者以光亮、厚爱与鼓励!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