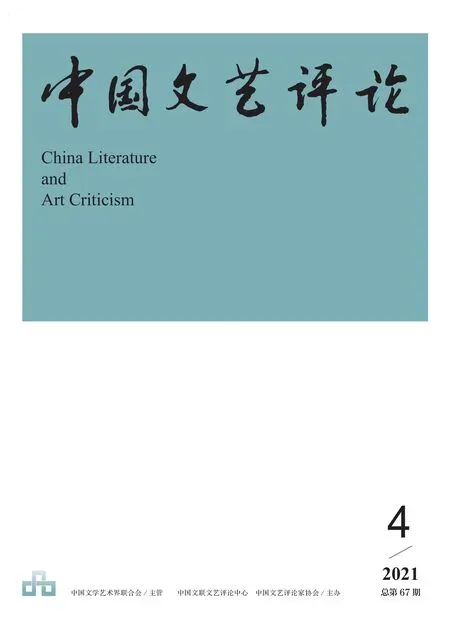说书人的艺术与哲学
——访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
采访人:张鑫

田连元简介:
评书表演艺术家,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艺术委员会原主任。1941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2012年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2019年获中广联“70年70人•杰出演播艺术家”荣誉称号,曾获首届国家人事部、国家文化部联合授予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奖,曾获“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一等奖等。代表作品有《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一、艺术人生:说好人间正道是沧桑
张鑫(以下简称“张”):
2020年12月12日是您的80寿辰,本溪市专门制作了“艺无止境学无尽时”短片,概括性地介绍了您从艺的历程。您6岁学艺,7岁登台,14岁从艺,17岁养家糊口,20岁进团,23岁当团长,从艺65年,不仅说书,还弹过三弦,唱过京剧,演过话剧,说过相声,当过导演,做过主持人。您能否描述一下自己的人生轨迹,特别是人生中值得铭记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里程碑式的事件?田连元(以下简称“田”):
我们家是三辈儿说书。爷爷说书,父亲说书,到我这儿也说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就是说书人的命,走的也是说书人的运。过去的经历证明,我这辈子注定干这个,这就是命;我说书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直到今天的新时代,说书的运伴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发展。我最开始说书的那段时间,困惑过、迷茫过、犹豫过,但从小的种种经历无形中给我走上说书的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我7岁上台唱小段儿,这是我第一次登台表演赚了钱。新中国成立后,我上了小学,成绩名列前茅,梦想考大学,不想干这个了(说书),但生活所迫,父亲逼着我干这个,于是14岁辍学学艺从艺。实际上我9岁拜师,跟着师父和父亲学,17岁那年在津南小站镇徐记书场正式说长书,然而“登台即告失败”,一场书下来,“盛况”也就十五六位听,最少时三四位。我灰心丧气,中途想改行,尝试着学速记、考中国戏曲学院、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弹弦。由于种种无法克服的原因,最终都没有办法实现。我无路可走,只能说书。这段时间,成败起伏,从天津小站到杨柳青,到胜芳镇再到静海县,有点起色后又不行了。
应该说,我走上说书的道路,充满了很多必然的因素。我小时候在天津,特别是住在南市东兴大街蕙联公寓的两年时间里,受到了艺术的感染和熏陶。辍学后,我经常到旧书摊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虎啸龙吟》……许多书都看。旧书摊成为我的自学书院,海量看书开阔了我的眼界;我看了很多天津京剧名家厉慧良、张世麟、小盛春、赵松樵的戏,和同楼住的京剧学员们一起练功;我向拳师李寿山学习形意拳,有幸还和武术名师岳家麟学习了套路,这为以后说书中形体协调和解说武艺提供了方便;东兴大街书场密集,名家荟萃,有陈士和、张健声、张立川、刘建英、张连仲、张起荣、郝艳霞、赵田亮、顾存德等,我经常听他们说的《聊斋》《三侠剑》《大五义》《岳飞传》《杨家将》《英雄谱》等,这是一个受熏陶的经历。经历了失败的演出后,我开始琢磨这些名角是怎么说书的,如何能说得更引人入胜,准备着新的舞台尝试。1959年我来到了济南,济南也是曲艺窝子,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名家和观众的认可。
在济南说书算是扎下了脚跟,好事总是连连。1960年,本溪曲艺团来招人,我从一名江湖说书的艺人,成为了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这段时期,我开始说新书,凭借几部作品,逐渐说出了名气。还记得刚到曲艺团时,团里不让我说书,而是让我给团里的台柱子刘彩琴弹弦伴奏,不过,这也让我收获了爱情。但我决心还是要说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曲艺团有场去彩屯书场说书的安排,没人去得了,于是我自告奋勇,一个人去,一下子火了起来,观众座无虚席。就这样,我在彩屯说了一年的书,为团里挣了不少钱,顺理成章地做了评书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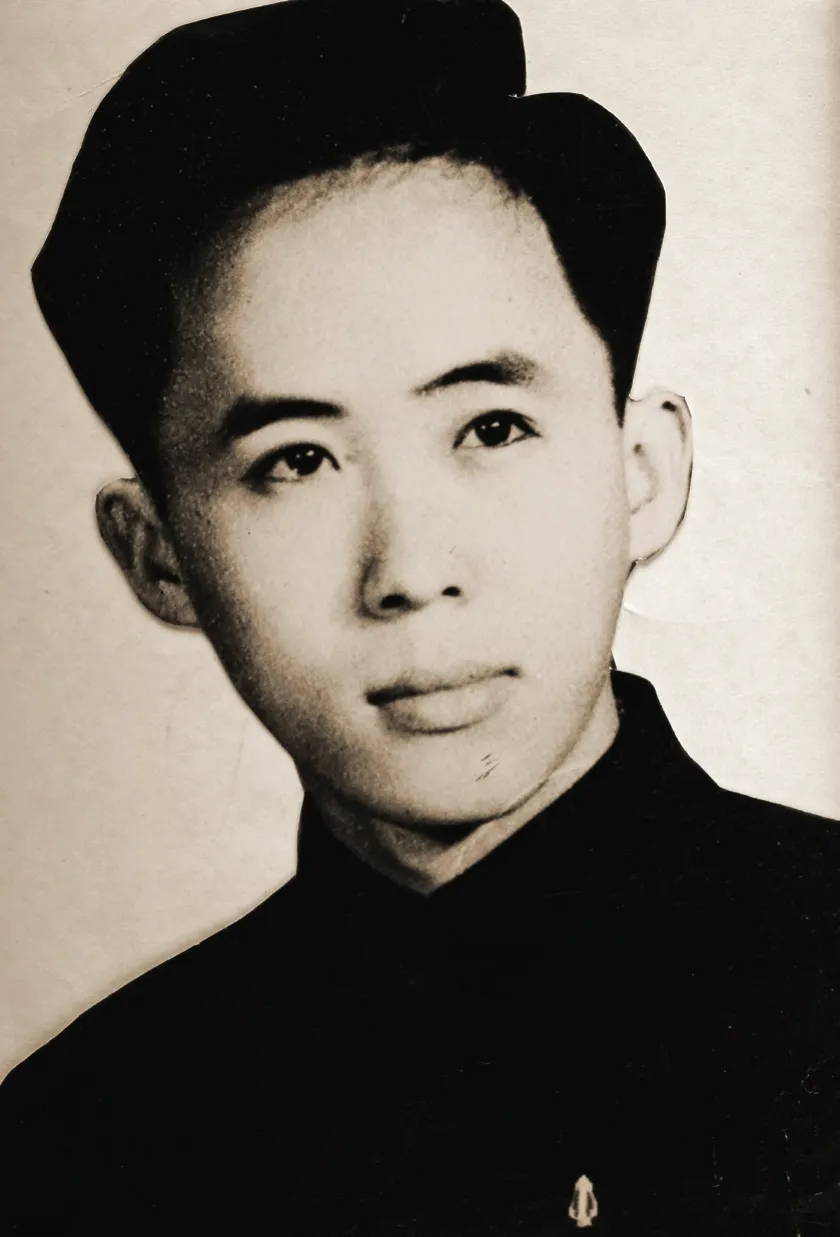
图1 21岁结婚后的田连元
1962年初,全国文艺界掀起了“说新、唱新、演新”的新高潮,提出要“厚今薄古”,不能抱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放,而是要讴歌革命斗争历史和英雄。这对说惯了传统书的老艺人们来说,无异于一场革命。不过辽宁省当时已经有了说新书的旗帜性人物——袁阔成、杨田荣、陈青远。杨田荣的《铁道游击队》、袁阔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全国家喻户晓。为了全面推动“说新书,说好书”活动的开展,时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主席王铁夫主持召开了现场交流会,各市曲艺团选派代表参加。我代表本溪曲艺团参加,这也是我第一次与辽宁省名家“大蔓儿”同台演出。这次演出,王铁夫对我非常认可,与我说了很多影响我一生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鞭策与鼓励。1963年,全国文艺界全面展开说新唱新,传统书不让说了,所有演员都得说新书,为此辽宁省特地举办说新唱新座谈会,做了一次汇报演出。我演了一段《虎穴锄奸》。演出后,袁阔成先生给我谈了说新书的感悟,他说:“如果一句不落地背下来就废啦,但也不能全趟着使”;陈清远对我说:“现在这个年龄能说成这样儿,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要再过20年,还这样,就不是凤毛麟角了。”名家的肯定增加了我说好新书的信心,也告诫我要不断地提高。
1965年,辽宁省搞了一次全省范围的说新唱新曲艺大会演,我创作了一篇评书《追车回电》,意思是追赶着列车往回打电话。当时正是学雷锋的高潮时期,这部作品恰恰反映了铁路职工学雷锋的先进事迹,演出非常成功,观众掌声不断,笑声一片。《追车回电》一炮打响,很多报社、杂志社纷纷采访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了这个作品。自此,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评书演员田连元了。于是1966年3月,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录长篇广播评书《欧阳海之歌》,这是陈毅元帅评价很高的一部小说。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邀请我录制《欧阳海之歌》《渔岛怒潮》两部书。辽宁台录制的《欧阳海之歌》播出后,反响非常之好;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制,更令我向往。
然而,这一切成为了泡影。1966年5月16日,还没等我去北京录评书,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我那时已经担任曲艺团业务团长三年了。我这个“当权派”首当其冲地被贴了大字报,还好我历史出身没有问题,只是被罢了官。而且,“文艺八条”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准参加任何的文艺活动。于是,我就下乡了,上山砍树,下田插秧,当了农民。在我以为我的艺术生命就此终结时,县里要排样板戏,没有合适的人选,找到了我,让我出演《沙家浜》,学习《杜鹃山》,我的从艺之路因此没有戛然而止。有了这个经历,我逐渐恢复了舞台演出。1973年辽宁省东片文艺会演,我创作表演了评书《新的采访》,又返了小段《没演完的戏》,取得了成功。之后,顺利地回归了本溪市,到歌舞团工作。

图2 1974年田连元演出剧照
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了,文艺界迎来了春天,大家重新振作、鼓足干劲为艺术拼搏奋斗。1981年,文化部组织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我创作的《梁上君子》获得了一等奖。此后,我被文化部抽调参加全国巡回演出。在这支巡回演出队伍里,有河南大调曲子演员胡印荣、绍兴莲花落演员胡兆海、扬州评话演员惠兆龙、湖北小曲演员何忠华、相声演员师胜杰、苏文茂,等等。这次巡演历时三个多月,走了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足迹一千多公里。我到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当地的曲艺名家,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也与这些当时全国曲艺界的名家新秀切磋技艺,交上了朋友。改革开放后,思想逐渐解放,被埋没的、停止的传统艺术复苏了。这种形势下,本溪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录制一部传统长篇评书,我就想到了《杨家将》。书播出后,反响热烈,掀起了本溪市听传统书的高潮。这当中,我把《杨家将》说到了体育馆,五千多人坐得满满的。在体育馆说长书,我这儿是首创。随着广播版《杨家将》的成功,1986年,辽宁省电视台正好想把评书搬到电视上,于是找到我录制电视版评书《杨家将》。我据理力争评书栏目至少20分钟,否则无法演出。这就是电视评书比广播评书少10分钟的最初原因。我决心在20分钟的时间内让电视评书与广播评书有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电视里面不但要听,而且要看。这就要求有丰富准确的面部表情、和谐合理的形体动作,注重语言的节奏感、形象性和生动性。为了录好《杨家将》,我每天到公园里过一遍。就这样,电视评书《杨家将》一经播出,特别是在首都北京播出后,让我在全国家喻户晓。从此以后,我走上了中央电视台,多次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乃至后来还到首都体育场演出,和当时最火的《西游记》剧组一起巡演。到了1990年,中央电视台打算改版一个曲艺杂技类的综艺性节目,找到了我。这个节目就是《曲苑杂坛》,由我和汪文华主持。《曲苑杂坛》播出后,马上引起全国十分强烈的反响。我参与了整个栏目的创设、策划和撰稿。《曲苑杂坛》成为中央电视台保留时间最长的文艺栏目,收视率超高。后来,我又主持过辽宁台的《共度好时光》、中央台的《综艺大观》。如果说电视评书《杨家将》是首开电视评书之先河,是一部开山之作,那么后来的电视评书《水浒人物传》就是升华之作了。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我录制的《水浒人物传》,反响非常好。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央电视台筹备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时,聘请我担任了顾问。现在,我还在不停地写新书、说新书,主要写革命英雄和道德模范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希望传递给人们更多的精神力量。

图3 田连元为中央电视台录制长篇评书《水浒人物传》
回顾从艺这些年,我曾经不愿意说书,命运又逼着我说书,当我愿意说书了,又不让我说书,后来我能说书了,又让我改行种地不让说书,结果最后不仅能说书,而且说得家喻户晓,就这样走到了今天我还在说书。
张:
社会上有“评书四大家”之说,您位列其中。在您成长为评书大家的艺术道路上,有什么人对您影响至深?田:
我觉得,大家也好,大师也罢,都不如说我是说书人。这样既不卑也不亢。因为诗人、商人,还有现在的达人,这不都是人吗?说书人这个词比较中性,也比较准确,而且真正达到是个人的标准,也很不容易了。在我这个说书人的人生道路上,按照时间顺序,有这样几个人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第一个是范云。范云是我青年时期的良师益友。他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多才多艺,带眼儿的会吹,带弦儿的会拉,唱歌唱得也好。他曾教给我三弦独奏曲,比如《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他跟我讲,他在音乐学院的老师的三弦儿“铲头”是象牙雕花的、指甲是天鹅翅骨做成的。他说三弦这个乐器,在乐队里边谁也压不住它。范云让年轻的我有了一种不自卑的感觉。范云的父亲被定了“历史反革命”,但范云很乐观豁达,他创作音乐和曲艺作品,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就干脆署别人的名字,只要能发表就行。他不论人生道路多么坎坷,始终在拼搏奋斗,他一身艺术细胞,最后不搞文艺了,去自学了法律,专门帮助老百姓打官司,还成为了中国民事调解十大律师。他曾和我说过,“就想做一个大写的人”。在青年时期,我遇到范云这个人,从他身上悟出了很多道理。像范云一样,还有几个人,在我青年时期遇到了挫折时,是他们的三言两语,让我坚持了说书。在天津胜芳书场,老板吴庆山鼓励我,“观众少不光因为你的原因,白天人家都去干活了呀,眼下又是‘大跃进’,又大炼钢铁,谁有工夫来听书啊!来十个八个的就不错了!你说吧,我看将来你能出来,你要成了大角儿,别忘了在我这庆山茶馆练过买卖,到时候我请你你可得来。”还有在济南说书时,偶然的机会,我替了给当时济南最火的说书名家张立武演早场的张太清先生说了两天《呼延庆打擂》,由于中场是张立武先生接场,他早早就来了,在外头听我说了两天。后来,他徒弟告诉我,张立武先生说我“将来再发展发展,能出息个角儿”。他们的鼓励和温暖的话,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我坚定了说书的信心。
第二个就是我到了本溪曲艺团后遇到的王铁夫先生。王铁夫是老革命,曾被列为“延安八怪”之一,对曲艺和戏曲非常有研究。在1962年“说新书,说好书”现场交流工作会议上,王铁夫把我叫到面前,和我说了一番我意想不到的话。他说,“匠人,就是会了一门艺术,也很熟练,不断地重复着去演,去再现,去挣钱、发财、娶媳妇,吃好的,穿好的……艺术家是对一门艺术不单单驾驭了它,还要不断地出新出奇,不断地突破新的高度,一辈子也不满足、不满意”,还说:“艺术就像是跳高,大家都能跳过去的高度是一般的艺术,少数人才能跳过去的则是较高的艺术,只有你一个人跳得过去的,那就是独具个人风格的艺术”。他还给我列了一个书单让我读书,嘱咐我这些书要认真读、做笔记,说书要借鉴其他门类的艺术,要做到无所不学、无所不看,工夫在书外,思考在书内。王铁夫还说,“你今年二十多岁,等到四十多岁时艺术上也成熟了,要走出去,走遍全国拜访名家,交流技艺,开阔眼界,当你五十多岁的时候,回到家里闭门著书,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整理自己的艺术作品,著书立说,要成大说书家”。王铁夫一席话,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遥不可及,但后来想,艺术创作就是要不断地给自己出难题,我的人生轨迹真像他算定似的,都是金玉良言,让我终生受用。
张:
您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评书表演艺术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田:
首先要做一名合格的人。我25岁说了《欧阳海之歌》,在本溪有了名气。我45岁说了《杨家将》,在全国火了。当有了知名度后,确实有很多人喜欢你,把你当作明星。但我始终认为,人必须有定力、有定性。人生旅途得有刹车闸,像汽车一样,既要有速度,也得有闸。没有闸的人,怎么能不出事故?所以,你得想到做的结果会怎么着。不想结果,那怎么能行呢?尤其搞表演艺术的人,你在台上和屏幕上让人看,你得要耐看,禁得住别人看。这个人怎么样,身后怎么回事儿,没什么问题,这才行。但定力、定性需要好好修炼。如果是人心向上,往上走路的话,你要费力费时,还要勤于思考,越走越高,越高越亮,终能达到一种至高境界,这就是“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的境界,这样才可以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才可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想,舞台可兼容天下之事,演员当做有益人民之人。再者,成为一个合格的说书人,还需具备比较全面的从艺条件。概括起来就是说、演、评、博。然而,这四个要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
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天生就是说书的。同样一件事儿,到这个人嘴里边,就说得生动爱听,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还挺幽默,挺逗乐儿。这就具备了这种表述的能力。“说”,就是讲故事的叙述能力。
“演”就是表演,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得要有形体动作。你的胳膊腿儿,动作的协调,得有个基本功。经过训练,才能把自个儿规范化了。京剧是程式化表演,这是中国的一种表演体系。程式化是因为它一切都是规范好的,比如文武场、锣鼓经、京胡、二胡、琵琶、小三弦都有用场。而评书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就因为演员得动起来才行。评书艺术不见得都像京剧,在服装道具、化妆脸谱方面有讲究,但评书也有形体,也得要锻炼。
“评”就是评论。评书无评,如目无睛。评论基础是什么?是文化。说书人要有作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想,没有思想,你说出的和别人得出的结果都一样,那有什么意思?人家把说书人称作说书先生,就得有先生之处。举个例子,施耐庵写《水浒》,有很多东西没有写明白。因为《水浒》最初是说书人说出来的,那时叫做《大宋宣和遗事》。其中,有个人物叫孙二娘,绰号“母夜叉”。这个就没有交代清楚。按理说,一个女的,起个外号应该起漂亮的,为什么起个外号叫母夜叉呢?这里边儿就有一个孙二娘外传。因为她爸爸是绿林中人,外号叫山夜叉。她还有个姐姐,叫做孙大娘(《水浒传》都没说)。还有个人物,神机军师朱武,但著作里没有表现出神机妙算。于是我加了一个朱武审鸡的桥段,把朱武的人物性格给丰富了。
“博”就是修养和素质。人类发展到今天,知识浩如烟海。哪位也别说全知全懂。所以,大家都称评书演员为先生,实际上他是一辈子的学生。说书人要终生学习,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事儿,永远在学,永远在跟随着社会的发展、跟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展、跟随着自己的追求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
最后,用个打油诗概括一下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说书人吧。“难时不会会更难, 恰似登高又攀岩, 寻常只须绕山转, 临顶却要汗洒干。”
二、学术人生:构建评书表演理论体系
张:
您担任过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教师,四进北京大学办讲座,2004年后又在辽宁科技大学曲艺系专职授课。您对评书理论建设有哪些思考?田:
改革开放后,我出任本溪歌舞团业务团长,要负责团里大型演出,还得担任导演。那时候,上海有个滑稽戏《酸甜苦辣》非常火,团里安排我去上海学习这个节目,把它移植成北方的相声剧演出。这个事情我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按照剧情内容、人物的个性区别、人物规定情境的对话情绪,重新设计包袱和编排。所以,我当了导演,就得学习戏剧的表演方式。于是,我认真地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通过学习比较,结合表演实践,我感受到评书艺术作为古老的传统艺术,一定是有表演体系的,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表演体系。我们知道,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了公孙大娘的启发,在他书法里,人们能看出舞剑的感觉。这就叫做功夫在诗外。我们搞曲艺也不能囿于界内。对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理论,反过来审示我们的评书艺术,它既是简单的艺术,也是深奥的艺术,关键就在于你怎么把它深入进去,一人多角你怎么把它演好。这里边儿的要求太多了。我接触过比较多的表演艺术种类,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属性,这就是表演给观众看。这里就存在观众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就是观众接受心理学。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观众,他们的接受心态是不一样的。当年说新唱新,观众就认为做清新的演员好。话又说回来了,艺术道路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随着时代走。改革开放让人们都乐了,现在老百姓不乐的不爱看。观众接受心理学需要我们一线的演员好好地研究。

图4 在北京大学给大山讲如何说书
另一方面,我到大学讲座和授课也是一个因素。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请我到北大讲课,我先后去了四回。那时候,中央电视台《评书联播》节目停了。我心里就问,是不是评书艺术不行了?是不是观众不认同了?我需要找到答案。我觉得,一门艺术本身行不行,决定于青年。而北大的青年最有代表性。因此,我决定到北大说书和讲课。我在北大说完后,一看效果非常热烈,学生头脑反应太厉害了,他们总能先等着包袱。所以,评书艺术不是没有观众,就连高级知识分子对它也是接受的。后来,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也讲过这方面的课。在汪景寿教授支持下,我又访问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给他们讲中国评书艺术,这种实践的经历使我对评书艺术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其实评书艺术跟文学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血缘关系的。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离不开说书人。评书是一种讲述文学,它不同于阅读文学,你要说出来,人一听就懂,所以必须简单明了、生动灵活,而且还要深刻、有哲理,像杜甫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感觉才行。鲁迅讲小说的起源时,认为古人们可能是劳动之余闲着没事了,还没有文字,就靠说话,聊点儿事儿。后来有了文字,才有了措辞、语法之类的。所以,评书要早于文学作品。其实,宋朝就有“说三分”了,到了明朝罗贯中才写出《三国演义》。评书艺术是向人类传播知识、道德、观念、理论的一种艺术。旧社会老百姓没文化,他靠什么知道历史,知道关公正义和曹操奸诈?就是靠说书人说的东西,这个影响改变不了。评书作用是潜在的,甚至是难以名状的,它在人们心中产生的影响是很难描述清楚的。而这种作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培根铸魂”。
张: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您的《评书表演艺术》,这是中国曲艺发展史上第一本评书高等教育教材。在这本前无古人的著作中,您提出的评书理论是怎样的?田:
我认为,评书表演艺术理论甚至可以扩展为曲艺表演体系,就是营造想象艺术的表演体系。对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布莱希特表现派、中国戏曲程式三大表演体系,评书表演体系是另外一种。因为评书演员或者曲艺演员,一方面要营造想象环境,营造想象人物,营造想象事件。这里,演员的表现方法是一人多角儿、虚拟表演。另一方面,跟其他表演体系都不一样的是,曲艺演员要塑造自我,就是营造想象的本人。而其他艺术形式都要抛掉自我。比如体验派讲究,你演这个匪徒,你就是匪徒,把自个儿忘了;表现派讲究,你找准了这个人物的感觉了,你就是这个匪徒。中国的戏曲有个程式,髯口、花脸都是刻画角色的。对于刻画人物,他不能跳出来一点儿和一会儿。所以曲艺演员这里边有一个营造自我的问题。营造什么样的自我,就是你演员在台上站着,观众就对你关注了。通俗点儿讲,叫台缘儿。你站在台上人就爱看,有舞台魅力。我有时候讲,演员就是气功师,你演出,观众承认你了,那这就是你的作用,跟着你哭,跟着你笑,跟着你紧张,观众反馈回来了,就是认同你。不只是评书,包括相声、鼓词,都是营造想象的艺术。比如骆玉笙唱的《丑末寅初》,早晨五六点钟怎么上学,樵夫怎么上山了。侯宝林的《夜行记》,说得栩栩如生,大伙儿都乐。还有《关公战秦琼》。这些都是想象。黄宏有个作品,叫“子弹的自述”,写一个子弹,怎么从厂里制作出来,怎么送到前线,全篇没有一个人。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达到的。想象是最美的,而且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所以曲艺就是把你带入这种想象和审美当中,让人回味无穷。这里还有打造演员的问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曲艺是角儿的艺术,作品人人传唱,你就火了,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想象艺术应该作为一种门类、一种表演体系。表演想象需要经营打造出来,最终得到观众的认同。
三、无我人生:一门心思传承评书艺术
张:
我了解到这两年,您一直在忙着建党百年重大主题评书创作,请您谈一谈创作的情况?田:
我形成对我们党的最初认识,是在8岁那年。1948年,我父亲带全家到天津咸水沽镇说书演出。当地一个地痞叫王六儿,听书不给钱还骂人,封台、捣乱,最后还得请他吃饭。这件事成为我们全家人的心结,难以解开。转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津南咸水沽进驻了“土改工作队”。在我家外间的闲屋住了四个工作队员,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自从他们一住进来,就天天帮我家挑水、扫院子,他们经常开会很晚才回来,但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爸爸说:“这共产党的官,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没过多久,在李家书场召开了一个“坦白大会”,公审地痞流氓王六儿的罪行,有人揭发了他听书不给钱还讹饭吃的事情。最后,工作组宣布定他为坏分子,劳动改造,定期汇报,天天要拿着扫帚扫大街,收拾垃圾。很多群众说:“这就叫当报不报,时候没到,共产党一到,坏蛋全得报!”我全家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共产党是让老百姓顺心的。这是我小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感和认识。后来在“文革”时期,要求讲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本溪有个军长级干部,就问本溪有没有能讲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演员,有人把我推荐上去了。于是我根据《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背诵毛主席诗词,分为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来讲。我讲了以后就火了。全本溪各个学校工厂、矿区都听我讲,有的干脆全天停产,一天八个小时不停地听我讲。我这嗓子就是那时候累坏的。后来有人提出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怎么几个小时就能讲完的,于是就被叫停了。改革开放后,文艺界迎来了春天,我感觉共产党斗争历史是应该讲的。我也看到,电视剧、电影里很多东西过去都不讲,现在都可以讲了,就是把握分寸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说书人都在说当代的书,比如南宋就讲杨业的故事,《大宋宣和遗事》讲的就是梁山起义的故事,都是当代人讲当代。而且我们国家一直倡导说唱新,《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都有评书。
从说书的角度看,现在党史很多内容,比如左倾路线、右倾路线,老百姓看不懂。而通过说书,可以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的斗争过程,共产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失败到成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是一部斗争哲学,这种斗争哲学比二十五史都有现实意义。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认为,我应该写一个合理的、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展现我们今天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说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是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起码也能听明白的生动的故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想说的是共产党的故事。2014年,我开始创作实景评书,讲共产党的历史故事。从上海一大、南湖红船,到南昌起义、井冈山朱毛会师,都到实地那儿去说。一共录了20集,最后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播出。

图5 田连元在家舞扇 摄影:赵凤兰
有了以上基础,在2019年,我萌生了到2021年,我们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创作一部共100集的反映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评书——《话说党史》。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构思。后来联系到了学习强国平台,他们非常支持,我们商定录制广播评书。但写起来真是太费事了,时间必须准确,人名不能出错,事事都得找到根据。现在我已经创作了32集,也录了10集。不论怎样,我都要把这个任务完成。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要有创造史诗般的雄心。搞艺术就是给自己出难题儿的,我有这个信心和决心。
张:
您曾经说过“本来没有我偏要来,来了又走,还是没有”,这是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应当说,您现在一门心思都在传承评书这门艺术上,这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田:
你刚才说的是我给自己写的碑文。我一共写了两个,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他当过皇帝、大臣、元帅、娘娘、盗贼,等等,等等,都是假的,如今长眠于此是真的”。评书这门艺术,是演员凭借一身技能, 运用语言、形体、观众感觉等诸多元素调动观众进入演员的规定情境和创造世界。评书看似是很简单的艺术,一个人表演,道具不多,但绝不能简单化理解。千万不能把说书简单化理解为只要有张嘴、有个好使的脑子、能背词儿、把故事掰扯明白了,就能混饭吃。说书难就难在你要说活,一个人说的要像电视剧一样。所以说,评书是营造想象的表演体系。这种虚拟表演,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故事来。说书人的嘴,唱戏人的腿。戏曲艺术与评书艺术不同,严格来讲是半虚拟表演。戏曲表演中,演员得扮上,穿戏服、画脸谱,喝酒得有杯,打起来得有刀枪。而评书包括其他曲艺种类,基本什么都没有,全凭演员的声音和表演虚拟出这些东西来。所以,要把评书传承下来,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比较现实的思考。
我觉得传承评书艺术,通过高等教育规范化科学化的模式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撰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评书表演艺术》这本教材的初衷。高等教育体系培养的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高校不一定培养出曲艺家,就像在高校学数学不一定成为数学家,学文学不一定成为文学家一样,但一定会培养出传承曲艺、爱好曲艺、传播曲艺、弘扬曲艺的各领域人才。我现在有12个徒弟,我就向他们讲明白一个道理,他们不见得成为大说书家,但是他会成为很好的传承者。而且我坚信只要这个评书艺术传承下去,将来一定会出大说书家。
张:
十几年前,您在接受采访时就思考过网络时代评书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评书不仅不会消亡而且会更好发展的论断。事实也证明如此。从喜马拉雅APP上搜索,您的评书点击率少则千万,多则达数亿人次。您是如何看待新时代评书发展前景的?田:
知史方能知未来。任何艺术形式,只要能引发社会正能量的轰动,引发人们对作品的认同,这种艺术形式就能在社会当中站住脚。评书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的发展史比其他曲艺门类的发展史都全。明代有话本文学《三言二拍》,宋朝就有给皇帝讲评书的艺人,唐朝有唐人小说。在民国时期,北京有“艺坛三绝”,即谭鑫培的京剧、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双厚坪的评书。这里有两个是曲艺,而那个时候电影刚进入中国。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了广播,评书上广播了;有了电视,评书上电视了,有了网络,评书又上网络了,只要出现新的媒体传播形式,评书就能渗入进去。因为评书从形式上来讲比较简单,接受程度来讲也简单,不但成年人能听懂,小孩儿一听也能明白。评书通俗易懂,其他艺术形式,比如交响乐,没有一定的乐理,听不懂大调儿、小调儿。最重要的是评书有更深层的意义。“说书唱戏劝人方”,评书是培根铸魂的艺术。现在我们看,评书节目有过万人空巷的情况,广播评书有过,电视评书也有过。从这里边我就悟出一个道理:评书艺术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它不会灭亡,不会衰老,只是要看以什么形式再出现,科技越发达,可能越兴盛。最后用一首打油诗来回答新时代的评书发展吧,“想象空间大,随身处处听。安全无辐射,伴君万里行。闹中求憩静,心态不失衡。常道古今事,寓教中华情。”
访后跋语:
2021年1月19日,我来到北京丰台七里庄田连元先生的家中采访。由于这些年工作的关系,和田老师已经很熟了,他对中国曲协的工作特别支持,经常参加协会举办的展演比赛、慰问演出、座谈研讨等活动。但是为了做好此次专访,我也是做足了功课,认真拜读他撰写的自传和著作,查阅了几十篇他撰写的和撰写他的文章,了解田老师的经历,进而确定了采访题纲。结束整整四个半小时的采访后,我更加感觉到田老师的经历就像评书里面的故事一样带着传奇色彩,他的思想观点也如同评书中的“评”一样精彩独到。采访中,田老师金句不断,他讲“艺术创作就是要不断地给自己出难题”。他就是一个不断给自己出难题,然后努力去解决难题的人。这些年中国曲协在组织编撰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教材,其中《评书表演艺术》一书的负责人,我们早在2013年就想请田老师担纲。然而在2014年5月28日,田老师遭遇车祸,小儿子去世,自己也身受重伤。这对一位老人是多么大的打击啊。我们只有等他身体逐渐康复,才能把这个事情托出。2015年6月的一天,我们登门拜访田老师,与他沟通此事,当时心里很没底,不知他能否答应。可当面聊过后,他表示至今没有一套总结出来的评书表演理论很是遗憾,认为评书这门艺术一定有自己的理论,毅然答应撰写这本教材。然而撰写教材谈何容易,但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的努力下很快完成了,我们非常感动。田老师为了评书事业,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录制《话说党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记得2019年7月,在“向祖国和人民汇报”——庆祝中国曲协成立70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周中,我和田老师聊天,他悄悄地告诉我,最近立志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光辉伟绩的长篇评书,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推出。我非常惊叹田老师在创作上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十分钦佩他总是能给自己加担子,因为这个创意完全出于他的个人行为和一名老党员艺术家对党的忠诚。采访结束后,我为专访起了这个题目——“说书人的艺术和哲学”,诚如田老师讲“评书演员,大家都称为先生,实际上他是一辈子的学生”,他的艺术与哲学已经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