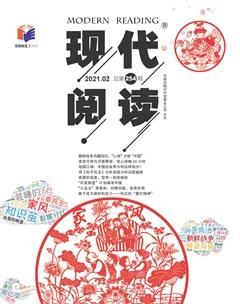古文不古,万古常新?
古文,泛指古代的文字。中国文字的书写以方块字为主,称为汉字。古代的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简帛、隶书、篆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一些古老的字体如甲、金、简帛等,很多现代的专家学者都能大致辨认出来。汉代以后楷书流通最广,到今天还是全民日用的字体。20世纪50年代以后汉字虽有繁、简之分,但只是两套并存的书写形式,所谓繁简由之,基本上并不影响沟通和表达。而汉字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有生命力而又鲜活的文字,连联合国都在使用。欧洲的拉丁文相对来说就显得古老陌生,流通不广了。
古文亦指古典的文章,或指古代文体,又称为文言文。中国古文的历史跟汉字一样,源远流长。可以说,有甲骨文的时候,就有了古文;在甲骨文以前,口说流传,后来记录下来的,也是古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反对骈文束缚思想,窒碍性灵;主张恢复周秦两汉的古典文风,自由书写,畅所欲言,具有文艺复兴的意义,同时亦有普及教育的意味,因此引起了一代文风的改革,由骈入散,解放文体,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而这也是文言文最辉煌的历史。中国的古籍文献,例如《文苑英华》《四库全书》等,几乎全部用文言写成;甚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历代相传的文献,也使用汉字载体及文言书写的系统,以此保存文化,并视为珍宝。
古文跟現代的白话文相对,又称文言文。晚清政府为了救亡,开发民智,面对时代的呼唤,推广国语,提倡白话文。光绪二十四年(1898)《无锡白话报》创刊,之后杭州、绍兴、苏州、宁波、上海、安徽、广东、西藏、伊犁、潮州、北京、蒙古等地的白话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盛行,文言文黯然失色,也就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白话文当道,但在个别小众的圈子里,文言文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以一种有内涵、有品味而又高雅的方式存在。此外,随着网络书写的流行,现代人喜欢“我手写我口”,导致口语横流,更因为科技发展及新鲜事物的出现,涌现了大量新创的“潮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一旦“潮语”主导了新闻媒体及书写领域,白话文可能很快也会汇入文言文的系统,成为新一代的“古文”。没有哪种新文体是永远年轻的,但古文却能够万古长青。
为什么说古文可以万古长青呢?古文也曾年轻过,随着年代的层层累积,就像树干的年轮不断加密一样,焉能不古?古文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载体,运用“吸星大法”,鲸吞天下,兼包并蓄,无所不容;然后经过集体的吸收和消化,再通过历代作者的反哺锻炼,渐渐定型为一种稳定规范的文体,更变得易学易用了。此外,除了食古而化之外,古文也不断地汲取当代的新词语、新句法、新观念、新思维。
《古文观止》每一篇都深具创意,各有个性,否则陈陈相因,读者早就闷透了,又怎能流传久远,弦歌不绝呢?从《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开始,里面就有很多精彩的对话,例如“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句,虽是公元前722年的口语记录,距今2700多年了,听来还是亲切明白,虎虎有生气。其他如“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背城借一”,“乐而不淫”等,都出于《左传》,现代人读来也没有什么隔阂。由此看来,将来的“古文”仍会不断吸收现代汉语的词语和句法,以及外语翻译等,融为己用,变幻多姿,自然可以万古长青了。
假如说口语是我们的母语,也就是第一语言,那么古文就是我们的第二语言了。第一语言是不学而能的,只要在相应的环境中生活,就不难掌握;而第二语言就得通过学习掌握,例如学好英语要多读多听多讲多写,而学习古文更为简单,古文跟我们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通过阅读就可以写出简明通顺的文言文。读者不妨做一个小实验,每星期读一两篇《古文观止》中的篇章,多读几次,弄懂了字词句法,明白文章大义,那么一年之后,文言文写作自然就会条理清通,而白话文亦得心应手,愈见精进了。至于思维深度、意象芳华、感情意境,那就得看个人的造化和努力的维度了。进一步来说,当代的“潮语”可以说是第一语言,而白话文就跟文言文一样,可能都是第二语言,我们写文章不可能全依口语直录,否则绝无文采可言,有必要通过学习来提炼和修饰。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实好的白话文还得从文言文中汲取养分,从而传神写意,挥洒自如,将来我们说不定还会回到文言文的母体之中,或文白兼融,或文白由之。但那是后话了,由于古今语言的质变,现在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不必混为一谈。
(摘自华夏出版社《经典之门(文学篇)》 作者:康震 陈致 等 本文作者:黄坤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