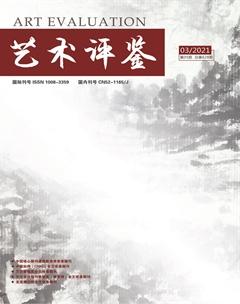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的相融关系
孙凯昕
摘要:中国古代向来重视音乐,无论是祭祀或宴飨时,都需要奏乐。儒家对于士子的六种基本要求是:礼、乐、射、御、书、数,“乐”亦包含其中,可见音乐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所以不少作家既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说明了文学与音乐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文学与音乐运用起来,便自然相融起来。上古时候人们已经通过“诗、乐、舞”表达思想感情,由于文学与音乐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这种不自觉的融合,引入文论作为解释文学创作的技巧。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都是艺术家在追尋“意境”,这都是内心情感的表达。
关键词:文学 音乐 关系
一、文学与音乐的起源
中国文学与音乐自古以来就有很厚的渊源,它们能够相融合是因为两者同是感情抒发的渠道。而艺术的根本特征在于情感,《礼记·乐记》“唯乐不可以伪”,所以无论在文学或音乐上表达的感情一定不能造假,必须是真情实感。《荀子·乐论》“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所以,荀子认为音乐是“人情所不免”。唯一不同的是,文字偏向于书写,音乐主要在于口传。文学是语言艺术,它通过语言来塑造形象,表达感情。音乐是听觉艺术,它通过旋律、节奏等手段来表达思想感情。《诗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文学与音乐在表现方式上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感情流露的艺术手段,是人类思想感情的抒发和呈现。
音乐与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音乐与文学都源自社会生活,反映当时生活现象,都能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是描述远古时期先民乐舞的场面,他们手执牛尾,载歌载舞。《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情动于中”是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内心感到痛楚,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所痛,就要通过唱,唱也不能充分表达,就要通过手脚来表达。诗、乐、舞之所以能三位一体原因是:诗歌、音乐和舞蹈都是感情抒发的渠道,文学与音乐都源于人的内在的情感。自从人类开始“杭育杭育”以来,音乐就陪伴着人类的生活。其中一个激发人们感情,是人们在工作或生活中感到痛苦,所以要通过唱歌来减轻痛苦。文学起源于劳动,有人们实际的需要,当人们内心感到痛苦时就会进行文学创作,感情是真实,不虚假,所以文学最初出现的形式乃口头创作。《诗经·国风》最能体现“饿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如《伐檀》《硕鼠》,被统治者所剥削,表现了劳动百姓,满腔牢骚,有怨无处诉,所以不得不借助诗歌,把内心的冤屈抒发出来。正因为这原因,部分文学作品,也能反映当时生活现象。所以,《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采诗之官到了初春时节,就会摇着木制的大铃在街上行走,采集人民创作的歌曲,然后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音乐,唱给天子听。所以说天子就算足不出户,仍能知天下事。
音乐与文学都源自社会生活,反映当时生活现象,审乐以知政,通过音乐能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白居易亦主张“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因此朝廷乐官把民间乐曲献给统治阶层之前,必须要对歌词内容甚至旋律加以改动和修饰。音乐与文学都表现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这亦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根本特征在于情感,听众可以通过声音知道演唱者或演奏者的心情。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心情,或喜或哀,而音乐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去描述的艺术。文学运用语言文字,音乐运用音符,而音乐与文学的最完美结合便是歌曲。从中国第一部的诗歌总集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音乐运用在诗歌上的情况。《诗经》的“风”是民间百姓和知识分子共同创作的作品,“雅”是贵族士大夫们宴飨时多用的音乐,“颂”是祭祀时使用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就知道音乐已应用到祭祀上。诗、乐、舞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是早期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另一个情况,表现在古代祭祀的形式上。《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因为内心有感而发,所以要通过诗表现出来,再合乐歌唱,加以舞蹈。音乐能够让神与人和谐相处,调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节奏能带动感情,甚至连动物都会随着音乐而起舞。王逸《楚辞章句》谓:“楚国南部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鼔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可见楚国俗人进行祭祀的时候,是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娱乐神灵,祈求得到他们降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在古代的祭祀中,有男祭祀者及女祭祀者,他们就像男演员与女演员,在祭祀的过程中,他们会载歌载舞,这已经是戏曲表演的雏形。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亦提到戏曲在艺术形态上必须综合语言、动作、歌舞等多种表演艺术,即通常所说的唱、念、做、打“四功”。唱,指表演中的歌唱;念,是指表演中具有音乐性的念白,所以这是歌唱的部分。做,指表演中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术和翻滚跌扑的技艺,这是舞蹈的部份。所以,从文学上来看,由《诗经》的风、雅、颂和《楚辞》所记述的祭祀载歌载舞,唐诗注重押韵声律,宋词讲究词牌,到元曲中歌唱与舞蹈相结合的情况,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文学一直都带有浓厚的音乐色彩。
二、文学与音乐的表达和掌握
儒家对于士子基本修养的要求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音乐位居第二,可见其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认为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并能提高个人的修养。《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诗、礼、乐三者纳入人生成长的三个阶段,而“乐”更是人生成熟的最高境界,可见孔子对乐的重视。《论语·先进》“‘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由于子路所弹奏的音乐显示出刚勇之气,不够平和,这也反映了子路的性格较冲动鲁莽,所以孔子不喜欢子路,导致门人亦不尊重子路。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音乐与人的性情的关联。所以,反过来音乐对于人的性情也会有影响,所以孔子主张应该听平和的音乐,才能让人心境平静。《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认为我们应禁绝郑声,因为郑声表达感情太浮靡,所以我们要远离郑声,就好像远离小人一样。孔子把郑声与小人同等看待,认为都是害人的东西,多亲近会对自己有危险。
在文学上,我们重视作家“人品与文品”,要求作家有好的道德修养,作品才会思想正确。音乐上亦然,由于音乐是要经过三度创作的艺术:一度创作是作曲家的创作,二度创作是演奏者对作品的演绎,三度创作是听众对于作品本身与演奏者的理解。二度创作的过程则需要演奏者除了具有高超的演绎技巧外,还应该深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深厚的音乐修养。所以,往往同一作品,经不同的演奏家通过不同的艺术处理,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作品完成之后的每一次演出过程和听众欣赏的过程都是艺术的再创作和再加工过程。文学上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是没有二度创作,而有作者与读者的直接沟通的三度创作。正如孟子所提出“以意逆志”,在音乐上,演奏者与欣赏者的理解亦包含在“意”里面,所以相同的作品,经过不同学历和阅历的读者进行阅读,理解亦会有所不同。
读者每次阅读作品和演奏者每次的演奏,都会产生不同的想象,这是文学与音乐相同之处,亦即文学艺术上的意象,文学与音乐境界的构成,意象起着融贯其中的作用。音乐是通过乐器来表达,文学是通过文字笔墨来表达,相对而言,音乐是抽象的,要依靠听众去感悟,想象的空间较大。尽管文学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但文学与音乐也是贵在“意会”而非“言传”,贵在“悠然心会”,而不是“逐句讲解”。
这种想象的境界,早在先秦时期,《老子》所提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可以体现。最美的声音是听不见的,最美的形象是摸不着的,最美好的东西是要通过人们自己的想象去充实的,没有任何人为痕迹,才符合自然。这时候的审美观念是以哲学为思想基础,还没有应用在文学方面。到了庄子在《天道篇》提出书籍不过是“圣人之糟粕”,指出“言不能尽意”的概念,说明了语言不过是“得意”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得意妄言”,不要受到语言的限制,要通过自己的想象、理解去掌握作品的意思,从而得到“言外之意”。所以在艺术上,包括上面所提到的文学和音乐上所要达到的想象境界,最终的目的也是要达到“言外之意”。这个“言不能尽意”,陆机在《文赋》进一步解释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他提出物、意、文三者的矛盾关系,指出作品所表达的状态与创作者脑海中本来的构思存在距离。
由于音乐较抽象,它主要是通过声音与节奏传达一种气氛和感受,想象的空间比文字大得多,不像文字具体,有框框的限制,所以在表达想象方面,音乐比起文学作品更有优势。音乐不像文学精确、直白地通过语言把内容表达出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想象开始引入到文学方面,并且开始注重感情的表达,和音乐与文学起源的原因一致,并以音乐为喻解释写作。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以演奏乐器为喻,解释作家之“气”对于写作文章非常重要,而“气”分清、浊,每个人都不同。就好像弹奏乐器,虽然大家都是根据相同的乐谱、节奏和速度去演奏,但由于每个人的用气、技巧存在差异,所以演奏的效果也不一样,就好像“气”是天生的,就算是父亲兄弟,也不能传授给儿子或弟弟。又如:陆机《文赋》“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絃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和,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故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这里的应、和、悲、雅、艳都是以音乐为喻。从而提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应,指声音的相互呼应;和,指和谐的音乐美;悲,指表达感情鲜明;雅,指格调纯正;艳,指绮靡,不能过于平淡。总的来说,是指在文学上写作要注重形式与内容上的配合。而“悲”是指文学创作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见陆机非常重视作家在文章中的感情流露。
除了开始把情引入文学,亦开始以“味”作为文艺上的审美标准。这种“味”是不能言说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想象,要通过读者或欣赏者自己领悟。正如陆机《文赋》提到“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犯”。若文章过于质朴,就会变得淡乎无味。所以到了唐代,除了注重意境,更是强调“味外之味”。就如钟嵘《诗品》提出:“滋味”,其言:“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而诗歌之所以有“滋味”,正是由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此外,司空图《與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这里提出的味外之旨,是认为“味”是判别诗歌好坏的首要条件。王昌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是从创作经验与体会直接概括出来的,他以山水诗、抒情诗和由意诗为例,说明三境的情况。皎然《诗式》提出“取境”:“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所以,皎然是力求把人工修饰与自然形成融为一炉,很重视人工修饰在意境创造中的作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转述戴叔伦语曰:“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严羽《沧浪诗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说明这种意境精彩绝伦又浑然天成,没有任何人工痕迹,并具有朦胧之美。司空图与严羽均是认为欣赏者在想象过程中,营造若即若离,似有还无的朦胧景象,才是艺术上最高境界的美。
三、文学与音乐的互渗与互补
通感是文学与音乐能够相融的渠道,文学家运用通感手法,把听觉转为视觉,体现演奏者的技艺和表达作家听到乐声的感受。唐诗中描写音乐的三大名作: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李凭箜篌引》、韩愈《听颖师弹琴》,它们分别以:以声喻乐、以典喻乐和以形喻乐的形式,把难以捕捉描绘的听觉形象,通过五官通感,转化为人们易于接受的视觉形象。通感,就是把感官贯通,是感觉的转移。文学家把听到的乐声,利用文字具体的描写出来,演奏家把自己对于乐曲的掌握,通过声音营造一个画面,传达给听众。所以,我们能够“看”音乐,“听”文学。下面第一个例子:
白居易《琵琶行》(节选)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官居翰林的白居易,因直言敢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以失宠的女子自喻,正如埋怨“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琵琶女。这是一首完整的乐曲,“转轴”两句是前奏,“银瓶”两句是高潮,“曲终”两句是终结。诗歌以声音,如急雨、莺语、私语、裂帛、银瓶、珠落玉盘、冰下泉流、刀枪鸣响来比喻乐声,让读者仿佛亲临其境。白居易受到琴声吸引,所以“邀相见”,最后达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可见,诗人用主观的感情理解乐曲,而音乐效果与人物感情的联系与共鸣使读者回味悠长,这也是音乐的感染力。另一首描写乐声的诗歌:
李贺《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诗歌以神话传说,如“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石破天惊逗秋雨”,典故,如“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乐声描绘出来。
再如:韩愈《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这首主要写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感受。据说有一个病人,躲在床上,听到颖师弹琴的声音,病就痊愈了,可见音乐有治愈人心灵的作用。韩愈也慕名前来欣赏颖师的乐曲,并把他听颖师弹琴的感受写成了一首诗。
这也是一首完整的乐曲,但在这短短的乐曲之中,乐声变化却是多样的。诗歌第一二句,声音柔和;第三四句,声音变得雄壮;第五六句,转入婉转;第七八句,乐声变得丰富;第九十句,以低沉乐声终结。乐曲中感情的骤然变化,很讲究演奏者的心理素质,他要在很短时间调整情绪,这比写作还要难。琴声的突然变化,诗人以冰炭同炉来形容。一方面,显示了演奏者的琴技精湛;另一方面,亦显示听者(诗人)的修养,能解其中意,诗人亦是音乐家。
除了上面所举的把听觉转为视觉的例子,也有一些以曲谱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清代袁嘉谷请音乐家把本来的“工尺谱”改为“五线谱”,整理为《诗经古谱》。
到了现代,音乐家林华创作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他以巴赫的序曲与赋格曲(Prelude and Fugue)作为基础,把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描述的诗歌情态以音乐进行评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是以复调音乐创作为主,所以在旋律的组合上已经比《诗经古谱》丰富得多。第一首“雄浑”,司空图在这部分表达的雄壮浑厚风格,包含了力量的变化和气的内在修养。林华在乐曲由开始直至第十九小节,安排双手都是在低音部份,形成浑厚的音色,加上强音符号和踏板的使用,加强了雄壮有力的气氛。乐曲从第十四小节开始,断断续续的加入了二分音符,再加上连续线,形成了一股连绵不断的气。但是这种气是变化的,所以在第三十六小节开始,音色不但跟前面形成对比反差,而且骤然的从p(弱)到f(强),然后回到p,ff,最后以fff结束。第二首“冲淡”,林华运用大量装饰音,表达司空图的“遇之匪深,即之愈稀。”仿佛你越是靠近这种美,它就离你越远。到了第十七小节,加入跳音,就是司空图多说的“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以短促的音,表达若即若离,不能抓住的感觉。司空图说“閱音修篁”,就是说听见乐声,仿佛置身于竹林里面,看到周围都是修长的竹子,可见司空图亦赞同音乐和文学的“通感”效果,所以不说听而说“阅”。第三首“纤秾”,乐曲音程(音距)不大,很集中,营造了流水涓涓和静谧的感觉。而在第十一和二十二小节,有高八度的旋律,仿佛是清脆的鸟鸣,一声连一声,所以画面显得非常丰富。第五首“高古”,乐曲开始只用左手演奏,是在模仿古典钢琴古朴沉实的声音。第十一首“含蓄”,在这首前奏曲中仅以降B(bB)为核心,但不是重复,而是带有节奏变化和伴奏的转换,给人欲语还休的感觉。
总结以上所言,文学与音乐从实际的感情思想表达,转化为文艺创作,形成了诗歌以及成为文学理论。在形式上,由原始的口头传播,到以文字记录声音,至有了具体的五线谱记录,可见文学、音乐在接受与传播方面是不断演进的。
参考文献:
[1]林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
[2]张伯伟.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与文学的关系[J].文学评论,1999(03).
[3]王玉玲.对音乐与文学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的研究[J].北方文学,2011(02).
[4]田春生.浅谈文学与音乐塑造形象方式之比较[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04).
[5]吕银才.三首唐诗中的音乐描写[J].洛阳工学院学报,2000(09).
[6]莫宇芬.“摹写声音之至文”白居易《琵琶行》与李贺《李凭箜篌引》对读[J].古典今读,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