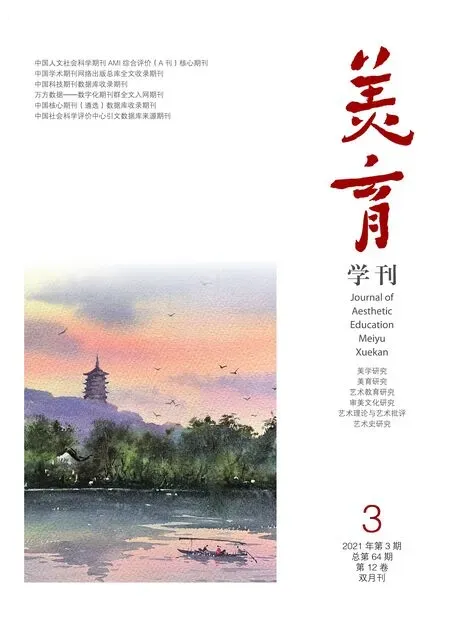佩夫斯纳设计史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视野
李 明,梁列峰
(西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重庆 400715)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2—1983)是20世纪建筑史、艺术史与设计史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他的学术生涯融合了不同社会的政治、价值偏好以及民族性,对西方艺术理论与设计史的影响至深至远。他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唤醒大众充分感知艺术与美的存在,特别是对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内核与技术材料外壳的观察,将其解读为20世纪最为激荡的产物。
一、学术生涯的沿革
1902年,佩夫斯纳在德国莱比锡的一个俄罗斯犹太家庭中出生,由于家庭的成长环境,1921年4月加入信义路德教会,大学时期受益于传统的“迁移教育”,因此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1921年至1923年期间,佩夫斯纳往返于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城市,师从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维尔纳·魏斯巴赫(Werner Weisbach)、鲁道夫·考奇(Rudolf Koch)、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从事文艺复兴、巴洛克艺术、样式主义的研究,并于1924年获得莱比锡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直至1927年期间又担任德累斯顿美术馆研究助理,专注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在此期间撰写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文艺复兴到洛可可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以及出版著作《莱比锡巴洛克——莱比锡的巴洛克艺术》(1928年)。
1929年,佩夫斯纳正式成为哥廷根大学的一名艺术史讲师(图1),为哥廷根大学的艺术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0年他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英国艺术史的研究,但好景不长,由于纳粹在1933年4月通过了针对非雅利安人的公务员法——《恢复专业公务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 Berufstentums)[1],这一法案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性质,致使佩夫斯纳于1933年9月9日失去了在哥廷根大学的教学职位。他不仅失去了在哥廷根大学的学术地位,纳粹当局还告诫他不能在德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为躲避德国纳粹的政治迫害,1933年10月佩夫斯纳决定向英国学者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ssisting Refugee Academics)提出申请,移居英国,从汉堡迁至伦敦。1934年他在伯明翰大学贸易系寻求到一份助理研究员的工作,1935年又去往戈登·鲁塞尔家具公司负责质量监督和对外销售,这是他对现代主义运动的特殊承诺,他已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现代工业设计与其提倡的“艺术社会学”理念。由于被迫流亡英国,佩夫斯纳对于成为被祖国“抛弃的弃儿”十分痛苦且缺乏安全感,同时身处异国他乡,又被视为英国国内的“敌国人”,这样双重的压力导致佩夫斯纳感到焦虑不安(1940年中期作为“敌外”被拘留),他的学术生涯以及个人生活都遭受到了背信弃义的政治和种族主义排斥的影响。此时的欧洲大陆距离一战爆发不足20余年,然而这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所留下的伤疤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性撕裂、种族类型强化也愈演愈烈,但佩夫斯纳依然热爱着他的祖国以及脚下的这片英格兰土地,更痴迷于专业领域内的学术研究,为此倾注了民族情感认同的大义以及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判断,因而在他的设计史或艺术史中有着不同的民族性和对现代主义运动的认同,这激励着佩夫斯纳不断尝试在艺术史、设计史等领域确立自己的专业地位,并逐渐成为英国著名的现代艺术史、建筑史与设计史学家。

图1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肖像,1929年,德国下萨克森州州立大学图书馆馆藏
1936年,佩夫斯纳出版了他在设计史上的成名代表作《现代运动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ofModernMoment:FromWilliamMorristoWalterGropius),由于影响巨大,该书又于1949年修订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再版,并对书名作出具有学科意义的改动,更名为《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ofModernDesign:FromWilliamMorristoWalterGropius),这也是首次以“设计”之名来解读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特征[2],不仅描述了国际现代主义建筑的民族性差异与家族渊源,而且明确揭示了现代主义设计发展的基本轨迹。该书打开了西方设计史研究的先河,堪称设计史学科发轫的里程碑,由此设计史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3]1937年,佩夫斯纳在英国的第二部著作《英国工业艺术研究》出版,他将其视为《现代运动的先驱》的“孪生兄弟”,该书向英国工业制造商宣扬德国包豪斯的设计哲学,以此从中揭示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将设计史从建筑史与艺术史的包容中自主分化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1940年,《美术学院的历史》一书在英国出版问世,该书中佩夫斯纳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看待艺术史,完善了传统风格史的不足,是一部考察西方艺术设计教育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4]281同时期的还有《艺术的过去与现在论集》,这其中包含了某种对包豪斯学派的赞扬,并将其视为某种无名集体主义意志的产物。1941年,佩夫斯纳历经曲折,任职《建筑评论》杂志编辑,其后的1942年又出版了被誉为“西方建筑史的标准教科书”的《欧洲建筑纲要》一书,他在书中进一步强调材料与技术的重要意义,将功能主义的道德看作是超越历史的风格,并表现了现代社会无阶级差别和反特权的性质,“没有个人崇拜”就是赞美一座现代建筑的典型术语。[5]在此之后,他担任了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讲师,后升职为讲座教授,其后因功勋卓著,学术名衔接踵而至,先后被任命为剑桥大学(1949—1950)与牛津大学(1968—1969)的艺术系讲座教授,并于1969年受封为爵士。这一时期,受出版商艾伦·莱恩的赞助支持,佩夫斯纳开始主编两套系列巨著:《塘鹅艺术史》(47卷)与《英国建筑》(46卷),《塘鹅艺术史》打破了战前封闭的读者圈,为普通大众提供了高质量的学问。而尤其是针对《英国建筑》系列,佩夫斯纳倾注了大量心血,书中梳理了从英国撒克逊时期到20世纪的大量代表性建筑,并一一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是充满了民主意愿的百科全书,直至1974年终卷《斯塔夫德郡》才得以问世,可以说该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史之一。[6]4佩夫斯纳在二战期间专注于英国艺术的非理性方面及本土化的民族风格,其研究成果在1955年的里斯座谈会上显得格外引人瞩目,最后通过归纳总结又于1956年出版了《英国艺术的英国性》。1962年《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溯源了20世纪现代设计思想与现代建筑的起源,以崭新的视角剖析这一设计史上的困惑阶段,突出强调了用于公共的建筑与设计及其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1966年在出版的《我们时代的建筑》中提出:“现代运动适合于所有这些关系重大的方面,适合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物质与功能的诸多方面,假定任何人都希望抛弃它,那似乎是愚蠢的。”1968年著有《艺术、建筑和设计研究》,1976年佩夫斯纳出版了他的终著《建筑类型史》,由此打开了建筑分类研究的新世界,这是一本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同设计史相融合的代表作,他认为建筑的风格是建筑史的问题,而建筑的功能是社会史的问题,揭示了建筑伴随着社会、生活方式、材料技术与审美心理的不断变化。作为设计史的先驱者,佩夫斯纳向我们说明了既要将设计史作为专项研究,更要使这种专项研究建立在艺术史、科技史、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因为设计本身就是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审美行为的综合体,同时建筑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建筑的功能与社会史、建筑的结构与科技史、建筑的形式与风格史、建筑的民族性同地理史交织在一起并贯穿始终。
在整个20世纪里,佩夫斯纳爵士撰写了大量的心血之作(图2),为现代艺术史论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将一生的使命感、专业素养与成就全部奉献给了设计史、建筑史与艺术史的研究,对于佩夫斯纳而言,不管你怎样评价这位“艺术巨匠”,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理论家。

图2 佩夫斯纳著作《现代设计的先驱》《英国艺术的英国性》《欧洲建筑纲要》封面
二、民族性的转变
青年时代的佩夫斯纳长期遭受来自反犹太主义的抵触与排斥,在进入慕尼黑学习之前就已形成特别复杂和脆弱的心理,他对于故乡的怀念仿佛毫无归属感,当流亡英国之时,这种情绪变得更加明显。同时他对迫使他流浪海外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充满了矛盾性与复杂性,尤其是作为一个因种族原因而被剥夺学术职位的学者而言,他对压迫者的政治表达还充满着一丝的同情。对此,他曾与一位伯明翰老师在交谈中表达道:“我爱德国,这是我的国家。我是民族主义者,尽管我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但我还是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除了混乱,别无选择,我不能希望国家陷入内战。”[7]佩夫斯纳的这种态度或许是由于作为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学者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怀,寄希望于国家社会能得到发展,文化上的进步以及面向现代化走向未来,在这其中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多重影响成因。伴随着德国纳粹社会运动事态的发酵升级,后期的佩夫斯纳也清晰地意识到纳粹的伪善面目。在到达英国之后,为适应本地社会生活,佩夫斯纳开始逐渐尝试抛弃新教德国的文化和信仰,但同时也充满着极其矛盾的复杂心理,这对于佩夫斯纳的艺术理论写作,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佩夫斯纳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时,总是对艺术中的民族性特别感兴趣,这种兴趣从20世纪20年代在莱比锡的学生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当初他在德国研究艺术史时,“国家艺术的民族性”这一思想就已经形成,各位老师也与他交流了这种民族性的看法,包括博士导师威廉·平德。然而,早在他的学生时代之前,在德国社会中,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就已经激发了对于艺术民族性的关注,佩夫斯纳见证了艺术和设计是如何被贬低以及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以作品宣扬民族性),完全被视作某种政治宣传工具以激发国家的种族精神。在这之后,佩夫斯纳对于这种极端目的的行为感到沮丧和失望,于是,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艺术作品中去揭露所谓的民族主义,并且开始变得非常敏感,其设计领域包括平面设计、工业产品、建筑与绘画。
佩夫斯纳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英国人持冷漠甚至敌视态度,在接下来的英国生活中,他的观点和公众角色方面都了令人瞩目的转变,成功地从有嫌疑的移民转变为受大众喜爱的学者,他是通过1945年初开始的BBC广播座谈实现了这一自我转变的。在这些演讲中,最著名的是“Reith”演讲系列,1955年10月16日,第一次在BBC的第三栏目播出,主题为“地理艺术”,此后陆续播出,并于一年后以书本形式出版,名为《英国艺术的英国性》。通过对该书的解读,揭示了佩夫斯纳开始产生对英国强烈的认同感,《英国艺术的英国性》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建筑设计。光滑的立面,大网格窗户和平坦的屋顶,这些都是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的特征,例如德绍包豪斯校舍,正如佩夫斯纳指出的:“网格是当代建筑的基础之一,它本应该使英国很容易接受二十世纪的风格。”[8]95而且佩夫斯纳将他曾经寄希望于德国社会主义形式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希望转移到他的新家乡英格兰,希望在此建立一个朴素的,未经装饰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但是,该架构无须类似于“无数数列递进”的形式,相反,它可以有意识地使自己摆脱人为约束。正如佩夫斯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提倡的那样:“如果英国设计者忘记学院的定式和人为对称的立面,并将功能赋予在英国建筑之上进行设计,那么,他们将会成功。”[8]179
选择作为“国际公民”留居英国的佩夫斯纳似乎有意地脱离了任何特定的民族性认同,虽然这种观察似乎使佩夫斯纳关于民族性的立场复杂化,但实际上正是佩夫斯纳形成的民族性理念使他对“英国艺术的英国性”保持信念。事实上,对于佩夫斯纳而言,正是他自己的跨国历史设计和移民身份,脱离了民族偏见与敌对视角,才使他成为如此敏锐的艺术民族性观察者。正如他本人在首次出版的《英国艺术的英国性》前言中所声称的那样:“我的前生可能被认为是特别有用的任务,在某个阶段以新鲜的眼光进入一个崭新的国家,然后逐渐安顿下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可能构成一个很大的优势。”[8]10毫无疑问,佩夫斯纳从未有过作为英国人的强烈感觉,他被迫成为英国的局外人,一个“陌生的土地上的陌生人”,但他渴望一个没有政治压迫的国际化存在,这样他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和设计艺术史中。
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的简单融合时常代表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文化,从德国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讲,他们的观点是理想主义和“精神上的”历史观。佩夫斯纳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也没有明确反对犹太人,他以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来到英国,坚定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纳粹的恶魔意图变得清晰之前,他将希特勒的政党视为这两种信念的载体。正如《现代艺术史》所说,他的目标是20世纪的大众理想主义,作为这种理想主义的推动者,就像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新建筑的建筑师一样,为更多的人们提供适当的住房。这也正是佩夫斯纳在其1931年的“德国犹太人协会”中提出的论点。他指出:“法国需要一百万套住房,德国需要一百一十万套住房,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才能为人们创造优质、实用、廉价但又不失生气的建筑空间,这是数百万人正在寻找的房屋。”[9]311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了改善住房的工作,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的民主和民主进程寄予了厚望,同样,对1933年和1934年新的纳粹政权同样寄予了厚望。但是,新的现代主义建筑并没有与第三帝国结合在一起,当然也就无法与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于是,佩夫斯纳寄希望于新的国度,以实现他的崇高理想。
受早期在德国受到的教育及其工作经历的影响,佩夫斯纳完全推崇理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原则,其《先驱》一书中也完全反对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的风格,甚至还对其评论道:“好的19世纪建筑是运用现代材料并满足其社会角色,而坏的19世纪建筑则是装模作样地模仿过去。”这同罗斯金的观点具有某种相似性。[10]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佩夫斯纳为了让整个时代的英国建筑保留下来,他向大众宣扬“精神史”,通过维多利亚建筑体现英国最强盛时代的自信“精神”,将怀旧情绪和民族自豪感导向英国民众,在后帝国时代的英格兰寻求它的认同。为此,佩夫斯纳不得不开始肯定维多利亚时期的装饰价值和折衷主义[6]81-82(1958年起担任新成立的维多利亚协会主席),重新开启建筑的个性问题。从事英国的非理性主义研究,他必须使自己先前所述的对立观点缓和起来。于是,他将自己视为两种不同的角色,即历史家的历史社会视角与建筑批评家的专业视角,以此来化解他的现代主义立场同他对于维多利亚价值的拥护之间的矛盾。佩夫斯纳这种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受到个人某种思想上有关民族性认同的转变的影响,这也是长时间的适应、认识、理解并融入新英格兰的结果,反映在了他的学术思想与实践中。但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成长地德国,所以他对自己的两种观点兼容并蓄,这其中蕴含着对于两国民族性的认同,因此面对他人对他自身矛盾的质疑时,他辩称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背离曾经热情宣扬过的“现代主义”。对于流亡学者佩夫斯纳来说,其设计史中的民族性本质差异体现的也是自身民族性意识的转变,民族意识的游离从对祖国的热爱到对异乡认同的转变,矛盾与复杂情境下的民族性归属既是德国与英国,又并非德国与英国,而真正的回归是社会责任感与作为艺术史家的个人情感体验,真正理想是现代主义对住房和社区普遍需求的回应以及对于“时代精神”的追求。综上所述,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的确蕴含着民族性特征,其设计史中的民族性差异一方面体现在对于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历史主义、折衷主义的认同,但是它们都是佩夫斯纳基于现实状况对艺术与设计观察或实践的系统总结,对于推动社会、艺术与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也都彰显了佩夫斯纳对于所生活过的脚下土地的热爱。
三、现代主义的理想
佩夫斯纳早年对巴洛克风格的研习经历,使他一生坚持两条信念:一是表达一致的时代风格概念,彰显时代的总体精神;二是无论艺术家还是艺术理论家,在表现时代风格的社会责任时,都需要对社区有所帮助。佩夫斯纳呼吁艺术家应服务于社会的“当代需求”,甚至将这种服务责任引导至自己作为艺术史学家的身份上,他将自己的学术功能解释为:调和学术以及直接应用。为了完成这份重任,佩夫斯纳提出了“艺术社会史”的概念,他在著作《美术学院的历史》一书中,对美术学院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以及与柏拉图学园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而且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包豪斯,他将现代主义设计的诞生解读为艺术与社会之间调整关系的结构。[4]3-8《美术学院的历史》初稿写于1930年至1933年,直到1940年才在英国出版。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佩夫斯纳见证了德国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发展,作为一位艺术与设计史学家,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种设计新风格,一种代表“时代精神”包罗万象的风格。[11]1931年,佩夫斯纳发表了关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风格的评论,将其特征概括为:采用钢铁与混凝土等新型工业材料的新建框架构造、自由空间、室内与外部空间通透明晰、横向水平长窗、平整屋顶。[9]303同时与柯布西耶所说这类新建筑源于法国的观点不同,佩夫斯纳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证明这类风格至少是同一时间也在德国或者更早之前就在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地产生,而并非只源于法国。
以此观点,佩夫斯纳开启了以德奥英美等国为基础的现代主义叙事,并因艺术史学者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1928年出版的著作《法国的建筑,铁的建筑,钢筋混凝土建筑》(描述了从19世纪法国新的建设性工程技术到20世纪最新建筑的发展,最后以勒·柯布西耶的建筑设计作品为终结)而大受启发。类似这样的研究方法激发了佩夫斯纳的创作灵感,并寻找到以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为创作原型的现代主义运动英雄,佩夫斯纳将他看作现代主义设计史上的“先驱”,并特别强调格罗皮乌斯对包豪斯艺术设计教育的贡献以及他的社会基础建设计划。佩夫斯纳非常赞赏格罗皮乌斯所扮演的社会性角色,作为包豪斯的开创者,他的目的就是协调创作出服务于集体的艺术或建筑。相反,佩夫斯纳对于柯布西耶的建筑在社会性功能与功利性方面的缺失进行了批评,并质疑柯布西耶的建筑设计实用价值不高,怀疑其技术美学的新颖性是否对使用者有用,是否会带来某种负面效应。佩夫斯纳认为柯布西耶的设计态度属于典型的19世纪形式唯美主义,而不具备时代属性,这是与社会及其需求的对立,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并总结道:柯布西耶是在自由流动的“空间幻想”中工作,其设计风格是一种技术浪漫主义的创造性狂热。对此,佩夫斯纳宣扬“为社区而创造”的重要性,他高度赞赏现代主义艺术创造和建筑设计,以及集体协同工作的观点,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现代派的艺术理论工作者应当肩负责任与使命,类似于他在德国期间出版的有关“现代主义运动”著作那样,向世人宣扬新风格理念及其优点,同时捍卫现代主义的立场,实现自己的宗旨,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然而,他的理想主义情怀被1933年的德国政治拒之门外,并不得不被迫转移海外,这宣告了他基于德国社会的民族性现代主义运动在现实发展中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1934年,在英国商务部负责人菲利普·萨尔甘特·佛罗伦萨(Philip Sargant Florence)的支持下,佩夫斯纳受到了来自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奖学金资助,旨在开展针对英国工业的实际调查研究。为此,他必须访问英国工业制造公司以及零售业的主管或设计师,以获取有关设计师的现状、设计方法及其设计单位成功实现优良设计的各种方法的新数据,最重要的是关于是否满足大众口味的数据。这项工业设计调查持续到1935年,并最终在1937年编著出《英国工业艺术研究》。在书中他提出的问题涉及公司的历史和规模、销售额度、行业中的设计准则以及是否设有专门的设计部门,并讨论了设计与商业艺术家的联系,与艺术院校的关系。正如佩夫斯纳在其中所叙述的那样:“如果现代风格与可以揭示我们时代特征下的私人财产的萎缩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的话,那么,这只能是由于艺术以及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表现的某种根深蒂固的时代精神而已。”佩夫斯纳对于英国工业产品的调查研究,囊括了从“高端定制”到“廉价批量”的工业生产,他将经济学的观察视角融入对社会学感兴趣的艺术史论中,并取得丰硕成果。他的研究报告分为“数据”与“结论”两部分,直观地反映了佛罗伦萨的经验主义方法,佩夫斯纳与佛罗伦萨不仅仅只是记录现状,而因现实情况难以满足他们的预期需求,为了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佩夫斯纳实事求是地告诉大众英国工业的真实情况,即90%的英国工业工艺都是毫无美学价值的产品,并谴责了所有“冒牌立体主义”、建筑立面、人工材料以及对细节与表面的强调,主张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品质设计,以此告诉大众什么是好的设计和坏的设计,并成功利用德意志制造同盟和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引起了英国本土制造商的重视。对于佩夫斯纳而言,现代主义设计也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它代表着对于生活的一种真诚的当代表达,艺术史家不能再与当代的需要脱离开来,这是因为设计是个社会问题。
佩夫斯纳的现代主义观点除了受英国本土展览会、出版物、个人调研以及工业设计委员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以德国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运动的指导,他突出强调“功能主义”这一核心标准,认为这是设计之美的先决条件,体现在形式的简洁以及对技术与材料的诚实中。佩夫斯纳对包豪斯风格的偏爱也满足了他的个人品味,他曾购置了现代化批量生产的厨房(图3),还热衷于推广钢管椅,在他的现代主义视角中,直接和简单以及功能的设计备受推崇,因为这是代表着时代的风格(图4)。此外,佩夫斯纳对于汽车设计也十分着迷,尤其是对流线型汽车设计感到满意,他认为流线型汽车可以成为现代运动风格和时代精神的真正标志,现代设计是钢铁的时代、速度的表达,而流线型代表着汽车制造商的一种“冒险和进取精神”,这类“现代化的外形”也满足了消费者的意愿,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以理想的方式和工业设计过程联系在一起。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对简洁新颖的迷恋与坚持功能标准之间选择平衡,即“功能的清晰,精确的表达”仍然是佩夫斯纳对于汽车工业设计的评估要求。

图3 厨房由埃里希·迪克曼(Erich Dieckmann)于1927年在包豪斯设计,最初由佩夫斯纳拥有,格拉西博物馆(莱比锡)馆藏

图4 左图为马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管状钢椅(1925)和家具(1927)(1)图片来源:N.Pevsner,《英国工业艺术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37年第7版。右图为高登·罗素有限公司(Gordon Russell Ltd.)所设计的家具套间(2)图片来源:N.Pevsner,《英国工业艺术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37年第5版。
在英国进行的工业设计走访调查,使佩夫斯纳产生了新的使命,在这一阶段,他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即道德的义务。为了获得更加详细的调查结果,他环游伯明翰,第一次关注到了较为贫穷的工人阶级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问题,他们被剥夺了太多的自由与生活乐趣,佩夫斯纳为此想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作为奋斗目标。他认为廉价产品的美学价值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坚信普通大众能够负担起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生活用品,为此还应提高产品的设计标准,他呼吁政府干预工业发展的计划、清理贫民窟并重新妥善安置民众、改善基础教学环境设施、实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水平,甚至还考虑以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他所认为迫切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彻底改变。
佩夫斯纳的现代主义叙事与他早年受到的德国教育及其工作经历紧密联系,他将史学与现代主义设计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相结合,分别在《现代运动的先驱》与《英国工业艺术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推广。他概述不同国家及其不同时期的设计风格,并深入刻画相关的“英雄主义史观”,结合英格兰与德意志的改革运动影响,从威廉·莫里斯到亨利·凡·德维尔德,再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及其包豪斯,这条连续的历史主义叙事脉络成为《现代运动的先驱》的核心,为佩夫斯纳在《英国工业艺术研究》中对当时情况的实际调研提供了历史背景。[12]《现代运动的先驱》用矛盾和冲突叙述了现代主义设计的缘起,从莫里斯排斥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师对于社会压迫无所察觉,到格罗皮乌斯兼容并蓄了社会责任和工业机械化,他们之间其实就是一个历史单元的阶段,莫里斯奠定了现代风格的基础,通过格罗皮乌斯,它的特征最终得以确立。佩夫斯纳将这一过程解读为一以贯之的努力,主要是为了改良高雅艺术脱离社会的状况这一社会弊病。[13]而在《英国工业艺术研究》一书中,佩夫斯纳将“设计标准化的出现同阶级差别的缩小”视为彼此相关的,该书宣传民居装饰设计以及日常生活制品中的现代主义,涉及阶级对现代工业设计的有害影响,对此,他评论道,“如今设计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大众而非个人”,佩夫斯纳俨然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看作是道德与社会改革的工具。
佩夫斯纳以《现代运动的先驱》和《英国工业艺术研究》两本著作搭配,相互补充、切换,建立了他的现代运动史观。在《英国工业艺术研究》中,他阐述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对于改善英国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解释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以包豪斯为代表的工业创新,借此高度评价了格罗皮乌斯是“时代精神”的里程碑。而在《现代运动的先驱》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英国在19世纪朝向现代运动所迈出的崭新步伐,革命性的转折从莫里斯开始。这样,佩夫斯纳完整地将英格兰和德意志这两块土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设计史里程,现代运动起源于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而今,在佩夫斯纳的倡导下它将以新的面貌回归英国,继续发展,直到恢复曾经的荣光。
四、结语
佩夫斯纳从未低估艺术史或设计史对于过去及现在所连接和产生的影响力,他认为设计师是一个发明和绘制物品提供给使用的人,当人们使用这些物品的功能时,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满足当代的需要。可以说艺术应该是实用的,赋予创造艺术的意义,就像是中世纪传达宗教思想和规范时一样。艺术与设计史学家应该时刻了解当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并将学术研究同当代需要联系起来,通过研究“人类心灵的视觉表达”,能够让设计师和社会大众认识过去的艺术家或设计师是如何面对当时的需求,又是如何勇敢地为社会的利益工作。[14]佩夫斯纳认为仅仅关注史论上的设计或艺术杰作、审视和描述其历史或美学思想背景下的意义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在艺术与设计史上追踪思想,查找功能线索,更好的艺术或设计家才能承担在社会改革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义务。此外,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也表明,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运动在艺术及设计史上的发展并非局限于地理上,它在国家间的界限中不受阻碍,应该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艺术或设计之间,实际上保有强烈的跨国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