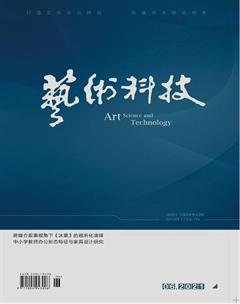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夺冠》中集体记忆的建构研究
摘要:受市场经济和政治宣传影响,电影这一媒介脱离不了话语的权力逻辑。主流体育题材的电影在构建国民集体记忆的同时,又能够成为维护权力合法性的利器。个人记忆话语在被民族国家话语收编的同时,体育传播场域的集体记忆也被打上了或深或浅的意识形态烙印。国人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召唤下,将自身奋斗与国家的愿景紧紧联系起来。本文以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夺冠》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如何使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策略,设定一种“创伤与受辱后的民族崛起”价值框架以构建集体记忆,研究集体记忆理论在体育传播场域中发扬中国特色的实践。
关键词:集体记忆;体育电影;女排;媒介;《夺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02
1 集体记忆与大众传媒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将集体记忆表述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重构。“过去决定和消解着现在,而过去又是虚无的一部分”[2]。集体记忆需要依赖媒介活动进行保存,媒介作为一种存储机制和传播手段,在集体记忆的形塑中充当了记录者、传播者等诸多角色。在体育传播的场域,大众传媒是受众接触女排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电影创作者以故事叙述的形式将集体记忆进行“再生产”,使之成为叙事与传播的主体,对集体记忆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排电影贯通记忆和想象的道路,重组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想象,呈现了一幅崭新的记忆图景。影视媒介具有直观迅速、代入感强、欣赏门槛较低的特征,使得大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集体记忆的建构权力,让集体记忆的传播范围与效果实现有效扩大。影视作品将原本对过去的私人的记忆与想象,转化为了对集体记忆的公共的回望和重塑,让集体记忆摆脱时间的线性结构束缚,成为一种经验的凝聚。受众自发参与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之中,使“身体缺席”变为“符号性在场”,使集体记忆的建构具有更多的能动性。
2 《夺冠》中集体记忆的建构
中国女排作为极具象征性的体育群体,承载着中国广大民众记忆的过去与未来,对构建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从一定意义来说,体育电影反映了时代的意识,不同的体育电影折射着不同时代的诉求,反映了时代的转向和发展,承载着国人对时代的感受和思想。陈可辛导演的《夺冠》是基于“中国女排”的国民集体记忆改编拍摄而成的一部纪实体育题材电影,电影里的故事时间跨度达40年。电影以郎平这一人物的经历为主线,“集合了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不同时期的价值观”[3]。影片选取三个时间节点,穿插不同时期中国女排的影像,唤起了广大群众对“女排精神”的时代共鸣与对体育精神变迁的思考。
2.1 20世纪80年代的苦难叙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刚刚回到正常的发展建设轨道,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所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4]。竞技体育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与国家的兴衰荣辱密切相关,体育比赛的胜负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形象,也影响着国人望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勇气与信心。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电影用暖色调和大面积逆光以展现回忆的场景,直接将观众带入20世纪80年代女排队员训练的情境中。质朴的服装和发型、墙壁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标语、高亢的吶喊声,无一不体现出这一时期奋勇拼搏的时代精神。当时,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所有队员几乎浑身都伤痕累累,但他们从肯不停止训练,影片中,青年郎平为了有参与训练的资格,冒着腰部受伤的风险苦举杠铃,为求胜利,不计后果。事实上,当年女排队员经历过大年三十晚上来不及吃年夜饭,就被召回训练的情况,“在我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爱国主义、报国主义是民族心理的支撑”[5]。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当让位于集体,电影中的这段故事情节揭示了一代女排人牺牲小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当美国已经用计算机分析训练数据时,中国的队员只能把网升高15 cm继续苦练,这一段情节将我国因技术落后只能靠努力的现实情况展露了出来。出国比赛前,青年郎平和陪打教练在机场喝“上海牌”咖啡,说了句“真苦”,相较于语言符号,视觉符号拥有着更强的表征以及话语构建的能力,咖啡作为影片中的非语言符号,其象征意义溢于言表,在电影后半段,郎平对新生代的女排队员们说“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苦过来的”“共同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构成了驱动力”[6]。
1981年,当中国女排对战日本取得胜利后,镜头转向了大街上,人们拿着彩旗、彩灯在马路上欢呼。全国都沸腾了,这一画面似梦幻又真实。中国女排获得“五连冠”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方面发展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人普遍存在一种“耻感”,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五连冠”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电影中,“国家振兴”成为叙事的结构框架,“孔飞力教授指出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7]。中国女排被塑造为泛政治化的民族英雄或是地方精英形象,“大部分受众会对‘最美人物产生一种敬佩和感动之情,甚至感到崇拜和敬仰”[8]。从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到不断崛起的过程,电影通过艺术化的呈现方式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复兴的无限憧憬复现出来,并纳入集体记忆的历史框架之中。
2.2 21世纪的沉寂与折戟
郎平作为美国女排的主教练带领美国女排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打败了陈忠和执教的中国女排,这一段矛盾在影片中被消声和弱化,只能通过观众席上的怒骂口型推测出这段饱受非议的往事。中国女排在2008年的比赛后走向衰落,电影中一个队员选择退出国家队去考大学,她认为打球不应该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应重视个体的命运与生活状态。当年的郎平在面对同样境地时却无从选择,为了集体荣誉与国家使命,她只能在打排球的道路上一行到底。两种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但却展现了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变化发展的背景下,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迁。最终,多年海外漂泊的经历、一身伤病的躯体、队友临终的嘱托等因素让郎平决心回归祖国,回归中国女排。
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者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认为大众媒介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纪念对公众议程影响深远。影片以“历经荣耀后落入低谷”作为叙事主轴,将“老女排精神的传承与革新”作为结构框架以构建新的记忆,由此,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内核被置入21世纪新的时代语境,连成了一段内涵饱满、层次叠起的记忆曲线。
2.3 改革阵痛后的再度夺冠
“思维决定内容”[9],重掌中国女排帅印之后,郎平对排球的理解积淀得更为深刻,科学的现代化实践方式和体育精神也极大促进了中国女排的革新,“夺冠”这一老女排毕生追求的至高目标,不再是新时代女排的唯一追求,运动员的成败得失与国家尊严荣誉之间的关系也不再被刻意放大。“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天然本性”[10]。每一个运动员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在达成集体荣誉的同时,也能实现自身幸福与未来规划。片中丁霞和徐云丽有一个互动的情节,她们互相猜对方心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徐云丽立马就猜到丁霞的答案是“自己”,这一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90后”的思维方式。郎平给女排姑娘们放假,让她们“去谈恋爱吧”,鼓励她们“过去的包袱我们扛,现在你们只管放开了打,享受运动本身”“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是拘泥于一时一事的成败,从而拥有更宽阔的胸怀和更为深邃的目光”[11]。
过去,女排精神是集体、是一代人拼搏的象征,现在,从个体角度为女排精神注入新的内涵,在中国崛起的今天,这种精神内化为强大自信的力量,它不再需要外化的表现去证明,中国女排除了使命感,有了更多的内生动力。这种对女排精神的新理解,促使郎平带领新一代女排重新回到世界之巅。“在经历过‘虚无飘渺后的个体生命选择,才是评判人性的准则”[12]。2013年至2016年,电影镜头打破时间轴线,在几场会议和新的训练模式之间反复切换,展现中国女排的变化。直到2016年奥运会,中国女排对主场巴西,比赛中郎平利用数据分析,采用策略替换球员,通过科技和智慧的组合,重新诠释了女排精神。电影中这一部分议程的设置更多地关注到了女排的专业性与人文精神。
3 集体记忆的建构的局限性
《夺冠》试图用中国女排精神的时代变迁来表现中国近40年的发展变化,“女性形象一直是电影和有关时局媒体的中心特征”[13]。郎平的人生经历最能彰显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她经历了40年来中国女排的巅峰与低谷。成为教练后的郎平角色由演员巩俐塑造,更多展现出的是一种含蓄、内敛的人格特质,受电影时长限制,剧情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和故事赋予人物更大的张力。电影为了串联历史与现实的记忆关系,维系集体记忆的精神内核,突出表现了女排队伍中的一些典型人物,如朱婷、张常宁、惠若琪等,当这些真实的女排队员出现在荧幕中时,真实与虚构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通过训练和比赛录像中的女排人物形象,观众只能依靠对这些运动员的有限认知和不全面的理解完成记忆的想象,不能了解到真实的个体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关系意识十分强烈,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大”[14]。“传播的本质不仅在于信息的传递,更在于关系的构建”[15],创作者想要讲述某位运动员的真实故事,往往只能利用台词来表现,无法更加深刻地在社会关系层面进行表现。
“艺术或多或少渗透着人世的各种情感内容和特定时代与民族的社会功利”[16]。从浅层次来看,集体记忆的构建来自大众传媒,但实质上却受多种因素影响,“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叙事视角的观照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性质”[17]。中国女排国民记忆的媒介构建蕴含着脉络清晰的权力逻辑,主流体育题材电影能够在构建国民集体记忆的同时,维护相关权力的合法性。
4 结语
个人记忆话语被民族国家话语收编的同时,体育传播场域的集体记忆也被打上了或深或浅的意识形态烙印。国人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召唤下,将自身奋斗与国家民族的愿景紧密联系起来。电影传媒使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策略,设定了一种“创伤后民族崛起”的价值框架,是集体记忆理论用于体育传播场域中以发展中国特色的有益实践。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
[2] 陈子诺.再谈《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时间意识[J].戏剧之家,2019(31):214-215.
[3] 周知新.试论中国兰文化的发展脉络[J].大众文艺,2018(07):246-247.
[4] 陈芳芳.试论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生态美学思想[J].艺术评鉴,2019(11):158-159.
[5] 庄众显.浅析唐诗宋词中楼台“愁”意象的人文情怀[J].汉字文化,2018(9):16-17.
[6] 刘千萌.人林共生时代:国有林区林俗文化建设探究[J].汉字文化,2020(4):174-176.
[7] 庄众显.我国古代神祗崇拜中多阶层作用互动机制分析——以关帝崇拜为例[J].汉字文化,2018(7):112-113.
[8] 黄闽倩.“最美人物”现象的受众审美心理分析[J].戏剧之家,2019(31):229-231.
[9] 张砚宸.說话是重要的修行——基于传统经典的阐释与反思[J].汉字文化,2020(3):58-59.
[10] 黄闽倩.生态美学视角下的春节文化探析[J].汉字文化,2020(10):171-172.
[11] 庄众显.浅析苏轼《赤壁赋》中天人合一思想[J].青年文学家,2018(20):80-81.
[12] 吴若菡.孤独与死亡笼罩下的个体生命追求——以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为例[J].大众文艺,2019(12):34-35.
[13] 朱克迎.姜文电影的人物形象美学赏析[J].戏剧之家,2019(06):85-86.
[14] 张砚宸.传统东方插花文化的历史探索及现代性融入[J].汉字文化,2019(20):168-169.
[15] 王全权,张卫.我国生态文明的对外传播:意义、挑战与策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149-153.
[16] 王全权,周碧琬.论国产动画电影中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及其影响——以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为例[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7-21.
[17] 朱克迎.人物纪实类网络短视频和人物通讯的叙事学比较[J].大众文艺,2019(07):85-86.
作者简介:季一格(1995—),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