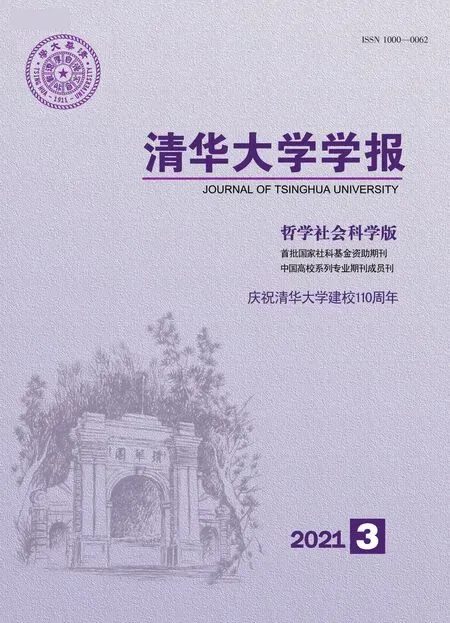康熙《皇舆全览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
韩昭庆 杨 霄 刘 敏 何国璠
利用地理坐标来表示地球表面任何一点的位置是目前通行的地图绘制方法,这一方法最早来自西方。中国传统地图绘制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很少考虑地物之间实际位置关系的山水画式的地图,另一类是基于一定测量基础上绘制的地图。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理论“制图六体”仅解决将地表三维的地物转绘到二维平面上的问题,①韩昭庆:《制图六体实为制图“三体”论》,《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4期。而无法解决地球球体是不可展开曲面的问题,故传统绘图方法无法准确表示较大范围地理要素之间的位置关系。清初康熙皇帝认识到这点,于1708年下令开展对其统辖疆域的测绘工作,测绘由清政府组织,来自西方的八名耶稣会士及一名奥古斯丁神父负责技术指导,地方官员承担后勤保障,最终于1717年完成测绘,并编绘成图,该图即康熙《皇舆全览图》(以下简称《康图》),这是中国史上首次官方组织实测,并用经纬度表示地理要素的地图,因其覆盖范围之广、测绘科学性之强,在当时举世无双,故在中国和世界地图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据汪前进研究,《康图》主比例尺为1:140万。②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该图系统地记录了三百年前占超过我国目前陆地面积2/3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③由于今新疆、西藏一部分未进行测绘,且没有明确的测绘范围,此数字是个约数;此外今内蒙古、贵州及吉林等省区境内各有小部分区域未测绘。保留了大量具有相对准确地理位置的政区地名和部分聚落的信息。据对本文第一作者主持完成的数字化福克司版《康图》初稿的统计,这些地名数量达9 222条,此外还有3 563座山岭及名称,标注名称的河流多达5 722条,蕴含丰富的地理信息,故《康图》亦系我国三百年前完成的一套地理国情普查资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因而亦成为我们在从事大范围、长时段的环境变迁等历史研究时,应当参考的一套地图信息资料,对其精度的研究将有助于学者对该图的利用与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翁文灏首开《康图》研究之滥觞,①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方豪补充了有关台湾测绘的中西文资料。②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图考》,见《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557—604页。此后的研究涉及测绘过程及测量方法的探讨、③丁延景、谭德隆、罗寿枚等:《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广东师院学报》1977年第2期。该图版本和各地测绘时间的考证、④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李孝聪:《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见氏著:《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第185—206页。该图投影方式的研究、⑤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陆俊巍、韩昭庆、诸玄麟等:《康熙〈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的统计分析》,《测绘科学》2011年第6期。该图表达的空间范围及在今图上的复原、⑥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历史地理》第3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9—300页。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影响、⑦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图面内容的研究、⑧杨丽婷:《清代东北历史地理研究——基于清廷三大实测全图的考证与复原》,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6年;靳煜:《康雍乾三大图上的西域——相关地理知识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7年。以及它与《乾隆十三排图》的关系等。⑨汪前进:《乾隆十三排图定量分析》,见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3—119页;韩昭庆、李乐乐:《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2019年第4期。康言对该图的测量工具、参与测绘人员构成、该图编绘的信息来源等方面进行了较以往学者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⑩Mario Cams,Companions in Geography: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C.1685-1735),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7.经过以上学者的努力,逐渐深化了我们对这次官方测绘背景、方法及过程的了解。
《康图》的精度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引起我国现代地图学奠基人曾世英的关注,他把北京等24个城市据当时实测结果推算出来的每个城市中心的地理位置,与基于《康图》及《乾隆十三排图》基础上编汇的《大清一统舆图》记载的相同地点的经纬数据进行比较。据该文计算得出,平均经差值为6.5′,平均纬差为3.125′,经差值大于纬差值,是纬差值的两倍。⑪曾世英:《经纬度测量与十八世纪以来之中国舆地图》,《地质论评》1942年第4—5期。曾世英文发表近半个世纪后,汪前进利用此图的英译本,对长城以南15省的497个测算点进行了精度的测算,得出平均纬度误差值为5.1′,⑫按照原文,正值平均误差值为5.4′,负值平均误差值为5.6′,按此计算其绝对平均误差值似应为5.5′。平均经度误差值为11.5′,平均纬度误差值最大的是河南省,为7.8′,最小的是贵州省,为3.2′;平均经度误差值最大的是广东省,为23.5′,最小的是江西省,为4.4′等结论,⑬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90年,第3—4页。这是当时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但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其结论亦具有阶段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无法得知当年的实测地点,故曾世英文和汪前进文基本都是自定义施测地点,这样得出的精度结果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性,为更好解决这个问题,须另辟蹊径。
一、《康图》绘制精度的研究资料及方法
康熙年间进行的大地测量,国内除了留下汉字或满汉标注的几种地图外,有关测绘的中文记载很少,而留下的测量数据更无从得知。不过这套地图经由参与测绘的耶稣会传教士之手,传播到了欧洲,由法国皇家制图人员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参照该图重绘之后,收录在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于1735年在巴黎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以下简称《全志》)中。除了地图,在该书第4卷末附表列出共641个测绘点的经纬度值,这是现存唯一的数据,本文研究对象即为《全志》所列的这些点值,这与汪前进文一致,不同的是,汪文使用的是英译本,本文采用其母本法文《全志》所附的地图、641个地名及其经纬度值。图1是北直隶部分地名及经纬度值表的范例,最小单位为秒。①Jean-Baptiste Du Hald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Vol.4.Paris:P.G.Lemercier,1735,p.473.

图1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附表中北直隶的部分经纬度值表
目前对古旧地图质量和精度的分析,主要有以下方法:一是根据起算点经纬度定位误差和调绘作业方案大致推算地图精度;二是根据古地图和现代地图中的同名点相对位置定量评价古地图的精度。关于《康图》的绘制精度,曾世英文与汪前进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计算结果可定义为绝对精度。由上可知,除极个别地点外,现今已很难确定当年在每个城市或州县施测的具体位置,故这样得出的精度结果可能失真。有鉴于此,本研究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参考《全志》书后保留的《康图》测绘点信息(其经纬度称为原值),对地理配准校正后《康图》中的这些测点进行数字化,采集其经纬度信息(称校正值),将校正值与原值进行对比,统计其偏移程度以表征《康图》绘制的相对精度。
1.《康图》数字化底图的获取
本研究中的《康图》数字化底图主要来自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扫描图,扫描精度为450dpi。鉴于一些扫描图折痕过大容易导致变形,山西、山东、河南、江南、江西以及四川省采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官网提供的电子扫描图,总共完成37幅地图的数字化。
2.《康图》地理校正与测点数字化
由于《康图》采用经纬网控制其精度,属于有较精确地理参考的地图。本研究在进行《康图》地理特征分析后,根据原图经纬度网格建立地图影像的空间参照,采用经纬线交叉点对扫描后的图幅进行地理校正。先将这些扫描地图中的中央经线经度调整为北京观象台的标准经度(关于中央经线为北京古观象台的分析见后),每幅图皆选取9个经纬度格网交叉点作为控制点,个别图幅或增或减,利用ArcGIS10.2完成地理配准,采用一阶多项式仿射变换完成数字化坐标与地理坐标的转换,并将每幅图所有点的总值的变换均方根误差(RMS)控制在0.05°以内。据汪前进研究,该图采用的投影方式为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亦称桑逊投影),②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但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本文决定采用WGS1984地理坐标系,其一,WGS1984地心坐标系是目前通行的一种坐标系,使用该坐标系可方便与目前基于同样坐标系构建的数据库的比较;其二,不同地理坐标系导致的省际范围的变形较小,对本文评价《康图》绘制空间精度的计算结果影响有限。在选定坐标系之后,分别进行点、线、面要素的分幅矢量化。
3.《康图》绘制相对精度定量评价
首先,提取矢量化后点图层中可与《全志》书后保留的测绘点相匹配的点,提取其经纬度信息,并与《全志》中测点的经纬度原值进行比较,计算两者偏移的程度。如果偏移值越小,则说明当时测量准确度越高,反之则准确度较差。这种方法由于无需考虑原测点在今天的位置,而是直接采用配准后地图绘制的相对位置(经纬度)与书后记载的同一地名位置相比,能较客观反映《康图》中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便于我们理解不同区域制图的相对精度。需要指出的是,法文书后虽然列出641个地名的具体位置信息,但由于地图中标注的地名与书后地名名称及数量不完全相同,难以做到地名的完全匹配。因此,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数字化福克司中文版《康图》,完成31幅地图的数字化,利用空间叠加比较的方式,复原《全志》图中地名的中文名称。与此同时,也利用书中记载的点的坐标值与福克司版《康图》相较译出中文地名,之后在ArcGIS中利用连接功能把《全志》图与书中具有相同中文地名的点匹配出来。值得指出的是,长城以北的地名存在地名汉译拼写变化较大且一些区域测绘误差较大的情况,而长城以南的中文地名拼写较易识别,按此方法,书后列出长城以北137个地名中,与所附地图中可匹配的只有82个地名,长城以南504个地名中,与所附地图匹配成功的有473条。
二、《康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
考虑到长城以北地区十分广袤,但可以匹配的82个点只占书后同区域范围内地名总数的60%,而且这些点集中分布在今黑龙江和内蒙古中部,故本文与汪前进文一样,对《康图》精度的计算也只限定在长城以南的15个省区内,该区域可以匹配的473条地名达94%,各省可匹配地名点数见表1。表1还显示了平均经差、平均纬差,以及最大纬差(负数表示偏南),最大经差(负数表示偏西),其中平均经纬差分别为《全志》载地名经纬度原值减去数字化产生的校正值的绝对值的平均值,最小经纬差一般为零,故表中未列出。

表1 各省可匹配点数及经纬偏差值表(按平均经差值由小到大排序) 单位:分
如果由原始数据计算,得出最大经差和最大纬差皆发生在河南,如表1中红色行所示。但通过对《全志》原图出现最大值的点的位置与书后记载的经纬度值进行对比之后发现,皆为《全志》书中出现的笔误。其中书后记载的河南仪封县(Y fong hien)纬度为35°55′E,经度为1°21′N,图上仪封县的经度值相符,但纬度实为34°55′E;卫辉府《全志》书上经度为1°12′30″N,纬度是35°27′40″E,与图上的纬度相符,经度实为2°12′30″E。这两个误差最大值经修改后,则河南修正后的平均纬差和经差分别为0.044°和0.023°,将这两个值替换后,计算得出法文图上长城以内15省的平均纬差为0.96′;平均经差为4.5′。平均经差差值是平均纬差的四倍多,大于曾文和汪文计算结果的两倍多。
表1显示除了湖广与陕西,其余13省平均经差皆小于15省的平均值,其中北直隶的最小,为0.72′,陕西最大,平均经差高达40.62′,远远超过其他各省值,这应该与陕西和始测点北京的距离有直接的关系。平均纬差最小的是山东,为0.42′,最大的是河南,为2.64′,其中10个省的平均纬差小于平均值。纬度的测量主要通过对正午太阳高度角和夜间北极星高度的观测两种方法,它的准确与否与天气状况、测量方法、测量工具以及测量人员的素质都有很大关系。河南即便修正后,其纬差仍然是最大的,河南的测量人员构成是雷孝思、冯秉正、德玛诺,他们测量的浙江省纬差也超过了平均值,为1.2′,福建为0.9′,江南为0.84′,与平均值相差也不大,故测量结果可能与测绘人员有一定关系。
由上可知,经差最大的省发生在西部的陕西和中部的湖广,分别为40.62′和4.62′,纬差最大发生在北直隶和河南,分别为2.09′和2.64′。图2是偏移向量图,可直观反映每个点的原值与校正值的偏移距离和方向,图上可以看出,除了陕西和河南的点偏移较为明显外,其余各省偏移程度并不大。图3系在今图上表示的各省偏移的平均距离,亦可反映各省标准值与原值之间的平均偏移程度趋势。两图的制作过程是,把数字化图上的WGS1984的地理坐标转换成Clarke_1866_Albers投影坐标系,以米为单位,得出校正值的投影坐标,然后通过ArcGIS上的连接功能把与《全志》图中匹配的473个点导入到图上,产生一套原值的投影坐标,得出图2。在此基础上,用书后点的原值减去校正值计算得出偏移距离,以省为单位计算得出图3。图3也显示,有9个省的偏移程度小于平均值3 987米,其中山东、江南及贵州的偏移距离最小,都小于3 000米,因而准确度最高,河南、大致相当于今湖南及湖北两省的湖广和包含今陕西和部分甘肃省的陕西准确度最低。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的偏移最显著,偏移距离几近60公里,是偏移程度最小的山东的26.8倍,成为15省中精度最差的一个省份。

图2 长城以南测绘点的偏移向量图

图3 长城以南各省平均偏移距离图
三、《康图》的绝对精度分析
以上研究揭示了《康图》中长城以南各省区绘制精度既相似又各有差别的特点,不过这种精度是一种相对精度,只有绝对精度才能获知该图的误差值。前述曾世英文与汪前进文计算的皆为绝对精度,但是采用的都是代用值,目前可以推知当时的测量点有三处,一处是北京的始测点,一处是原昆明市的钟楼附近,位于云南大学东陆校区文津楼东侧,①本文依据测点处所立的碑文内容分析,该测点为清初的一个测点。另一处是海南省三亚市“海判南天”刻石处。
笔者曾根据《全志》记载的北京零度经线的纬度39°55′反推,推测当时北京的零度经线可能为经过今北京故宫中轴线的经线,②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但是这个推测没有考虑到当时对纬度的测量仍然做不到十分精准的情况,故只是一种可能性。汪前进此前提出传教士是以通过北京古观象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但没有给出原因。③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第9页。根据笔者在《清实录》中发现的一条间接资料分析,可以论证汪前进的观点是正确的。“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己巳,谕和硕诚亲王允祉(即胤祉)等,北极高度、黄赤距度于历法最为紧要,著於澹宁居后每日测量。寻奏,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比京城观象台高四分三十秒,黄赤距度比京城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报闻”。④《清实录》卷二六〇《圣祖实录三》(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5页。由文中提供的畅春园纬度值与北京观象台的差值,可以算出当时观象台纬度正好是39°55′,而且这个时期又正好是《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年代,故现把零度经线经过的地点修正为过今北京古观象台的经线。此外,清末刊印的《大清帝国全图》的《凡例》明确记载,“图中经度以京师观象台为中线”,亦可为另一条间接证据。⑤《大清帝国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31年(1905)再版。至此,可确定《康图》是以今北京古观象台为当时开展全国测绘的大地原点。据笔者2016年3月分别在观象台门口和台顶实测的平均值的结果为39°54′23″N,116°25′42″E。由于这条经线当时设定为零度经线,无法与今日采用的过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产生的标准经度进行比较,所以我们只能比较纬度,其差值为37″,即当时的测值较今测值偏北约1 140米。云南大学老校区内的“云南第一天文点”,据笔者2019年8月的测量值为25°3′23″N,102°42′4″E。据法文书后记载,云南府的经度值为西经13°36′50″折算成今日标准经度为102°48′52″,纬度值为25°6′0″,二者的纬差和经差分别较今位置偏北2′27″、偏东6′48″。第三个测点根据宋爱军考证,该点系清朝《皇舆全览图》最南测量地点。①宋爱军:《“海判南天”与〈皇舆全览图〉》,《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第6期。据法文书的记载,海南共有7个点,最南的点书上记为Tsiao tcheou,图上记为Yaïtcheou,即中文中的崖州。当时测得纬度为18°21′36″,经度为西经7°44′0″,即108°41′42″,利用Google测得今日此点的位置为东经109°20′48″,北纬18°17′45″,纬差和经差分别为较今位置偏北3′51″,偏西39′6″。

表2 基于实测点位的《康图》绝对精度(经纬差) 单位:分
如同相对精度一样,表2中三个地点的绝对精度值也因地点而异。其中北京偏差最小,海南差值最大,这与前面得出的相对精度由北直隶、至云南,再至广东逐渐降低的趋势是一样的,说明相对精度的计算方法具有一定可取性。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地点的经纬差值并不小,但是当我们回溯到更早的时代,如利玛窦时代(1552年—1610年),会发现康熙年间的测绘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据方豪的研究,利玛窦利用近代科学方法与仪器作实地测量,并记载了中国8个城市之经纬度,将这些值与“今日”作一比较,方豪认为已经“颇相符合”。②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830页。方豪利用的比较单位是度,无法得出分、秒的差异,是比较粗略的比较。经差最小为北京的5°,最大的是西安的10°,平均经差高达7.8°,即便拿经差最小的5°与《康图》经差不到1°的值相比,《康图》绘制精度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再以古观象台的测值为例,把它与200年后的1907年据Brown对北京俄教堂测值推算的观象台测值39°55′1″E和116°24.7′N相比,会发现Brown测量的纬度值较《康图》只差1″,经差只有1′,直到1932年朱广才测量的观象台的纬度测值才做到与今天几乎一致,但是经度仍较今偏西13.5″。③曾世英:《中国实测经纬度成果汇编》,《制图汇刊》1943年第1期。此外,曾世英曾把1931年版湖南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和《申报中华民国新地图》上的湖南省地图与《康图》比较,高度评价了《康图》的测量成就。认为民国时期制作的两套湖南省图“较之二百年以前凭了简陋设备所得的结果,也仅做到不相上下的程度”,④曾世英:《经纬度测量与十八世纪以来之中国舆地图》。故无论与其绘制年代之前及之后的地图相比,《康图》皆是同时代地图产品中的翘楚。
四、《康图》各省绘制精度异同的原因
(一)相对精度较为一致的原因
图2的向量偏移图显示,《康图》的相对精度除了个别省份,总体偏移不大,且偏移程度相当,应与下面四个原因有关。
其一,丈量尺度标准的制定和确立。根据传教士安多记载,1702年康熙命令擅长几何学的皇三子胤祉主持测量一度纬度的距离长度的工作,从12月1日开始到22日结束,始测点是霸州东门外靠近城门的一座石头砌成的古建筑。⑤韩琦、潘澍原:《康熙朝经线每度弧长标准的奠立——兼论耶稣会士安多与欧洲测量学在宫廷的传播康熙朝经线每度弧长标准的奠立》,《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年第3期。最后按照一度纬度的经线长度等于200修正里的对应关系,规定新修正的一尺长度,约等于今天的0.308米,修正的1里等于554.4米,①Mario Cams,Companions in Geography: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C.1685-1735),p.79.简化并统一测量尺度为日后的全国测量打下重要的基础。
其二,法文书后罗列的641个点为当时全国测量的控制点,准确度相对较高。上个世纪翁文灏就指出传教士仅以九人之力,“自康熙四十七年始功,至康熙五十五年竣事,至五十七年而全图成”,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完成的工作主要是测定全国三角网,然后“各地之详图方可得而附丽焉”。②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这种认识可以雷孝思神父的记录为证:“受命作图者皆努力从事。各省重要地点必设法亲到,查阅各府州县志书,咨询各地方官,而尤要者即为以三角法测定全国三角网。盖应测区域幅员广大,欲从速成图,实以三角测量为最易。”③原文系法文,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876页。故据翁文灏文的分析和雷孝思的记录,当年传教士的任务主要是布设并测量三角网的控制点,这641个点应为当时记录下来的部分控制点。这些点皆经过仔细的测量,法文书后罗列经纬度的表头也明确了这一点,“部分实地观测的纬度和经几何测量得出的经度目录,用于绘制中华帝国地图,由耶稣会传教士根据康熙皇帝的命令进行观测”。
其三,传教士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测量工具。17世纪末,法国制造测量工具最有名的有Michael Butterfield,Louis和Jean Chapotot(父子关系)和Nicolas Bion等几家,此时无论是测量工具的数量还是准确性而言,皆胜于前代。④Mario Cams,Companions in Geography: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C.1685-1735),pp.102,24-25.据1720年代宋君荣(Antoine Gaubil)的记载,传教士们使用的一个可携带的直径70厘米的四分仪正是上面提到的Chapotot公司制作的,⑤Mario Cams,Companions in Geography: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C.1685-1735),pp.102,24-25.故巴黎制造的精密仪器为《康图》的绘制提供了契机。
其四,地图绘制的精度还与主持测绘的传教士密切相关,他们高超的技术、对基督教的笃信和坚守,并为之全身心的奉献皆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⑥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葛剑雄译,见《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6—212页。
(二)相对精度存在地区差异的原因
尽管总体上看,《康图》相对精度数据一致性较好,但也存在地区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其一,面积大小和测点数量的多少。据笔者数字化《全志》所附长城以南各省面积(见表3),在偏移程度最大三个省中,陕西和湖广的面积都很大,分别为43.13万km2和39.76万km2,存在区域面积越大,相对精度越小的趋势。此外,陕西境内仅列出29个经纬点,可匹配的27个点,而湖广的相应数字分别是54个点和53个点,即便这样,湖广的偏移程度已经偏大,则陕西偏移得更加显著,故精度与面积及测点数量皆有关。

表3 《康图》中长城以南15省面积 单位:万km2
其二,测量所花时间的长短与测量人员的水平。长城以内15省的测绘时间总计6年,各省测绘时间不一,如北直隶测绘时间为6个多月,江西与贵州不到5个月,①Mario Cams,Companions in Geography: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C.1685-1735),p.130.四川测绘的时间长达11个半月,②李孝聪:《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故法文书后四川保留的28个测点,应该只是部分测点,而且充足的时间也可以增加复测校正的可能性。此外,负责四川测量的传教士是雷孝思、费隐和山遥瞻,陕西的是麦大成和汤尚贤,雷孝思自始至终皆参与测绘,但麦大成则不然,麦大成是1711年加入,与雷孝思学习测量山东之后,他单独组织测绘队伍。事实上,由麦大成与汤尚贤负责测绘的有江西、山西、广东、广西和陕西等,这五省中除山西之外,其余四省偏移程度皆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河南面积仅为17万km2,测绘人员包括雷孝思、冯秉正和德玛诺,但是其偏移程度却排到第二大,比较特殊,这或许与另两位的测绘水平有关,又或有其他原因,有待将来研究。
五、结 论
曾世英与汪前进主要根据古地图和现代地图中的同名地点相对位置的偏移程度来研究《康图》的绘制精度,本文将其计算结果定义为绝对精度。但是除个别地点外,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康图》当年在每个城市或州县施测的具体位置,故前两位学者利用的都是代用数值,导致这样得出的精度结果可能会失真。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相对精度的概念,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康图》两个版本进行地理配准,之后对地理配准校正后《康图》中的这些测点进行数字化和地名匹配的工作,采集法文版中的经纬度信息,文中称校正值,参考《全志》书后保留的《康图》部分测绘点经纬度的原值,将校正值与原值进行对比,统计其偏移程度以表征《康图》绘制的相对精度。
除了湖广与陕西,其余13省平均经差皆小于15省的平均值,且差值不大,其中北直隶的最小,为0.72′,陕西最大,平均经差高达40.62′,远远超过其他各省值。10个省的平均纬差小于平均值,平均纬差最小的是山东,为0.42′,最大的是河南,为2.64′。从各省平均的偏移距离来看,山东、江南及贵州的偏移距离最小,因而准确度最高,湖广、河南和陕西准确度最低。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的偏移最显著,偏移距离几近60公里,是偏移程度最小的山东的26.8倍,成为15省中精度最差的一个省份。丈量尺度标准的确立、测点为控制点的性质、测图使用先进工具以及耶稣会士精湛的技术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是确保《康图》绘制精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但是受各省面积、测量点数量、测量时间,以及测量人员水平的不同的影响,使得各省之间的精度亦存在一定的差异。
感谢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徐锦华老师在查阅资料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