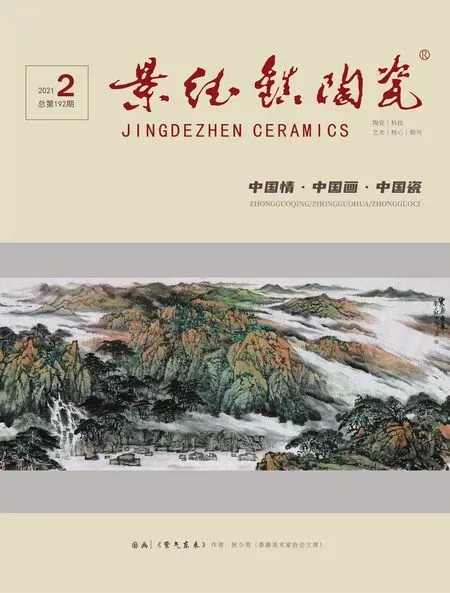民族文化影响下青花艺术造物的特质与风貌探讨
于 杰
一、蒙古民族文化对青花艺术造物的影响
1、信仰喜好与色彩
纵观历史,统治阶级的喜好会对艺术的走向和审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蒙古族自1206年成吉思汗立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至1368年被明所灭的百余年间,陶瓷艺术一改宋风,瓷业呈现出一种全面的创新气象和强大的创造魄力,游牧民族的色彩喜好、游牧传统、数字观念、装饰理念等均体现在青花艺术造物中。成就了独具特色的青花陶瓷艺术。
元青花的种种特征都与蒙古族的好尚血肉相连,据《史集》载,蒙古人的祖先是“有命于上天而生的”孛尔帖赤那,意为苍色的狼,其妻豁埃马阑勒,意为惨白色的鹿,也因这个传说,蒙古人一直崇尚青白二色。而且蒙古族最初信仰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奉“长生天”为天神,“其苍苍之色为神圣,其太阳之白为吉祥”,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代青花艺术的发展。
2、游牧传统与造型
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十分浓厚的民族内涵和文化积淀,因又曾居于统治地位,强势地保留了其风俗喜好。首先,蒙古人的迁徙习俗在建元后也得以延续,每逢春赴上都,秋返大都,他们转徙随时的生活多配以小型家具,器物多置于地面或低矮几案,瓷器高大有利于提取。同时为了迁徙方便,蒙古人在造型上也加入了特别的设计,如辽代鸡冠壶(图1)上“孔”的设计就是为了方便携带而在仿制皮囊、金银器时特意保留下来的,随着蒙古族人逐渐由游牧向半定居的生活状态转变,壶身“梁”(图2、图3)的设计应运而生,壶身也由适合马背上使用的高扁形转变为更符合定居生活的圆矮形。其次,蒙古族人饮食与中原不同,其饮食豪放,食物多为大块牛羊肉,食器大多厚重粗犷,形体巨大;但与之相对的是小型器物如青花高足杯也不见少数,这同样是因蒙汉文化交融,其喜好由酒精含量低的马奶酒到酒精含量高的蒸馏酒的转变而转变的。无论历史上孔与梁的转变、扁身向圆身的转变、高壶向矮壶的转变,还是的食器的大小形制,都是根据蒙古人民的生活方式而改变的。

图1

图2

图3
3、数字观念与装饰
蒙古族人“喜三重九恶七”,他们崇尚“吉祥三宝”,三与九都寓意吉祥,九是蒙古民族最重视的数字,据传是由于蒙古族的英雄成吉思汗“巧九喜九”,他出生后用九泉之水沐浴,九岁独立生活,二十七岁称汗。在一次征战失利向天祈祷时,空中落下一镞巨矛,随即下令用九十九匹公马鬃毛作其缨,九十九只绵羊来祭祀,并将这巨矛作为自己的军徽称为苏勒德,也正是成吉思汗对九的喜爱更加影响了蒙古族人对九的崇尚。
而七关乎惩罚,涉及丧葬。历来刑罚皆为整数,蒙古族虽沿用了唐以来的刑罚,但依忽必烈“天饶一下,地饶一下,我饶一下”的意思减为以“七”结算,所以在元代青花装饰中花纹层数如云龙纹象耳瓶(图4)一般,九层者甚多。

图4
4、装饰理念与革新
元朝的青花可谓异军突起,虽有传统题材的描绘,却常配伊斯兰特点的边饰,如珍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元代缠枝花卉纹菱口盘(图5),形成了多层分割、纹饰繁密、色彩艳丽、形式夸张的异域风格。元代的瓷器之所以有如此的创新和突破,首先是由于前代制瓷技术的深厚积淀,它有着唐宋先进的制瓷技术和艺术理念做后盾,在这基础上又注入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其中最为直接的要属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和土耳其工匠与中国本土工匠的共同努力,以及大批来自土耳其王公贵族或商人的来样定制的共同促进。正如吴仁敬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中所述:“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合,对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才使元代青花艺术展现出了独特的风采。而且元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这在为国家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为青花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思想的交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代工艺品的风貌,使其一改宋代装饰之简洁而走向繁复,更出现了异国风情的青花陶瓷艺术形式。
二、蒙古族文化在当代青花艺术造物中的融入与发展
1、融合传统与现代
传统理念与现代时尚看似两个相距很远的概念,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族文化符号的演化从未中断,并且孕育出一系列异彩纷呈的工艺美术成果。在当代青花艺术造物中,既要保留地域民族文化符号的传统精髓,又要把握现代艺术潮流,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技法进行重组与再创,从而使艺术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趋向与文化认同。

图5
2、关注人文情怀
陶瓷从一开始就兼具艺术观赏性与功能实用性于一体,当代蒙古族青花艺术的创新也要从功能上考虑,设计是以人为本、符合人的生理及审美要求的人性化设计,这也是近些年来十分重要的设计理念,被称作是设计领域的最高追求。功能性、人性化与其民族文化符号在艺术与设计中是相辅相成的,将艺术引入生活,同时也因民族、宗教、道德等的渗透使陶瓷艺术更加有了人文情怀。
三、总结
地域文化符号是地域文明、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能够引起人们共同的民族文化情感。广泛的将蒙古民族文化符号应用于陶瓷艺术造物中,已成为当今艺术领域的主流思想。在深入挖掘蒙古民族文化符号内涵的前提下,走现代特色的原创陶瓷艺术之路,是艺术与设计过程中理应贯彻的原则和理念,这不仅能丰富陶瓷造物的艺术表现,增强区域文化特性,同时也对振兴和发展民族特色文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