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周报》的背后
泉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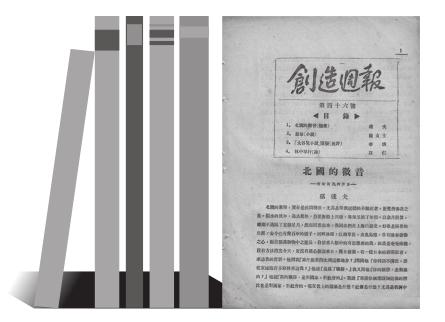
1923年5月1日《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中就发出了《创造周报》出版的预告,这预示创造社同人们又要以新的面貌出现于读者的面前。《创造周报》是前期创造社的主要刊物之一,它在1923年5月到1924年5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用52期思想论说赢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注意。这份刊物究竟在当时火到何种程度呢?“《创造周报》一经刊发出来,马上就轰动了全社会,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订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添人专管这些事。”
在《创造周报》创办伊始,时为创造社三驾马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是将它与《创造》季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它创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借助其周期短、篇幅小的特点以弥补《创造》季刊不足以反映时局重大变化,以及季刊中的文章引起的一些论争也常常不能得到及时答辩的缺憾,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就定位于刊发以具有“短、平、快”特点的思想评论、文艺批评为主,而创作和翻译则退居为其次。《创造周报》的发行量一直维持在3000—6000之间,在当时普遍注重创作的情况下,以翻译和评论为主的《创造周报》能够有这样的销售业绩已经十分不容易了,这从另一方面足以看出前期创造社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借此前期创造达到了它的全盛期。
壹
如果仔细翻阅《创造周报》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相较于《创造》季刊等当时文坛上的重要期刊来讲,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编辑策略,版面的设计相当简单,编排也非十分考究,内容上的错误相对于《创造》季刊来讲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那么多年青的读者对之趋之若鹜呢?创造社给我们最鲜明的印记无疑是其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人为核心的同人作家群体,《创造周报》共出版52期,共有文章201篇,在这些文章中郭沫若有72篇、成仿吾有30篇,郁达夫有13篇,他们三个人的文章总数大约有三分之二,不仅如此他们还轮流编辑,争作头一篇文章,这也是他们创办同人杂志的初衷和目的。
所谓的同人杂志,就是由趣味相投的作家集合在一起,但他们又不是结党营私,而是相互支持,互通有无,就共同关注的某个问题发出同一种声音,对别人的责难迅速作出相同的回应。同人杂志的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它也有非常致命的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并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人为核心的同人杂志——《创造周报》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特别是作为核心之核心的郭沫若与《创造周报》更是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通过考察《創造周报》中郭沫若所发表论文的数目及文章的类型便可以明显地看出郭沫若与《创造周报》的密切关系。郭沫若的文章一直持续到第40期以前,而且仅仅就在第20期没有发表文章外,8、11、12、13、15、28、29、34、35、36、37、38、39期是1篇文章外,其余的都在两篇以上,而成仿吾、郁达夫都没有能够发表如此数量的文章。而在41—52期中仅仅就41、42、47与52期有1篇文章出现。这较之前40期有了天壤之别。
从文章的内容与体裁来看,前40期郭沫若的文章主要是发刊词、翻译、诗歌、论说、通信、答辩、小说创作、杂感、寓言、介绍、研究、随笔等体裁的文章,而40期后的《周报》中郭沫若在有限的4篇文章中,仅仅就是3篇小说与1篇通信而已,与前一阶段十几种体裁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从文章所涉猎的范围来看,前40期主要的关键词是国家、艺术、革命、创造等等,而后期的3篇小说创作完全可以等同与郭沫若自我生存轨迹地生动写照。从这也似乎在预示着郭沫若在1923到1924年间的心路历程。
郭沫若的这些个人的行为与《创造周报》的兴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40期左右恰恰是《创造周报》由辉煌的顶点走向衰退直至停刊的开始。而《创造周报》创办这52期也即是1923年5月到1924年5月这段时间内,恰好也记录了郭沫若由日本回到国内从事文学活动由极力呐喊到无奈返回日本的整个心路的历程。一个人的命运的抉择与一份刊物的兴衰发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
郭沫若与《创造周报》建立起一种良性的连贯性,即版面之间的连续性。版面连贯性应主要强调本体性整体性和时间性整体两个层面,特别是内容丰富、版面构成元素复杂的期刊,策划者尤其要注意利用图片等手段吸引读者的视点,使读者阅读时有连续翻阅下去的冲动。
在《创造周报》的前42期中,仅仅就第20期和第40期中没有郭沫若的文章外其余的每期都至少有郭沫若的文章出现,其中有5期中有3篇文章,有20期中有2篇文章。而《创造周报》每期中包括通信、启示等非创作性的部分在内最多的也就5篇文章,这样看来郭沫若至少在前42期绝对是《创造周报》作家同人的核心。但是,从第43期到第52期终刊的10期内,郭沫若仅仅只在第44期和第47期发表了两篇小说以及第52期的一封通信。
郁达夫的13篇文章中的12篇也大多集中于前24期,而剩余的1篇则出现在第46期上。成仿吾的30篇文章中有13篇出现于前18期中,10篇出现于后10期中,而仅仅有7篇文章出现于从第19期到第42期的23期刊物之中。从第47期起郭沫若离开上海去了日本,《创造周报》就交由成仿吾来编辑和主编,因此在后10期中成仿吾的文章突然增多就不足为奇了,而从《编辑余谈》我们可以清晰的体味出成仿吾也是在勉力而为之,只是为了完成历史的使命而已。
这样看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郭沫若前期的编辑,就不会有《创造周报》的成功,而郭沫若的离去对于它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两者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便显而易见了。
贰
办刊物难,办周报类的刊物更难,主要的原因是如下:
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05)
《创造周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主要的是他们就拥有了这样一位“写文章的人”——郭沫若。
郭沫若在《创造周报》上刊发的文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精炼,富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鼓动力。《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是郭沫若刊发在《创造周报》第3号的一篇重要的论述文,文章开篇他便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直陈“中国的政治生涯几乎到了破产的地位”,“我们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我们受着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揉弄”,进而就呼吁到“我们要如暴风一样唤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要打破从来的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我想就是今天的读者阅读完这些激昂的字句后,也会迸发出热火灼烧的情感,更何况在“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呢?
难能可贵的是,郭沫若不是就仅仅只刊发《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篇战斗檄文,类似这样的充满火药味的批评文字几乎贯穿了《创造周报》的始末。如《艺术的评价》《神话的世界》《批评——欣赏——检察》《自然与艺术》《艺术家与革命家》《文艺上的节产》《瓦特·裴德的批评论》等一系列文章,正是郭沫若的这些文章,《创造周报》一下子便抓住了充溢着青春叛逆激情的“五四”青年的内心,使他们成为《创造周报》狂热的拥趸者,“青年作者的投稿不断增加,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每到星期六,总有不少读者在泰东书局的店头等候新出版的《周报》。案头上堆积得厚厚的新刊物很快就卖光了”(《郑伯奇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16),《创造周报》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他们走向文化战斗中心的舞台。
叁
郭沫若通过《周报》奉献给读者最好的礼物就是对于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的译介。正如郭沫若在翻译之前说:
尼采的思想前几年早已影响模糊的宣传于国内,但是他的著作尚不曾有过一部整个的 翻译。便是这部量有名的《查拉图司屈拉》,虽然早有人登了几年的广告要移譯他,但至今还不见有译书出来。我现在不揣愚昧,要吧他从德文原文来移译一遍,在本周报尚逐次发表,俟将来全部译竣之后再来汇集成书。
这部书的翻译一直持续到第39期,译到第二部第四节为止。而且郭沫若在第30期《创造周报》也即郭沫若将此书第一部翻译完成之后,专门撰写了一篇题目为《雅言与自力——告我爱读〈查拉图拉屈拉〉的友人》的文章。在此文章的刚开始部分郭沫若说:
我把《查拉图拉屈拉》的第一部译完之后,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是难解,要求我以后加些注译。仿吾也劝我在继译第二部之前,不妨先把尼采的思想,或者《查拉图拉屈拉》全书的真谛,先述一个梗概,以便利于读者。我在这一两礼拜来便停止了移译的工作,想依仿吾的劝诱,先把我对于《查拉图拉屈拉》的见解略述出来以当注译,但我再四忖度,在一种著作,或者一人的主要作品,尚未全部介绍于读者之前,便先把该作品或该作者的思想加以评究,这在授受两方,不仅是劳而无功,而且会生意外的障碍。
…… ……
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虚像;但我的反射率恐不免有乱反射的时候,读者在我镜中得一个歪斜的尼采像以为便是尼采,从而崇拜之或反抗之,我是对不住作者和读者多多了。一切的未知世界,总要望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劳力去开辟,我译一书的目的是要望读者得我的刺激能直接去翻读原书,犹如见了一幅西湖的照片生出直接去游览西湖的欲望。我希望读者不必过信我的译书,尤不必伸长颈项等待我的解释呢。”(《创造周报》第30号)
由此也显示了郭沫若对《创造周报》广大读者的尊重,和以读者为重的浓厚责任心。
为了满足读者更高层次文化阅读的需要,郭沫若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论文,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整理国故的评价》《古书今译的问题》《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天才与教育》等。观点清晰、深入浅出是郭沫若以上论文的共同特点,提出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更是郭沫若文章的特色,他在论述有关国家主义的概念时,就鲜明地提出:
我们中国本来是国家观念很淡漠的国家,在十几年前,军国主义正在世界上猖獗的时候,有许多人士很以此为可耻,而大提倡爱国。好在我们素来的传统精神,是远的目的是在使人类治平,而不在家国。我们古代的哲人教我们以四海同胞的超国家主义,然而同时亦不离弃国家,以国家为达到超国家的阶段。
通过这样的论述,就把复杂的国家主义阐释的清晰明了,读者也能领悟理解。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读者的重视,这也是《创造周报》为什么能够赢得读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沫若与《创造周报》互相成就了彼此,郭沫若决定了《创造周报》的兴衰成败,而《创造周报》也因其强大的传播效力,使郭沫若横刀跃马于“五四”新文坛,迅速成为了一颗闪亮的文化巨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