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对毛泽东的影响
刘悦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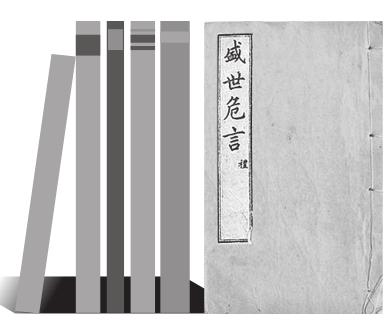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古今中外,经史百家,军事科技,阅读范围非常广博,其中有些书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他自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事情。而在他的少年时代,也有一本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的书,这就是清末实业家、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毛泽东家境尚可,因此小时候能够上学读书,学习了基本的文化知识。但是家境也没有富裕到可以让他一直自由读书的程度,因此在学习了基本的文化知识后,他的父亲便让他回家干农活了,这一年他13岁。但是,求知欲强烈的毛泽东已经放不下对书本的热爱和对知识的追求。3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向斯诺讲述了他少年时代读书求学的经历。他对斯诺说,他在干农活的同时,“还是继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但“经书除外”,这让他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就更这样了”,于是,为了读书,“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到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见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
人们在多年后回忆早年特别是童少年时期的事情时,能回忆起的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事情。《盛世危言》这本书是毛泽东从他的表兄文运(咏)昌处借的。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毛泽东早年手迹,就包括毛泽东给文运昌还《盛世危言》等书的还书便条,全文如下: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据考订,这张便条是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由长沙回韶山过春节期间写的,说明这本书在毛泽东处达七八年之久。之所以会有这张便条,据说是文运昌知道毛泽东嗜书如命,怕他不还,说:“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要先打条子后拿书。”故而毛泽东借书要打借条,还书也有便条,当然也可能是毛泽东因为书有损坏为了表示歉意才写的这张便条。不论如何,这张便条为少年毛泽东借读过《盛世危言》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毛泽东从文运昌处借的书,还有冯桂芬的著作《校邠庐抗议》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书刊,但是他对斯诺忆当年时只单单提到了《盛世危言》,而且还清晰地记得书中的主要内容,可见这本书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和對他的影响之大。
《盛世危言》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开阔了他的眼界,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使他对西方国家何以民富国强、欺凌中国,中国何以民穷国弱、屡屡挨打有了一定的认识,对郑观应提出的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主张和办法心有戚戚,所以他才“非常喜欢”这本书。受这本书的影响,毛泽东开始成为一个热切希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爱国的改良主义者。
二是重新燃起了他继续求学的愿望,他对斯诺回忆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这一年毛泽东16岁。之后他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可就在这时,“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的比较多。”“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这个表兄就是文运昌,这所新式学堂就是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想到这所新式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无疑也是受了《盛世危言》的影响。这一年毛泽东17岁。从此,这个走出韶山冲的少年一发不可收,在求学和求知的路上越走越远,从东山高等小学堂到湘乡驻省(长沙)中学堂,再到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在这过程中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新学说新理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盛世危言》之所以对少年毛泽东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自然是缘于这本书的新鲜内容和思想倾向。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郑观应。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16岁时应童子试,没有考中,即奉父命放弃了科举考试之路,远游上海,弃学从商。他早年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不仅积累了财富,更积累了经营、管理现代工商企业的经验。19世纪70年代被李鸿章揽入门下,从此跻身于洋务运动,备受李鸿章的重用,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重要职务。
郑观应并不只是一个追逐利润和财富的商人、实业家,更是一个爱国的维新思想家。他在从事于实业的同时,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自号“杞忧生”,正体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和渗透。对此,郑观应痛心疾首,“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为探索自强御侮之方,他积极了解西方的富强之道,“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在他看来,“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将自己的观感、思考笔之于书,刊布于世,期望引起国人对国家命运的重视和对自强之道的探索。他著述甚多,主要有《救时揭要》(1872)、《易言》(1880)等,而《盛世危言》(1894)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
如果说,《救时揭要》主要是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罪恶行径,反映了他对西方列强的义愤和痛恨,那么,《易言》则开始提出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方法,即改变传统做法(“易”即改变),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郑观应把《易言》称作《救时揭要》的续篇。《盛世危言》则是郑观应维新思想的集大成,标志着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走向成熟。所谓“盛世”,不过虚晃一枪,或者暗含讥讽,重点则在“危言”,即警醒国人之言,当时很多人就直接以“危言”称该书。
郑观应主张向西方学习,在方法论上与洋务派是一致的。但是,在学习内容上,却超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在他看来,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铁路电线、声光化电固然要学,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他是最早注意到西方国家富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中国人之一,批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技术是舍本逐末:“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他明确指出:“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业万难兴盛。”具体到经济上,郑观应还是主张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代表人物。
《盛世危言》造端宏大,包括附录在内共约200篇文章,内容十分丰富,从目录中即可见一般,诸如学校(2篇)、西学、议院(2篇)、自强论、公法(即国际法)、通使、交涉(2篇)、条约、汰冗、革弊、商战(2篇)、商务(5篇)、铁路(2篇)、电报、邮政(2篇)、银行(2篇)、开矿(2篇)、练将、练兵(2篇),如此等等,既有布新,也有改旧、除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富强救国”。可以说,《盛世危言》是当时一个全面系统的现代化方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此前一直接受传统教育,课上读的是“经书”、课外读的是《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旧小说的少年毛泽东,在看到这些文字时会是怎样地感到新奇、兴奋和激动。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引导他迈上继续求学、求知的道路,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作为郑观应最重要的著作,他对《盛世危言》十分重视,不断修订。1894年成书时是5卷本,1895年修订为14卷本,1900年再次修订为8卷本,尽管卷数增加又减少,但整体篇幅是一直增加的。除郑观应亲手修订的3个版本外,坊间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盛世危言》在当时是畅销书,发行量相当大,这也是生活在农村的少年毛泽东能够读到这本书的原因。我们现在难以确定当年毛泽东读到的是哪个版本,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年毛泽东读到了这本书,并深受这本书的影响,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是毛泽东个人之幸,更是中国之幸。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郑观应这位维新思想家和《盛世危言》这部他的代表作三致敬意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