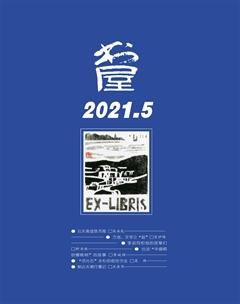白薇在重庆
熊飞宇
1946年1月,白薇在致刘海尼的信中,感慨地说:“抗战以来,奔流了两年,埋没四川乡下六年。”刘海尼在《记白薇》中亦说:“抗战初期的两年间,白薇是在各处奔流着的,到重庆的她大部的时间都埋没在乡间。”具体说来,白薇是在1939年冬,从桂林出发,经贵州到达重庆。对于途中见闻,白薇作有《陆司机》和《钓丝岩上的石工歌》两诗,以记其事。
初到“战时的新都重庆”,白薇“带着滚滚的热血”,四处寻找工作。她找过史良,但史良认为,抗战时期,“什么人都应该站在他本来的岗位”,“写文章的”,“就写你的去吧,何必找职业呢”?并表示“严重的沉默”。几经碰壁,白薇过着“没住处,少饮食,受寒冷的生活”。1939年12月28日午,白薇晕倒在较场口街旁,抬归,“脉要断,心停跳”,连医生都不愿施救。直到新年元旦一早,才“从晕梦中醒来”。后搬到乡下将养一月,才逐步恢复(《作家书简:白薇致谢冰莹》)。此处的“乡下”,应指南温泉,时有商家投资所建的简易竹屋,可租住。
此后,《蜀道》上不时可见白薇的零星信息。《蜀道》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新蜀报》所辟副刊,先后由姚蓬子、梅林、王亚平主编。1938年6月,白薇经田汉、洪深、阳翰笙等人介绍加入文协。到重庆后,曾在“风雪寒天”架竹板在文协客厅住了几夜,早上五点半即拆去。因为无钱“和大家共伙食”,也“只吃红薯和阳春面”。1940年6月10日,《蜀道》的《文艺简讯》云:“沙汀已来渝,住南温泉文协宿舍,白薇亦于昨日移去。”所谓“移去”,当指从租屋移到文协宿舍。至1941年2月13日,《文艺简讯》又云:“白薇近自南温泉迁住重庆。”由此可见,白薇居南温泉,至少有一年时间。关于其居住环境,白薇在《地之弃子——寄冰莹》有过描述:“我住的房间很小,又是当西晒,临厨房的火坑,邻居是穿着破烂的老百姓,也嘈杂得令人头痛心烦,不能写作。警报也天天照例响,要到十几里远的山中去躲。”1941年8月底,白薇再度“卧病南泉”,至9月底方痊愈。对南温泉的生活,白薇一直充满美好的忆念,曾写作诗歌两首:一是《孩子麦登》,“记南温泉一孤儿”;二是《邵承基》,“记南温泉的一个小朋友”。
后来,阳翰笙为白薇“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特约编导”,“工作是开会讨论剧本”,月薪五十。1940年3月2日,《蜀道》有简讯云:“白薇近参加中国制片厂及中国万岁剧团编导工作。”至9月25日,又有简讯说:“阳翰笙离政治部第三厅后,将致力于中国制片厂及中国万岁剧团之编导工作。”正是因为工作上的交集,阳翰笙的日记便不时出现白薇的名字。1942年1月1日午后二时,阳翰笙“参加文协所主持之茶会,席间与白薇、海尼闲谈”。谈到《天国春秋》,海尼问:“你写女人写得那样的好,是不是受了你太太的影响?”阳翰笙笑答:“也许是的吧。”1月12日晚,白薇去见阳翰笙,托他找工作,说“想做导演”。4月4日,文化工作委员会会计程泽民自赖家桥来,阳翰笙就“会内人事调整问题”商谈甚久,转商之于郭沫若,“郭也很同意”,“从此白薇工作可望得一解决”。据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4册),1942年,白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组员。第二组主要从事文艺研究,组长田汉,与白薇素有师生之谊。东京时期,白薇曾以易漱瑜之介认识田汉,得其指导,阅读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田汉到桂林工作后,则由石凌鹤代理组长。
白薇在文委会,地位“不及一个准尉司书,和孩子剧团的小女孩”,与“不大识字的太太是一样的待遇”,甚至不及上士勤务兵的待遇。除自己烧饭、洗衣、缝针、挑水之外,还不得不开荒种地,收获蔬菜杂粮来补助生活。其困居乡下,“过着像鲁滨逊漂流荒岛那样的孤独生活”,常常临江面水,“信口胡唱”。与之同病相怜的,则是一个在多家打杂的下江老太太。谢冰莹后来有一篇《黄白薇》,谈及此时白薇的生活境遇:“她住在赖家桥的乡下,过着自己挑水,自己种菜,自己做饭,上班下班的生活,如果有事进城,就得像一个行脚僧似的,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到那里,谁留她住下,她就随便在地板上或者凳子上、桌子上躺下来。”有一次,谢冰莹和白薇在重庆天官府文委会的办事处楼上的地板,“和几个勤务兵混在一道”过了一夜。而“郭沫若、冯乃超就住在隔壁”,“房间里摆着舒适的沙发、衣柜、梳妆台”。至于“可怜的白薇”,“冬天却穿着十几层单衣,连一件旧棉袍都没有”。不过,白薇对郭沫若却充满敬意,在《屈原》上演之后,还写下《致我最敬爱的诗人》,歌颂郭沫若。对冯乃超,白薇认为其“道德有余,而明察不足”,以致文委会“弊端奇出”,曾写信痛责,但冯乃超却欢喜道好。
1945年1月10日晚,阳翰笙收到白薇来信,“内容牢骚很多”。因此,陽翰笙决意“这次进城”,就“她的工作问题”,与郭沫若、冯乃超“再作一次彻底的研究和决定”。不意3月30日,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白薇再次失业,病居重庆。7月26日晨,白薇回到赖家桥,病上加劳,阿米巴痢疾复发。从8月4日晨至9日,才勉力支撑,写信给“荪荃、海尼、清君、晓梅、子妥、叔珂、剑冰、君慧、会悟、德君、雯卿、荃鸿、声韵、沈慧及所有关心我的姐妹们”,算是“生活的告白”。
白薇原本诸病缠身,重庆时期更见反复,相关记载处处可见:
1941年8月29日,《蜀道》的《文艺简讯》云:“白薇近患猩红热症,卧病南泉,颇为沉重。在渝友人均甚挂念。”
1941年9月7日,《蜀道》云:“白薇病状转佳,闻猩红热已至结痂时期,不久当可恢复健康。”
1941年9月26日,《蜀道》云:“白薇病已大愈,重庆友人闻讯后至为快慰。”
1942年1月22日,梅林日记云:“夜深了,白薇还在邻室走来走去,不断咳嗽着,有时似乎在开热水瓶,有时似乎在磨墨,而有时似乎走到厨房下去煎药。夜是深沉的,冷寂的,她的每一动作的声音都似乎带有凄凉味。一个女作家,从封建的幽灵塔中走出来,在广垠的人生底旅途上,她曾经在凄风苦雨的黑夜里独行,她曾经在惑人的阳光下振臂向天宇高歌,她曾经在万花怒放的春天欢笑舞蹈,她曾经为了‘正义感,为了‘利他主义,献出她的鲜血和皱纹;而现在,在众人熟睡的深夜,她咳嗽着走进厨房煎药……”
1942年3月13日,《蜀道》云:“白薇病已愈,将移赖家桥乡间休息。”
1942年6月4日,《蜀道》云:“白薇最近又在乡间患病。”
1943年4月14日,《蜀道》云:“白薇近又患病,正诊治中。”
1943年6月10日,阳翰笙日记云:“白薇又病,大家很关心,决定送伍佰元给她做医药费。”
1943年8月3日,梅林日记云:“收到白薇的一首长诗《陆司机》和信。她又生病了。斑疹伤寒,刚从医院出来,现在住在乡下休养。”
1945年8月12日,白薇在致梅林的信中说:“我廿六下乡,当夜热病极重,倒床多天,热减而阿米巴痢疾复发,明天不能到会,恭祝胜利。”
1945年12月16日,白薇在写给五妹黄碧遥(九如)的信中,谈到在多雾的重庆居住日久,也就得了“重庆病”,即风湿症,是夏曾花费六万多元,也未医好,并且“雾季总是猛咳数月,脸腿都肿”。
对于白薇的贫与病,文协及各界友人均不断施以援手。1944年4月16日下午二时,文协在文运会(曹家巷文化会堂)召开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大公报馆赠款一万元,老舍现场决定以此款分赠贫病同人:张天翼、王鲁彦各三千元,卢鸿基、白薇各二千元。同年7月15日,文协总会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在收到多起捐款之后,文协于7月30日开会,决定将第一批基金“立即分配”:王鲁彦一万五千元,艾芜一万元,张天翼一万元,白薇五千元。不过,据李长钦《白薇年谱》,“文协将捐款五千元送给她,当即退还”;“后来病倒在床,文协要送她一万元”,也被婉谢。安娥也曾回忆说:“有一次文协帮助她大约是五十万吧?她却除了自己用了极少数外,第二天听说翦伯赞穷且病,便把钱全部送给了他,弄得翦伯赞先生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所谓“五十万”,恐是误记。1945年8月12日,白薇在致梅林的信中曾说:“蒙给我拾万元巨款,真是衷心感激!请将全款交给任钧,由他给我买药并带来。”
白薇退捐的消息不胫而走,且距离事实渐行渐远,至1946年3月29日上海出版的《大观园》第15期,已变身为另一版本:“著名女作家白薇,卧病北碚数年,某会亦给予补助,函白亲领,白惑于宣传,以为有大宗津贴可领,乃欣然扶病入城,无何,所得者五千元支票一纸耳,白大忿,掷诸地,跄踉至碚,而病乃益重。”实际上,当白薇“为着病为着穷”,不得不领受“细微的接济”时,常向刘海尼悲苦地诉说:“这是可耻的!我是不能接受这些钱的,怎么能让我写点东西出来?我就可以不饿死。我不愿接受别人的钱,然而我又不能不接受,你理解吗?我是多么的难受呀!”白薇还将这些想法,以泪和血,凝铸成《救济贫病作家给我的感想》(一名《对救济贫病作家有感》)。
也正是在重庆,白薇与刘海尼成为莫逆之交。刘海尼(一作刘海妮),浙江温州人。曾留学日本。1938年,从福州退驻重庆,参加文协,从事写作。作品多见于《现代妇女》、《妇女》等。据其《记白薇》,二人的相识缘自“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文协主办下的一个文艺晚会上”。当时白薇“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衣服的样子已有点过时,颈上打着白绸的领结,手里提着一个黑布做成的警报袋”,“不大说话,只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边”。“她的沉默和安娥在全场中的活跃,刚成了一个反比例”。吸引刘海尼注意的,是白薇“一种特别的姿态”,其中“有着一个女人内心隐藏着的某种生命的重量”,显示这位“中年的女作家在生活的途程上已有点疲劳,但没有死亡”,“还跟她的生命做着最后的挣扎”。白薇的“警报袋”,亦曾出现于梅林194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白薇有一个包袱,珍贵异常,倘有警报,托代为照顾”,里面装的是“一叠未修正的剧本原稿,和一叠由她自己设计印的道林纸的稿纸”,另有几张相片:“一张是她打出封建的‘幽灵塔逃到东京时拍的单人小照”,“是一个美丽小姑娘的再现”;“另一张是从日本回国后拍的,侧坐着,脸上没有笑容”;“第三张则为五六年前的肖像”。
刘海尼住在下罗家湾,位于今之渝中区上清寺。结交之后不久,白薇即去拜访刘海尼,谈过去上海文艺界的活动,谈田汉《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谈冰心、丁玲,并主动讲述自己与杨骚的恋爱。这里顺带补充说明白薇与冰心的关系。1936年9月1日的《现代生活》第3卷第4期,曾发表彭子冈的采访报道《记白薇》。问及冰心,白薇说:“撇开思想不谈,我非常喜欢她,想见一见。她个人方面的道德是崇高的,她有她的‘才,她有她的‘体验。时代激变下去,她会慢慢进步的,只是慢一点而已。”重庆时期,冰心与白薇之间至少曾互通音讯。1943年3月25日,冰心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刚给白薇写几个字,忽然想起赵清阁,不知她近体如何?”赵清阁与两人均相熟,可能是二者联系的纽带。
从南温泉进城,白薇常到刘海尼寓所同住,“每晚总谈论许多问题”,“常常争执得很厉害”,有一次甚至差点决裂。其间,刘海尼也到过南温泉两次,一次去看白薇,一次去洗澡。两人“游小温泉,爬山,跑警报”,每次“都有杨骚在一处”。后来,白薇随文化工作委员会搬到赖家桥乡下,因为生病,刘海尼前去探望,但一见面便起舌战,直到深夜三点。白薇责备刘海尼“对妇女运动不热心”,讥笑她“对文艺太感兴趣”;狂热述说自己“对妇女工作的志向”,希望有人能和她“真诚合作”。从两人的相处中,刘海尼认识到白薇的“天真而仁爱”,但“很任性”,“不能经常地驾驭自己的理性”,然而“因为太真,她吃亏,她受苦”。而安娥对于白薇,虽然见面时只是局促地表示“是是”、“好好”、“对对”,内心却充满“崇拜”与“尊敬”,甚至因为刘海尼和白薇作密友,就“直截了当地也崇拜海尼”。在安娥眼中,白薇“不但是妇女,也是‘人性的骄傲”。
白薇寓居南温泉时,杨骚也在。刘海尼认为,“在重庆,杨骚对白薇是尽了应尽的友情”,“他们友谊地过活着,为了使白薇生活宁静,杨骚把自己的房子让出给她,而自己搬到白薇的笼似的房子里住”。当时文协的朋友们也在窃窃私语,希望他们能够破镜重圆。安娥在《我想白薇》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沙汀“非常善意”地为白薇设想,“在重庆南温泉文协会址”加以劝说,结果“白薇却狗血淋头的把沙汀骂了几个钟头,沙汀只能把被窝蒙头掩耳”。对于这次冲突,白薇在《地之弃子》中已向谢冰莹一一道过,可谓声形并肖。不过,白薇对沙汀并不记恨,称赞其人“坦白无邪”。后来沙汀在回忆录《睢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區的生活》中,也曾叙及这一事件:“有一天,她到文抗来串门子,闲谈当中,忽然灵机一动,我把自己筹思过多次的一项建议,向她提出来了,希望她同杨骚成为夫妇。没料到她立刻火冒三丈,对我连声诘责,并一步步逼近我,光景很可能让我吃几耳光。我呢,也就只好随着她的逼近,逐步退到房间的旮旯里。”“由于我的退让,解释,她的扑打姿态,也只说明她对我的建议多么生气。结果可并未动手,最后气也消了,照样同我友好。”但刘海尼认为,“悲剧已注定他们永久的命运”。随着杨骚远赴南洋,两人的复合也便失去了机会。
自白薇与沙汀争吵之后,风言风语便在重庆传散开来,甚至老舍也不允许白薇住在文协,认为她闹得“满城风雨,有伤风化”。后来,妇联、中苏文协以及好些“前进”文化人,都对白薇冷眼相看。尤其是妇女界,更将其谣传得“丑恶无边”,以致1945年在郑瑛家,姐妹们正在商量国家大事,一见白薇“碰来”,如同看到特务一样,“惊逃四散”。至于赖家桥,更是一个“谣言窝”。在白薇看来,最善于制造“毒害的风云”者,当推梁文若,还有骆剑冰、池田幸子等人。甚至梅林(信中未直呼其名,据前后文推断),也是一位“自私善妒”的作家,“不乐”自己住文协,却造谣说是老舍的意思。1951年9月11日,白薇将自己在重庆所受冤屈与悲苦,致信邓颖超,尽情倾诉出来,并为了使真相大白天下,请求将信在《新中国妇女》连载发表。
虽然四面悲歌,但白薇在重庆,仍参加过不少社会活动,现略述一二:
1940年4月7日下午四时,文协假粉江饭店(一说“国泰饭店”)举行重庆会员大会,纪念该会成立两周年,到百余人。由邵力子主席,老舍报告会务。七时聚餐。白薇“刚放下饭碗”,即被马宗融拉去看戏,后写成《从演出谈〈国家至上〉》,发表于《中央日报》1940年4月16日的《平明》副刊。
1940年6月8日,《妇女生活》月刊主编沈兹九召集女作家座谈会,讨论“妇女与文艺”问题。白薇、陆晶清、刘海尼、赵清阁等十余人参加,而“发言以白薇为最多最实际,情况至为热烈”。
1940年6月9日午后七时,新华日报社在一心花园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参加者有以群、蓬子、黑丁、戈宝权、臧云远、胡绳、罗荪、光未然、沙汀、葛一虹、艾青、梅林、白薇、潘梓年、吴敏、力扬、戈茅、曾克,潘梓年主席。座谈笔记刊登于7月4日与5日的《新华日报》,其中未见白薇的发言内容。此次座谈会,沙汀与白薇俱在,与前引《蜀道》关于二人“移去”南温泉文协宿舍的简讯有抵牾。
1945年2月22日,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签名者达三百一十二人,白薇列其中。
1945年4月8日六时,重庆各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各先生。到会宾主有郭沫若、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黄炎培、董必武、王若飞、谭平山、陶行知、张志让、马寅初、邓初民、郭春涛、史良、沙千里、施复亮、翦伯赞、侯外庐、高崇民、孟宪章、何公敢、吴藻溪、史东山、阳翰笙、于伶、吴祖光、夏衍、高龙生、胡风、冯乃超、宋之的、白薇、傅彬然、梅林、叶以群等百余人。
又,《白薇年谱》云: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周公馆”招待陪都的妇女界人士,白薇应邀出席。详细情形,《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已有生动描述,但具体日期则不清楚。据国民党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的跟监报告《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卅日》,9月5日下午四时五十分,“陪都妇女界代表吕云章、刘王立民(明)、彭子冈、浦熙修等十二人往桂园访毛泽东,当由王炳南介绍,晤谈约三十分钟始离去”。不知白薇是否就在此行?跟监报告虽然详细,但有残缺:毛泽东是在“双十协定”签署后,于10月11日九时四十五分起飞,离开重庆,而10月1日之后的跟监记录尚未面世;同时跟监也有遗漏,如9月3日晚六时,毛泽东会见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文化界的朋友”,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相关事宜可见诸阳翰笙日记,但跟监报告却无记录。《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则提供了两种可能:9月5日,“会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9月22日,“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综合来看,毛泽东会见白薇,可能性较大的是在9月5日。不过,后人对此所作的渲染,或已过甚。
抗战胜利后,白薇急于回家,9月进城,住一月,无计可施,复返赖家桥。但乡里机关早已解散,差不多都人去屋空。11月1日,又进城寻找关系,但“船、車、钱都找不着”,不得已再回乡下。至1946年6月7日,《飘》第11期又借黄碧遥之口透露白薇近况:“最近有封信来说,可能买到船票,先到汉口,然后再看交通情形,或回湘南省亲(舍间父母尚健在),或来京、沪。此刻她还没有到京、沪,不是已回家乡,便是没有买到船票。”1946年6月中,白薇终于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