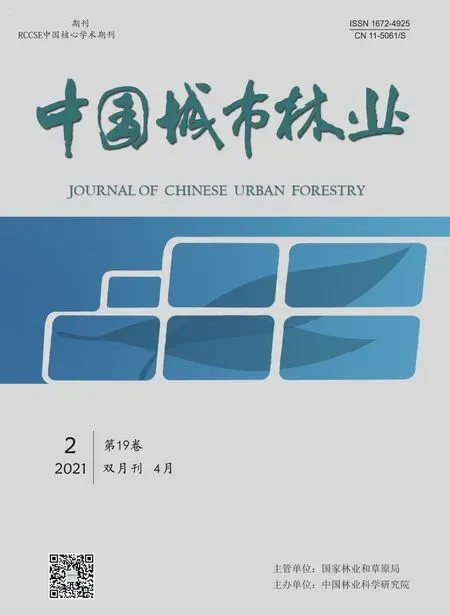引入“设计生态”的城市公园设计策略*
金云峰 吴钰宾 邹可人 丛楷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发展的主流转向寻求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转型”成为城市的生态现代化过程[1]。在城市人居环境中,公园作为城市的生态绿肺和社会的催化剂,是构建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环境和逐渐消解的原始自然,人们在设计实践中常常陷入“人工与自然”的对立矛盾之中,缺乏有效的可持续设计理论和方法。当今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已经超越了过去以形式主义为追求的模式[2],生态策略介入设计应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从而能适应高速发展、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
1 “设计生态”相关研究与讨论
1.1 景观实践中生态思想的转变
随着城市发展挤压自然空间、引发环境危机,规划设计中的“生态”取向已成为一种共识。“生态”的基本内涵为“有机体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作为形容词时,“生态”往往表达了“有自然的、近自然的、对自然低影响”的价值取向[3]。19世纪中下半叶兴起了以生态科学为核心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然而难以很好地解释风景园林核心的“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4],同时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设计的内涵[5]。
当今,“生态”的概念呈现泛化的趋势,20世纪末出现了以“生态隐喻”为特征的设计思想,“生态”不只局限于有机体内部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各种复杂联系方式或复杂系统都可以纳入“生态”的视角,例如人居环境中的各种物质、事件、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等[5]。同时,规划设计师更加关注景观生态的“过程性”内涵和人的主体性[6],于是一些学者提出,生态策略的介入应该转变思路,应从“设计结合自然”转变为“设计生态”。
1.2 “设计生态”的提出与应用
“设计生态”(Design Ecology) 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对景观功能和过程的研究和实践。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术界出现了关注景观过程性的理论,并在设计实践中利用和引导自然过程,而后诞生于90年代的景观都市主义延续了这种理念。正如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 所提出的“人类需要发明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态学来挑战缺乏创造力、想象力及带有科学偏见的传统生态学”[7],20世纪末以来的城市景观实践开始融入一种基于场地过程的创造性的景观生态学思想,并在城市废弃地的修复和更新中大有可为,例如北杜伊斯堡公园、纽约清泉公园等。在这种设计思想的影响下,国内也开展了类似的生态实践,例如唐山南湖公园、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土人团队实践项目等。
目前对“设计生态”的研究多为概念探讨和初步应用。2006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筑学院就以Design Ecologies为主题探讨了城市、建筑、景观实践等方面的当代可持续设计[8];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相关研究将“设计的生态”(Designed Ecology) 定义为“人工设计的生态系统”,强调设计的对象是这种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程[9-10];翟俊[11]从方法上提出景观通过生态创造和修复等方式来介入和干预环境的改变。
对“设计生态”的理解取决于对“生态”概念的解释,结合以上认识,本文认为“设计生态”是一种以场地过程为基础的动态设计,在受到生态破坏的人居环境中,通过景观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生态过程,激发自然的能动性,塑造景观功能。如前文所述,若将“生态”作为各种复杂联系方式或复杂系统的比喻,笔者认为“设计生态”的范畴有所拓展,将设计过程本身视为一个复杂系统,无论是否设计了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只要设计的过程是“生态”的,也可被称为“设计生态”,这与科纳提出的“更重视设计的过程(processes)、策略 (strategies)、组织机构(agencies)、支架(scaffoldings) ”[7]有相似之处。
“设计生态”重新审视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12],通过设计城市中的人工生态触发城市发展的机会,从而启发更加开放的设计策略,在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将大有可为,但是否能适用于我国的复杂城市环境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1.3 “设计生态”与“生态设计”概念的比较
“生态设计”(Ecological Design) 广泛使用的定义为“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13],过去的生态设计侧重生态因子评价、土地适宜性分析等定性定量的科学技术方法,可以视为一种被动式防御型设计方法[14],“尽量”“最小”等概念也较为模糊。然而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设计往往呈现出一个悖论,一个精心设计的“自然”背后是由密集的资金和技术堆砌而成[15],反而违背了生态的价值。
实际上当代的生态设计内涵已经得到大大扩展,生态不再限于技术性概念,其社会性、文化性、审美性更是设计的核心。仅是仿造自然的生态设计会导致设计创造力的缺失,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不可预知性要求景观的生态化设计过程是适应性和创造性的[16]。康世磊等[4]提出景观本体特征包含时间性、关系性和创造性,正契合了“设计生态”的设计对象是随时间变化的、开放的、不确定的景观过程。“设计生态”作为一种基于“空间-时间”的过程性设计方法被提出,比之“生态设计”为“生态”提供了更好的注解,在概念上更加深入景观的特征,同时也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
1.4 “设计生态”的内涵
基于前文对“设计生态”概念的认识,设计的核心是动态的自然过程、人地关系和适应性变化,本文提出“设计生态”内涵包含3个层面。
1) 自然层面。将自然要素作为载体,生态策略作为人工干预自然过程的媒介,引导和优化景观的自然生态过程使其向预期方向生长,触发场地再生。
2) 空间层面。文化创造景观,景观反映文化,自然景观和“事件景观”与人群发生长期的互动关系,需要创造容纳多种长期或偶然的过程及其关系的空间,并进行不断地调整。
3) 机制层面。景观是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风景园林学科应整合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动态管理决策机制的运作使景观适应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引入“设计生态”的城市公园设计策略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生态功能和人居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在高密度城市中为公众提供了自由交往的场所,直接体现了设计作为结合自然和人工的一种文化活动是否合格。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公园在其生命周期中将不断地发生调整,“设计生态”要求始终贯穿基于“空间-时间”关系的过程性思想,设计策略强调对各种动态过程的关注和设计引导,包括重现自然的生态策略、承载服务的空间策略和因时制宜的机制策略3个层面。
2.1 生态层面:基于过程的修复再造
2.1.1 干预和引导自然生态过程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生长性、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设计师不作任何干预,可以通过在设计中引入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态媒介,控制生长环境条件等手段帮助引导或加快生态过程[17],从而触发和引导其向预期的方向生长,激发场地自身的更新能力。生态工程技术为人工干预提供了一种低消耗、低维护、低排放的技术支持和设计介入手段[18],能够提供更加高效的解决方案,为场地打造一个“人工自然生态系统”以应对变化的未来。
曼谷都市森林公园是一个人工再造的生境,其植被生长被设计为一个人工干预的加速演替的自然过程。设计团队塑造了多个坡地,在第一阶段根据植被的演替速率和灌溉水源条件配置树种布局和栽植密度,鼓励植被经历自然选择,后续阶段中通过人工控制植被覆盖率、湿度和营养水平等促进多层次林冠层的生长,将原本需要30年才能形成的状态缩短至10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全新的生态系统[19](图1)。

图1 曼谷都市森林公园的植被演替优化过程(图片来自参考文献[19])
2.1.2 生态过程的复合性设计
场地上发生复杂的生态过程时,设计师需要基于场地特质和设计目标对不同的生态过程采取不同介入程度的设计手段,并将各项生态过程通过并置、叠加等方式整合为一个内在联系紧密、和谐统一的系统。为实现公园中各项动态生态过程的融合,设计师需要对场地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形成清晰的认识,从而提出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措施,并持续关注后续的场地变化。
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是国内营造野态自然的代表性公园案例。西湖疏浚后淤泥形成的次生荒野形成了复杂的场地条件,设计团队采取了多种设计手段:划定“生境岛”保留原生植被并不加干预作为自然演替的样本;适当疏伐生境岛以外的植被,引入兼具观赏性和适应性的下层植物,营造丰富生境;在安全地带设置栈道和设施,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20];同时江洋畈公园的场地条件还一直在持续变化,设计团队进行持续地跟踪和调查。
2.2 空间层面:功能融合的社会文化服务
2.2.1 构建容纳和激活事件的空间
除了自然景观,城市公园中代表城市生活的事件景观同样重要,包括各种公共功能和活动,为此需要构建一个能包容和适应多种过程的“容器”[21]。景观中的活动空间是真正使人与自然发生互动关系的地方,各种城市事件、公共活动构成了公园的实质性内容。设计师需要设计的“生态”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而产生了不同形态,通过重塑历史文脉、保留场地记忆、转变服务功能等手段引起人们的共同认知[22-23],从而让场地上的时间和历史保持延续,激发空间活力。
巴黎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师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 没有使用模仿或再现自然的传统设计手法,而是采用“点-线-面”层叠的人工化秩序构建了一个容纳多种事件和未知变化的“容器”(图2),展现了开放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他的红色构筑物、林荫道和10个主题小园为公园创造了允许各种公共活动和事件发生的空间形式,并为未来的加建、更新、改建提供机遇[24],在探讨公园如何应对城市发展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图2 拉·维莱特公园的层叠系统
2.2.2 协调人地关系的时空设计
在城市公园内,自然要素和人群都是空间的使用者,两者对空间的使用方式构成了公园活动的动态合集,但也引发了在使用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设计手段对多种自然过程和社会事件的混合和互补关系进行协调。
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发生使用矛盾时,可以通过立体分层等形式组织人与自然的关系,减少相互影响的同时又能共享同一空间。曼谷都市森林公园在植被演替初期设置空中步道和观景台,减少游人干扰的同时也使人们能近距离欣赏林冠的成长过程,在森林成熟稳定后,设计师在地面上新辟小径,增加林下体验。
不同使用者在不同的时间使用场地,可以通过分时设计的方式来解决,提高场地在各个时间段的使用效率。与洪水为邻的金华燕尾洲公园通过地形设计形成了多级梯田可淹没区,当洪水来临时,被淹没的梯田形成洪水缓冲区,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沙土、水分和养分能让植被更加茂盛地生长,露出了平时可以嬉戏的亲水空间,打造了多样化的体验空间[25](图3)。

图3 金华燕尾洲公园应对季节性洪水的分时设计(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25])
2.3 机制层面:动态开放的设计管理模式
2.3.1 基于学科交叉的适应性管理策略
管理行为直接引导景观的发展方向,风景园林设计必须重视设计的管理策略,尤其对于需要时间落实的大尺度项目,过程中必然受到生态保护、公众需求、城市开发的影响,因此必须制定阶段性的适应性管理策略。在多伦多当斯维尔公园设计竞赛中,场地位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地区,面临着城市发展的种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詹姆斯·科纳的方案将公园的长期发展过程视为一个“生态系统”,通过制定阶段性的适应性管理措施促进公园生态的生长[26]。为了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应性管理策略,景观实践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单学科背景的设计师完成,风景园林学科也已经超越了以往仅作为风景和绿地的范畴,需要通过跨学科的共同努力与合作,结合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以综合性协同规划设计推动城市发展[26]。
2.3.2 连接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面向公众的公园项目如果仅仅依靠技术实现生态改善,而缺乏与人在社会、文化观念上的联系,将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设计需要联系社会行动和政策,注重生态参与,包括多学科交叉、公众参与、公众教育等。在我国当前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的情景下,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细化政府职能、丰富参与途径等自上而下的手段提高公众对自下而上参与城市建设的热情[27]。例如在深圳香蜜公园的公众参与实践中,由政府引导和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在公园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管理运营的全程中调动包括市民、专家、企业等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图4),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真正落实公众使用需求[28],使其成为一个广受市民好评的乐园。设计行为与政府部门、机构组织、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引发大众参与,能有效组织城市资源,及时反馈和调整,将公园面临的负面影响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活力。

图4 深圳香蜜公园公众参与模式
3 结语
在国家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背景下,为实现城市的系统性、宜居性和生长性,公共开放空间设计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29-30],我们需要思考“当今的风景园林需要怎样的生态学”,而不能被动地完全依附于生态学和生态技术的发展。“设计生态”作为一种基于场地过程的动态设计方法,通过引入混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引导下一阶段的发展,对构建具有适应性和生命力的城市景观(尤其是大型公园) 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发展潜力,但是在我国能否适用,目前还需要更多实践项目的论证。除了城市公园外,城市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产生了许多零散的绿色空间,尤其是呈现破碎化的“失落空间”,因此,在迫切需要实现资源整合的现状下,“设计生态”将为连接和更新城市人工环境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和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