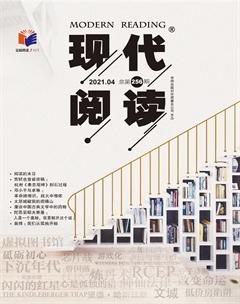新安江畔画中行
春寒未去,我已经惦记起不远的徽州——也不知为何,这个地方有一种魔力,让我恍惚感到故乡般的亲切,它让我想起童年,那带着泥巴、青草的气息以及傍晚袅袅炊烟的日子。
这回去徽州,不為油菜花,不为古村落,主要是想看看新安江。自古以来,徽杭联系就颇为密切,一条山路(徽杭古道),一条水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把两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重镇串联起来。这里有最为典型的江南山水,多少画作、诗词因此诞生,我对徽州向往已久。
每次出门与自然相近,我必定要守候天明,因为太喜欢一天之初的无人之境。看新安江山水有两种玩法,一种是在歙县县城坐船游览至深渡镇或反向行之,一种是驾车而行。后一种一定要走004县道,因为只有这条道是贴江而行的。从歙县县城出发,上路不多久,来到南源口大桥附近后,道路就开始沿江而行了,此时一条路通向深渡镇,一条路通向卖花渔村。我猛然想起几天前国家地理中文网某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提到过后者,朋友晓良也转过相关帖子给我看。此时才清晨6点,遂改变直达深渡镇的计划,转而开往位于洪岭的卖花渔村——该村之名中的“卖花”是真,“渔村”则因唐末洪氏迁居于此,逐渐形成村落,村形如鱼,村人姓洪,喻水汹涌,鱼得水则生机盎然,故村人在鱼字边加三点水,称为渔村。
大清早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山路曲折,约莫半个小时抵达,整个村子刚刚醒来,偶有早起的人遇到我,问:这么大早就赶来啊!我却感到迷茫:图片里那些漫山遍野的梅花呢?村人说“你来晚啦”,于是我有些失落。但看家家户户门前都是无数株老梅的样子,不难想象,这个以卖梅花为业的村落,在某个时间点,该有多么热闹。有时候就是这样,同一个地方,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到来,带着不同的心境,便判若两地。我急吼吼爬上村旁的山顶,大概是没吃早饭的原因,到达山顶时险些昏厥过去。眼前的村落被山峦环抱,水雾弥漫,时而见山不见村,时而见村不见山。我一个人坐在山上的亭子里,任饱含水分的空气扑面而来,不久,头发、衣衫皆湿,然后才默默离开这个独特的小山村,并自我安慰道:也许在那梅花盛开的时节,就不可能这样独享安静和PM2.5值为20的优良空气了——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从洪岭下来,拟直奔深渡。返回到南源口大桥时,目光被对岸的淪岭下村吸引,一路行过王家淇、南屏村、金滩村、坑口村,春雨无声如丝,烟水弥漫山间村落,油菜花初绽,鸟儿在草木间穿梭啁啾,早起的村民驾着轻舟,安静地划过江面,静等鱼儿上钩。面对如此美景,我止不住停车发呆或拍照。到达漳潭村时,景致的美达到极致。江水在这里温柔地拐了几个大弯,对岸漳潭村的黑瓦白墙,被柔嫩的绿色包围。高高的马头墙上,烟云飘移,平缓的山顶时而出现,时而隐没。远近、虚实、动静之对比,营造出一种如中国传统山水画般的美感。我停下车,沿着新安江边步行一段。停泊于岸边的渡船,看到有人挥手,便缓行而来,载客而去。眼前的无声画卷,仿佛让人身处与世隔绝的另一时空,让我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虽然远隔千里,但田园牧歌式的美,却有相通之处。隔着新安江,望着对面的漳潭村,所有关于徽州的过去,像电影画面一般在脑海里浮现:古老祠堂牵系的严密宗族制度,巍巍牌坊昭示的功名或贞洁故事,一条条古道背后蕴含的徽商发迹历程,都让我对这块人文渊薮之地充满好奇。
过了漳潭村,深渡镇就不远了,只是越靠近目的地,却越让人失望。深渡作为新安江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显然更为热闹而“繁华”,宽阔的码头停满机动船,岸上摆满零食小摊,船头站着揽客的船主。待看到镇郊烂尾的高楼和别墅,失望感越加浓重,这些新楼无论体量、形制还是格局,已然没有徽州的影子。
(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长歌行:中国人文地理发现之旅》 作者:林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