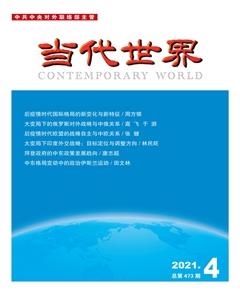拜登政府能否弥合美国社会分裂?
徐海娜 姚寰宇
【关键词】拜登;美国社会分裂;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分歧;中间道路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4.009
2021年1月7日,隨着美国国会确认,乔·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最终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本次大选将美国旷日持久的政党、选民、族群等全方位的极化现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面对社会分裂,拜登在2020年11月7日胜选演讲和2021年1月20日就职演讲中,一再承诺自己将“成为一位谋求团结而非分裂的总统,成为一位眼中没有红蓝差别而是心怀整个合众国的总统,成为一位赢取全部人民的总统”,带领美国走向“团结一致、治愈分裂”的道路。[1]虽然拜登表达了弥合分歧的强烈意愿,但美国极化问题的化解面临十分严峻的现实挑战。
2020年美国大选凸显美国社会多重分裂
2020年美国大选将美国的社会分裂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这不仅体现在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在关键议题上的竞选政策存在根本对立,也体现在两党的选民群体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裂。
一、竞选政策凸显两党理念对立
美国的政治分裂首先表现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政策理念的对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美国民众认为在本次大选中两党分裂已超过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且政党冲突的激烈程度远高于贫富、种族、城乡差距等引发的冲突。[2]两党总统候选人在关键领域的政策主张明显对立。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上,两人的分歧在于经济和疫情防控何者优先,特朗普坚持以重启经济为先、疫情防控工作要配合经济重启,而拜登则坚持疫情控制为先、经济重启要让步于疫情防控;在因“弗洛伊德事件”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司法及警察制度改革方面,拜登要求政府加大对警察和检察官的监督,并降低监禁率,而特朗普则全面支持增加对警察权利的保护,并要求加大对部分罪犯的处罚、取消无现金保释;在税收问题上,拜登拟废除特朗普2017年减税法案;在移民问题上,拜登承诺在上任百日内废除特朗普任期内的移民政策;在医保问题上,特朗普推动废除奥巴马总统时的《平价医疗法案》(ACA),而拜登则希望在《平价医疗法案》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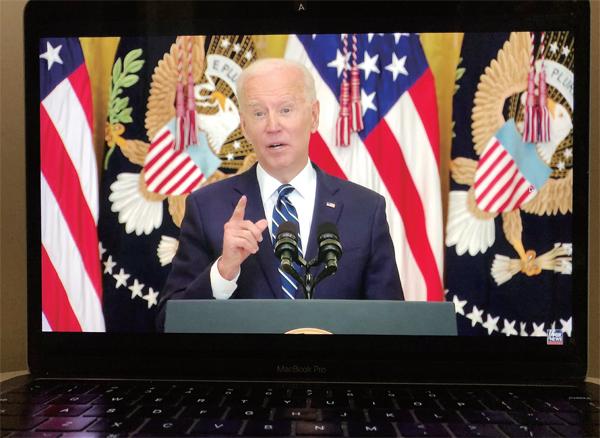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上,特朗普坚持以重启经济为先、疫情防控工作要配合经济重启,而拜登则坚持疫情控制为先、经济重启要让步于疫情防控。图为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举行就任总统65天来的首场记者会,他表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经济仍是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二、选民身份、投票动机分化严重
2020年大选的出口民调显示出美国选民严重分化。爱迪生研究公司的出口民调数据显示:从种族来看,白人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中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均高于拜登;而非白人群体的投票情况则恰好相反——非洲裔和拉丁裔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远高于特朗普。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对拜登的支持率略高于特朗普,而特朗普在低于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中支持率比拜登高一倍。从选民政治倾向来看,89%的自由派选民支持拜登,85%的保守派选民支持特朗普。值得关注的是,64%的中间选民支持拜登。[3]美国社会撕裂还体现在两党支持者群体在重大问题上认知迥异。支持拜登的选民更关注种族平等、新冠肺炎疫情和医保政策,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则关注经济、犯罪及安全问题。双方支持者在种族、气候、堕胎等问题上立场悬殊。
三、“两个合众国”的对抗
在2020年大选中,民众投票率之高为历届大选所罕见,民众对两位候选人的支持度也是旗鼓相当。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经济严重下滑、失业人口暴增,但特朗普仍然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落选的总统候选人,这充分体现出特朗普的民意基础之牢固。
虽然拜登最终赢得大选,但有民调显示,拜登支持者中有68%的选民是为了反对特朗普,仅有46%的选民是为了支持拜登。[4]从某种程度上说,2020年选举是“挺特派”与“倒特派”的斗争,拜登只是坐收渔利,赢在了“倒特派”“只要不是特朗普”的理念上。两派在经济政策、社会福利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种族问题等各方面都持有相反或对立的观点。如对于种族问题的看法,因“弗洛伊德事件”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后,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86%的选民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84%的支持者认为种族问题在美国微不足道,并且认为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公平公正;而拜登的支持者中78%的选民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表示支持,82%的选民认为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对黑人存在明显不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宣称,大选折射出美国现在已成为“一个美利坚,两个合众国”。[5]
四、不同利益集团及意识形态严重分裂
资本利益集团、宗教及意识形态是影响美国社会分裂的重要因素。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多元主义的基础之一,对美国决策过程有着重大影响力。[6]但2016年之后,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加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以“美国精神”传承者自居,斥责民主党是“美国精神”的背叛者。两位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来源显示出其背后的资本利益集团不同。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调查,拜登的资金主要来自金融、证券、电子、互联网等领域,特朗普的资金则主要来自博彩、房地产、能源等领域。[7]从选民的宗教信仰来看,基督教福音派或白人重生派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76%,反对拜登的比例则高达62%。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暴力冲击,大量参与者以基督教、上帝等名义打出宗教口号,《大西洋月刊》等媒体称此为“基督教暴动”。[8]不同的宗教、资本利益集团分别为两位候选人倾注大量资源,激化了两党对立,加剧了美国社会分裂。
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社会分裂根植于美国历史之中,但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并不能结束冲突,只能通过商定规则来化解和减少矛盾。[9]在意识形态分裂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的“妥协政治”正在逐渐消亡,极化政治正成为主流,并且这种分裂逐渐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安全感正在从外转内,右翼担心民主党将把美国引向“社会主义”,左翼则担心特朗普连任将导致美国走向“极权主义”。
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政治理念分歧开启美国社会分裂的源头。到19世纪50年代,北部资本主义制度与南部奴隶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美国内战爆发。20世纪以来,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总统等持续“左转”,到了里根、小布什总统等又带领美国持续“右转”,两党的政治分裂日益加剧。经过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美国政治分裂已如“脱缰之马”。在此发展过程中,两种政治理念都出现极端化趋向。美国人在经济、种族、身份认同等问题上的分歧成为美国社会分裂加剧的主要动因。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如此描述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称美国已经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1%有、1%治、1%享”。[10]调查显示,近几十年来,美国收入增量更多流向了高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所得越来越少,其结果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不断萎缩;据经合组织测算,美国基尼系数高达0.434,是七国集团(G7)中最高的。[11]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贫富两极分化采取有效措施。奥巴马执政期间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将诸多产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巨型企业从中获益颇丰,中小企业利益严重受损。依赖救济的穷人增多,国内阶级对立激化,进而刺激了激进政治运动的发展。2009年“茶党”运动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分别代表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发自民间的“反对大政府”“反对大公司”的行动是对奥巴马政府“大到不能倒”经济政策的直接回击。2021年初,美国股市“游戏驿站轧空事件”,是散户对金融巨鳄进行的报复性反击,其实质是底层民众与富人之间的经济对抗,凸显出贫富两极分化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重要根源。
二、种族对立日趋严重
种族问题是深植于美国历史的“原罪”,从美国建国伊始延续至今。以华盛顿为代表的诸多美国国父都是奴隶主,美国内战后虽然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但并未消除种族歧视。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被黑人选民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奥巴马能够在解决种族问题上有所作为,但事实却使黑人选民大失所望。奥巴马的黑人身份非但没能弥合种族分裂,反而成为他处置相关问题的掣肘。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过分谨慎,在涉及黑人刑事案件时多次以沉默或回避应对,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分裂和对立。当奥巴马连任总统后,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上升为过度的“政治正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种族主义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反弹。2016年特朗普胜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美国白人族群的反击,“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使“白人至上主义者”与特朗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特朗普任内多次发表种族主义言论,与种族主义极端势力频繁互动,攻击少数族裔议员,引起少数族裔尤其是激进黑人群体的强烈反感。
三、“谁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300年来美国的核心文化从来就是17—18世纪早期北美定居者的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其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和道德观念。[12]随着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开始接纳越来越多与传统盎格鲁—新教文化价值观不同的外来移民。而多元文化主义者与盎格鲁—新教文化中心论者在堕胎、同性恋权利、控枪、移民等问题上的对立愈发尖锐,美国社会的“熔炉”效果逐渐减弱,开始进入“文化战争”的极端对立状态。这种文化对立被民主党与共和党利用,两党分别代表多元文化主义者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中心论者,他们为了取悦各自的选民提出越来越多的激进政策。奥巴马执政后期,在控枪、移民等问题上接连受挫,采取以颁布总统行政令的方式绕过国会来推进多元文化主义者偏好的政策。特朗普在政策受阻时也效仿其做法,并全面推翻奥巴马的政策。这场“文化战争”愈演愈烈,使美国大众更加迷茫,不同族群的对立已经跨越观点分歧并上升为身份认同,难以缓和收场。
四、特朗普执政加剧社会分裂
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在特朗普执政期間达到巅峰。美国选民对僵化、低效、腐败的传统政治的厌倦促成了特朗普上台执政,他们寄希望于一个“局外人”为国家带来改变。特朗普非但没有改善美国的社会分裂,反而使这种状况变得更为严重,甚至在其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引发了政治动乱。共和、民主两党分别以特朗普和桑德斯来吸引右翼及左翼极端势力的支持,导致共和党更右、民主党更左,两党建制派被迫向两边分野。特朗普与传统媒体相互攻讦,使得这些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整体下降。特朗普通过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散布个人政治理念、直接与其“铁盘”对话,使民主党与共和党既存的政策差异进一步固化为身份认同的鸿沟。
影响拜登政府弥合社会分裂的主要因素
面对美国社会分裂严重的现状,拜登政府将不得不努力求变,最大限度弥合分歧并推动美国恢复发展,同时巩固自己的执政根基。然而,想要弥合社会分裂,拜登政府仍面临多重阻力,前景并不乐观。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存在着支持“再联合”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这是拜登政府开启社会弥合分裂之路的有利因素。
一、影响拜登政府弥合社会分裂的不利因素
影响拜登政府弥合社会分裂的不利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政治人物的,也有来自党派间斗争和选民的,还有来自党派内部的。
一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压力。特朗普尽管输掉了大选,但获得了7400多万张选票,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仍对共和党和美国政局有较大影响力。特朗普卸任后,公开对共和党进行分化。在2021年2月28日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卸任后的特朗普首次公开亮相并发表讲话,将包括美国国会共和党党团主席、共和党内的“三号人物”利兹·切尼在内反对他的共和党人称为“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呼吁支持者“将他们都赶走”。[13]尽管特朗普声称自己不会另立门派,但他与麦康奈尔等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使得共和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分裂压力。考虑到特朗普的政治号召力和影响力,那些想要弥合分裂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将面临巨大的考验。特朗普一直没有排除其角逐2024年美国大选的可能性,这将增加美国政局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梦魇”不仅是拜登和民主党人要面对的难题,也是未来共和党谋求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
二是美国两党不断走向极化,彼此间的分歧难以弥合。福山认为,当下“否决政治”已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运作,“否决为上、治理为下、党争不断、效率低下”的政治模式让两党极化达到顶峰。[14]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对奥巴马的政策几乎做到了“必反”,而特朗普执政伊始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如今拜登显然面临同样的考验。同时,如何兑现竞选承诺也是拜登政府必须面对的考验。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运动团体是拜登胜选的一大助力。2020年5月,拜登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背书,承诺进行司法公正改革,并推进对黑人企业和社区进行经济资助和住房改革。拜登获得了这部分黑人选民的强力支持,在大选中收到了可观的回报。拜登胜选后,有关团体立刻要求拜登兑现承诺,要求他在医保、住房、教育以及警察制度改革等方面立即采取行动。这让拜登陷入两难:如果迎合非洲裔选民,那么势必会损害警察等群体的利益,加大政府执法部门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如不兑现竞选承诺,则将极大地伤害非洲裔选民的感情,损害自身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利益。
三是民主党党内分裂严重。初选期间,民主党内20余名候选人的“混战”充分体现出该党内部分裂严重。作为温和派,拜登在上任后不得不面对诸如桑德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拥有大量支持者的激进左翼势力的压力。作为总统,拜登在某些政策上无法避免与党内各股势力产生分歧甚至对立,需要妥善应对。与此同时,民主党党内诸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总统奥巴马等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和选民号召力的高层成员,在拜登执政后也频频公开发出激进声音,给拜登执政的独立性带来极大压力。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拜登没有接受民主党党内初选时伊丽莎白·沃伦等部分候选人提出的将非法移民排除在处罚对象之外的激进提案;[15]在对黑人进行赔偿的问题上,奥巴马公开称美国对所有黑人进行赔偿是“完全合理的”,[16]但拜登对此事仍表现得比较谨慎,他支持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赔偿问题,还没有完全支持这项立法。
二、拜登政府弥合社会分裂的有利因素
尽管美国社会在种族、阶层、价值观等层面已经出现背道而驰的张力,但美国政界、美国社会的主流意愿仍是渴望团结、弥合分裂。
一是美国政治传统对极端分裂行为仍能起到规制作用。任何政治体制,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政治规矩。这种规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调和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是美国社会制度长期运作的结果,根植于人们的信仰之中,有时甚至比法律更有力量。[17]而“基于宪法的法治”这一“美利坚信条”得到了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支持。目前,这一信条虽然面临挑战,但在两党体制内仍发挥较大作用。尽管特朗普曾试图削弱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但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都在阻止其突破底线。在特朗普的行为逐渐失控、其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各级官员都与特朗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切割”。以副总统彭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为代表的共和党大佬带头“倒戈”,各州的共和党人纷纷效仿。在经历政党极化和“特朗普主义”的狂风暴雨后,在支持“美利坚信条”的两党中间派通力合作下,美国政治仍有可能回摆到一个正常水平。
二是美国国内有弥合社会分裂的动力和基础。尽管美国选民在政治理念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大部分选民都表示希望总统能够成为一个促进团结的人,而不是一个分裂者。2020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9%的拜登支持者和86%的特朗普支持者都表示,他们希望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能满足所有美国人的需求。[18]弥合分裂仍是广大民众的诉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2020年大选出口民调显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传统票仓都出现了动摇:特朗普赢得的黑人和拉丁裔选票超过了60年来任何一位共和党人,但他在2016年赢得的数百万福音派信徒在2020年时却把票投给了拜登。[19]美国选民阵营的叠加交错和转变,表明美国社会仍有较强的修复能力和可能性。
三是危机处理或将成为拜登弥合社会分裂的关键所在。历史上,危机是对总统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之一,而能否妥善应对危机则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如果總统应对得当,其支持率会显著上升,竞选连任都不成问题,林肯和罗斯福都是成功的例子;而危机处理不当,则失败在所难免,卡特和特朗普均是反面例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果拜登能够妥善应对,成功带领美国渡过危机,那么其所带来的“聚旗效应”将成为弥合国内分裂的重要助推器。[20]
结语
美国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表明,其国内分裂已经深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并且烈度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从美国国内及国际评论一边倒的悲观论调来看,形势不容乐观。民主、共和两党如不能放弃党派成见,美国的社会分裂将不会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层面。但是,两党建制派都已经认识到,如果继续任由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操纵美国的政治走向,美国将成为意识形态深度分裂的国家,甚至可能出现事实上的分裂。从2020年大选看,保持中间路线是拜登胜出的关键,如果能继续走温和的中间道路,妥善解决民主党内的派系矛盾,并在清算“特朗普主义”方面与共和党温和派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建立一个跨党派的中间派政治联盟,弥合社会分歧或可奏效。然而,从拜登政府已推出的政策来看,弥合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妥协仍然存在难以跨越的关卡。拜登想要“成为一位赢取全部人民的总统”,可谓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甘冲)
[1] Camila Domonoske and Barbara Sprunt, “Hope, Healing and ‘Better Angels: Biden Declares Victory and Vows Unity,” November 2020, https://www.npr.org/sections/live-updates-2020-election-results/2020/11/07/932104693/biden-to-make-victory-speech-as-president-elect-at-8-p-m-et.
[2] Katherine Schaeffer, “Far more Americans see ‘very strong partisan conflicts now than in the last two 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s,” March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3/04/far-more-americans-see-very-strong-partisan-conflicts-now-than-in-the-last-two-presidential-election-years/.
[3] “National Exit Polls: How Different Groups Voted,” November 2020,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11/03/us/elections/exit-polls-president.html.
[4] 同[3]。
[5] Richard N. Haass, “One America, Two Nations,” November 2020, https://www.cfr.org/article/one-america-two-nations.
[6]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7] 特朗普团队的竞选资金来源参见:“Top Industries, federal election data for Donald Trump, 2020 cycle,” https://www.opensecrets.org/2020-presidential-race/industries/donald-trump?id=N00023864; 拜登团队的竞选资金来源参见: “Top Industries, federal election data for Joe Biden, 2020 cycle,” https://www.opensecrets.org/2020-presidential-race/industries?id=N00001669。
[8] Emma Green, “A Christian Insurrection,” January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1/01/evangelicals-catholics-jericho-march-capitol/617591/.
[9]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7页。
[10] Joseph E. Stiglitz,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March 2011,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11] Juliana Menasce Horowitz, Ruth Igielnik and Rakesh Kochhar, “Trends in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September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1/09/trends-in-income-and-wealth-inequality/.
[12]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4页。
[13] “Donald Trump CPAC 2021 Speech Transcript,” Feburary 2020,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donald-trump-cpac-2021-speech-transcript.
[14] 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载《美国研究》2016 年第2期,第61页。
[15] Nick Miroff and Maria Sacchetti: “Biden says hell reverse Trump immigration policies but wants ‘guardrails first,” December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biden-immigration-policy-changes/2020/12/22/2eb9ef92-4400-11eb-8deb-b948d0931c16_story.html.
[16] Aris Folley: “Obama says reparations ‘justified,” February 2021,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40536-obama-says-reparations-are-justified.
[17] 同[6],第63页。
[18] Claudia Deane and John Gramlich, “2020 election reveals two broad voting coalitions fundamentally at odds,” November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06/2020-election-reveals-two-broad-voting-coalitions-fundamentally-at-odds/.
[19] William H. Frey, “Exit polls show both familiar and new voting blocs sealed Bidens win,” November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2020-exit-polls-show-a-scrambling-of-democrats-and-republicans-traditional-bases/.
[20] 所謂“聚旗效应”是指面临重大国家危机时,美国公众搁置政治分歧一致支持总统的倾向。参见:Linebarger, Christopher, Enterline, Andrew J, and Liebel, Steven R, “Third-Party State Domestic Politic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During Interventions into Civil Conflic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9, No.2, 2018, p.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