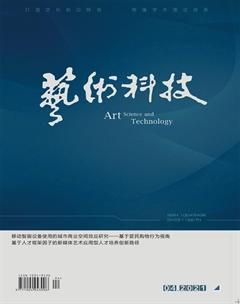《果酱拌水》与《暴风雨》互文研究
摘要:乔治·拉明是最早乘坐“帝国风驰号”移民英国的加勒比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书写加勒比黑人被殖民的历史以及后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在本土和宗主国的生活现状,表达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主题。在《果酱拌水》中,作者从书名、人名、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等几个方面互文重构莎翁名剧《暴风雨》,在表现殖民主义题材的创作中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加勒比文学;《果酱拌水》;《暴风雨》;互文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2
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20世纪60年代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1969)里阐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在其研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化现象时提出的[1]。其基本含义是文本、话语与其他文本、话语的关系,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从广义上讲,互文不仅包含参与最终文本的一切文本,还包括形成这一切文本的其他文本与话语[2];从狭义上讲,互文主要指文学作品的起源、作用与互动,人们借此探讨文本中通过引用、默示、谐仿等方法与已有文本建立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互文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主导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以投入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可以说,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经典的影响,加勒比作家乔治·拉明(1927—)的小说《果酱拌水》(1971)也不例外。
《果酱拌水》是乔治·拉明的第5部小说,与其第2部作品《移民》相似,描写了几位生活在伦敦的加勒比艺术家的遭遇及认同危机[3]。无论是书名、人名、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命运,《果酱拌水》都与莎翁名剧《暴风雨》有互文的成分,只是殖民发生的空间有所改变,由边缘转向中心,《果酱拌水》也因此被学界称为“生活在英国的凯列班们的故事”。本文拟从互文角度浅析《果酱拌水》与《暴风雨》的关系。
1 “果酱拌水”的由来
拉明生于前英属殖民地巴巴多斯,从小接受殖民教育,深受英国文学经典的影响[4],拉明对《暴风雨》烂熟于心并有意将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运用到了小说《果酱拌水》中。该书1971年在伦敦首发,主要探讨殖民、移民、流放等主题,讲述了3位西印度艺术家的移民动机以及在英国遭受的毁灭性影响。小说在架构上参考了《暴风雨》,呈现出主要人物与大英帝国和本土岛屿之间的关系[5]。换言之,《暴风雨》是《果酱拌水》故事情節及人物塑造的灵感源泉。首先,书名“果酱拌水”取自《暴风雨》的第一幕第二场:“你刚来的时候,用手抚摸我,疼爱我,给我里头放了莓果的水喝,还教我怎么称呼白天和夜晚发亮的大光和小光。那时候我爱你,带你看岛上的风貌,淡水泉、咸水坑、荒地和沃土。我该死,竟那样做!愿西考拉克斯一切蛊物——蛤蟆、甲虫、蝙蝠——都降到你们身上。”[6]普洛斯彼罗初来乍到,像慈父一般关爱孤苦无依的小凯列班,给其“放了莓果的水”喝,并用自己的语言教育驯化凯列班,旨在使其成为一名忠实的奴仆,这杯莓果水是维系二者关系的情感纽带,在普洛斯彼罗的荒岛殖民统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年后的凯列班为摆脱普洛斯彼罗的奴役和束缚,竟然用后者教给他的语言诅咒以普洛斯彼罗为首的殖民者,这时,殖民语言扮演了负面角色,已然成为去殖民化的有力武器。凯列班的这一幕词同时预示他欲与普洛斯彼罗决裂的决心[8]。拉明以“放了莓果的水”(果酱拌水)作为书名也暗示着小说中3位艺术家所处的困境与《暴风雨》中的凯列班并无二致,作者把这种处境描述为“最可怕的殖民方式:利用情感约束的殖民手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拉明是在逆写旅程。在《暴风雨》中,是普洛斯彼罗造访了凯列班的荒岛,在《果酱拌水》中却恰恰相反。在《果酱拌水》中,他将莎士比亚这位出生于16世纪的剧作家的政治主题和那些出生于20世纪的后殖民艺术家的困境有力地联系了起来[9]。
2 人名的互文及象征意义
褆顿理想破灭,孤独难耐之际在荒原上偶遇作为米兰达化身之一的米亚(Myra),试图重新了解自己的过去[10]。在《流放的喜悦》中,拉明把米兰达描述为“天真无邪的凯列班的另一半”,将凯列班形容成“米兰达少女时代可能成为的残缺部分”。在《果酱拌水》中,褆顿和米亚经历相似:他们失去纯真、错位、疏离、被强取豪夺[11]。米亚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天真无邪的米兰达遭受性虐后幸存的化身,作为一名克里奥尔人,她首先跟随父亲被流放到圣克里斯托布尔,继而在家园遭受同样的命运。她跟小说中的凯列班们一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地位卑微,是普洛斯彼罗殖民历史的受害者[12]。她与褆顿的邂逅加深了后者对个人及其岛国历史的了解。小说中米兰达的另一半化身是褆顿的妻子兰达(Randa),这可以从米兰达(Miranda)一分为二的名字看出。为换取褆顿的人身自由,兰达不惜委身于驻圣克里斯托布尔的美国大使,结果却遭到褆顿的唾弃[13],她绝望之极,最终在圣克里斯托布尔自杀身亡,这与米亚在伦敦过着自暴自弃的娼妓生活异曲同工。
作为凯列班和普洛斯彼罗的翻版,拉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无论在西印度还是在英国本土都表现出了殖民经历的方方面面[14]。普洛斯彼罗象征正在失去殖民势力的大英帝国:他是给岛上带来光明和知识的殖民者,是前种植园主,遭废黜的暴君。凯列班代表整个加勒比,代表他继承的岛屿,土生土长的凯列班在殖民体系中被视为怪物、孩子和奴隶,但凯列班正是革命力量的源泉[15]。《果酱拌水》中烧毁高尔·布赖顿庄园并蹂躏普洛斯彼罗女儿米亚的动乱就是凯列班反抗普洛斯彼罗独裁统治的一种表现。
褆顿在荒原上向米亚描述的具有和解意义的灵魂仪式在《暴风雨》中也能找到相似的事件:当普洛斯彼罗呼风唤雨将他的敌人同船一起沉入海底时,无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都从水里复活了,与海地的灵魂仪式惊人地相似[16]。普洛斯彼罗是被殖民者无法回避的痛苦现实。拉明喜欢用海地灵魂仪式推进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认为这是一种从困扰和制约人意识的死者手里解放生者的途径,为当代新殖民势力和尚未终结的旧殖民残余提供了一次和解的机会[17]。
3 凯列班们的命运
然而,灵魂仪式暗含的和解在小说中并未实现。7年来,独立后的圣克里斯托布尔依然承受着英国的殖民统治,褆顿决心归国奋战[18]。他与房东高尔·布赖顿夫人多年的暧昧关系成为他看似容易跨越的障碍。从情感层面上讲,对褆顿与高尔·布赖顿夫人关系的描写,一方面展示出他對这个照顾自己的老妇人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褆顿为摆脱后者的过度束缚而努力抗争的过程[19]。从象征层面来看,这映射出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暗示殖民国需要作出决断才能脱离母国的控制,必要时还需付诸武力。费尔南多的介入加速了二人关系的破裂,也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者略去了谋杀的细节,但显然,褆顿为获取自由不得已勒死了老夫人[19]。
相比之下,音乐家罗杰的自我毁灭则不尽相同。他讨厌祖国,移民英国是为了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20]。他闭门造车,行为怪异——白天在自己的住处创作,夜晚到妻子的寓所歇息。他与妻子的关系在后者的容忍下勉强维持,直到妻子怀孕,危机才真正爆发[21]。妻子是白人,自己是黑人/混血儿,出于对血统不纯的恐惧,罗杰否认孩子是自己的。这是罗杰极度排斥自己与生俱来的种族文化混杂性特质的有力象征,体现了其对自我的否定[2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痛恨自己出生地的原因,因为那是一个杂居成性的岛国。他对尼科尔的依恋不足以说服自己接受一个血统不正的孩子。在欧洲文化霸权面前,美国白人妻子对罗杰心理创伤的慰藉是暂时的[23],虽然她也来自前英属殖民地,有着同样的殖民经历。放弃自我的罗杰不能融入英国文化使其痛苦不堪,妻子怀孕更是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于是,在尼科尔失踪自杀后,罗杰也终于精神崩溃,成为纵火狂。
演员德里克在各大剧院跑龙套,僵硬的尸体是他扮演的唯一角色,他没有台词,只需听从指示摆出相应的死姿[24]。七年如一日的僵尸演绎没能让德里克出人头地,更不用说一炮走红,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他在灯红酒绿的伦敦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得不到认可,甚至被别人瞧不起,最终因强奸女主角未遂断送了自己的前途[25]。
这3位好友最终因被指控谋杀、纵火、强奸等罪行锒铛入狱,这与《暴风雨》中的凯列班企图犯下的三宗罪及受到的惩罚极其相似[26]。
4 结语
《果酱拌水》对《暴风雨》的互文明显,在殖民主义霸权的影响下,拉明笔下的人物命运是悲惨的,全然没有莎翁戏剧里主要人物的美好结局。
凯列班作为一个无知懵懂的儿童登场,此时他代表的是被殖民的初始状态,之后被流放异化成“他者”,最终觉醒,强烈反抗普罗斯彼罗,展示了其去殖民化的成长过程。拉明对凯列班经历的描述,实则是对西印度人民慢慢觉醒、逐渐摆脱殖民历程的间接反映,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呈现。
参考文献:
[1] 陆剑萍.显性互文的象征表达——以《推销员之死》和《拜金一族》为例[J].海外英语,2019(16):208-209.
[2] 王富银.莎士比亚戏剧两译本的翻译伦理研究[J].英语广场,2019(10):13-15.
[3] 宋伟,成玉峰.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以电影作品《梦》为例[J].英语广场,2020(15):42-45.
[4] 王旭霞.《海上无路标》的艺术特色剖析[J].英语广场,2019(01):05-07.
[5] 刘婷婷,张弛.浅析《面纱》中的双重东方形象[J].英语广场,2020(23):3-7.
[6] 莎士比亚.暴风雨[M].彭镜禧,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17-18.
[7] 鲍志坤.《宠儿》象征主义分析[J].英语广场,2019(12):6-8.
[8] 陈桂霞.以深层生态学的价值观论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胡髭老人”[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6):73-79.
[9] 吕鹏,张弛.库切《耻》中的后殖民空间想象:帝国风景、性别与动物权利[J].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2020(02):39-44.
[10] 栾雨菡,张弛.走出创伤的阴霾:《宠儿》中黑人女性主体性的构建[J].英语广场,2020(25):3-6.
[11] 张柯玮,张弛.《喜福会》中身份建构的生态女性主义意义[J].英语广场,2020(12):3-7.
[12] 赵一霏,张弛.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看《秀拉》中女性主体意识的重建[J].英语广场,2020(08):3-8.
[13] 朱颖,张弛.“帝国的管家”:后殖民视阈下“史蒂文斯”的他者形象[J].英语广场,2020(05):8-11.
[14] 陈丽屏.《伊甸之东》的叙事空间解读[J].名作欣赏,2018(9):66-69,139.
[15] 袁喜欢,胡斐.浅析《摩尔·弗兰德斯》体现的女性主义[J].英语广场,2020(22):3-6.
[16] 潘莺.基于荣格心理学理论浅析小红帽蜕变之旅[J].英语广场,2020(01):9-10.
[17] 袁家丽.“权力的游戏”:《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的性别政治与文化协商[J].戏剧艺术,2019(2):123-132.
[18] 奚昕.回归与重塑——“人格发展理论”在英美文学通识课程中的实践研究[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9(1):49-51.
[19] 李思炎,戴雪芳.《黑猫》中主人公的畸形心理探究[J].英语广场,2020(22):10-13.
[20] 唐思怡,周莉.生态批评视角下对《走进帕米尔高原》的研究[J].英语广场,2020(26):10-12.
[21] 朱蕾,王旭霞.觉醒的女性——论《莳萝泡菜》中薇拉的人物塑造[J].英语广场,2020(17):14-16.
[22] 陈红梅.混沌的阈限:自我探寻·艺术抉择·审美人生——以《他们眼望上苍》为例[J].三峡论坛,2019(5):60-65.
[23] 田海荣,葛纪红.浅析小说《我弥留之际》中的创伤隐喻[J].英语广场,2020(5):8-11.
[24] 庄筱钰,王旭霞.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英语广场,2020(26):29-32.
[25] 李芳.从合作原则看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J].英语广场,2020(32):56-59.
[26] 郑长明.边塞诗的认知心理空间构建[J].汉字文化,2020(21):210-212.
作者简介:王涛(1977—),女,重庆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